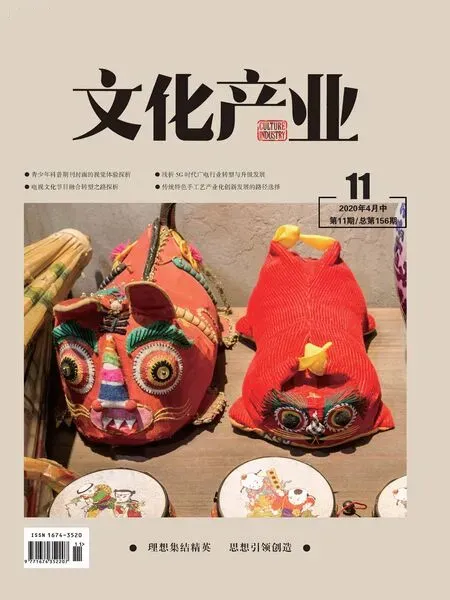电视文化节目融合转型之路探析
——以央视《中国地名大会》为例
◎狄丰琳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经历了游戏娱乐——益智类——真人秀——海外节目模式引进的过程,电视文化节目迎来了新的繁荣期。电视文化节目围绕诗词、戏曲、民歌、国学、文物、家书等主流题材进行全新视角探索,秉持“以文化教育为宗旨、以电视传播为手段,以传播知识为目标”①,践行“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自主创新原则,掀起了文化风尚的创作风潮。
2019年央视推出《中国地名大会》,以地名为切口、以电视媒介为载体,通过追溯地名文化,对华夏版图进行了一次与时俱进的丈量,赋予观众地名知识和精神涵养,唤起大众潜藏于心的家乡情结与热土情怀,在文化寻根中加固着集体认同。
一、融媒体时代电视文化节目的交融亮点
(一)内容层面的交融
1.冷知识与热媒介的交融
传统文化与大众媒介的交融,既为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提供了更便捷的媒介选择,也能拓展传统文化传播渠道,丰富传统文化的视觉表意实践。《中国地名大会》将少为人知的地理文化冷知识借由大众媒介传播,既有新度又有热度。
2.传统讲述方式与年轻化语态之间的交融
《中国地名大会》运用了流行词汇、现代化的喜剧手法、时尚元素附着等手段,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创作的巧妙融合,使厚重的传统文化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贴近观众。在人物命名上创新采取“地名式自我介绍”方式,姓名前冠以“祖籍”,如阿拉善·鲁健,绥德·康震等,凝结着个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骄傲感与归属性,在观者内心建立起独特意蕴与情感丰沛的新型空间。
3.传统地理文化元素与视听艺术符号的交融
《中国地名大会》第九期的“闻名不如见面”环节,别出心裁地播放了“五岳群英传”动漫化短视频。让五位动漫人物为五座名山代言,拟人化的五岳向观众娓娓诉说每一座山峰的历史与现实;多元又立体的设计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唤醒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节目趣味不断升级。
4.地理文化内容与故事化呈现的交融
电视文化节目充分运用电视媒介的独特属性,借助科技的辅助,在光影中诉说与展现故事的叙事特征。《中国地名大会》节目组请来了“云中哨所”守望者、第一代珠峰测绘人等能人志士,通过场景再现及感染力渲染后的故事编排,完成了叙事交融。
(二)形式层面的交融
1.传统文化单一定式与多样元素相交融
在电视文化节目形式设计上,选取核心元素与周边元素相联结,此举扩大了电视艺术的辐射范围,有效提升了文化影响力。《中国地名大会》设计出“地名+”的模式,“+”是跨界、是变革、是开放、是重塑融合;“地名+”就是地名与各个文化主题领域(包括音乐歌曲、答题竞赛、文化解读等)相结合。但这并不是两者简单的直接相加,而是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及传媒平台,让地名与各个文化主题领域进行深度融合,为电视文化节目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2.游戏环节与地名知识的交融
游戏环节是综艺中必不可少的艺术表达手段,《中国地名大会》将地名知识分解为选择题、线索题、版图题、视频题、阵列题。这样使“地名”这一较为抽象的名词生动直观地呈现在受众面前,增强了节目吸引力和影 响力。
3.精英化与大众化的交融
电视文化节目拥有精英化,节目质量才能得到彰显和提升;拥有大众化,节目才会更易被接受与传播。《中国地名大会》实现了中华地名文化与西方美学中“游戏”精神的融合。这种交融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英特征被削弱,也让大众更易接受娱乐外壳包裹下的中华传统文化。
二、电视文化节目交融的必然性
《中国地名大会》兼具文化性、情感性、艺术性及时代性,它不仅是当下融媒体形态的多维度尝试,也是电视文化节目生存方式的有益探索。
(一)使电视文化节目具有文化性与情感性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②
《中国地名大会》像一个文化微型景观,以地名文化为主,历史、民俗、科学等学科高度交叉,通过影像传播,展示地方特色与民风民俗,唤醒民族整体记忆。正如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社会遗产传承是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之一③。通过海选自主报名及定向寻找嘉宾方式网罗地名达人,以口述历史形式传递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使节目充满强烈的文学氛围,成为具有审美情趣的视觉艺术。
(二)使电视文化节目具有艺术性
多元节目要素、多种传播途径、多样传播生态,为电视节目的艺术格调升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1.多元节目要素
作为节目元素之一的题目,是增强趣味性、互动性的重要内容,也是承载传统文化的关键环节。《中国地名大会》题目设置综合了条理化叙事模式、多样的叙事手法、独特的叙事视角,拓宽了电视文本的深度与广度,实现了地名文化碎片化叙述优势最大化。
叙事文本也是节目的重要元素构成。托多洛夫主张用二分法把叙事文本分为故事和话语,在故事层面关注故事的产生及构成,在话语层面关注故事的加工与表 达④。从故事维度上看,《中国地名大会》选取有针对性、故事性强且视听效果便于呈现的地名,将地名文化的探寻变成一场全民活动。从话语维度上看,节目形式不断拓展,包裹严肃文化内核的是热血沸腾的竞演外壳,“地名矩阵”与“地名天梯”环节格外吸睛,桌游、音乐、建筑交融在舞美、灯光、电路设计渲染上,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
2.多种传播途径及多样传播生态
《中国地名大会》以“融”为媒,打破了圈层壁垒与平台束缚,触碰到更广泛的用户群体,舆论阵地及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不断扩大。
一是多个媒介平台融合创新。“媒介平台是指通过某一空间或场所的资源聚集与关系转换,为传媒经济提供意义服务,从而实现传媒产业价值的媒介组织形态。”⑤该节目不断拓展传播渠道,建立传播矩阵,使多平台分发的单一报道已经演变成同一素材的分平台整合,中央和地方新媒体、央视全媒体、多种自媒体协同展开宣传,合力扩大外宣影响力。
二是多种媒介形式的融合创新。“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定义,告诉人们何为公共的、共同的社会生活的规范。”当下,语言、图像、活动、声音等媒介相互组合,人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也是调整生活形态、重塑价值观的过程。科技的进步使电视文化节目融合形态不断革新,如AI、VR、AR、全息投影技术、多光影采录、弹幕互动、虚拟形象跨屏互动、小程序参与等有益尝试使传统文化跃然“屏”上,满足了观众在娱乐、文化、视觉的多重需要。
三是媒介转换带来的新融合,明确了节目定位,带动了产业链发展。承载同一IP的媒介经过产品化运作构建出多个衍生品,继而再次促成新的融合。如故宫博物院与文化企业合作,将丰富的历史文本转化为动漫、影视、手办等媒介产品。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文化文本的叙事增殖和跨媒体转型提供了更多可能;这种转换方式,也使其他媒介拥有为电视文化节目提供造势平台与宣传营销的可能。《中国地名大会》可以借鉴故宫博物院文本交融与生产的思路,围绕“地名文化”,展开产业链打造,推动地名文化与新媒体传播的深度融合。
(三)使电视文化节目具有时代性
一方面,时代精神赋予电视文化节目与众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地名大会》节目组带领观众领略新疆罗布泊、黑龙江大庆等祖国大好河山之壮美景色,一起触摸地名里最硬核的富含“中国精神”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电视文化节目将宏大的中国精神落地到每一个小小的地名当中,使时代精神变得生动而具体,于无形中呈现主流价值观。
三、融媒体时代电视文化节目的守正创新
近年来,电视文化节目的勃兴给疲软的综艺市场注入了“强心剂”。与此同时,电视文化节目面临着题材扎堆出现、创新突破难度大、招商宣传有局限等问题。因此,节目创作者要不断深化创新,用文化价值积极导引受众。
(一)审视文化调性,坚守品质高地
电视文化节目通过题材选择、节目架构、人物设置、参与感与仪式感的营造,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一种新的时代形态。但当下电视文化节目题材多扎堆于书信、诗词,不妨另辟蹊径寻找独到的切入点,从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中探索可发展的空间。年俗、传统乐器、对联等也是可供开拓与挖掘的题材,让“阳春白雪”式的高雅艺术经由艺术化表达实现大众化转向。
(二)拓宽艺术表达,合理编排叙事
大众对信息与文化的渴望上涨,过度娱乐已无法满足知识诉求,易陷入知识诉求与难以获取的双重焦虑中;且观众的知识储备及接受程度不一,文化交融的“冷”和“热”以及“繁”和“简”的界限难以轻易把握。因此,了解受众兴趣并抓住受众的心理兴奋点十分重要。
(三)持续推陈出新,契合时代要求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各级各类媒体要聚焦爱国主义主题,创新方法手段,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使爱国主义宣传报道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有情感、有深度、有温度。”⑥优秀电视文化节目讲究文明传承,传承上有创新,师古而不泥古,讲好“中国故事”,围绕时代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不断创新及深化传统文化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样才能成功地将节目制作者的“考量”嵌入观众的“期待”。
《中国地名大会》将地名知识和传统文化交融演绎后所萌发的新意,满足了受众日益迭代的审美需求,彰显出传统文化魅力和时代风采。
【注释】
①刘晓欣:《电视文化节目研究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第12期。
②[英]爱德华·泰勒,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张萍:《故事·话语·叙述交流:〈奔跑吧兄弟〉的叙事学分析》,《中国电视》2016年第6期。
⑤谭天:《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国政府网,www.gov.cn/zhengce/2019-11/12/content_5451352.htm,2019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