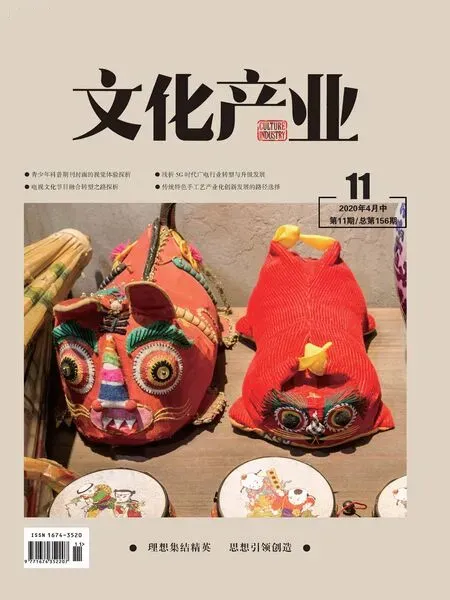浅论香港电影早期的地位变化
◎张晨宇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上海 200438)
相较于大陆电影工业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文化圈层意义上的突围,最终建立起独特的中国民族电影体系而言,香港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以岭南本土文化为基础,由世界范围内多种社会力量混合、交融而形成的电影文化聚集体,作为东西方电影文化集中交汇和冲突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电影产业发展与电影艺术创作的前沿阵地。随着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交流的程度日益深入,香港电影产业与艺术的发展也逐渐跨越出了电影这一社会文化传播媒介的类型,向社会的其他方面延伸。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大陆电影工业体系的逐渐建成与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选择北上,与内地电影制作者们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合作。在产业层面形成集群的香港电影已经逐步接纳了内陆电影工业体系,实现了产业层面上的融合。
一、香港电影的诞生及第一次北上
(一)从诞生到北上
放之亚洲范围内而视,中国电影的起步或许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批,当1905年谭鑫培在丰泰照相馆摄制出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时,日后声名大噪的亚洲电影地区都尚未诞生电影的萌芽。日据时期的韩国政局动荡,与此同时日本浅草电气馆刚刚引入了电影机,1913年,戈温特·巴尔基的《哈里什昌德拉国王》代表印度电影的出现,而直到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斯梅尔·库尚博士才拍摄出伊朗第一部电影。而在香港,电影的文化传播比中国大陆电影起步的时间还要早。1896年,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赴香港放映了《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电影。随后,在1898年,爱迪生公司的摄影师也来到香港,拍摄了《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锡克炮兵团》等一系列纪录片。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出品,但它们在香港拍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香港电影发展的萌芽。
由于受到香港英据时期社会政治形态和本土民族文化的冲突影响,香港电影行业便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诞生了。1909年,由梁少坡导演、本杰明·布拉斯基摄影的《偷烧鸭》成为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而梁少坡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导演。1913年本杰明·布拉斯基与黎民伟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标志着香港电影业的正式诞生,不同于早期上海电影发展由国人、华人等为主要电影力量进行制作的组织形式,香港电影早期的电影制作组织多半为“中外合作”的形式。这样的情况既源于电影作为西方文化传播技术所产生的特点,又源于香港长期处于英据社会形势下所产生的文化交流与冲突。因此,虽然香港电影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始终无法将电影行业发展对社会所带来的作用有效划归入本土的民族语境中。相反,香港电影文化发展由于局限在英据时期香港的社会文化形态中,为了电影行业的有效发展、向本土民族语境靠拢,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广泛向上海电影借鉴、学习。在拍摄完《偷烧鸭》后,梁少坡、黎北海等人北上上海学习当时先进的电影创作技术与电影行业建设经验,于1922年创立了香港第一家电影公司——“民新”电影制片公司。1930年,联华电影公司香港分厂创立,梁少坡被聘为编导,这也标志着香港电影第一次北上的基本结束。
(二)北上的原因
较之上海在中国电影发展早期的声势浩大,香港电影在这一时期也在逐渐摸索着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社会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香港电影文化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思想导向上,都尚未寻找到较为明晰的方向。日后经香港电影人之手发展壮大的功夫电影等电影类型,在此时并不具备成熟的土壤(中国第一部动作电影《荒山得金》由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制作)。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电影的主要发展力量集中在上海地区,出于对本土电影工业建设的急迫需求,上海成为外国先进电影工业技术与行业建设经验引进的最大入口,这一时期,香港电影更多的是以上海电影为师,进行自身体系的建设与摸索。
二、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重心的南移
(一)重心南移
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突变,大陆地区稳定的社会环境迅速恶化,上海作为大陆地区接受电影文化影响最为广泛的地区,面临十分严重的威胁。“一二八”事变后,明星公司被烧毁,联华在沪的一部分业务遭到毁灭性破坏,这段时期,上海地区的电影制片公司纷纷选择南下,1934-1937年期间,中国电影发展经历了第一次重心的南移。这一阶段电影重心南移,香港成为南移的目的地,最终形成中国电影“香港——上海”轴心,这次变动不可以片面地归结于战争前夜社会形势变动对电影行业造成的影响,更源于20世纪上半叶大陆地区电影政策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所带来的影响。
(二)从内外环境分析电影重心的南移
从外部环境来看,大陆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官方对文化领域控制日渐加强的主要因素,电影检查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得民族影业发展相对自由、相对稳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内地影人为了寻找更为适宜自身发展与更加稳定的市场,不得不被动南移。另一方面,从内在动因而言,此次南下的根本动因仍然是市场扩张的内在需求与经济驱动的共同作用。当时,南洋市场由于长期以来的地缘因素影响,成为国产影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故我国影片制造商,十余年来无不以南洋方面之购片,为其大宗之收入也”。而武侠神怪片作为电影奇观度最高、最能吸引当时观众注意力的电影类型之一,更是广受南洋观众喜爱,1933年粤语声片《白金龙》的大卖,使粤语声片在东南亚一带大热,一时供不应求。但由于国民政府禁拍武侠神怪片、粤语声片,内地片商在大陆本土进行早期类型片市场拓展的行为遭受了到诸多限制(以《火烧红莲寺》及其续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类型片因涉及武侠神怪而被国民政府禁止拍摄或放映)。此时香港地处“法外之地”,远离战火与电检制度,为处于困境中的上海片商提供了一片理想之地。
此时,香港仍然处于英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国民政府对于电影的管制无法对香港电影产生重大影响,并且香港的电影监管较为宽松,国民政府中央电检会无权对香港电影进行行政与法规上的约束。与此同时,香港地区作为向南洋地区广泛输送中国电影的最大出口,以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质,粤语等具有代表性的岭南文化(尤其是两广地区文化)成为连接中国电影与南洋电影市场乃至海外电影市场的重要文化媒介。很多当时在内地无法上映的影片,可以在香港获得走向海外市场的机会。如在内地被明令禁止的《火烧红莲寺》,在香港得以上映并传播至海外。在香港——上海这一中国电影轴心初步形成的阶段,大量的电影商人和电影创作者借用了电影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地缘要素,纷纷南下,规避政治对于电影的管控。这批南下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成为20世纪后半叶香港电影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电影重要力量的种子与先声。
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也无意之中影响了之后的香港民族电影风格,1932年开始,夏衍、阳翰笙、沈西苓等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始加入各大公司,参与到电影制作中来,使左翼电影发展迅速,成为电影界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而面向现实、抨击时弊的左翼电影越来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一时间,左翼电影的影响迅速在香港电影圈层内散布开来。1932年10月,由天一公司代为摄制、广州合众电影制作公司出品的《战地两孤女》在香港上映,成为第一部在香港公映的、全程粤语对白的影片。同年,《东北二女子》《飞絮》以及1933年的《共赴国难》等电影,均是由左翼电影运动人士制作的。这一时期,由于左翼电影人士的积极工作以及民族解放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传统意义上属于武侠神怪、才子佳人类型的商业电影迅速失去了市场存活空间。
政治社会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打击,使得大陆电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了较为困难的发展时期。不同于世界范围内其他电影区域早在电影诞生初期便实现了社会政治环境的统一与经济体系的稳定,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发展的早期,社会环境极其不确定,各个地方政治权力交错割据,致使中央政府必须将文化上的统一手段纳入政治统一的考量范围之中。1936年之前,两广地区由陈济棠势力统治,而陈济棠对于中央国民政府电检会所提出的“禁止粤语片拍摄、制作与放映”的禁令反应甚微,因此,香港地区粤语片的发展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保护。与此同时,由于受行政命令影响较大,大陆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影片制作受到了极大的约束。粤语片受国民政府管控力度较小,怪力乱神、才子佳人等在南洋地区具有类型片优势的商业电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挤压了大陆电影的发展空间。此时,大陆电影人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也加快了南下的速度。
三、结语
20世纪30年代这一次内地影人南下,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历史事件,对香港电影的兴起与中国电影之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一环。南走香港的电影力量,以武侠神怪片、古装片、粤语片为制胜法宝,抓住历史的机遇,顺势抢夺东南亚电影市场。此次南下也是早期影史上一次“走出去”的有益尝试。而第一次内地影人的南下,更是为香港电影之后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力量以及类型题材上的开源,邵醉翁等人成为日后香港电影行业发展的奠基人。而在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神怪武侠、才子佳人等类型电影,也在经过香港电影中民族和社会语境的转译后产生了大量再生性文化生态,成为日后香港电影得以对世界电影产生影响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