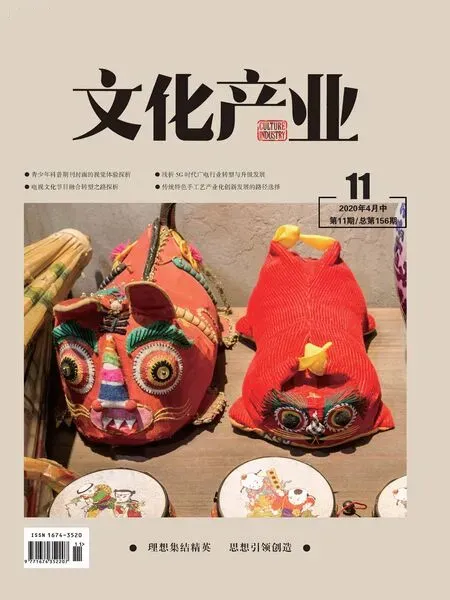佤族传统物候历探析
◎郑 帆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云南 临沧 677000)
佤族是世居云南省西南部的“直过民族”,聚居在澜沧江与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延展地带上,也是中国、缅北、泰国和越南部分地区的跨境民族。佤族经历了从穴居野处的狩猎采集到农耕的发展过程[1]。农耕是佤族社会和文化的根基,把握农事节期对农业生产来说至关重要。在计时工具和历法没有出现以前,人们“只能依靠对天象、气象和物象的观察来决定农时、指导生产、安排生活,即所谓观象授时”[2]。因此,“观象授时”便成为佤族先民惯用的纪时方法,如今在佤族村落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物候历的沿用,人们继续以天象、物候来检验历法的准确度,并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它。
一、观物候
人们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中,感受风霜雨露、草木枯荣、鸟兽虫鱼归来复去的季节变迁。人们遵循大自然的变化规律,掌握农作物从下种到成熟的习性,主观上将时间划分为不同段落。掌握了自然物候的周期变化规律后,在不同的时间段落里人们就可以提前计划、安排相应的农事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候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量。
(一)以花期作时令钟
佤族以植物的花期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比如路边的白花开了就不能撒种和育秧。以佤山地区常见植物的萌芽、抽叶、开花、结果、落叶作为耕种庄稼的可视的时间参照标志,人们在观察类似这样的自然物候变化的经验基础上,产生了时令意识。
(二)以鸟啼声断农时
农业靠天吃饭,农作物的备耕、播种、培育、生长、成熟、收获,都依赖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人们根据谷物生长的季节特性,安排适宜的耕作制度。佤族习惯用动植物的生物时间来确定季节和生活时间。鸟啼声是一种常见的记时方式。过去每到开春、播种的季节,老百姓就以几种鸟的叫声作为报时器。其中有一种“bu bu”鸟,其大小毛色和斑鸠相似,它一叫就表示栽秧季节已晚;还有听到“ji guo”鸟叫声农民就要收工回家。
物候观测的结果是综合气候条件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气候条件对生物的影响。不同的鸟啼声既是农事活动的时间表,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时间刻度,什么时间耕种什么作物都随动植物的活动习性对气候的灵敏反应而定,物候的提早或延迟,是老百姓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的测量仪。农业收成与鸟类活动、气象转变的规律密切相关,同时是生活作息时间的参考标志。佤族民间神话或传说中有一些关于物候定农时的记述,如《司岗里》中讲道:“安木拐在芒杏丫口为母亲送葬,送葬时举行了动物歌咏比赛。安木拐拿出一块金子对动物们说:‘哪个的歌唱得最好,就把这块金子奖给它。’比赛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戏帅(春蝉)的大合唱。……第二个节目是额列(绿青蛙)的小合唱。……第三个节目是格郎晚(一种秋虫)的独唱。……后来,佤族就把格郎叫的日子定为秋收的节令。”[3]
佤族先民把春蝉鸣叫的日子定为撒旱谷、撒秧的节令,把青蛙叫的日子定为薅旱谷的节令,把秋虫叫的日子定为秋收的节令。尽管动物被拟人化出现在神话故事里,但现象也源于生活,人们以动物叫声为标志判断季节及农作物耕种的时间。
管物候反映了早期历法萌芽阶段的农事活动。民族历法的形成与本民族身处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人们观察周边动植物生长形态和习性特征,形成一种时间意识,成为节日时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观月象
佤族还把注意力投向天空中日月星辰的形状和方位的变动,以此来判断自然时序转换的原因。佤族通过目测月亮的出没与形状,来判断时间周期,以月亮的一次圆缺为一个月,十二次圆缺为360天,这也是佤历赖以形成的基础。每逢佤族新米节(农历八月十六),每户人家从地里摘回第一批成熟的庄稼、时蔬瓜果,祀请祖先尝新,以此酬谢祖先的庇护,期待来年更好的收成。每月15、16日通常是月亮最圆满的一天,汉族俗称“望日”。佤族择月满之日过新米节,也表示与祖先团圆,共享丰收的喜悦之意。
关于望朔月现象与天干地支的解释,从佤族民间故事中可窥见一斑。人们开始懂一些简单的天文地理知识,甚至以天数计算事记,后来便形成干支属相记日、记事、取人名字[4]。
月亮对佤族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过去人们无法准确估算每个月的天数时间,只能依靠丰富的想象力,认为月亮和人的生理特性一样,以“眼见为实”,理所应当地把“云遮月”当作是“月亮埋到土里睡觉”。时间遵循的是“见月则走”“不见月则停”的规律。文献里也记载了佤族先民观天象定节序:“不知四时节序,惟望月之出没以测时候。人病则命巫师路旁祭鬼。地多平川,土沃人繁,村有巨者户以千计。然民不勤于务本,不用牛耕,惟妇人用钁锄之,故不能尽地利。”[5]
说的是古时候哈刺(明代佤族称谓)肤色黝黑,居住在山岭上,以苦荞为食,和其他民族不通语言。蛮夷之族没有懂阴阳医术的医生或者僧人,于是大大小小的事均以占卜鸡骨来卦断凶吉,也没有推算日月星辰流转的时间历法,所以不知道四时节序,只有根据天上望月的出没来观测时间。
佤族的日子,没有历史书卷记载。在没有引用汉族夏历和农历前,推算方法只能依靠长老口耳相传,由村落里专门负责推算日子的老人达万“算日子”。一年有360天、12个月,通常小月有29天,大月有30天,通过肉眼观测新月形状决定大小月,为了弥补望朔月与太阳年的偏差,大概两三年出现一次闰年,年和月靠设置闰月来调整。旧时有的佤族村寨,头人每年二月份都会到特定的河段看游鱼有没有上水,寨子外特定的岩石上野蜂群飞回来了没有,如果鱼没上水,野蜂迟迟未来,头人就会增加一个闰月,称之为“怪月”。有的地方是通过观察桃花是否开放来决定是否增加这个“怪月”[6]。我们已经无从追溯古老时代历法的创制历程,但它却是人类童年时期对时间现象的美好诠释。
三、结语
自古以来,人们通过感受自然界的物候变化,体验周而复始的时间循环,农业丰歉状况完全取决于自然万物的节律。“时令意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运动变化的长期经验与思考,物候历的编制就是古人依据时令意识对自然时序的经验描述。”[7]古老的物候历是佤族现代历法的自然基础,成为佤族岁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佤族农耕社会时间体系的根本。佤族的时空观念承载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佤族通过观物候随时节的变化判断时间段落,不断丰富佤族的用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