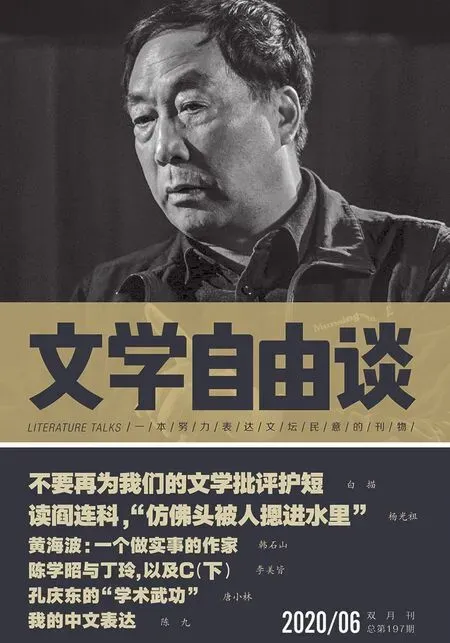我的中文表达
□陈 九
我曾多次谈到自己写作的特点,比如形容自己是“第三只眼”,以第三者角度观察海内外文化现象;或者像清教徒,没什么功利追求,只因有话想说有感而发,才义无反顾地写起来,写下去。不过也有人问,为什么非用中文表达不可呢?
对呀,为什么呢?
三十多年前来美留学,一个主观愿望就是要把英语说好,天真地以为只要英语过关,表达绝不是问题。为此我竭尽全力,听力室的“牢底”差点被我坐穿,因为只有把听力提高才能改进发音,否则䞍等着闹笑话。那天女老师带我们留学生看《侏罗纪公园》,dinosaurs(恐龙)我觉得眼生,就按读音规则,第二音节重读,“歹拿扫斯”。话音未落,女老师笑得前仰后合:什么“歹拿扫斯”?是“呆呢扫斯”!她一笑,别人也笑,臊得我哟。还有一次,刚出公寓门遇到查理教授,他招呼我:你住在这儿?我连忙把地址告诉他,请他来玩。公寓是apartment,我突然想起另一个词suite(套房),发音是“似卫特”。如果说“似卫特”他也能懂,结果我把suite与suit(西装)搞混;后者发音是“素特”。我说我住在“素特”里。查理教授满脸狐疑:你确定住“素特”里?确定确定,我的“素特”欢迎您。
时间长了,英语能力自然会有改善,听课考试做论文,没什么问题,感觉越来越自如。我跟荷兰来的马克住一屋,他说他爸是海牙法庭的法官。他讲英语口音很重,但词汇量大,连马路用语都知道,给我不少启发。荷兰人善饮,一到周末我们就去酒吧。不过我也帮过马克。那天他在买二手车,马上要付款,我正好路过,说等一下。打开化油器一看,很多黑色积碳,马上判断是某气缸的油环磨损,严重烧机油。我耐心解释,服得他手舞足蹈,说,走,咱喝酒去!
后来马克买了辆1979年的沃尔沃,他还是喜欢欧洲车。我们四处兜风,到湖边裸泳,去阿巴拉契亚山里会私酒贩子,跟农场主的女儿学骑马。不久马克交了女友,我也差不多,英语交流突破校园局限,进入生动的生活,表达当然也丰满起来,甚至俗文俚语和所谓脏话都春风扑面。我被人家带起节奏,扑朔迷离得有些不真实,像看翻译片,看到一半自己进去演,结果台词不熟疲于应对。比如周末烤肉,知道BBQ是烤肉,真烤起来一大堆细节:工具,香料,火候——特别是香料,五花八门。还有对力量的推崇无处不在。我们把钥匙锁在屋里,邻居路过,说小事一桩,转身就把大门撞开,锁也坏了——诗人木心说“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边是“你锁了,一撞就开了”。开心就是硬道理,做什么都可能,也都不奇怪,让我豁然领悟天地人伦的份量,顿感自己是异类,表达反倒更不好拿捏了。
按说随着英语能力的娴熟,表达应该更轻松才对。我起初认为,完全可能将表达的充分性从汉语平移到英语上,更换的只是语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英语说不好时,交流的是基本需求,听课啊,购物啊,别人之所以会听,是因为人的基本需求是相似的。一旦交流日渐充分,表达肯定向情感和价值观深入,交流也就成为文化的碰撞,并卷入社会历史的认知,复杂性随之加大,大到男欢女爱也无法平衡。比如对家庭的看法,中国传统的父母子女关系对我来说很自然,我经常给母亲打电话,不时收到家中的邮包,还以此作为人间温情,好心与对方分享。意外的是,日子一久,人家竟凭空生出诧异的质问:我跟你谈朋友还是跟你父母谈?你是你,你还是你父母驻俄亥俄办事处主任?问得我哑口无言。
坊间有这样一种印象,美国人说事情往往比较简练,三句话结束。同一件事我可能会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最后才到点上。开始以为是词汇量不够大;有这个问题,但不全是。对当年我们这批留学生而言,来美前已有人生阅历。比如我自己,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驻马店特大水灾抢险,第一届高考,经济改革,思想解放……我的存在是社会经历和家庭影响的物化。当我三十岁那年像野草一样漂泊至此,不可能把前三十年完全归零,很自然地会在交往中展示已有的知识积累和生命价值,并以独立的眼光审视美国社会。遗憾的是,这里的人对你前三十年没兴趣。特别是就业以后,我在主流职场工作了近三十年,无论英文多努力,如果表达风格,包括逻辑、举例和幽默,与职场的期待不合,就很难一帆风顺。有人说美国职场的中国人干不过印度人,问题就在文化差异上;换句话说,你的英文表达即便足够充分,但因文化差异也难以尽情尽兴,很多观念情感无法交换,对方不会真感兴趣。你知道他在应付你,他也知道你讲的并不重要。你虽然需要表达,但对方并不需要倾听。
关于“为何用中文表达”的问题,我与董鼎山先生有过交流。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参加抗日地下组织,做过《申报》记者,二十七岁赴美读研,又在美国做过《时代周刊》专栏主笔、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和他的瑞典裔夫人生活了一辈子。在外人看来,他已完全美国化,英文能力远在绝大多数本土美国人之上。就这样一位杰出的美籍华裔学者,依然积极参与祖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用中文撰写了三十余册书籍,向中国介绍美国社会,影响了一大批“改开”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精英。五年前,董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仙逝于纽约。
在与他近三十年的交往中,董先生坚持说中文;我太太是上海人,他俩碰面还非要讲上海话不可。董先生的老派上海话语速较慢,节奏感更强。我们每次去看他,除了给董夫人蓓琪带一个黑森林蛋糕,我太太必给董先生做几款本帮菜带去,烤麸、龙井虾仁、百叶结烧肉,都是他的最爱。有几次与董先生微醺,兴奋之余他要我唱京剧“劝千岁”,还指明马派,说其他门派唱的那句“那刘备本是中山靖王的后”,被马派省去“中山”二字,更加顺口。回忆当年在上海参加抵抗运动,他和弟弟董乐山躲在楼梯下的隔间里,从木板缝隙看到宪兵的皮靴踏过楼板,发出咣咣的响声;谢晋元团守卫苏州河四行仓库,夜间可以看到对射的子弹流星雨般呼啸往来。我问他为何不把这些生动画面用英文写给美国读者,董先生莞尔一笑说:“伊勿感兴趣,莫啥意思。”每次看望董先生,董夫人蓓琪总是先和我们寒暄片刻,便随即离开。她离开时的几句话耐人寻味:董,现在是中文时间,你尽兴说中文吃中餐吧,be happy(开心哟)。
面对董先生的睿智和董夫人的善解人意,我无法想象因为来此读书生活就得把以往的侠肝义胆热血情怀“清零”。这不可能。在表达问题上,我和董先生是相通的。我有个石溪大学同学,那时经常一起查资料做功课,还跑到杰佛逊港看钢管舞。几年前在曼哈顿与之巧遇,我像当年一样用中文招呼他:你跑哪去了哥们儿?有趣的是,他用英文回答我:对不起先生,我不会说中文。然后转身离去。我尊重他的选择。漂泊生涯最无奈的就是见怪不怪,人性比想象的要离奇得多。野草他乡,诸事难料,想怎样表达是个人私事,大家保持着真正的“社交距离”,谁也不必对历史文化负责。然而,或许是前世的宿命,当有些人情愿洗心革面淡化自身文化背景时,我们却老马知途,选择了一路走来的继承与恪守,而且这样的华人是绝大多数,他们未必都是作家,但不妨分享同样的文化情感。
所以,中文表达的冲动正源于英文表达的不够充分。对我而言,当英文表达难以尽兴、缺乏共鸣时,中文便脱口而出。表达是刚需,是硬道理,此处不表达,自有表达处。人文情感是经历的积累,是一条连续曲线,包括过去和现在,祖国和异国,像晚霞一样丰富绚烂,像河水一样潺潺流淌,根本无需额外的动机。
记得三十年前我开始写诗时,最初是把在俄亥俄写的英文诗翻译成中文。当时纽约的“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经常举办中文诗歌朗诵会,该组织由董鼎山、夏志清、唐德刚、郑愁予等人发起,董先生任会长。他们都是英文能力超凡的学者,却在中文表达方面寄托了深厚情感;我也从这里开始了与董先生等名士作家的多年交往。承蒙他们的感召,当年纽约中文文坛可说是云蒸霞蔚,我的中文写作应运而生,无比幸运。我们沉浸在创作的快乐里,也分享着朗诵的欢悦。那时,“纽约诗会”影响很大,有人甚至乘飞机从外州赶来参加,地点就选在当年胡适和杜威教授共同创办的“华美协进社”,曼哈顿东六十五街,也是梅兰芳、老舍光临过的那间小礼堂,董鼎山、夏志清、唐德刚、王鼎钧、郑愁予、赵淑侠、王渝等各界名流都来参与。那是中国文化在纽约的一件盛事,也是诗歌经典被网络“绝杀”前的回光返照。我们承蒙天顾,难得地共享了一段珍贵的“唐宋遗风”。
从此一发不可收,从诗歌到散文再到小说,用中文写作完全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在所有属于我的时间里,悄悄把自己变成故事中的角色,乘着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把从小到大的种种感受浸在情感里,再撒尿和泥一样重组,像一个光屁股小男孩在残阳如诉的绚烂中纯净地玩耍。别让漂泊的恭卑黯淡我生命的意义,别让逼仄的文化氛围刺伤我的自尊,让一切孤零零的感觉滚开,把所有的赞美和轻蔑置之度外。我像一个徘徊的幽灵,因为有话要说,才为构筑生命而极尽表达。你可以认为这是对外部世界的某种逃避,一种内敛自省的苦渡,清风明月的独白,是无边无际的安静与放手,或为保持内心平衡,不被平庸的居家生活逼得到大街上放枪,而给自己创造的宗教。我是一部蒸汽机车,所有煤炭都已填进炉膛,就这一锅了,能烧多久烧多久,能跑多远跑多远,把所有滚烫的世俗抛开,天地悠悠长风板荡,让我的多情与丰富在内心开花结果,然后绽放。
当年留学海外的初衷,其实就是想出来转转,“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没料到会走这么远,这么久,以至于到了英语都不足以抚慰灵魂的地步。多年来,我对中文表达的一贯追求,是想抵消野草他乡的孤独寂寞,还是为倾听远在天边的山河呼唤呢?
我说不清。
2020年9月5日,纽约随波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