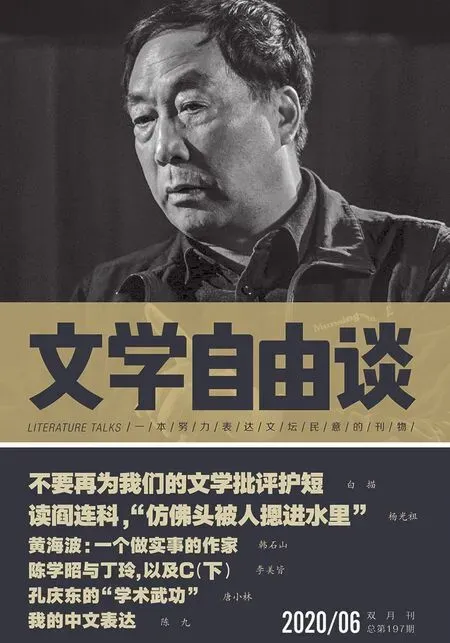黄海波:一个做实事的作家
□韩石山
多少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写作者,一定要做实事,才可能成就其声名。所谓的“深入生活”,终归是“客”,文字上的功夫再好,只是一种技能。好比伶牙俐齿,先得有话可说。
好几次,都想写文章了。又想,空说,没有意思,得有个实在例子才好。按说,说我也行,可我从学校出来,在吕梁山里教书,一个村子,再一个村子,一做就是十几年,能把年轻人吓着,该有个更切实的例子才好。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黄海波女士。
这样称呼,对别人好,有名有姓,还有性别;对我来说,就怪怪的,因为我平常总是叫她小黄。70后的人,按说不小了,架不住我更不小,也就一直这么叫着,顺口,也亲切。
认识小黄,真够早的。早到什么时候?拿不准。手机上一问,答案来了:1991年她毕业后没几天。别的,不用问,我全知道: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一毕业就分配到《太原日报》编副刊。我常给《太原日报》写稿,多半副刊用,相识并来往,也就成了家常事。
那些年,兴在家里吃饭,我又喜欢跟女孩子交往。老伴知道我这个德性,也不见怪。一来二去,小黄的根底,也就知道了个大概:父母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同班同学,南方人,1965年毕业,分配到山西。先在下面县里做事,几年后调到省城,都在教育厅系统,一个在教研室,一个在教科所。在县上的时候,就有了三个姑娘,来省城后,个个出落得花儿一般,漂亮又略有差异,好事者分别称之为淑女、才女和美女:老大淑女,老三美女,小黄是老二,名校出来,写得一手好文章,自然就是才女了。她说这些的时候,还有几分得意,不窄的脸盘上,漾开宽宽的笑纹。在我看来,说一个女孩子是才女,并不是什么尊崇,极有可能是,既不淑也不美,只能说也还有才。我将这个意思跟她说了,且说,萝卜里头,白的叫白萝卜,黄的叫胡萝卜,青的不好叫,只好叫“心里美”。她笑笑,心里怎么个恨,看不出来,脸上还是笑意盈盈,且说韩老师的捷才,谁也比不上。
小黄怎么个有才,那些年,还真看不出来,能感觉到的,是她的大气。后来我甚至想,最终成全了她的,或许正是这种大气的品格。
小黄编副刊,又爱写文章。报社有个规定,编辑在自己编的版面上写的文章,不开稿费。她跟我女儿韩樱也是朋友,便署了我女儿的名字,于是我女儿便不时收到一笔小稿费。起初我以为,女儿不过是转一下手,积攒多了,还是要给小黄的。跟小黄说起,小黄说,用不着,给樱妹子吃个零嘴吧。
自然,她的文章,不会光在《太原日报》上发,别的报上,外省的报上,也是常发的。过了几年,出了本书,叫《小资女人》,北京的华文出版社出的。其时,我正在编《山西文学》,最见不得的,就是所谓的乡土气,还有那个什么派,自然不敢明说,打的旗号是“唯陈言之务去”。见了小黄的书,观其行文,语感甚佳,一看就是当作家的料,很是高兴。便摘了两章,在刊物上发表,同时配了我的一篇长长的评论,名曰《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作家》。
靠我这么个老蚍蜉(老匹夫),哪能撼动什么派这棵大树?过了几年,到了退休的年龄,就灰溜溜地走人。
此后多少年,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交往着,只能说彼此还记着此彼,没有高雅到“相忘于江湖”的地步。质言之便是,我过着我的清苦的书生的生活,她过着她的安逸的“小资”的生活。我们共同的朋友,有的升了官,有的发了财。我有时还会心生羡意,或者说是溢出几滴酸酸的妒意;她呢,恬淡得很,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这一点,最是让我服气。我想,这就是身世好、素质高的地方吧。
我退休后,在太原住了几年,耐不住此地高亢的文化气氛,借了陪老伴看孙子的名头,在北京赁屋住下,学了古人的“万人如海一身藏”,与小黄的交往就更淡了。只是仍不时见她有文章发表,不再是“小资女人”的腔调,平实多了,成了对少女岁月的回味。从时尚上说,是退了一步,从文章的品质上说,是升了一格。
说是在京长住,每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还是会回太原住一两个月的。记得是2015年吧,听说我回来了,小黄请我吃饭,在一个公司的会所里。我去了,她正在门口等着。我上台阶的时候,还看见她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在默默地读;到了跟前打招呼,才抬起头,一脸的惊喜。我注意了一下她手里的书,是本英语会话手册。
不像往常,吃饭多是一桌子人,这次就我们两个。一坐下就说,她要去美国了。我以为是移民,她说,那岂不把东海害了?东海是他丈夫的名字,在省上某厅当着处长。说开了方知,是去美国研修一年,对方学校出资。她想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确定自己往后多少年的修为,做点彰显自己才能的事情。
这才意识到,她在门口读英语会话手册,原来是干这个的。
“嗬,立大志了!”
我这人,贱得很,什么时候,都改不了浅薄的毛病。
知道我这个毛病,她不恼,只是淡淡地说,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可是受不了别人看她的眼神,觉得她是穿穿戴戴,碌碌无为。想开了,也不怨别人,四十岁的女人,是该做点正经事了。这世上,有为无为,不过是一念之差。签证已经办下来了,过一个月就走。听说我回来了,想听听我对她此行有什么好的建议。
还得说句大话,我这人,真本事没有,给人提建议,什么时候都是一套一套的。当时说了什么,全忘了,现在还能记得的,只有一条,就是选定了什么方向,关于那个方面的书,要尽量多买,带回一个集装箱,都不算多。且告诉她,我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人物,发现凡是留学回来带书多的,都成了大气候。比如李健吾,留法归来,藏书甚多,迭经损失,直到1966年前,社科院还在楼房外,单独给他一间平房放书。
她赴美的研修方向,事实上已经定了,就是看到这些年太原的老城区,正在一片一片的拆去,想到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正在消失中,该用一种方式,将这个城市的记忆留存下来,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世。这是方向。赴美研修,要找的是方法,是着手处。
一年后,研修期满,回来了。正好我又回太原避暑,这次是我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饭店的雅座,为她接风。
“来回机票不算,对方付的费用不算,我个人在美国一年,花了二十万人民币。”
一开口,先吓了我一跳。心里惊异,嘴上还能兜得住,打趣说:
“不会是全买了名牌吧!”
知道我是开玩笑,她淡然一笑,说起了在美国一年来的经历。
我听了,现在还能记住的,一次是去美国某地一个广场浏览,遇着一个老太太,恰是这个广场的设计者,于是便请老人家去喝咖啡,第二天又带了花束去府上造访。再后来,去一个旧工厂改造的艺术中心,在艺术中心的咖啡座,正好遇上这个标志性建筑的设计者,又是请喝咖啡,又是登门拜访。一宗宗,一件件,都是花钱的事儿,又都是大有教益的事儿。我听了,当即赞叹说:
“这世上,没有舍不得花钱,能成了大事的!”
她笑了,说,就知道韩老师喜欢这个调调,所以就先说了那个二十万。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具体的人名地名,过了也就忘了,现在要写这篇文章了,给小黄发微信,要她将那天讲过的,写成文字发给我。发来了。按说该将她的文字,化为我的文字,一想,费这个神做什么,直接引过来不就得了。下面是她的回复,自然也就是她的口吻:
初到美国,待了一个多月,我选中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克里夫兰演艺中心。这是一个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电影黄金时期的建筑群,电视兴起后遭遇生存挑战,险些被拆掉。幸好有建筑师运用城市更新的手法进行改造,如今作为克里夫兰的经济发动机之一,负责吸引全美游客来这座城市进行消费。Peter van Dijk,师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易·康,布洛松草坪音乐中心是他的代表作,但他投入精力和情感最多的正是我要研究的克里夫兰演艺中心。几经周折见面之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说说吧,是什么把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士带到这儿的?”那一天,我和Peter交谈了五个多小时。从他对克里夫兰演艺中心的重新塑造中,我了解到一座旧建筑为什么值得保留,特别是修复它的费用比建一座新剧院还要多;了解到如何让历史建筑焕发出新的生命;了解到建筑师如何决定城市的未来……在那之后,我在不同城市走进过Peter修复的老建筑,当我向管理员说出他的名字时,每每会受到特别的礼遇。2018年,八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他在电话里说:“明天克里夫兰演艺中心最大的那个演出大厅会为我举办生日宴会。多遗憾,你不在这里。”在美国的一年,我一个人开车在路上走了将近三万英里,除了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匹兹堡这样的大都会,还去过五大湖边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建筑是一个时代思想、审美、技术的集中体现,读建筑就是读历史,每一代人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就写在那些被精心保护、修复,并仍在使用中的老房子上。老房子成了我进入当地人生活的一个入口,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和游客谈论自己生活的街道、自己的童年和年轻时的恋爱。所以走到哪儿,我都成了一个受欢迎的Chinese Lady,很多当地人抢着和我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在超市买做鸡汤的佐料,一位女士很热心地帮我找到,站在过道边上和我聊起来。我告诉她,我是一位访问学者,来自中国,本职工作是记者,喜欢写普通人的故事。她羡慕地看着我,说:“你是个天才。”这句听起来一点没有创意的话,对我却是醍醐灌顶。我肯定不是写得最好的,但我能写,能表达自我,能替普通人表达,这对于她来说,就已经是天赐的才能了。这个才能除了让我混口饭吃,或者让我偶尔像大公鸡一样骄傲地走来走去之外,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让她这样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能够改变世界。从那天起,我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
就在她回来的那个秋天,我在北京,记得是9月吧,小黄打来电话,说是她出了一本书,要给我寄来,问我要地址。给了,寄来了。一本装帧雅洁的书,名曰《一个70后女神的时尚史》。我是不办刊物了,若办着,还会写一篇新的评论文章,大赞小黄的这种做法,乃为文之正路,作家之正宗。出书,总要滞后一个时间段。我知道,这是她将此前的文章,做个了结,往后,要做她的大事业了。
果然,2017年夏天,我回到太原,听说她倡导的“时尚回响”活动,已经办了起来。办事机构名为“时尚回响工作室”。第一步,先是征集带有时代记忆特色的物品。过去的征集点,在太原展览馆的地下车库里,现在搬到太原师院的一个教室里。我捐出了我在1993年花一万多元买的四通2406型电脑打字机。据她说,在另一个地方,他们租了一个库房,放置的东西,已满满当当。现在不光是她一个人在做,志愿者也有一大批。那天我见到的,就有好几个,从事的行业也是各式各样,多是年龄比她还要大些的知识女性。
他们的“城市记忆·时尚回响”,去年前半年在省图书馆办了一次展览,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年底,太原市专门为“时尚回响”项目开了一个论证会,计划建一座城市记忆馆,把实物和附着其中的记忆展示出来,让这些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用品,来讲述中国的过去,昭示中国的未来。
现在的小黄,比以前更忙了。前些日子,太原有名的商业中心钟楼街改造,拆了一大片。她闲了,不时去小街小巷转悠,常会有惊喜的发现。就在上个月,她给我发来一段视频,附言说,韩老师看了,定会有切身的感受。
视频名叫《四岔楼住过一个了不起的爸爸》,说她去钟楼街后面,走进四岔楼胡同,看到一处特别漂亮的老房子,很破了,还能看出当年的丰采。进了院里,正在收拾东西的姐妹俩,邀请她进屋里看看。石灰墙上,挂着一个老人的照片,端庄而有威仪。姐姐说,这是他们的爷爷,老山西大学毕业,在鼓楼街的银行做事;日本人打太原,扔炸弹,一条腿炸断了。桌上摆着父母的照片,岁数不小了,看去都很英俊,说母亲是进山中学的校花,父亲是进山中学的高材生。父亲后来去大连上的大学,回来参与了太原化肥厂的创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为一个小事(上班时间给女儿拿牛奶),就让开除了,只好四处打工,在一些小厂当技师,也当工人,有时还要爬上烟筒修什么。屋里一角,有个茶炉,妹妹说,这是在八十年代初,为了一家的生计,姐妹俩只好在夜市上卖茶水。爸爸特意设计制作了这么个小茶炉,只需做饭的炉火,就能烧开一茶炉的水。如何进水,如何过火,都是父亲精心设计下的。说到后来,抹着泪水说:
“老人家到死,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这个茶炉,收废品的要,我们就是舍不得。”
听了这句话,我真的流下了眼泪。我家是没到这个地步,但好也好不了多少。
视频中说,七天后,小黄再到这儿,房子已经拆掉,只有院里的那棵大槐树还在,能不能保住,也不好说了。那个茶炉,她是拉走了,可是怎么安置,一时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除了收集物品,小黄还发起了一个“爱写作”小组,鼓励普通人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40件物品里的改革开放史》,作者四十个人;一本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作者七十个人。今年要出版的《小康路上的光阴故事》,作者也是七十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任何写作经验,经过在时尚回响工作室的实物征集、写作辅导,现在围绕自己的一段经历,写两三千字不成问题。进步最大的一位,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写作,不仅让他们的自我评价提升,也帮助他们更理性地看待自己的人生,同时这些文字也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她不说我也知道,这还只是她的前期工作,后期工作,将是据此写出一部大书来。
我相信,多少年后,黄海波为这个老城市留下的“回响”,无论是实物,还是文字,必会显出更为宏亮的声响。当然,我最为希望的还是,眼下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地,大张旗鼓地做好这一工作。这,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2020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