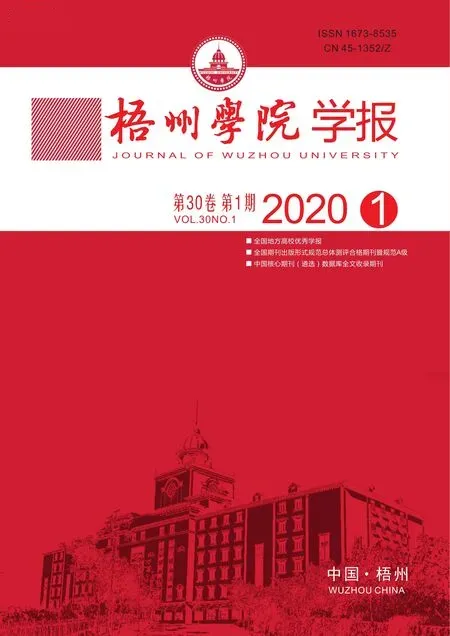近40年释契嵩研究综述
霍玲玲
(安徽师范大学 文艺学,安徽 芜湖 241002)
契嵩生于真宗景德四年即公元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即1072年。其俗姓李,字仲灵,自号为潜子,藤州镡津(今广西省藤县)人。因年少聪颖,在他7岁时母亲钟氏便把他送到离家乡不远的东山寺出家。在13岁时为沙弥,14岁受戒足,19岁开始了“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生涯,遍参名师。最终他在筠州洞山晓聪门下得法,成为云门宗法嗣,因其擅长习禅著书,成为当时一代名僧。
契嵩一生著述颇丰,除了《辅教编》《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被纳入大藏之中,还有《嘉佑集》《治平集》等。然其诗文后世散佚严重,后经门人收其著作辑成《镡津文集》。因这一文集具有极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引诸多学者对其进行探究。近40年(1978年至2019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对契嵩的研究,1978年至2010年30年间,专著仅有两部,期刊论文大约30篇。但是在2010年至2019年这10年间则有4部专著和近65篇论文。由以上的数据可知,第4个10年有关契嵩研究的著作、期刊论文数量急剧增长,研究也越来越全面。现将学者对契嵩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5个方面,并逐一分析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
一、契嵩生平事迹的考证与研究
关于契嵩的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平事迹的考辨,而关于契嵩的交游考,则研究较少。最早对契嵩生平事迹进行详细考证的是郭尚武先生,他在《契嵩生平与〈辅教编〉》一文中言:“我曾广稽典籍,撰写了年谱,约二万字,为节省篇幅,特将考据所得结论,作一简明年表。”这一简年表内容详赡,考证了契嵩从出生到逝世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后的学者也都深受这一简表的影响。笔者翻阅大量的资料发现,学界一致认为契嵩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郭先生扎实的文献知识为以后研究契嵩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
与郭文同一年,1994年祝尚书《三寸舌不坏的契嵩》一文中也介绍了释契嵩的生平。但相较于郭文以考证的形式,祝文则侧重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契嵩的一生[2]。
在祝文、郭文之后,邱小毛在《北宋释契嵩的生平及文论》[3]以及《镡津文集校注》[4]中均对契嵩的生平进行过概括性的简述。邱文关于契嵩生平事迹的论述基本和郭文一致,只有少数是对郭文考证不当的地方进行纠正和补充。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对契嵩生平事迹进行研究之外,杨锋兵[5]、郑洁敏[6]等人也在其论文中提及其生平事迹,但是他们在研究上依然遵循郭尚武的观点,尚无新意。总之,郭尚武和邱小毛在契嵩生平事迹考辨这一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后来的研究者也无一例外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在交游考中他们也没进行系统的考证,后来的学者应该对契嵩交游进行详细的研究,契嵩一生为护法奔走,交游对象应涉及文人士大夫。笔者认为要对契嵩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对其交游经历进行更为深层次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二、契嵩著作考述研究
契嵩著作考述研究多集中在对《镡津文集》的版本与流传,以及其诗文著作具体时间的考述上,这种扎实的文献考证技能,值得后人学习。
(一)《镡津文集》的版本及其流传研究
关于契嵩《镡津文集》版本研究,以笔者管之所见,国外较早对这一方面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椎名宏雄,其撰有《〈镡津文集〉の成立と诸本の系统》一文,该文既讨论了《镡津文集》之成书过程,又梳理了散藏于日本多种《镡津文集》版本之间的关系,其叙述甚是详细。但是学者对此人的研究成果不甚重视,也因其介绍的版本远在日本,文献难以查找,所以此文献的价值也未能体现[7]。而国内研究《镡津文集版本》较早的是祝尚书,其于1999年《宋人别集叙录》一书中仅对文集的版本进行了整理,并没有对各个时代此文集的流传状况作细致的考察[8]。
在祝尚书之后,2012年邱小毛在《古籍整理研究》上发表《〈镡津文集〉的成书与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残本考》一文,主要从释怀悟与《镡津文集》的成书和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残本考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证。第一方面,邱文据释怀悟《镡津文集后序》一文指出文学史上前人研究中的错误,同时指出《镡津文集》成书的相关疑点。例如,卷11《移石诗叙》注:“自此元别为卷。”邱小毛认为:“‘先’、‘元’者当指《嘉祐集》编次,注者当为怀悟本人而非刊刻文集的元僧。”而非祝尚书所谓“元”指宋刊本;还指出祝文中关于元残本编次不是怀悟编次原貌的错误论断。第二方面,邱文详细地考证了元残本的具体刊刻年代还考证出今天国家图书馆所藏《镡津文集》元刊残本是由幻住庵释明本、释永中师徒二人发起重刊。因元残本基本保留怀悟编次的原貌,邱文认为它具有珍贵的文物和突出的文献价值。邱文的优点在于对文集中相关疑点考证,而不足是仅对元刊残本这一个版本进行详细的考证和论述[9]。
继祝、邱研究之后,2013年蒋艳萍发表在《南阳理工学院学报》上的《〈镡津文集〉版本源流考述》一文中,主要对《镡津文集》在各个时代的流传状况进行细致的梳理,并且对各个版本进行简略的比较。此文还由版本流传历程得出两条变化的结论,即绍兴原稿流失,仅有20卷遗稿;元明之际文集由原来的20卷发展到22卷。蒋艳萍认为宋清存有刊刻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契嵩文学素养高和作品水平高;第二契嵩思想无论对乱世还是太平盛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蒋文优点在于对《镡津文集》四个版本即祖本——怀悟、宋刊本、元至间刊本、明代刊本、清代刊本进行梳理,较之前的版本研究有了较为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其文献价值不可小觑[10]。
同年,纪雪娟在《宋僧契嵩〈镡津文集〉版本考述》一文中通过对版本流传、各版本章节编次、内容整理这三个方面分析得出镡津文集分为两个系统即:宋刊本、元残本;另为永乐后诸本。纪雪娟还认为,后一个版本因明代僧人在重修时未尊重原文随意篡改,所以告诫后人谨慎使用[11]。
纪文相对蒋文而言,内容有所丰富,蒋文仅仅是对版本流传进行梳理,各版本之间比较也较为简略。而纪文则不仅包括版本流传,还对《镡津文集》成书经过进行详细的考证,尤其对《镡津文集》各版本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全面详细的比较,这一特点是上述所有研究都没有的。此文有利于后来学者更为清晰地把握《镡津文集》各版本的基本情况。随着《镡津文集》版本研究的深入,定源(王招国)于2014年在《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上发表的《日本藏〈镡津文集〉版本及其文献价值》一文,可以说有着极大的价值,原因在于其论述了散藏于日本的《镡津文集》,并且对日本《镡津文集》的两个版本即——“米泽本”和“国会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这两个版本的特征和两个版本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此文虽也存在着没有对两个版本之间的文字异同进行勘校分析的问题,但瑕不掩瑜。此文,有利于后来学者了解《镡津文集》在域外的流传情况,而且还启示后人需要对域外佛教文献更加关注[12]。
2017年彭子龙在《〈镡津文集〉版本考略》一文中,主要把《镡津文集》众多版本按照卷数的不同,分为二十卷、二十二卷、十九卷3个主要的版本,并且对这3个版本进行考证。考证过程中对蒋文、祝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13]。前人的研究主要根据年代的不同进行版本的分类,而按照卷数进行版本分类是此文最大的特色。它的优点不仅在于能够全面地梳理、客观地辨析《镡津文集》各版本的状况,还有利于把握各版本之间的流传继承关系。不足在于缺少对非主要版本卷数的考证与研究。
除了上述学者研究之外,王红蕾[14]、钱东和江晖[15]等人皆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镡津文集》的版本进行过考察和阐述。总之,学者对《镡津文集》版本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全面,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依然存在疏漏和不足。学界也期待后来的学者能够纠正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二)诗文著作的考辨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有关契嵩著作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不单单是著作,著作通常也只是起着铺垫的作用。虽然研究这方面的论文较多,但系统性不够强。笔者认为以下几人关于契嵩著作研究价值较大。
陈士强《契嵩见存著述考》上下两篇,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围绕契嵩所有的著述进行系统的整理以及严密的考证。除此之外,它还将契嵩现存传世的著作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为后来研究契嵩思想文论的学者提供重要的参考[16]。
除了陈先生研究之外,周大任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契嵩见存著作及其思想研究》一文中,将契嵩的著述从内容上分为两个方面,即:禅门谱系和一般的著作与诗文。并对契嵩著作的存佚情况进行概括性的描述[17]。这篇文章对后来学者探究契嵩文集版本以及诗文考述这两方面都有极大的价值。
在2012年,邱小毛对郭尚武先生的《契嵩年表》进行补充考证、补充[18]。邱先生首先肯定了这一年表价值且说明绝大部分是真实可靠的,但也认为其存在着错讹。例如《年表》景祐二年(1035)表文:“至杭州,与天竺寺僧祖韶交游。”邱先生认为契嵩在景祐二年没有到达杭州。除此之外,就是有关诗文写作具体时间的考证。例如《年表》中认为,宝元元年(1038)作《送真法师归庐山叙》而邱认为此文应当写作于庆历三年(1043);作《郎侍郎致仕》诗应为庆历元年而非皇祐元年;作《入石壁山》诗当在皇祐三年(1051)而非皇祐五年(1053);作《秀州资圣禅院故暹禅师影堂记》当在嘉祐己亥,即嘉祐四年(1059年)而非皇祐五年(1053);《年表》至和三年(1056)认为《辅教编》五书:1.《原教》《广原教》;2.《劝书》;3.《孝论》;4.《坛经赞》;5.《真谛无圣论》。而邱先生认为五书不包括《真谛无圣论》。
以上是邱先生对郭尚武先生《契嵩年表》中的错误进行纠正。笔者认为,邱先生论证的基本遵照原有的文献,有理有据。其做法启示后来的学者要对权威敢于质疑,在质疑之后,还应通过考证,得出更为精准的答案。
在纠正之外,邱先生认为《辅教编》入大藏,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北宋佛教伦理化进程的完成。而《契嵩年表》对《辅教编》这一内容未作说明。邱先生经过考证得出在嘉祐二年(1057)和嘉祐三年(1058)这两年,契嵩上书吕溱,并随书寄献《辅教编》一部三册并且向朝廷宰辅重臣寻求支持,其目的在于向仁宗皇帝上书以求扩大《辅教编》的影响。辅教编最终成书在治平三年(1066)。
令人欣喜的是,谭新红、冯红梅在继郭先生和邱先生之后在对契嵩有关著述方面更为全面、客观的论证,使这一方面的史料更为详实。谭、冯在《北宋契嵩编年系地考》一文中共考证契嵩55篇文和21首诗的编年系地,这些诗文的编年系地考价值在于明确郭文编年证据以及辩正郭文和邱文的误编之处。然契嵩诗文近300篇,目前尚有200左右的篇目没有编年,有待后世学者继续补充和完善[19]。
谢天鹏关于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一文主要对《嘉祐集》《治平集》《论原》进行考论[20]。他首先对《嘉祐集》《治平集》的时间和性质进行考辨。就《嘉祐集》的时间而言,谢文从契嵩回王存的书信,即《答王正仲秘书书》《嘉祐集》内文章时限以及《嘉祐集》内容这3个方面进行考证,得出其写作时间为嘉祐三年(1058)至治平三年(1066)间,且考证出此集主要以儒学性质为主。而《治平集》谢文则认为其写作时间在《嘉祐集》之后,且其主要体现佛学性质。其次,关于《论原》,谢文主要从《论原》之名和《论原》之时两个方面进行考证。他从4个方面证明《论原》是契嵩自己所编撰的系列。至于《论原》的创作时间,谢文则认为《论原》属于《嘉祐集》的部分,应成于嘉祐七年(1062)以后。所以其最终得出,《嘉祐集》《论原》之编成皆应在嘉祐七年(1062)至治平三年(1066)这4年之间。
谢文虽然考证严密,但是《嘉祐集》和《论原》的时间在嘉祐七年(1062)至治平三年(1066)这4年之间,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是此文的一大缺憾。
除以上学者研究之外,祝尚书[2]、远尘[21]等也都曾对契嵩的著述进行过简单的叙述。但是,契嵩的著述研究除了陈先生较为系统的研究之外,其他学者仅就某一篇或几篇进行研究。而且相较于《镡津文集》的版本研究而言,呈现出不全面、不系统的特点。
三、契嵩思想研究
(一)契嵩佛学思想及其所修禅史研究
1.契嵩佛学思想研究
最早对契嵩佛学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刘贵杰,其在《契嵩思想研究——佛教思想与儒家学说之交涉》一文中指出契嵩定禅宗印度世宗为二十八祖,这成为禅宗祖系的定论[22]。
2009年李似珍、李宇杭在《契嵩思想时代转换的启示》一文中也对契嵩禅宗定祖进行论述,相对刘先生的文章,二李之文还认为契嵩为禅宗定祖引起天台宗不息争论的同时,也对后世禅宗史的讲述产生深刻的影响[23]。
2001年王予文先生在《契嵩及其佛学思想》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契嵩对三教融合思潮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还研究了契嵩以儒、道两家思想为内容,以禅宗教学为方法。由此形成了完整的三教理论体系。王先生认为契嵩思想理论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一观点,有待后来的学者进行客观、全面的考证[24]。
继王先生研究之后,2005年聂士全的博士论文《实相与悲相——以释契嵩为中心的佛教真俗关系》从四个大的方面对契嵩佛学思想进行全面地论述。他先考证了契嵩思想产生的内外学背景,接着着重叙述大乘佛学5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即论述本与迹的关系、权与实的关系、真与俗的关系、理与事的关系、世间与出世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考察了性与情、心与识的关系并且指出华严与禅宗关于真俗方面的不足,最后对佛教真俗关系作出新思考[25]。此文的价值不止在于对契嵩佛教思想的深刻论述,还为学者思考契嵩儒佛、政教关系提供借鉴。
随着有关契嵩佛学思想研究的深入,陈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撰了目前为止研究契嵩佛学思想比较全面系统的一部专著——《契嵩佛学思想研究》。此书不仅写了其佛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佛学思想的特征以及佛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深入的分析了契嵩的“二十八祖”说、“六祖”说、“儒佛一贯”说、“佛道一贯”说、“禅教一致”说和“顿渐一致”说[26]。
2009年远尘的《契嵩禅师的佛学思想与著述》一文主要从契嵩独特的佛学思想体系和反映佛教思想的著作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禅净合一”的思想,并且认为契嵩有关护教的著作和禅学思想对中国佛教史产生深远影响[21]。
综上,关于契嵩佛学思想的研究较为全面但深度不够。尤其在2009年之后单纯关于契嵩佛学思想的文章屈指可数。学者应该紧扣其佛学思想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契嵩所修禅史研究
学界除对其单纯的佛学思想研究之外,亦对其所修禅史进行了研究,这部分的研究偏重对契嵩关于“禅门定祖”说的评价。
早在1992年陈士强先生就在《佛典精解》中对契嵩《传法正宗记》《正宗论》的体例和内容做过简洁的介绍,并且对《传法正宗记》作了客观的评价,首先肯定它是继《传灯》《广灯》之后,《续灯》《联灯》《普灯》之前的一部有影响的禅宗谱系类著作。其次陈文认为就《正宗记》本身的禅宗传法世系而言,并没有多大的特点[27]。
相对于陈士强先生的研究,陈垣在其《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既对《传法正宗记》又对《传法正宗论》进行了论述。此文主要考证了《正宗记》的版本、《正宗记》的内容并且对《正宗记》的得失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关于契嵩的《正宗论》,陈垣认为其虽善于文,但因受感情的支配,在考史方面没有成就[28]。陈垣的这一评价过于激进,可能契嵩在有关史论的考证方面存在不足,但是契嵩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2015年刘立夫的《禅门定祖说略论》一文指出,契嵩确立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之说的原因在于中国佛教各派的“法统”之争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除此之外还有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刘文还认为契嵩的“禅门定祖”说的论证虽经不起推敲,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更是肯定了契嵩对禅宗历史发展的贡献[29]。
2017年郑佳佳《论契嵩禅宗谱系说对菩提达摩的考证》主要探讨了契嵩宋禅宗谱系说中对菩提达摩人名、传记演变、入华纪年和达摩道4个方面的考证。郑文认为契嵩对菩提达摩缜密的考证虽不是站在学术考证和历史真相的立场上,但依然有利于菩提达摩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宋代禅宗的振兴[30]。
总之,关于契嵩所修禅史研究的文章陆续出现。这些文章大都对契嵩“禅宗定祖”说持肯定的态度,肯定其对禅宗发展史的贡献。
(二)契嵩儒释融合思想研究
学界有关契嵩儒释融合思想方面研究的成果颇丰。近年来由于学者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度的挖掘,亦或以儒释融合这一视角对契嵩的其他思想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限于文章的篇幅,本文仅详细分析具有代表性学者的研究。
最早对契嵩儒释融合思想研究的是郭朋先生,他在《从宋僧契嵩看佛教儒化》一文中认为,“儒佛一家”的思想本质是佛教儒化的思想,且这一思想经过南北朝、隋唐的发展至宋达到了高峰。他以契嵩为中心,从五戒与五常、孝论、赞中庸、赞礼乐、赞五经这5个方面,对契嵩所撰文章中所含“佛教儒化”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其认为契嵩为了维护佛教的生存,不断地改造佛教以适应儒家思想。这一改造过程其实就是佛教“中国化”。郭先生关于契嵩“佛教儒化”的观点对陈钟楠等后来的学者颇有影响[31]。
继郭先生之后,张清泉的《北宋契嵩儒释融会思想研究》一书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契嵩儒佛思想的融会。它主要考察了宋初儒士反佛特殊的社会背景、契嵩维护佛教的思想理论,还分别剖析了儒释融会思想中的儒学基础和佛学基础。这本书堪称研究契嵩儒释融合思想最为完整的一部作品[32]。
相较于其他人的研究,方友金给予契嵩这一思想高度的评价。其撰写的《论契嵩儒释一贯思想》一文,从“同于为善”“心一迹异”“戒孝合一”三个方面论证了契嵩“儒释一贯”思想,并且认为契嵩儒释一贯思想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创新,从而使这一思想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33]。
研究角度比较新颖的是台湾学者妙谨,其以诠释学的角度不仅分析了儒佛三个方面的融合,而且分析了契嵩儒释融合思想对诠释学的意义在于建立对话双方的语汇和共同交流的情境[34]。而陈雷撰写的《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一文的主要观点是,契嵩是从“义理”和“治世”的角度论证儒佛两家具有一致性[35]。
陈斐与张轩则是继郭朋先生之后也对契嵩著作内容进行了分析。他们分别从契嵩的《非韩》与《辅教编》进行分析。陈斐认为契嵩“非韩”的依据是儒释融合思想。且认为这一思想的本质就是——契嵩用儒家伦理会通佛家戒律,用佛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36]张轩则紧抓《辅教编》得出契嵩儒释一贯采取的理路是“借圣人立威”与“内圣外王”。通过这一理路说明契嵩“儒释一贯思想”具有一致性而不是相同性,因为这一思想特征是儒化过程中既保持了佛学的高妙,又与儒学并行不悖[37]。
除了上述书与期刊论文外,硕士论文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多。但这些研究仅是对上述学者研究的补充和细化,很少创新。因此这里仅仅罗列了篇目。如于翔飞的《宋代佛教的儒释一贯思想》、郑洁敏的《契嵩儒佛融合思想研究》、祁恪昌的《契嵩儒释会通思想“初探”》、李雨杭的《试论契嵩思想之“谈辩境域”》。
除了以契嵩“儒释融合”为主体进行研究,还有很多学者把“儒释融合”这一思想当作视角对契嵩其他思想进行研究。例如韩毅、付莉、杨静、李冰、代玉民、张培高等对契嵩儒释一贯思想中的“中庸”思想进行研究;王秋菊、李梦、郑佳佳、吴彪等对契嵩儒释一贯思想中的“孝道观”研究;魏道儒、张永梅、冯书杰等主要对儒释一贯中的“孝道观”研究。
总之如前文所述,学者对这一思想的研究颇深、取得成果也较大。不足点是学者对契嵩在宋学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关注不够。
四、诗文理论及诗文创作研究
学界对契嵩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诗文理论以及诗文创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上,以下分别论述这两方面的研究。
(一)诗文理论研究
台湾学者李雀芬是对契嵩文学进行全面详细研究的第一人。其在《北宋契嵩文学观》硕士论文中对契嵩“文”“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追溯了“文”与“道”之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不同的状态。值得肯定的是,这篇选取了唐朝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朝古文大家欧阳修,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与契嵩之观点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韩愈的“文”与“道”之间的关系看似文与道合,而实际上“道”与“文”是主从关系,柳宗元则主张尊“道”不废“文”(文指文采),欧阳修则主张“文道并重”。李文通过契嵩身处之环境、契嵩表达文学观的文章、后人对契嵩文学评论以及契嵩具体实践创作中得出契嵩“道充文至”“人文言文兼备”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38]。
继李雀芬之文后,邱小毛的《契嵩的生平及文论》一文中认为中唐至宋初的古文家所提倡的“道”是儒家的正统之道,而契嵩的“道”是既包括儒家之道也包括佛老之道。契嵩虽重“道”也不废“文”,甚至提出“其言欲文”的主张[39]。
2010年杨锋兵在其博士论文第五章第一节中简略概括了契嵩的文学主张。认为契嵩作文的目的是发仁义而辨政教;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是“人文”“言文”兼备[5]。杨文关于契嵩文学主张的观点与前人相比,并无新意。
2014年张勇的《契嵩〈非韩〉的文学意义》一文观点新颖,认为契嵩重“道”轻“文”。张文经过严密的逻辑梳理得出,契嵩虽然赞同韩愈的文道关系论,但是契嵩并不认为韩愈真正做到了“文以明道”。如举出契嵩对韩愈“不及儒之至道”“虽甚文、道不至”“第文词人”三个方面的批判;除此之外还论述了契嵩对韩愈文风的“尚奇好怪”“以文为戏”“为言不思,不顾前后”以及韩文中的“谀辞”等方面批判。张文认为契嵩对韩愈这些批判的文学意义,一方面锻炼了契嵩的写作水平,但是更深的意义则在于它影响了后来理学家对韩文的评价,它所折射出的“重道轻文”思想也成为理学家文论的基调[40]。
2018年徐波《论契嵩以“文护法”的文学意义》一文中论证契嵩在“性命之学”方面超过与他同时的古文家,并且认为契嵩之“重道”并不是简单对“文学性”的破环,而是追求对“道的超越”,即追求文章思想的深度和超越性。这一超越性的文学意义就如徐波所说:“契嵩以古文家的对立者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古文家的文与道,他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古文运动’并不像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取得了彻底的胜利。”[41]
虽然近40年来对契嵩的文学研究也有增加的现象,但是有关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仍然不够。之所以要对契嵩文学观和诗文创作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因其文学价值巨大。如《四库总目》评契嵩:“第就文论文,则笔力雄伟,论端锋起,实能自畅其说,亦缁徒之健於文者也。”馆臣在总评数僧中又云:“第以宋代释子而论,则九僧以下大抵有诗而无文,其集中兼有诗文者,惟契嵩与惠洪最著。契嵩《镡津集》好力与儒者争是非,其文博而辨。惠洪《石门文字禅》,多宣佛理,兼抒文谈,其文轻而秀。居简此集,不摭拾宗门语录,而格意清拔,自无蔬笋之气,位置於二人之间,亦未遽为蜂腰矣。”从这两条引文中不难看出,契嵩与北宋的文坛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但相对于契嵩思想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并没有对其文学方面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诗文创作研究
有观契嵩诗文创作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经整理仅发现邱小毛、杨锋兵、李雀芬、曾惠芬、黄惠菁等人对契嵩的诗或文进行过研究。
对契嵩诗歌和古文创作均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杨锋兵和李雀芬。杨锋兵在其博士论文《契嵩思想与文学研究》一文对契嵩散文内容及风格、诗歌内容及风格均进行了总结[5]。李雀芬虽也对契嵩诗文内容和风格进行详细的论述,但其文章主要是通过契嵩诗文创作的实践验证其文学理论[38]。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意义非凡。
仅从契嵩诗歌创作角度进行研究的是曾惠芬、黄惠菁。曾惠芬的硕士论文《契嵩唱和诗研究》一文,主要透过契嵩所编《山游唱和诗》探究其唱和诗的内容以及其唱和风格[42]。而黄惠菁则主要探究契嵩60首古律并且赞扬这些古律诗是契嵩一生才学情性的反映。尤其推崇其古律中抒情言志内容的诗歌。认为这部分诗歌一方面与北宋诗文革新精神有所交涉,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43]。
而邱小毛、曾琼则仅对契嵩古文进行研究。邱小毛在《释契嵩古文创作艺术浅探》一文中主要探究了契嵩古文中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三种主要文体的艺术特色[44]。在邱小毛研究之后,曾琼的硕士论文《契嵩古文研究》主要研究契嵩古文内容及其古文艺术特色。关于古文内容和杨锋兵论述基本一致,而契嵩古文的艺术特色,曾文则概括为“简而奥”“博而赡、折而宕”“平而畅”[45]。
综上,学者对契嵩文学观的研究仅侧重对其文道关系的研究;对契嵩诗文创作研究中的诗歌研究,仅仅对其古律诗以及唱和诗进行研究,研究的广度也是不够的。
五、比较及影响研究
专门对契嵩与其他僧人的比较、以及其文与其他文人的比较、契嵩自身比较这类文章几乎不曾涉及,有关契嵩影响类研究方面的文章也非常之少,这些影响简单可以分为3类,以下分述之。
第一,对文学的影响。在上文所提到张勇《契嵩“非韩”的文学意义》以及徐波《论契嵩以“文护法”的文学意义》,张文认为契嵩“重道轻文”的思想对理学家的文论基调产生影响。徐文则认为契嵩的存在是对文学史上有关“古文运动”取得彻底胜利的否定。
第二,对士林风气的影响。高建立的《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一文主要探讨契嵩佛学思想入世归儒对宋代士林风气产生的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有利于士大夫以心性理论重新审视人生;其次通过参禅礼佛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归依;最后有助于士大夫认识到佛学思想的强烈思辩性特点对于儒学有“补偏救弊”作用[46]。
第三,对理学的影响。周伟明、钟金贵的《学说互摄与学风互镜——兼评释契嵩人性论观照下的宋儒学风及其后世影响》一文认为宋代的大儒出入佛老之间同时兼采众长从而开启宋儒谈佛论禅、三教交融互摄的风气,这种风气催生了宋明理学[47]。而查金萍《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一文认为契嵩“非韩”激发了理学家关注本体论的思维模式[48]。相对于周伟明、钟金贵,查文还论述了契嵩“非韩”对当时排佛运动的影响以及影响了时人对韩愈的评价。
总之,关于契嵩之比较与影响研究这一领域,有待学者积极开拓。以便学界对契嵩纵向把握。
近40年来学者对契嵩及其《镡津文集》研究范围有所扩大,研究视角也逐渐多样化。但研究仍呈现出不全面、不深入。如契嵩生平事迹缺少对其交游的详细考证;《镡津文集》及其著述考证中依旧存在不少疏漏;思想上仅侧重对其“儒释一贯”的思想研究,对其佛学思想缺少深度的挖掘;文学观及诗文创作研究,文学观仅从“文与道”之关系为切入点进行论述,且新意不多、诗歌内容较有价值的研究仅涉及唱和诗以及古律诗;比较研究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忽略其作为一个僧人对禅学的发展与影响。虽然有所成就,但不足之处依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