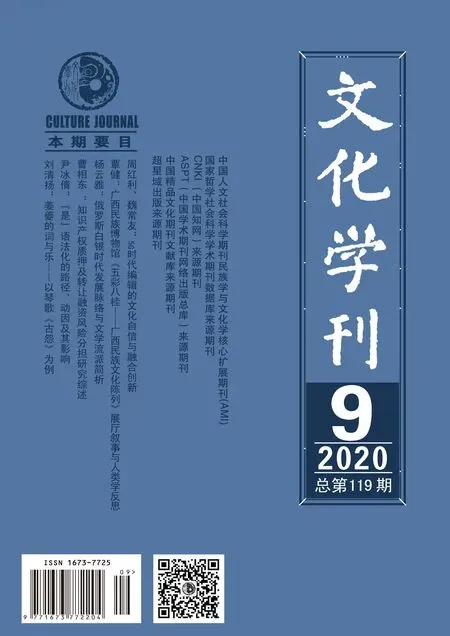郭实猎《康熙皇帝传》简论
钱律之
郭实猎是19世纪普鲁士传教士,作为第一位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相当引人注目。随着新一批传教士来华并展开对中国的研究,此前耶稣会士在西方的话语权逐渐被替代,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阶段,郭实猎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依托娴熟的汉语和多年在华经历,他写下多部广为人知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创办了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期刊,并在西文刊物《中国丛报》上刊载多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关于清朝康熙和道光皇帝的传记。《道光皇帝传》的单行本在海内外多次再版,国内学界亦有《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一文做注脚。而收录于《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开篇的《康熙皇帝传》却鲜为学界所知,更无研究。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至鸦片战争,该文是目前已知欧洲唯一一部关于康熙皇帝生平的全传,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本文将就其来源及版本流传、主要内容、叙述特点以及价值影响作一讨论。
一、《康熙皇帝传》版本源流及主要内容
(一)《康熙皇帝传》版本源流
郭实猎的《康熙皇帝传》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未有单行本,而是附于《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中。该书由英国伦敦费舍尔出版社首版于1843年,作为其此前编辑出版过的一些介绍异域风情画册的延续,该书邀请到了出版社此前合作多次的阿罗姆和怀特进行创作。前者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基于以马戛尔尼使团随行画师亚历山大为代表的多位英法画家的中国风情画,创作了128幅精美绝伦的钢版雕刻插画。古典文学家怀特负责文字工作,他曾为19世纪中期为包括《都柏林历史指南》《图说爱尔兰》在内的一批风俗画册执笔。
在两人创作期间收到的众多来稿中,包含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创始人之一的亚历山大·约翰逊提供的《康熙皇帝传》,他与郭实猎多有通信往来[1]。得益于制作和内容的精美丰富,该书出版之后在欧洲畅销一时,成为近代西方介绍中国的经典绘本作品。不过,或许是出于体例完整性的考量,这篇传记在1858年的再版中被删去,此后再编辑也都延续该版[2]。
书中收录的百余幅描绘当时清帝国风貌的钢版雕刻插画亦在21世纪初引起了国人的兴趣,多家出版社陆续刊印其译本,如202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清帝国城市印象》、201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2017年台海出版社的《西洋镜: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等。由于它们全部译自1858年的英文版或其再版以及国人兴趣大都只集中于其中的版画,因此未有中译本收录《康熙皇帝传》,更不必说对它的了解和深入研究了。
(二)《康熙皇帝传》体例与内容
《康熙皇帝传》以英文撰成,凡共72页,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继承皇位(1661—1666);第三部分,亲理政事(1667—1672);第四部分,北方纷争(1677—1701)。
引言部分可分两节。首先介绍17世纪末18世纪初世界上三位伟大君主,即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皇帝彼得大帝以及中国清朝皇帝康熙。通过对比,引出“康熙是一位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当之无愧的杰出人物”这一评价。尔后,介绍满族的历史沿革。依次叙述清代之前的唐代靺鞨时期、辽代与两宋的女真时期、金朝灭亡后族群的分裂以及明代女真部落从明代到清代入关前势力逐渐壮大的过程,文章对爱新觉罗氏的产生与壮大至顺治何以清明治国这段历史有详尽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爱新觉罗·玄烨在四大臣辅佐下即位至亲政的历史。彼时,郑成功在台湾立足并拥护明政权,是为康熙朝一大隐患。此外,文中对“康熙历狱”作了详尽描述,以杨光先和南怀仁为代表的满汉两派官员在该问题上的对立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有更具体的表现。
第三部分是介绍康熙亲政后的一系列措施,介绍他在文化上注重西学和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在政治上开展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汤若望去世后,皇帝决定用实证解决宫廷内关于历算的争执,结果是南怀仁完胜。此后,南怀仁见宠于康熙,为清帝国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康熙朝分别与漠北厄鲁特蒙古部族和沙皇俄国的两次纷争。在对漠西厄鲁特蒙古部族的发展沿革作简单介绍之后,文章通过引述《张诚日记》还原了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准噶尔的场景。与此同时,清帝国与沙俄之间始于顺治年间的纷争也有了以缔结条约为标志的显著进展。
该传记书写材料主要来自中国官修史书及前辈耶稣会士的著述,如法国耶稣会士所撰之汉学奠基之作《中华帝国全志》和法兰西公学院汉学主席雷暮沙的《中国杂纂》。如此援引片段式的资料使郭实猎对历史事件的描摹细致入微,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历史事件叙述之间缺乏连贯性与逻辑性。论及规模较大的军事时,郭实猎的处理仅是生硬拼接,事件之间缺乏过渡,对传主个体生命经验的描摹和对帝国发展态势缺少全局性把握。
二、郭实猎与前代传教士著述异同
由于来华耶稣会士的宣传和启蒙思想家的推崇,康熙帝成为17至18世纪欧洲“中国热”时最为西人所知的中国君主。在《康熙皇帝传》之前,欧洲已有很多关于他的著述,多为与之有过亲身接触的耶稣会士所作,包括张诚的《张诚日记》以及南怀仁的《鞑靼旅行记》。其中,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于1697年出版的《康熙帝传》是第一部由西方人所作的较为完整的关于康熙的传记。由于康熙末年开始推行的长达百年的禁教政策,中西交流逐渐衰落,西方关于康熙皇帝的记忆也随之淡化。至19世纪上半叶,郭实猎《康熙皇帝传》的问世才再一次向西方展现康熙皇帝的生平。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中西双方经历了政治、经济实力的颠覆性对调,故两位传教士在各自的作品中也倾入了各自的历史认知与现实关怀。
(一)自我身份与客体对象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急欲取代国力日渐衰微的葡萄牙成为新的宗教大国,同时,法国皇家科学院正积极派遣团队开展海外考察。因此,白晋等传教士肩负着宗教、政治和科学的多重使命来到中国。白晋就在《康熙帝传》中屡次提及法国优越的艺术和科学,更不用说随处体现意欲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理想。对于他而言,康熙对天主教传播实施的宽容政策几乎是一种神迹,他认为这些中国人的倾向以及他们皇帝本人的倾向都是上帝授予的。他夸耀康熙有“有惊人的记忆”和“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对一切疑难问题能作出最公正的判断”,甚至将他与路易十四相提并论。白晋将自己对于传播宗教的使命感以及对路易十四的忠诚注入作品之中,将流布福音的希望寄托于笔下那明智果敢、理性宽容的康熙身上。而当郭实猎作品发表时,中西方矛盾已全面爆发,中国形象随着一系列宗教事件以及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彻底贬损。相较于白晋,郭实猎没有政治和科学的包袱,他自称“爱汉者”,对于康熙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和对此前一系列汉学著述的补充和延续。因此,从表达方式来看,郭实猎更注重表达的是客观的历史认知。例如,同样是对传主的评价,郭实猎由于缺乏亲身经历因而在文中涉及不多,寥寥几句也只是依赖于前辈传教士的描述。例如,他认为康熙有着成熟、开明的头脑,谙熟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也注重数学和物理的学习,这或许是整个帝国里唯一一个重视科学的中国人。再如,郭实猎夸赞康熙敢于带着实验的真理去反抗国家的全部朝臣,这种坚定、果敢与对真理的纯粹坚持和对偏见的包容都是值得钦佩的[3]。
虽然读者从只言片语中仍能感受到郭实猎对这位皇帝的崇敬之情,但这仅仅是出于对此前欧洲关于康熙帝认识的一种延续,并没有真情实感的倾注。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两代传教士的写作风格不同,将郭实猎的《道光皇帝传》纳入考察范畴可以得明晰的理解。该传出版于道光皇帝崩逝的两年后,以17个章节的篇幅详细记述了道光帝的生平及其为政要事,兼叙该时期的中外关系和世界大势。虽未与传主有过接触,但作为这一政权统治下诸多涉外事件的亲历者,郭实猎在《道光皇帝传》的写作中倾注更多的是个人经验和对清代君权的整体把握及理性思考,这些是《康熙皇帝传》中所未有的。
(二)微观细节与宏大叙事
在对传记所记述事件的详略安排上,郭实猎与白晋两人也有很大不同。后者撰写这篇传记时多选取与康熙皇帝亲身相处时印象深刻的片段与细节,如他耳闻皇帝如何耐心地为来告状的百姓主持公道或者他目睹皇帝如何同情因为荒年而陷入贫困的百姓,为他们豁免年赋、开仓济粮。郭实猎的作品虽大量援引前人著述,但体例上大致遵循了主流线索,一一论及那些诸如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准噶尔之战或者统一台湾等在后世历史语境中被津津乐道的“大事件”,而白晋对此却只是概括性提及。例如,同样是对《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的叙述,郭实猎是不厌其烦地引述《张诚日记》中的内容,甚至细致到每一天具体发生的事,白晋却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与其说白晋的《康熙帝传》是传记,不如说是这位传教士对康熙皇帝的回忆录。白晋亲历康熙时代,甚至与传主有过密切的接触,同时,他完成这一作品时康熙仍在位,历史尚未对其形成客观的评价与总结。因此,白晋作传时倾向于以自己的记忆作为素材。在一百多年后的19世纪中叶,随着康熙时代的远去和相关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版,郭实猎得以参考更多元的文献,保持对一段历史更宏观和理性的把握。对于作品中所要论及的“大事件”的挑选,郭实猎应该也做了筛选。除去引言,《康熙皇帝传》中几乎只剩下皇帝与传教士的互动以及康熙朝几次因危及政权而进行的战争。同样是传教士的郭实猎,他对历史上耶稣会士与传主的互动倾注更多笔墨是合情合理的,传记的另一重心却仅仅关注康熙朝几次对内外战争则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这篇传记中提及的参考作品本身涉及的内容不止于此。例如,《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中详细记叙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这一康熙朝盛事,但郭实猎并没有选择参考。根据该传记及其参考文献的出版年份推测,其正式写作时间应当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世纪40年代初。其时,中英两国因鸦片贸易而滋生矛盾,剑拔弩张,郭实猎作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翻译官参与其中,十分了解时局的走向。在撰写《康熙皇帝传》时,郭实猎或许正是有感于现实中那场(即将)发生在没落的清王朝与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在素材的筛选上有如此偏重。
(三)非宗教著述中的宗教色彩
除了作为19世纪新教传教士作品有区别于前代的特质外吧,《康熙皇帝传》也保有两百年来由于作者身份所决定的迥然不同的风格,即明显的宗教色彩。郭实猎的文中随处可见被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基督教事业与君主品质及各国文明:
评价满族入主中原:“满族这样一个文明程度低同时缺乏勇气和战斗经验的关外民族,却能在同明王朝的争权夺利中取胜,这样伟大的革命应当是上帝造就的。”(笔者译)[4]
评价顺治帝信仰佛教:(笔者译)“人类是如此矛盾,纵使在感到痛苦时迫切地向宗教寻求安慰,肉体却在艰难的赎罪之路前畏缩了。因此,人们必须得到上帝的指点才能进入安稳的精神世界,即使对于自以为是的异教徒顺治来说也是如此。”(笔者译)[5]
像这样在非宗教类著述中渗透着的宗教色彩,在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作品中也均有体现。例如,白晋在《康熙帝传》中就认为“是上帝通过科学和艺术丰富了他(康熙)的头脑,培养了他的高尚情操,并激发了他对圣教的兴趣”。可以说,这是传教士写作的共有特征。
三、余论
欧洲持续近百年的“中国热”在18世纪末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后而彻底退去,进入19世纪后更是荡然无存。郭实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中西关系转捩点上对双边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物。虽然他抱有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却碍于交流障碍无法深入内地亲身体验,但也通过三次航海经历和在中国沿海地区生活的经验以及前辈传教士的著述,获取了对中国的一定认知。因此,他的作品为窥视这些相关问题提供了某种混杂新颖与陈旧、抽象与具体的独特视角。这篇《康熙皇帝传》不为主流视角纳入郭实猎作品体系内,就其体量和写作方式而言,都不及他自己的其他著述。但是作为19世纪唯一一篇由西方传教士撰写的康熙传记,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将这位昔日欧洲人热切关注的中国皇帝重新引入西方社会的视野,渗透着特殊时代中这位传教士汉学家的历史认知、现实关怀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