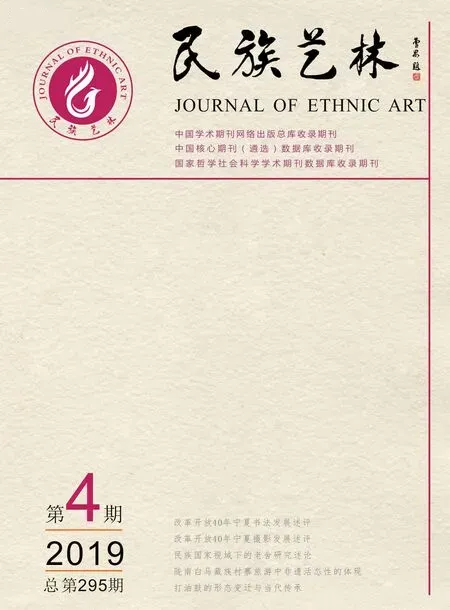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研究
芦静静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侗族迁徙古歌主要包括了《祖公之歌》《祖公上河破姓开亲》《祖公进寨歌》和《祖公落寨歌》等一系列古歌,此外还有不少相关的异文变体。侗族迁徙古歌是关于侗族先民迁徙、定居、婚姻和改革等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的古歌,它以祖先的迁徙为主要线索,涉及侗族古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堪称侗族的史诗。由此,侗族迁徙古歌往往被看作侗族的一组事件序列、一种历史,但却忽略了其中的空间元素。龙迪勇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事件都既是时间维度的存在,又是空间维度的存在。如果仅强调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无疑是对事实的歪曲,对真实性的遮蔽。”[1]时间与空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在此意义上,侗族迁徙古歌不仅只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时间艺术,更是涵盖时间的空间艺术。侗族迁徙古歌依托侗族祖先所处生存环境中的物理空间而进行白描式的、原生态式的书写,并将其所看、所想、所悟和所经历的内容通过不同的空间体进行叙事说明。据此可以看到,侗族迁徙古歌自身所携带的文体属性和内容特性使其空间叙事特点更加鲜明和突出。而近年来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恰巧为研究诗歌空间叙事提供了一种契机,尤其是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这篇论文的出现,使空间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使得人们借助空间叙事理论来重新审视侗族迁徙古歌这一诗歌文体成为可能。同时,现象学提出要回到“事物本身”,其实质是悬置成见返回到最原初的境域,即返回到纯粹意识领域。从现象学出发,侗族迁徙古歌的表层意蕴体现了客观性和物质性的第一空间认识论,深层次则是将想象力融入对人与空间、自然的内在关系研究当中。因此,在空间叙事学和现象学的观照下,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空间表达,参与了古歌的叙事;而且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观念意象,凝聚了侗族人民的心理能量和生命意志,蕴含了浓郁的诗性特色和审美意蕴。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本质上则体现为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融合互渗,继而古歌也成为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结合体。
一、空间意象的呈现
意象是少数民族生命力的珍贵留存,渲染着其所属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基色,涵纳着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族群意识,意象在后来的发展中也逐渐成为少数民族独有的地方性标志和文化符号。换言之,意象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珊·朗格是将意象视为艺术本体的第一人,她提出:“意象是艺术和文学创作的核心形式要素,但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2]依据于此,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呈现出如下表征。首先,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主要是指侗族先民迁徙途中的场所空间。这些场所空间意象凝结着侗族先民的生活记忆和自然经验,从而进入自然意绪和历史氛围之中,并成为古歌中故事发生的场域和情境。其次,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是一种符号。这些空间意象从潜意识中提升出来,然后从物质性的实体空间抽象为内涵价值意义的精神空间,并逐渐演化为一个完整而明晰的文化符号。再次,侗族迁徙古歌的空间意象具有一种叙述特质。马明奎曾经说过:“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3]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本身所携带的双重空间属性便已蕴含了叙述所需要的起因、结果和意义。由此,空间意象符号的表述运动最终实现为古歌的演唱实践。
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体的时间和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空间。[4]侗族迁徙古歌讲述了侗族祖先为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选择从梧州、浔江和胆村等地出发,而后在沿江沿河等地上岸建立村寨的迁徙定居故事。在这个迁徙过程中,侗族先民每天都在这些场所空间中劳动和生活,这些空间可以说是侗族先民行动和意识的最初定位之所。这些场所空间也被人感知和利用,随后成为“活”的空间进入古歌中承担着重大的叙事功能。侗族迁徙古歌中空间意象的叠加进程则绵延为主体体验的时间流,这也使得侗族迁徙古歌成为一系列空间意象组合起来的一个时空体。那么,意象在古歌中的分布和绵延则构成了整首古歌的空间和时间,意象成了古歌的建筑砌块;如果离开了意象,古歌就会失去形体上的依托和价值上的蕴含。加斯东·巴什拉曾经说过“诗歌的组构就是众多意象的集合”,[5]12古歌亦是如此。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指的是那些表示地点或隐含着地点的意象,而且它们往往还和一些方位介词相连出现。侗族迁徙古歌中常常会频繁出现一些空间意象,比如“梧州”这个场所空间意象在《侗族祖先哪里来》这个文本集合中出现的次数高达17次;而“浔江”“胆村”这些场所空间意象出现的次数也颇多。比如《侗族祖先哪里来》这首古歌:“我们侗家祖先,落在什么地方?就在梧州那里,就在浔江河旁,从那胆村一带走出,来自名叫胆的村庄。”[6]又或《祖源歌》这首古歌:“梧州地方田坝大,音州地方江河长。”在这些诗节当中,“梧州”“浔江”和“胆村”等这些地方场所性质的名词,不仅仅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意义存在,而且还作为侗族古歌中的空间意象存在。
此外,在侗族迁徙古歌一系列的空间意象群中,还存有核心空间意象。核心空间意象在空间意象群中处于焦点的位置,其他意象的存在都服务于此空间意象。核心空间意象是整首古歌中意义最核心的地带,也是侗族人民精神的“圣地”。同时,核心空间意象也是古歌进行叙事的空间触发物,它们身上特殊的秉性给侗族先民的迁徙提供了强烈的动机。侗族迁徙古歌中的核心空间意象则是古歌中经常出现的“村寨”“寨子”和“村庄”等意象,比如《我们的祖先江西来》这首古歌中常常会出现“村村寨寨都住满”“又见一个小村庄”“只恨寨子扩不大”“重的地方就扎寨”等之类的诗句。而“村寨”“寨子”和“村寨”等这些意象在这个文本中共出现5次,它们充当着侗族先民迁徙路上的精神之源。侗族祖先在古代社会中经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村寨”“寨子”和“村庄”等这些空间对他们来说具有很强的类似于“家”的性质。可以说,侗族祖先跋山涉水迁徙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找到可供侗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定居地——村寨。可见,“村寨”“寨子”和“村庄”等这些空间意象是侗族先民迁徙的意义来源,也是侗族祖先民精神世界当中的基点。基于此,“村寨”“寨子”和“村庄”等这些神圣空间便能够在古歌文本中不断衍生出价值意义和主题内容,生发出与侗族迁徙历史相关的人物和故事等。核心空间意象不仅是侗族人民统合在一起的地方,而且还是侗族人民精神共同体的依靠和支柱,其他的空间意象无此特殊意义。
总而言之,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不仅能够作为背景空间或者物理属性的空间存在,而且还能够作为整个侗族心理情感和精神意义的归属地。同时,这些空间意象还组构了古歌的整体空间,保持了古歌对侗族迁徙事件的原生态记录。
朱光潜认为诗歌是“从混整的悠久的而流动的人生世相中摄取来的一刹那,一片段”,并最终实现“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7]侗族迁徙古歌中所摄取的那些空间意象,不仅为侗族迁徙古歌提供意义发生的场所和审美的可能,更为侗族人民提供精神力量和生命能量。侗族迁徙古歌中经常出现的“梧州”“江”“河”“村寨”和“村庄”等空间意象,它们虽然普通常见,但却是一种神意氤氲、诗性盈园的场域,包含着对这个民族独有的含义和代码。侗族迁徙古歌不仅将这些物理空间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且也把侗族先民迁徙的物理实践进行叙述和记忆。同时,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作为诗歌的构件,也能够生发出诗歌这一文体所需要的人物、形象、故事和情节等叙事因素。继而,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从普通的组织作品的构成地位提升为核心性与实体性的地位,将古歌的诗歌性与小说性特征完美融合在一起。
二、空间意象的叙事功能
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不仅作为文本意义的来源,而且还具有叙事学上的意义。侗族迁徙古歌的空间叙事打破了时间性的万能叙事,将空间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故而空间在整个诗歌运动组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侗族迁徙古歌中的每个意象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诗性空间,占据着诗歌整体空间中的某个点或是某个位置,因而那些空间意象可以看作古歌空间叙事的基本单元,整个空间意象群的安排组合则构成了古歌叙事的主要内容。继而,侗族迁徙古歌中的叙事主要以空间意象作为一个叙事因子或叙事单元,并通过众多空间意象之间的连缀、跳跃、切换和并置等方式呈现出“故事”的一种叙述方式。因此,空间意象在古歌中呈现出强大的叙事功能,古歌的空间叙事的实质就是古歌空间意象的叙事。
首先,古歌中的核心空间意象成为叙事的支点。叙事支点是指整个故事能够进行叙述的“基点”,故事中其他叙述部分也是围绕此“基点”展开。侗族迁徙古歌中经常出现的“村寨”“寨子”和“村庄”等这些空间意象因其本身所携带的价值意义使其成为侗族古歌进行叙事的支点,包含了整个叙事文本的主题意蕴。在侗族迁徙古歌中,“村寨”“寨子”和“村庄”等这些空间不只是古歌中呈现出来的物理空间,在深层面上它们还是侗族祖先的精神空间。这些核心空间意象不仅是侗族祖先抵御天灾人祸的念想,而且还是侗族先民安家乐业的源泉。此外,它们还是子孙后代美好生活的保障。集侗族祖先这些美好愿望于一身的核心空间意象,自然而然地成了侗族祖先选择迁徙的起因;而这当然也是侗族迁徙叙事古歌能够出现的原因。如《祖源歌》:“另外去找幸福的村庄”;《忆祖宗歌》:“从此分为寨,从此分为村。家家安居住下,人人种田为生”;《祖公上河》:“村村寨寨人兴旺,男耕女织乐无疆”。
其次,侗族古歌中空间意象的安排组合掌控了叙事的秩序。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叙述者需要对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重新组合处理。而在这之前,叙述者必须先要从万千事件中挑选出最有意义的事件作为叙述对象,还必须给予选出的事件以某种“秩序”——将选出的事件赋予形式化或结构化。诺伯格·舒尔兹曾经说过:“人对空间感兴趣,其根源在于存在。它是由人抓住了在环境中生活的关系,要为充满事件和行为的世界提出意义或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8]空间给予记录的事件以某种“秩序”,也就是说,空间使事件形式化或结构化。侗族迁徙古歌的叙事不是对侗族祖先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再现,也不是事无巨细地将其经历的每一个空间场所都记录在内,而是对过去事件的重新选择和组织,并将其赋予稳定的叙事“秩序”。侗族迁徙古歌中“梧州”“浔江”“胆村”和“村寨”“寨子”“村庄”等这些空间意象的延展和出现,使得侗族迁徙古歌的内容必然要按照它们出现的顺序进行叙述和安排。比如《祖源歌》中,主体部分的叙述顺序大致就是:梧州(这个地方无法满足生存)→寻找新的村庄(找到,但住满了人)→翻山越岭到达贯洞(建立村寨定居)→村村寨寨都高兴。
再次,侗族迁徙古歌中空间意象的连接转换推动了叙事进程。侗族迁徙古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尤其是演唱艺术,对叙事进程的快慢有着很高要求,而古歌的叙事进程有赖于空间意象之间的过渡和切换。在侗族迁徙古歌中,空间意象每切换一次,诗歌叙事就往前推进或是转折一次。两个空间意象之间连接转换的间隔,必然也会影响到叙事进程的快慢。如《忆祖宗歌》:“木究、演究宽又平,可惜江水不由人。那个地方,田在高山上,水在低处流,种棉长不出,种谷无收成;女无饭饱肚,男无衣遮身。侗家心着急,客家也是发怨声。老家住不下,要把生路寻;祖公沿河往上走,扶老携幼向前行。”从“木究”“演究”这两个空间意象到“河”这个空间意象之间的转换间隔很长,叙事内容相当详细,则叙事进程就非常缓慢。又如《祖源歌》:“梧州地方田坝长,音州地方江河长。”“梧州”和“音州”这两个空间意象的转换间隔非常短,虽然加快了叙事进程,但叙事内容相对比较简洁。从这两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古歌中相邻空间意象之间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事实上它们彼此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却决定着叙事进程的快慢。在这样的诗歌进程中,古歌的叙事也会随着意象的过渡切换或走向高潮或走向平淡,从而带给听众一种高低起伏、跌宕回肠的感觉。
在以往的古歌研究中往往忽略了叙事性的观照视角,事实上,古歌存在着独有的叙事传统和发展脉络。侗族古歌之所以是其民族珍贵历史留存,也与其叙事性的特征密不可分。侗族迁徙古歌中所选取的那些空间意象亦是对其叙事性的加持,空间意象在古歌运动组构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叙事性的辐射性增长,从而使得古歌的叙事越发立体丰满,真切可感。侗族迁徙古歌中空间意象的叙事始终与古歌整体诗节呈现的形式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古歌既受制于空间意象的安排组合,但又与其融为一体,组成一个完整的诗歌空间。古歌中的空间意象支撑起文本的整体结构,同时,这些意象所携带的叙事属性和功能作用则展现了古歌内在的运动方式与结构规律,激发了古歌的艺术生命力。
三、侗族迁徙古歌的叙事模式
基于空间意象的叙事功能分析,能够得出侗族迁徙古歌空间叙事的基本模式便是从一个空间意象到另一个空间意象的过渡或切换,但是意象之间的过渡和切换也往往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侗族迁徙古歌中抽离出来的叙事模式大致呈现如下:原有空间意象(无法满足生存)→寻找另一个空间意象(该空间也无法满足生存,于是稍做停留)→继续寻找下一个空间意象(能够满足生存)→在该空间意象内建立村寨(定居生活)。此外,这个叙事模式在有些古歌中是以复制循环的方式连续出现。接下来,此处便以描述侗族祖先迁徙和定居的《侗族祖先迁徙歌》为例子进行说明。梧州(讲述这个地方无法满足生存)→寻找新的住所空间胆村(但住满了人,只好继续往前走)→翻山越岭到达古州、盛娥(建立村寨定居)→过上好生活。再如《古邦祖公落寨歌》:木究(遭大旱无法生存)→逆水而上至河沙坝(环境恶劣无法生存)→继续沿河而上到达古邦(建寨定居)→过上好生活。
从古歌叙事模式中可看出,侗族先民对空间的认知和选择并非是整体、数量化的全部覆盖,他们总会选取那些能够促动人类精神灵魂的空间表征物。空间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认知结构,包括实体显现和心理精神化两个基本维度。[9]由此,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也呈现出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古歌当中的物理性空间,指向文本的直接可视性;一是心理情感运动空间,指向文本的价值意蕴,空间的显现基源于此而获得它的物理形态和精神理念。同时,古歌中空间意象的感知和利用是心理情感推动的,空间意象的选择是心理情感主导的,空间的安排是受到现象的心理秩序掌控的,而由空间所导致的联想想象活动也是心理情感联结的。简而言之,心理情感贯穿了空间选取、运动和组构的全过程。继而,空间不能被完全分离于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但心理情感运动空间却主导了空间意象的生产。由此,空间构成与显现都以心理情感为动力核心,决定了与此相对应的侗族迁徙古歌叙事模式是一种心灵模式。普列汉诺夫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10]在古歌的叙事模式中,心理情感结构是起关键和主导作用的深层动力系统,抽离出来的一系列空间场所意象组构的叙事模式则是表层操作系统;心理情感和空间意象的通感与融会则呈现出从现象到心理、从表层到深层、进而再从心理回溯文本、从空间场所走向词语和符号的冲腾凝结、沉浮往来的过程。那么,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作为心理构件向题材涵化和变现的根本方式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情感与世界的统一,现象学与人类学的统一。至此,侗族迁徙古歌也从不同方向和维面指向了主体心理的情感深层。侗族迁徙古歌以心理情感作为核心,聚合着空间意象,并组构空间意象体系,继而生成古歌空间叙事的模式,而演唱者或听众也能够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意象体系引起情绪共鸣,体验到其所蕴含的心理情感。当然,正是侗族人民这种心理情感的共通性,才使得不同时代的侗族人民在面对流传至今的古歌及其空间意象体系的时候,都有相近的审美心理活动,都能产生大致类似的情感情绪。
侗族迁徙古歌诞生于空间与文学活动的审美实践之中。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空间实际上是侗族先民生命运动的外在征象,其内在抽象形式主要表现为发生学意义上审美经验的心理情感运动。在此基础上,侗族古歌的空间叙事模式向外能够延伸到主体的活动场域,向内能够剖析主体的心理情感。侗族迁徙古歌以空间意象为切入点,通过心理情感的深层动力系统和叙述模式的表层操作体系的相互配合,完成审美活动发生的一般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理性的空间属性虽然表征了空间意象在古歌中的整体存在,但心理情感却是其本体和本源。侗族迁徙古歌则是侗族人民在心理精神领域求得审美理想与人生价值的一次实践,侗族迁徙古歌的空间意象是侗族人于生命体验和自然万物之间构拟出来的一种意向性关联,这其中不仅蕴含了世界的领悟,而且投注了存在的意义。总的来说,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是其在心理情感的逻辑上回向主体体验的情境延展,并且还能够在其演唱流传的过程中逐渐生发出本体喻指和价值蕴含。
四、结语
综上,侗族迁徙古歌以侗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实践为基点,以心理情感为核心动力,聚合了一系列的空间意象,彰显了空间意象强大的叙事功能,体现了空间物质性和情感性的本质,考察和审视了空间、时间与人存在的内在关联性和影响性。从空间意象的分析来看,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不仅承载着侗族先民的生命体悟和自然体验,而且成为叙事的逻辑起点。同时,侗族迁徙古歌以迁徙情境和听者受众为条件,悦纳主题、叙述、信息、情感乃至精神等诸多层次,熔铸成一条意识之河,从侗族人民的心理世界流淌到现实世界。继而,古歌能够投注于历史、文化和世界三个题材义域,完成文化景观、地方性标记、族群意识和符号象征的塑造,生发出心理能量、生命意义和民族凝聚力的价值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