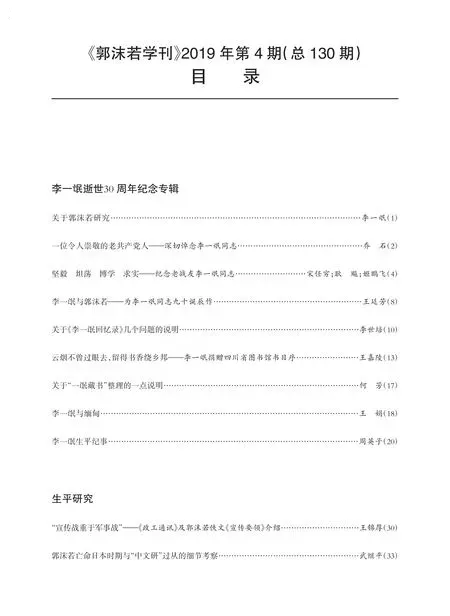论郭沫若对甲骨三堂的评价
——兼论郭沫若历史人物评价标准
周书灿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甲骨四堂”称谓的缘起,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未有定论。1942年4月1日,董作宾在《跋鼎堂赠绝句》中说:“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可备一说。事实上,早在此之前的1939年,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一书的《序》中亦说到:“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显然,最迟至20世纪40年代,“甲骨四堂”的称谓在学术界基本已家喻户晓。被列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曾分别于不同时期,对于其他三堂的学术研究屡屡作出过诸多评价,大家点评大家,较之一般学者的评论,显然,更为客观中肯。然而,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甲骨三堂的学术评价,也屡有主观臆断和不实之论。因此,对于不同时期郭沫若对甲骨三堂的诸多学术评价,应该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原则指导下,予以更加理性的思考和重新审视。
一、对甲骨三堂学术贡献和地位的充分肯定
综观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郭沫若的一系列论著,不难发现,其对甲骨三堂的学术评价总体上以肯定为主。郭氏对甲骨三堂学术贡献和地位的肯定,严格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少见解独到深刻,客观公允。
诸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氏充分肯定罗氏“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盛赞罗氏“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郭氏曾积极评价说:“甲骨自出土后,其蒐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郭氏屡屡指出:“罗氏蒐藏既富,而于文字的推广流布亦不遗余力。其前后拓印行世之书……特别是《前编》和《后编》,是研究甲骨文字必要的典籍”;罗氏《殷虚书契考释》“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总之,郭氏对罗氏的甲骨学贡献和成就从总体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郭氏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盛赞“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
他的蒐藏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蒐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蒐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此外,郭氏用“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评价罗氏金石器物、古籍佚书搜罗颁布的贡献和价值。
郭氏对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和地位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郭氏充分肯定王氏在史学上的划时代成就:
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些有惊人的成就。
郭氏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屡屡指出:“王氏于卜辞研究实当首屈一指,孙、罗均非其比也,其所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乃自有卜辞研究以来之最大贡献。其中虽有少许当更正之处,……然其大体固皎然无恙也”。在以后的著作中,郭氏又进一步论及:
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
在卜辞的研究上,王国维是有很大的贡献的,经过他的细心的阐发,不仅许多文字得到考释,并使《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殷代王室的世系也几乎全部得到了证明。
郭氏还赞誉王氏《殷周制度论》之作“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学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以为圭臬”;“其遗书全集中所收之《观堂别集》及《殷礼徵文》、《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等均为研究卜辞者所必读之书”。此外,郭氏还盛赞王氏《宋元戏曲史》“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郭氏对王氏多领域的学术贡献均予以关注并高度首肯。
在分别对罗振玉、王国维学术贡献和地位作出充分肯定的同时,郭氏从现代学术史的视角对罗王之学的学术贡献和地位,尤其是在甲骨学方面的贡献和地位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大抵甲骨文字之学以罗、王二氏为二大宗师”,“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郭氏对罗王之学的贡献和地位的评价,毫无刻意的拔高或人为的贬低的主观成分,总体上做到了中肯公正,客观公允。
郭氏对董作宾在甲骨学尤其是卜辞断代方面的成就较早予以关注。早在殷墟科学发掘之前,一度有少数国内外学者曾怀疑甲骨卜辞的真伪问题。1930年,郭氏较早论及到殷墟发掘的意义及董氏《新获卜辞写本》的价值:
顷蒙燕大教授容君希白以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见假,始知董君于一九二八年冬曾从事殷虚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八十一片。辞虽无甚精萃,然物由发掘而得,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
郭氏在《卜辞通纂》的序中论及:“董氏之创见,其最主要者仍当推数‘贞人’,其他均由此所追溯或派演而出”。郭氏论及董氏“贞人说”对于甲骨学的重要学术意义:
“某日卜某贞某事”之例,所在皆是。曩于卜贞之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贞人之说创通,于卜辞断代遂多一线索。
此后,郭氏继续论及:
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郭氏较早论及董氏《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书的贡献:
(董氏)《甲骨文断代研究》之作,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以求之,体例綦密。贞人本董氏所揭发,坑位一项尤非身亲发掘者不能为,文虽尚未见,知必大有可观。
此外,郭氏还赞誉董氏:

迄1933年,郭氏看到董氏《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后,再次评论到:
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编,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而使余尤私自庆幸者,在所见多相暗合。亦有余期其然而苦无实证者,已由董氏由坑位、贞人等证实之。余读此文之快味,固有在寻常欣赏以上也。
综合以上论述,郭氏评论到:
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虚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及《甲骨年表》《集刊》二·二,均有益之作也。
综上可知,郭氏较早对董氏的甲骨学贡献及其在甲骨学上的崇高地位予以充分肯定。
随着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郭沫若对甲骨三堂学术贡献的评论,尚未完全到位。如此后有的学者高度评价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兴起,实在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充分肯定王国维“通过对世系称谓的研究,确定了一些甲骨的具体年代,……这就为后来的甲骨文断代研究开了端绪”,“也正是王国维,首次将已碎裂为二的甲骨缀合复原,还其本来面目,……这就为后来的甲骨缀合工作开创了先例”。另有学者充分肯定董氏“《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使在金石文字之学影响下形成的甲骨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把甲骨学研究纳入了历史考古学范畴,从而使甲骨学由金石学的附庸,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董作宾等学者用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全面整理甲骨文,为我们复原商代的占卜和文字契刻规律奠定了基础”。综上可知,由于时代的局限,郭氏对甲骨三堂学术贡献与地位的评价,尚未达到当代学术界主流认识的高度,但大体看来,其以上对甲骨三堂学术贡献与地位的评价,并未由于个人好恶与相互之间政治立场不同而夹杂个人的情感和偏见,以上评论基本上均出自学术目的和动机,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原则。
二、郭沫若质疑批判甲骨三堂学术的价值与局限
和对甲骨三堂学术贡献和地位的充分肯定类似,郭沫若对甲骨三堂的学术质疑与批判,总体上亦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
诸如郭氏批评包括罗王在内的一流的古文字学家,“素少科学的教养”,对于古文字资料,“不能有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
罗、王二氏其杰出者,然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其笔端。在这种封建观念之下所整理出来的成品,自然是很难使我们满足的。
又如,郭氏以《遹簋》“文考父乙”、《匡卣》“文考日丁”等器铭文为据,批评罗氏以“以日为名”作为区分殷、周青铜器的标准“不一定可靠”,“象罗振玉的《殷文存》那部书,主要根据‘以日为名’而搜集的七百种以上的器皿,差不多全盘靠不住”。再如,郭氏批评王国维“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批评“王氏于社会科学未有涉历,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应该强调的是,郭氏对罗王的绝大多数批判,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于“殷末与西周并看不出有若何剧变。例如青铜器便无法完全辨别”等论断则可视为郭氏的一家之言。
此外,郭氏该阶段亦曾批评董作宾:“惟惜董君于近代考古学上之知识,无充分之准备:发掘上所最关紧要的地层之研究丝毫未曾涉及,因而他所获得的比数百片零碎的卜辞还要重要的古物,却被他视为‘副产物’而忽略了”。后来,郭氏读到1929年12月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五种重要文献,很快改变了对此前的看法:“第五项(按:指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及后记》)前已得见其单行本。因于地层之研究未叙及,故余曾颇致不满,今得读本期报告,特在读过第一第二两项之后,始知董、李二君实煞费苦心”。显然,郭沫若对董作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样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郭氏对甲骨三堂的批判,融入了不少非学术因素,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原则,影响到学术评价的客观公允。如郭氏“仅凭着一本《国学周报》的《王静安先生专号》”从极力发挥早已被证伪的罗振玉窃取《殷虚书契考释》署名权及王国维死于罗振玉逼债说,到近乎彻底否定罗振玉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扬王抑罗的旨趣格外明显。郭氏文中的“(王之死实际出于罗之逼,学术界中皆能道之。)罗更参加了伪满洲国,那倒是他的一贯之道的了”“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讳的必要了”,“罗振玉是一位极端的伪君子……他的自充遗老,其实也是一片虚伪,聊借以沽名钓誉而已”等论断,因人废文的主观倾向颇为突出。事实上,以上带有浓厚主观好恶的评论,与评价罗振玉的学术,并无直接关联。
同样,50年代以后,郭氏将对董作宾的学术评判也深深烙上政治批判的印记。诸如1950年2月17日,郭氏著《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一文。如果说文中“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的‘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的评论尚带有一些学术批评的味道,其他如“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到了家”,“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等乱贴标签、扣帽子、上纲上线的评论,则充满着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浓厚的情绪宣泄的政治色彩。又如郭氏批评董氏“不逻辑竟到了这种地步!……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之类火药味十足的评论,及1953年9月19日,郭氏在致杨树达的信中“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之类过激的文字,则犹如一篇犀利的讨伐檄文,完全不具备纯正学者的平和心态和最起码的学术道德素养。
40年代后,郭氏对罗振玉学术的全盘否定及对董作宾的无端指斥,违反了中国传统学术批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敦厚”的优良风尚,其对罗振玉、董作宾批评中所暴露出盛气凌轹、支离牵涉、影射讥笑的作风,亦受到学术界的指斥和批判。如杨树达先生在1953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写到:“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李济先生评论说:“大部分看见过这篇文章(按:指《蜥蜴的残梦》)的人们,都以为这是篇纯政治的文章,不包含任何学术的意味”,“实在没有必要……把《蜥蜴的残梦》所说的若干话过分地当学术批评看待”。杨、李二氏对郭沫若的批判,对于培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建立科学的人物评价标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郭沫若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再思考
早在1921年,郭沫若较早指出,“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素以人民为本位”。迄20世纪40年代,郭氏又屡屡提到,“人民本位”是其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样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
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出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郭氏继续言及:
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
郭氏分别谈到王安石和李岩:
我对于王安石是怀抱着一种崇敬的念头的。……他有政见,有魄力,而最难得的是他是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
(李岩)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学术界对郭沫若评价历史人物的“人民本位”标准的学术价值从总体予以高度的肯定,如有的学者指出,郭沫若对许多学术问题的研究,“既是严格的科学讨论,又具有现实的革命意义”;“郭沫若明确提出‘人民本位’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不仅在学术上有开创的价值,而且在政治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人民本位”标准中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如不少学者注意到,“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民则通常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迄1959年,郭沫若继续论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
郭氏以对曹操的评价为例: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
综上可知,迄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将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由此前的“人民本位”发展为“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学者指出,郭沫若的历史进步标准并不是放弃了原有的“人民本位”观念,而是在更大范围内、以更长远的目标涵盖了人民利益。郭氏严格按照“人民本位”和“历史进步”标准对各类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然而,随着新时期多元人物评价标准的提出和评价标准体系结构的建立,郭氏历史人物评价的“人民本位”和“历史进步”标准,也往往呈现出一系列学理疑问和逻辑疑难。学术人物显然属于郭沫若所说的历史人物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如果刻意地用“人民本位”和“历史进步”标准对学术人物进行评价,则很容易将学术人物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一系列混乱。郭氏不同时期对甲骨三堂的学术批判,即屡屡受到政治影响下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评论的公允和价值。
郭氏评价历史人物的“人民本位”和“历史进步”标准,既是一个合格的史学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一革命性极强的政治话题。郭氏这一标准的提出与完善,显然与其学术家、革命家合一的特定身份有直接的关系。在郭氏的著作中,“人民本位的中国文化的批判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工作”等话语屡见于其各种论著。郭氏称柳亚子“不仅是一位革命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革命的史学家”,盛赞闻一多“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他(指闻一多)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显而易见,郭氏所极力肯定和推崇的柳亚子、闻一多为革命而学术的治学态度,也正是其学术思想的最鲜明的特色。在这一学术思想的支配下,郭氏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他反复强调:“要端正历史观点,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从历史发展中阐发人民创造力的伟大”,“必须精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治好历史”。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郭氏才陆续撰著出被学术界公认为马克思史学里程碑式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一系列煌煌巨著。与此同时,为达到为革命而学术的目的,郭氏坦言其初期的学术研究也屡屡“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郭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要加强理论和方法上的基本素养,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教条化:“中国的古代发展和马克思的学说不尽相符”。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指出,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渗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使得学术与政治两者因此得以沟通,学术最终成为他参与社会、介入政治的一种方式,他的学术实践的成绩与失误皆在于此。郭沫若在评价甲骨三堂学术贡献与地位问题上的得失,正是郭沫若为革命而学术的思想在学术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记董氏膏方微商爱心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