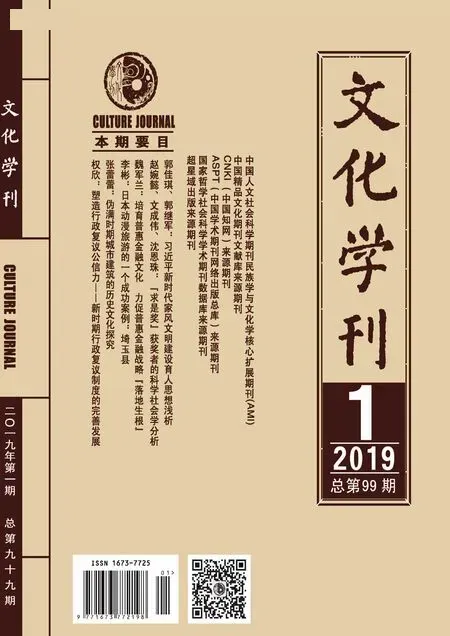论患病对麦卡勒斯小说创作的影响
寇喜兰
文学创作是一种植根于自我经验的主体性艺术。作家在创造或虚构一部作品时,自身的经历会对其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在作家的个人经历中,患病经历又是很多作家都会有的生命体验。据调查,世界上身心完全健康的知名作家并不多,统计显示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个占比是非常小的。这说明,很多知名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病患的折磨。但即便如此,也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可知疾病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无论是哪种疾病,都会使作家们的情感比普通人更加深刻、敏感和复杂,也会使他们创造的文本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1]。疾病使作家拥有比普通人更深刻的生命体验,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更独特的审美倾向。通过文学这种媒介,他们将疾病形诸笔墨,从而使自身的主观经验客体化,进而上升为一种有普遍性的认识介体。
一、患病经历与素材挑选
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上,麦卡勒斯是一位书写疾病和残疾的作家。她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散发着疾病的气息,而她自己又是一位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她在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些现象几乎都能在作家本人身上找到原型。如,《没有指针的钟》中法官所患的中风[2]麦卡勒斯也患过。另外,她在作品中屡次塑造一些身高离奇的畸形女孩,这也是她自身真实情况的写照,像《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3]、《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奇[4]和《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艾米莉亚[5],皆是如此。麦卡勒斯有着身高过高和喜欢男性装扮的问题,在少女时代,她就比同龄女孩要高出许多,13岁身高便在173厘米。不仅如此,她还总打扮得像个男孩子,经常穿着脏兮兮的网球鞋或女童子军的牛津布鞋,而不是像其他女孩穿着漂亮的高跟鞋和长筒袜。为此,她经常因为男孩子的装扮被周围的人取笑和排斥。麦卡勒斯的尴尬处境,便借助小说中米克和弗兰奇来展现。即使是成年后,人们经常看到麦卡勒斯的装扮是她穿着粗棉布裤子或男式长裤,顶着一头短发,手拿香烟,这又类似于她小说中所描述的成年女人艾米利亚。
由此可见,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却也是立足现实生活加以虚构创造,并不是什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人们常常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没有生活原型或者现象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在麦卡勒斯短暂的一生中,疾病就占据了她一半的生命。患病经历对她的影响可谓是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她的创作,更是影响颇深。从她童年时期开始,身体不适和疼痛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恶性贫血、风湿热、中风直到最后的瘫痪,疾病困扰着她,也早早结束了她的生命。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在《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中写道:“恶性贫血,伴随着一次次发作的胸膜炎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是她早期的痛苦;15岁时,她得了风湿热,但被误诊和误治。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在她30岁前,左边的身体就瘫痪了,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在以后的10年里,卡森的身体每况愈下,到40岁时,如果换了一般的人,早就死了。”[6]也正如卡尔所言,麦卡勒斯确实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在这漫长的患病生涯里,不仅是她的身体备受摧残,就是她的心灵,也在时时刻刻饱受疾病的煎熬。
总之,这种漫长的患病经历使麦卡勒斯在生命面前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刻的体验,更加敏锐的感觉,也是她小说创作取之不竭的财富。她曾说她作品中的每个故事都是她经历过或将来有可能发生的[7]。小说中人物所患的疾病,她基本上也都患过。正是如此,她才能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残病人物形象,写出他们的痛苦和不幸。这诸多的残病呈现正是作家将自身的病痛体验融入文学创作的缘故,是她内心饱受痛苦的充分展现。在此过程中,她不仅解救了自己,实现了自我价值,也为美国文学增添了新的风景。
二、患者身份与人物选择的偏好
麦卡勒斯的患者身份使其在小说创作中更加愿意关注残病人群,书写残病人群。她笔下塑造的残病人物很多,如哑巴辛格、驼背李蒙、中风的法官、患白血病的马隆和患心脏病的艾利森[8],等等。笔者认为,麦卡勒斯对残病人物的偏爱、倾注的同情,与她自身的患者身份是密切关联的。
患者身份使她更能理解也更想表现残疾人独有的情感。在麦卡勒斯五十年的人生岁月中,瘫痪在床二十多年,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即使之前没有瘫痪在床,却也在饱受病痛的折磨。疾病限制了麦卡勒斯的行动空间,将她从自然、同伴和广阔的社会现实中隔离出来,影响了她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正常交流,造就了她内心的孤独。但孤独是普遍的,是相通的,是人类共存的一种内心体验,并不仅仅是她一人的感觉。正如吴俊在分析瘫痪对史铁生心理影响时说:“残疾者所感受到的最深刻的痛苦,其实是一种被弃感——一种被所属群体和文化无情抛弃的精神体验。”这种被弃感被吴俊描述为孤独感,是残疾人内心常有的一种情感体验。麦卡勒斯要写出自身以及更多人的孤独困境,选择她自身所熟知的残病人群再恰当不过了。将残疾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孤独拿来表现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孤独,指明孤独的无处不在,麦卡勒斯更有发言权。因为,这是她熟悉的一个群体,她理解他们的孤独和困惑,拥有过与他们类似的情感经历。
所以,当麦卡勒斯将自身身体体验到的苦痛与折磨渗透到她的写作中时,便形成了我们眼中看到的一切:在一座又一座沉闷而乏味的南方小镇中,一群畸形而怪异的人接连不断地在上演着“喧哗与骚动”的人生。他们没有健康人的体魄和心灵,始终徘徊在孤独的边缘,情之难托,爱而不得。另外,麦卡勒斯写残病人物的孤独也隐含着作者对人类精神困境的关照和审视。在小说里,每一个场面无不是人类困顿境遇的缩影,爱无能、梦想和信仰的破灭、无所归依、寻找自我,等等,不仅是作者个人饱受孤独的折磨,更多的人都和她一样,身陷孤独的囹圄。正是麦卡勒斯对自我孤独的深刻体验,使其能对人类共同的命运产生共鸣,作出探索。也难怪克劳斯·曼评价她是“对人类的灵魂最终的无法安慰和不可救药具有如此惊异的洞见的孤独的猎手”。
三、结语
文学作品虽然不是作家经历的再现,文学人物也并非作家本身,但文学创作一定是作家基于个人经历进行的虚构。所以,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总是不免将现实中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情感带入文学中。麦卡勒斯之所以在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残病人物形象,这和她本身身患残疾、饱受病痛折磨是分不开的。是她对疾病的深刻体验,造就了她笔下许许多多的残病人物形象。她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他们身上,她写他们,就像在写她自己一样。这也正是作家个人经历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表现。总的来说,在疾病给作家带来的影响中,既有过早地结束作家文学生涯的消极影响,也有促进作家对生命的洞察、激发作家创作力的积极影响[9]。“一个病人,一个波特莱尔式的人,尤其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在三十年中由于癫痫症或别的什么病,因此能创作出许多健康作家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作品。”普鲁斯特的这段话正是疾病给作家以积极影响的最好诠释。虽然不能说是疾病才使麦卡勒斯成为20世纪美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但麦卡勒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疾病一定发挥了其他经历替代不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