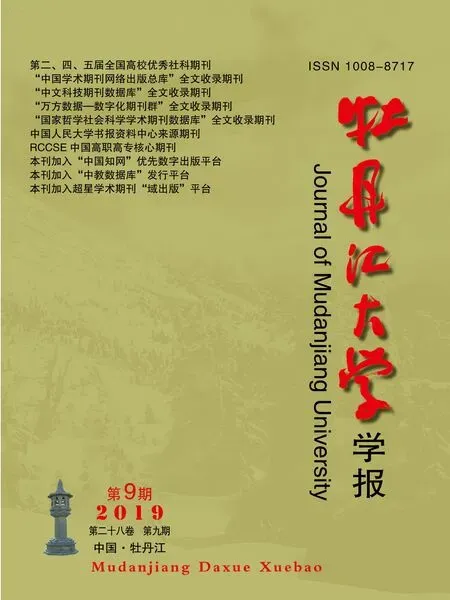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京华烟云》的女性观及其成因
杨 静 茹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之初就有“现代版《红楼梦》”之称。这部小说中塑造了90多个人物,其中将近50个都是女性角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女性世界。林语堂笔下的女性有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古典女性,也有现代精神影响下的叛逆女性,还有兼具中国传统美德和西方现代精神的“完美”女性……本文拟以这些女性形象为中心,对林语堂的女性观及其成因略作探讨。
一、对传统女性的推崇与赞赏
出于对女性的崇拜和爱慕,林语堂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成为“美”的化身。她们不仅拥有姣好的容颜,而且贤良淑德,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具有优雅的气质和高贵的人格。从《京华烟云》中曼娘、莫愁的身上,可以明显感受到儒家传统女性的温柔娴静、端庄有礼。纵观林语堂的一生,近30年都客居海外,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儒家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始终情系祖国文化。这反映到他的女性观中,就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女性的极力推崇与颂扬。
(一)孙曼娘——中国旧式妇女的典范
孙曼娘,一个自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熏染,严格遵守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她性情文静、端庄善良,自幼就被许配给平亚,在情窦初开的日子里,二人始终以礼相待。在明知平亚病重,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她依旧坚持“冲喜”嫁入曾家,并表示:“活着,我是曾家的人;死了,我是曾家的鬼。”[1]84平亚病逝后,她始终深居简出,以处女之身终生守寡,最终在遭受日寇侮辱后自缢身亡,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在曼娘身上,能看到中国旧式女子所应有的完整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四个方面的传统教养,即我们常说的“四德”。公公曾文璞不满她外出吃饭、看电影,认为寡妇的活动范围就应该在家里。对于这样的严苛要求,曼娘毫无怨言,反而觉得有道理,从此外出更加小心翼翼。曼娘的妇德还表现在她谦逊有礼、宽宏大量。在面对弟媳牛素云肆无忌惮的挑衅和欺辱时,为了家庭和睦,她忍气吞声,从不埋怨。曼娘尤为擅长女工,在她看来,读私塾远没有做女红重要。为了使曼娘这一人物成为中国传统妇女的典范,作者让她一味妥协和顺服,好像完全不知道反抗为何物,于是就成了旧道德的坚定守护者和实践者。
从一定意义上讲,作者虽然借助曼娘这一形象暴露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抒发了对旧式封建礼教的控诉和厌恶,但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妇女美德的由衷赞美。在作者的精心刻画下,曼娘就如同古书上掉下来的一幅美人图,绝世而独立,高贵而典雅。
(二)姚莫愁——聪慧贤能、温润和善的“封建淑女”
姚莫愁是作者塑造的又一中国儒家女性的代表,生性稳重沉静,不爱慕虚荣。虽然贵为千金小姐,但她身上丝毫不见娇奢气,反而勤俭顾家。她认为女人不应该看太多的书,说女人不要太聪明,赞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莫愁倾慕才貌双全的孔立夫,却含而不露,选择通过“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形式嫁给立夫。由于自小受到母亲的严格管教,也接受过传统教育,她极为重视家庭,在莫愁心中,家庭是她的全部,也是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的场所。她最大的心愿便是家人幸福安康,家庭圆满和睦。她从不过问政治,不追求权贵,并且始终限制立夫投入政治活动,压抑着他的激进思想,努力创造一个宁静平和的家庭环境。正如小说中立夫所感:“莫愁一心所想,一身所行的,就是为了他的舒适,为了他的幸福。”[1]339莫愁拥有儒家所期望的女性的一切美德,沉稳、明理、端庄,同时还具备现实的精神、通达的智慧。她以富贵之身嫁入孔家,虽然一大家人的生计几乎都靠自己的嫁妆维持,但莫愁依然能够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充分顾全丈夫的面子和自尊。
与木兰相比,“莫愁少一点浪漫情趣,多一点现实精神,少一点才气和灵性,多一点母性和妻性,是一个具有‘新知识’和‘旧道德’的‘贤妻良母’的形象。”[2]
总之,无论是曼娘还是莫愁,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符合中国古代关于女子的传统审美观——温柔大方的贤妻良母形象。从这类形象可以看出作者鲜明的女性崇拜思想,喜爱女性,尊重女性,以及对中国传统女性所具有的优雅气质和高贵人格的赞美。
二、对叛逆女性的理解和同情
“五四”时代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人们开始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爱情自由。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也由此被唤醒,她们勇敢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命运,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对封建男权社会发起的严峻的挑战。在林语堂的笔下,除了曼娘、莫愁这样的传统女性之外,还有银屏、素云等大胆抗争的现代女性,她们不愿意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品,其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银屏——封建秩序的挑战者
银屏的首次出场是在第一章。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城,姚府正举家南下避难,她因浓妆艳抹而被姚夫人训斥。首先,作者在小说开头这样介绍一个丫鬟,她在穿着打扮上敢于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服从她的主人,这就暗示读者,这个小丫鬟不同于一般的底层社会女性;其次,这是在逃难的路上,理应穿着简单,然而银屏却打扮得花枝招展,暗示出她可能会是那种给大家带来危险和破坏的人;第三,银屏选择在如此危险的情境下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这表明更为灾难性的事件可能会发生,而她在危险时刻会是一个麻烦。可见,她的性格完全违背了传统封建社会关于女性的道德标准。
因为不同于传统底层女性的软弱和可怜,当姚太太威胁让她离开姚少爷时,银屏没有痛哭求情,而是以实际行动去拯救她的爱情。她首先离家出走,掌握主动权;等体仁出国回来后,迅速与他秘密同居,这能看出银屏在面对危机时冷静机智的处理能力。接着她采取了第三次行动——以情妇的身份为姚少爷生下儿子,以此来确保她的地位。为了报复姚太太,她想方设法不让体仁回家,以此来获得快感,可见她个性冷酷且报复心极强。然而她最终还是成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儿子被抱走后,银屏在绝望中选择自缢身亡。
作为一名仆人,银屏是叛逆的。她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体仁身上,企盼能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爱情与幸福。然而她自始至终都在被上层阶级所拒绝,只有在死后才被姚家人勉强接纳和认可,她的人生悲剧也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控诉。在二十世纪初的北京,还有无数的女性发起了对封建礼教的挑战,然而最后她们都没有逃出社会的牢笼,成了那个不公平社会的牺牲品。也许林语堂是想向我们展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女性在面对强大的封建等级压迫时,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获得上层阶级的承认,表达出他对这些追求自我解放的叛逆女性的深刻同情。
(二)牛素云——自我意识强烈的叛逆女性
在小说中,牛素云是作为反面形象存在的。她的父亲是个恶名远扬的贪官,母亲心机深沉、贪恋权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牛素云,骄纵、刻薄、虚荣。她与木兰第一次见面就暗自比较,认为自己裹脚以及认识高官家的女儿都是胜于木兰的地方,这也足见其爱慕虚荣。她既瞧不起出身寒微的曼娘,又嫉妒高贵大方的木兰。牛家失势后,她觉得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自身不孕又使得她在婆家抬不起头,整日郁郁寡欢。素云不同于逆来顺受的传统女人,她作风张扬,行为大胆,当她觉得自己在曾家遭遇不平等待遇之后,就果断地走出封建家庭,寻找自己的平等。
另一方面,素云自我意识强烈,富有冒险精神。离开曾家后,她做起投机生意,感受到了金钱的魅力。她逐渐认识到,女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生活、享受生活的,并且有权利获得财产上的独立,到后来她甚至开始售制毒品,成了有名的“白面王后”。最终,素云在姚、曾两家人的教育和感召下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体会到了国仇和家恨,于是就开始主动为革命者传送消息,秘密开展革命工作,被日本人抓住后,最终为国献身。素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找到了自我,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素云并不讨人喜爱,但这一形象的塑造无疑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中国女性同命运的抗争,以及对自我的重建,表达出了作者对叛逆女性身上所表现出反抗精神的理解和欣赏。素云的人生经历就是近代中国女性追求自我身份的例证,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挑战了一个好女人的封建标准。
银屏和素云都象征着当时的中国女性对封建父权制的挑战。或许她们力量薄弱,不能撼动所谓的封建传统,但她们的反抗绝不是毫无意义的。银屏的一生都在努力地朝上层阶级靠拢,追求所谓的较高的身份和地位,这种精神在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中国女性中是很有价值的。牛素云毅然离开封建家庭追求她个人的自由和价值,而不是被男性主宰的社会所禁锢。她重新评价和重建自我的勇气,对于改善封建父权制下的女性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林语堂塑造这两个叛逆的角色,即表现出他对反传统的现代女性的欣赏,也寄予了他对深受儒家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的深切同情。
三、对理想女性的喜爱与追求
一直以来,林语堂始终坚持充分肯定女性的生命存在和人生价值,他呼吁:“我愿意看见新时代的女子,——她要无愧的标立、表现、发挥女性的不同,建造新女性于别个的女性之上。”[3]150可见,他的女性观是进步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作者将木兰作为贯穿小说的中心人物,既赋予她超凡脱俗的气质和才华,又使她扮演着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把经过其文化道德筛选的全部女性美揉合于他的女主人公木兰一身,使木兰达到形体美、心灵美、人性美的高度统一,继而升华到理想美的境界。[4]
木兰出生在一个富有之家,她的父亲姚思安是一个道家信徒,主张无为而治,不刻意约束儿女。受父亲的影响,木兰逐渐形成了豪迈豁达、诙谐幽默的个性,她向往美好的事物,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一颗童心,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木兰曾经深爱立夫,但她也坦然地接受了与荪亚成婚的命运,也体现出她性格中“顺乎自然”的道家思想。在嫁入曾家之后,她天真无邪、洒脱自然的本性丝毫没有改变。她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吹口哨、看电影、进馆子、放风筝……这些在别人看来“不正经”的行为,木兰却乐在其中,她也因此成了公婆眼中的“疯儿媳妇”,丈夫口中的“妙想夫人”。
除了受到父亲的影响,木兰在母亲姚太太那儿也接受了许多“世俗智慧”。在母亲严厉的中式传统教育下,木兰身上表现出了中国女性的传统妇德:为人善良温和、通情达理、贤良谦恭,做饭、剪裁、缝纫等样样精通。由于深谙治家之道,木兰婚后颇得家人及仆人的尊重,成为众人眼中的“管家少奶奶”,丈夫心中完美的妻子。她轻松地接受了所安排的一切,并尽到了作为一个完美的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恰如有学者所说:“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综合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的才智,薛宝钗的美貌和史湘云的风姿。”[5]52她是林语堂心目中“理想的完美女子”的写照,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矛盾重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发生碰撞。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木兰除了从父母那里接受传统儒道文化的浸染,还接受了现代教育,她从十几岁时就开始思考“男人与女人的分别这件事”,也经常和父亲谈论“新时代的女子”的话题,是一个“新式的女孩子”。“木兰有几种女人所没有的本领:第一,她会吹口哨儿;第二,她会唱京戏;第三,她收集古董,而且能鉴赏。”[1]60可见,木兰称得上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下,集传统美德与现代性于一身的奇女子。
林语堂学贯中西,受到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木兰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她是新时代背景下具有现代精神的传统完美女性,是作者最为喜爱的一个角色。透过木兰这个形象,我们能看出林语堂心目中的那种理想女性的品质,她们不仅要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还需得有现代西方女性的解放思想、自强自立,这也是作者女性观的独特之处。
四、林语堂女性观的成因
由于长期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林语堂不断接受着多元文化的冲击,他曾称自己是“两脚踏中西文化”,因此,在思想和实践上都充满了矛盾——既传统又现代,既理想又现实,亦中亦西,这些矛盾存在于林语堂身上,构成了他独特的文化特征。同时,他在对待东西方文化上,并未简单赞扬或否定,而是能够较为全面地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不难理解他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体认。从对《京华烟云》的几类女性形象分析可以看出,林语堂的女性观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西方女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痕迹,他从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地位入手,多角度地深入探究了女性问题,其独特的女性观凝聚了关于人性的思索,是中西交融、相互贯通的,要分析其成因,还得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以及特殊的时代背景入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林语堂在西方生活多年,但骨子里流淌的仍是传统文化的血脉,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他曾对孩子们说:“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可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6]80众所周知,《京华烟云》的创作受到了《红楼梦》的直接影响。林语堂曾浸淫《红楼梦》多年,是一位典型的“红迷”,“可以说,《红楼梦》是林语堂女性崇拜最为直接的来源和启示之一。”[7]1938年,林语堂开始了《京华烟云》的创作,他在许多方面都刻意模仿《红楼梦》,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即是以之为模本,但这种模仿不是一味地抄袭,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林语堂一方面积极吸取了《红楼梦》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另一方面也给《京华烟云》加入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元素,使之适应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这无疑是一种创新。林语堂曾直言不讳地说:“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微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于宝玉。”[8]342总之,《红楼梦》中所刻画的女性角色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崇拜意识不仅影响了林语堂的人生观、文学观和女性观,也促使其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二)西方文明的浸润
林语堂的一生都对女性问题研究情有独钟,他始终都在关注女性,并对她们给予极大的关心和爱护,这种女性观与其在欧美国家接受到的先进思想有很大的关系。1929年,林语堂翻译了倡导妇女解放的罗素夫人的论著《女子与知识》,书中提高女性地位、肯定女性权利的观点对他的女性观产生重要影响,之后还翻译了丹麦作家布兰地司的《易卜生评传》、萧伯纳的《茶花女》,其中所体现出的女性解放意识也使他深有所感:“现在的经济制度,你们都明白,是两性极不平等的。女教员薪水总比男教员少,英美诸国也是如此,在英国则甚至法律不许太太们教书,无论中外,女人可进去的职业(如按摩、打字、女招待等)总比男人可进去的少,而在女人可进去的职业中,男子还会同你们竞争,而在酬劳机会天才上都占便宜。”[9]1081936年林语堂远赴美国之时,世界女权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美国社会呼吁男女平等、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此后三十年,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令他耳濡目染,促使他关注女性的自主与独立,关注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些先进思想与文化推动了林语堂思想的进步,而他又将这种思想注入到了笔下的女性形象之中,使其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敢于大胆走出家庭,追求自我幸福。
(三)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
《京华烟云》写于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外来文化正在发生剧烈碰撞,呼吁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人不断增多。人们高举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帜,发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在当时,很多作家围绕“何谓女人”的话题做出了探讨,并且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力图向读者呈现中国女性的独特存在。鲁迅以其深沉的笔触写出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被奴役的天性,她们可怜而又可恨;茅盾刻画了二十世纪初热烈狂放的时代新女性;张爱玲则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大多数女人所具有的世俗本性。而林语堂女性书写的角度较为新颖,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任何一个女性都是迷人而富有魅力的,她们有着丰富细致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具有古典色彩,温柔大方,端庄贤淑;另一方面,女性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具有时代气息,热情奔放,追求自由。这是林语堂女性观的真实写照。此外,对于像银屏、牛素云这样饱受争议的叛逆女性,作者没有一味否定,而是看到了她们身上人性的复杂,将其塑造得更为饱满立体、真实生动。总之,林语堂小说中的女性或是拥有传统的德行修养,或是具有时代智慧、聪颖豁达,亦或极具反叛精神、敢于挑战权威,这是那个时代带给林语堂的对女性的特有认识。
总之,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凝聚了他自身的生命体验,浸润了《红楼梦》的熏染,熔铸了中西方的精华文化,既矛盾又和谐。在他心目中,“真正理想的女性恰是那些有着独立思想、现代精神,并能与传统道德文化和谐共处的女性,她们没有完全迷失在男权本位的社会中,而是努力在新知识与旧道德之间寻找平衡,最终实现幸福的人生。”[10]她们的形象带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不仅作为艺术形象存在,更是承担着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作用。这既是《京华烟云》的价值追求,更凸显了作者独特的女性观及其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