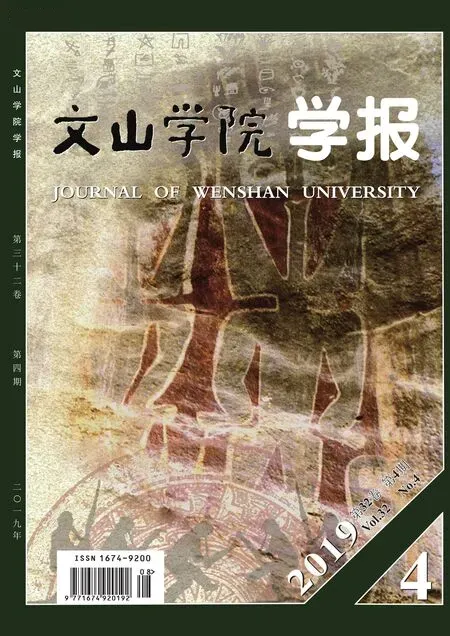《百年孤独》中的异域形象书写探究
靳莹晖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宗教抽象:马孔多小镇的二元建构
在《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小镇的命运轨迹是神话和寓言所凝结成的拉丁美洲历史的缩影,它如同一个神秘离奇又落后愚昧的古老乌托邦,依靠个人意志和自由被建立起来,并没有文明社会意义上的管理与规范,居民生活的自然化状态让这个小镇一度连死亡都从未降临过。在马孔多小镇的中心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上帝存在。他们的“上帝”并非是基督教意义中的上帝,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神,如太阳、月亮、天地等等,文本中游荡的灵魂、自己会动的锅炉、嘎吱作响的遗骸无不传达了万物有灵的宗教情绪,这种印第安人最初级的原始宗教思维是拉丁美洲三大古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卡文明的精神内核,自始至终贯穿在布恩迪亚家族的行为理念之中。吉普赛人的到来和乌苏拉发现与外界的通途并带来大批移民这两个叙事情节开始打破了马孔多朴素的宗教观,让这个世外桃源彻底暴露在外部“文明”世界的目光之下,外来者们在布恩迪亚家族每一代人的身旁穿梭着。保守党一派的镇长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带来了政治独裁;赫伯特先生和杰克·布朗先生利用美国香蕉公司来掠夺财富、压榨工人;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和菲兰达强加给镇民们中世纪天主教的种种精神桎梏……虽然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但这些外来者形象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无一例外都是欧洲天主教殖民统治的傀儡。因而以布恩迪亚家族为代表的小镇居民与“外来者们”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分别被抽象化为原始自然宗教信仰与强势的天主教信仰的话语较量。
这些带有宗教殖民性质的小镇外来者们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异域形象范畴,亦称之为“他者”形象,这个“他者”形象并非后殖民主义视角中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话语色彩的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the other”,而是比较文学形象学视野中“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1]。拉丁美洲的普通民众在文本中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他者”身份,转而成为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自我”,欧洲殖民者反而成为了“他者”形象,两者之间实现了注视者与被注视者、消费者与被消费者之间的身份转换。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让-马克·莫哈认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他者’形象都具有三重意义,它同时是异国的形象、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以及作家出于特殊感受创造的形象”[2],即现实性、文化性和想象性三者的结合,《百年孤独》中的“他者”形象亦不例外。作品在世界上享有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品的声誉,就足以证明作者对文本异域形象现实性与想象性的成功塑造,它们既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又“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成为了真实社会语境中的想象集合体。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他者形象的文化性,《百年孤独》中异域形象的本质是马尔克斯对本民族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改造。一方面,16世纪以来西班牙殖民者迫使大量土著印第安人抛弃原始信仰而改奉天主教,以便加强对殖民地经济和精神上的控制,证明文本中具有宗教殖民性的异域形象是出于对真实历史事件感知的痕迹而被创造出来的,并非是“根据缺席”(萨特语)。另一方面,殖民地人民本身在舆论、精神生活甚至是潜意识层面对这些宗教殖民形象狂热、憎恶、亲善等复杂态度,都被马尔克斯在作品中精准地提炼出来,既自觉地复制了部分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描述,又有自身个性化和情绪化的表现,作者的创作方式实现了对社会集体想象物迷恋与批判意识之间的某种平衡,从而将温情脉脉的宗教殖民性的丑陋面具彻底撕开,给予公众舆论反向的启迪作用。马尔克斯用强烈的自觉意识建构了布恩迪亚家族与外来者们二元对立与融合的结构模式,形成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完成了在马孔多小镇这个虚构地域范畴内对两种宗教信仰抽象化的二元建构。
二、他者形象:宗教殖民主义话语的代言人
无论小镇村民们如何激烈地反抗,神父、镇长、资本家等马孔多小镇的外来者们总是理所当然地使用暴力血腥或迂回曲折的方式步步为营,潜移默化地加深了资本主义文明对这片原始土地的控制,这本就是他们眼中“落后”文明该有的宿命——服从或消失。马尔克斯对他者形象这种魔幻而客观的描述反映了某种话语与权利的相互关系。福柯提出,群体的话语实践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权力实践的方式,话语的实现同时也是权力的实现,因为权利与欲望始终围绕着言语的合法性展开斗争。从这个角度看,文本中的“自我”与“他者”的较量顺利地成为了两种话语在某一情境下对权利的争夺。尽管马孔多小镇在文本中拥有了“自我”的身份,但它的宗教话语仍处于弱势的地位,只能以自我目光注视着“他者”的宗教殖民形象的话语霸权在文本中由蔓延生长到肆意妄为,进而更深刻地揭示出异域形象在整个“马孔多”社会权利体系中的强势地位。马尔克斯通过弱化写作者本身对文本主宰权的客观叙述方式来趋向于对“他者”的否定和对“自我”的反思。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两类典型的宗教殖民性质的“他者”形象对“自我”精神与生活上的影响。
(一)“宗教信仰的引导者”——神父形象
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是从镇外的沼泽地被请来主持婚礼的,这样一个本该拥有神圣职业的“他者”形象却被描述为“一个刻板的老头,毫无欢悦的职业使他僵化了,瘦得皮包骨头,肚子老是咕咕作响……他的神态与其说是仁慈,毋宁说是无知”[3]72,他对马孔多的人们“在灵魂方面的事直接跟上帝商量”的行为大吃一惊,于是决定留下来“播撒上帝的种子”。在到处游说镇民们皈依天主教无果的情况下,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开始筹钱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于是四处化缘、甚至依靠身体离地的神力表演来赢得大家在观念和物质上的支持,镇民们此时对神父的态度由一开始的全然不信已经转换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本该严肃崇高的弥撒仪式被替换成了赚人眼球的杂技表演,这里明显带有作者对殖民者传教方式的批判性调侃。此时因为“疯癫”而被绑在树上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保持着理性主义的精神揭穿了神父的小把戏,“这非常简单,这个人处于物质的第四态”,并要求神父用铜版照片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连神父自己都觉得如果再跟布恩迪亚交流下去,自己的信仰就要岌岌可危了,“于是便不再来看他了”。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坚定守护者,但这并不代表他愚昧固执,恰恰相反,人类原初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他一生都在追寻真理与科学。此事是神父传教过程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从侧面说明了“他者”眼中的“野蛮人”反而使用现代科学取得了与宗教信仰之间博弈的一次胜利,充满了讽刺意味。但尽管如此,大家出于灵魂中那种原始宗教的善良、顺从和同情等因素,依旧慢慢接受了神父不厌其烦的说教,开始给孩子洗礼、给圣节定名、给垂死者做临终善事,教堂的成功建造标志着殖民话语的权利开始扎根,小镇最终走上了基督化与自身信仰融合的道路,镇民们在对立和不解中痛苦地顺从。
如果说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还是一个虔诚而认真的传教者,那么后继者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简直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堕落生活的传播者。他肩负着培养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成为一名神父的责任,乌苏拉对此充满了希望并坚信上帝这个强大的守护人会庇佑布恩迪亚家族的兴旺,然而神父的全套的天主教神学教育并没有使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得到神的启发,反而在主持第一次圣餐仪式之后诱导他走上了一条堕落的道路。神学教义讲解与斗鸡“鬼把戏”相结合的荒唐办法充斥在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智慧”教义中,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很快就在斗鸡圈中崭露头角,在现世生活上逐渐显现出浪荡的迹象并与成为神父的原定人生轨迹渐行渐远,由此布恩迪亚家族的后代颓势尽显,宗教殖民所产生的精神毒害在这个略显滑稽又可悲的叙事桥段上已经显示出了深入骨髓的腐蚀性力量。之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十七个儿子齐聚马孔多小镇之时,他们出于好玩的心态让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自己的额上用灰画上了十字,却无论如何擦洗不掉,间接导致了他们被轻易认出而在一夜之间被暗杀的人间惨剧,圣体仪式间接成为了布恩迪亚家族后代被屠戮的帮凶,以至于整个布恩迪亚家族对圣灰节星期三的宗教仪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与恐惧,而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这一“他者”形象后期则变得疯疯癫癫,被作者戏谑地描述为“老年性痴呆症的初期症状”,再也没有人愿意相信圣体仪式,这些叙事情节无不象征性地展现了宗教殖民文化所带来的恶果将马孔多小镇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两个异域的神父形象代表了殖民时期千千万万被派到美洲进行宗教殖民的天主教徒,他们带来的殖民文化如同瘟疫一样不可遏止地在美洲各地蔓延,扰乱了其本身的自然化进程,加剧了殖民地人民精神与生活上的双重枷锁。
(二)“生活方式的规范者”——主妇形象
雷梅苔丝是政府外派到马孔多小镇的第一位镇长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七女儿,在她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结婚之后,迅速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姑娘成长为熟谙世事又落落大方的家庭主妇形象,在“他者”形象系列中,雷梅苔丝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上帝天使,她既拥有美丽的外貌,“肤如百合,眼睛碧绿”[3]50,又拥有善良理智的天性,尽力协调家庭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完全担起了一个优秀家庭主妇的责任。父亲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因此也获得了布恩迪亚家族的信任,渐渐地将保守党势力扩展到了小镇的边边角角,顺利地将“镇上大部分房子在全国独立日那天刷成了蓝色”,父女两人的“文明传播”行动在社会和家族中同时进行,雷梅苔丝努力用基督教教义中所要求的道德与秩序为布恩迪亚家族建立起和睦的生活状态,她的到来仿佛给这个孤独的家族罩上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幸福光环。这温情脉脉的美好泡沫所掩盖的真实现实却是异域殖民者对布恩迪亚家族的宗教感化,雷梅苔丝不自觉地利用自身圣洁的宗教情感制造了虚假而短暂的和谐,但布恩迪亚家族本身的劣根性并没有得到任何程度的改善,因而最后导致了她和腹内双胞胎意外死亡的惨剧。宗教殖民中最具人性化的感化行为不仅失败了,且更加剧了这个家族命运的悲观色彩。雷梅苔丝形象塑造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身为殖民者的后代却并没有被作者恶意地丑化,反而成为文本中试图努力拯救布恩迪亚家族的天使,可惜宗教殖民文化注定不能拯救这个因为自身的文化困境而陷入衰败的家族。
菲兰达是一个来自同她本人性格一样整日“为死者奏鸣”的陌生城市的“他者”形象,这个形象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父权制与宗教殖民双重话语权利的转换。她拥有惊人的美貌,但少女宝贵的青春却日日消耗在修道院里毫无意义的课程上,沦为了中世纪天主教陈规陋习熏染下冷漠刻板的卫道工具。她从小就被未来会成为女王的荒唐理念所欺骗,却阴差阳错地被选作自由党与保守党争权夺利的政治棋子而嫁给了奥雷良诺第二,无奈地变成了布恩迪亚家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一直处于父权制度下的“失语”状态与身份定位的巨大落差加剧了菲兰达心灵的扭曲,她将从小被“培育”出来的天主教阴暗僵化的本质在马孔多彻底暴露了出来。看似后来终于拥有了话语权利的菲兰达在本质上依旧是天主教文化的传声筒。菲兰达在乌苏拉年迈以后迅速成为了家族的“女王”,有条不紊地实行自己的宗教控制计划,她先从家族日常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将吃饭时间、诵经过程、门窗的开关习惯通通变成了一种严格的程式,然后进一步控制亲生骨肉的人生轨迹,让女儿梅梅牺牲所有娱乐活动从小就练习“连修女们都视为博物馆里的化石乐器”的古钢琴,只为能让她这个母亲在客人的眼中看到羡慕和欣赏,从而满足自己可笑又残忍的虚荣心。儿子霍塞·阿卡迪奥也被她强迫授予了教皇的命运,远赴异域的神学院接受教育以便成为马孔多新一代上帝的代言人。菲兰达毁掉了孩子们的爱情和前程,将整个家庭变成了冰冷的统治机器,通过压制家族里其他人的自我意识来保证自身主体性得以实现,家族成员因无法走出自身的孤独困境而不能团结起来与之抗衡,她将本就岌岌可危的布恩迪亚家族推向了更加无可挽救的深渊。同为异域家庭主妇的雷梅苔丝和菲兰达,呈现出善与恶两种截然相反的宗教殖民的话语形式。
三、他者言说自我:拉丁美洲的文化困境
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曾言,“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4],也就是理论意义上的自我镜像,这是他者形象“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于是“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成为了分析隐秘的自我形象的重点。尽管布恩迪亚家族在面对外来宗教思想的侵扰也曾做过种种努力并在关键问题上坚守自己的朴素观念,如尼卡诺尔神父拒绝为自杀的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举行宗教仪式和把他葬在圣地里,但乌苏拉坚持为这个可怜人举办了隆重的葬礼;阿卡迪奥拒绝向尼卡诺尔神父忏悔,他并不承认人生来就该带有的某种负罪感等等。但软弱、退让和妥协依旧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基本态度,也是拉美人面对宗教殖民侵略的基本态度,产生这种态度的文化原因是马尔克斯乃至整个民族时至今日依旧面临的文化困境。
拉丁美洲是一个混合文化的地域,在“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尚未成长为稳定文化系统的情况下,已经发展成熟的欧洲天主教信仰以改头换面的施予者姿态强行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截断了土著文化正常的对自我身份确定性的过程。两种不稳定的文化因素保持着各自的形态在拉美这片土地上纠缠角逐,天主教的海外传播事业表面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成为了拉美绝大多数人民的主要信仰。“殖民者的语言对殖民地文化和语言进行的播撒和渗透,这使得被殖民地的土著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的身份,在一种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完成了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5]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这种信仰的一致性已经成为了表面现象,民众用本土化的方式解释天主教教义的抽象概念,它进一步异化发展成了民众的天主教,居民们竭力摆脱被殖民的痕迹并与那些奴役过他们的人群顽强抗争。但无论宗教文化形态如何改变,民众们如何仇视殖民者,拉美民族的身份认同依旧没有实现,民族意识依旧薄弱,他们的灵魂仍然漂泊无依地游荡在这片充斥着混合异质文化的土地上。
严肃而沉重的外部生成语境促使马尔克斯赋予费兰达、伊萨贝尔神父形象宗教殖民的本质,他们传递了拉丁美洲对那段痛苦历史的诉说,这属于拉美民族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因而一方面“他者”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各色“他者”形象在与“自我”的互动中强化了自我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雷梅苔丝、吉普赛人身上又带有乌托邦意味,乌托邦式的“他者”是质疑现实的,带有对权利合法性的永恒质疑和颠覆社会的功能,拉美人民灵魂无家可归的文化困境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民族的劣根性,拒绝科学、善于逃避、冷漠处事、民族意识薄弱,如果不决心改变,这是怎样发达的文明都无法拯救的缺陷,作者并没有因为本人身份而做出有失偏颇的描述,反而是从不同方面理智分析了困境的源头。可见,《百年孤独》中的异域形象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两极张力之间游走,呈现出复杂的双重属性。《百年孤独》以原始居民的身份对异域“他者”形象的塑造,代表了马尔克斯本人对拉丁美洲自我文化身份迷失的清醒认识,“他在挖掘出民族的劣根性、批判旧文化愚昧落后的同时,扬起了鲜明的反宗教殖民主义的大旗”[6],努力找寻民族身份认同感,探索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