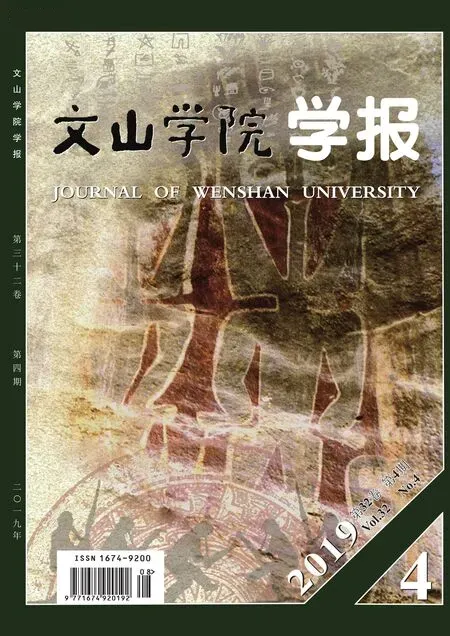试论清代湘西地区外来作物引入的得与失
杨秋萍,吴 俊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清代是中国引入外来作物的高峰时期。一般情况下,从国外引入并得到广泛种植的作物,通常都会出现多种异名。玉米即是如此,在中国又称包谷、西番谷、罂子粟、腰边豹等,据统计,其同物异名竟多达99个。[1]外来作物引入中国普遍种植,其间存在的得与失,因不同地区的生态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特别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争议最大。蔬菜水果的引进,对生态的正负作用则不是很明显。由此看来,仅注意其外来作物的正面作用或负面作用,都有失偏颇。故而本文将视角置于清代湘西地区外来作物引种后所引发的正反面作用,力图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以服务于当代的生态建设。本文拟选择主要的传入作物展开讨论,不当之处,还望学界诸贤指正。
一、玉米引种得失的讨论回顾
从玉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角度着手研究者,主要有蓝勇探讨了外来物种引进对南方丘陵山地地区造成了“结构性贫困”。[2]他力图澄清玉米的引进对丘陵山区的生态负作用,生态受损会使相关民族也陷入贫困之中。韩昭庆通过分析明清方志、奏折、游记以及民国档案等资料,发现玉米的种植与石漠化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她认为,喀斯特山区地表土层薄,坡面陡峭,一旦规模种植玉米,植被覆盖率必然下降,从而极易诱发石漠化灾变。[3]其结论是聚焦于玉米引进后的生态负效应。杨庭硕认为外来作物引种,引发了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巨变,使生态环境产生大面积的“石漠化”生态灾变。[4]其独特之处在于,不仅关注到了外来作物引种对生态的负作用,还关注到对民族文化的负作用,并将文化与生态作为一个共同体去展开负面效应的综合探讨。不难看出,该文深受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说”的影响,注意到文化与生态之间的互动制衡关系,因而其结论的深度和广度较之类似论文显得更深入中肯。秦和平指出玉米、马铃薯等外来作物的引入,在无意中改变了川西各民族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劳动力转移等文化内容,也导致了民族人口的大量迁徙,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十分巨大。[5-6]他对研究外来作物的深度和广度都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对当代生态变迁的认识也显得更加深入和精准,对其间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当代更具参考价值。
为此,笔者将以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借鉴,对湘西地区外来作物的引入展开地域性的探讨。笔者拟从文化生态视角,去探讨玉米及其他外来作物的引入对湘西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并兼顾其间的正负作用展开系统性的讨论,试图阐明外来物种的引进对文化与生态的综合性影响,进而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使之成为当代生态建设的参考和借鉴。
二、“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生态民族学以“文化生态”共同体为基本研究单元。[7]它是相关民族文化与其所处生态系统经过长时间协同演化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其中既包含了众多的生态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同时又表现为对所处生态环境的加工、改造和利用,使之与原来的自然生态系统有所不同,因为已经渗入了相关民族文化的特点。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能够达成相互耦合的稳态延续状态。[8]但是,外来作物的引入,打乱了稳定的共同体,进而引发文化生态的重构,以至于其表现出来的影响可能会正面、负面兼有之,而且往往难以预测。甚至到了科学发达的今天,要做出准确的预测,也有巨大的困难。
改土归流以前,湘西地区的苗族、土家族,其民族文化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耦合运行状态。据史料记载,湘西地区各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被称为“刀耕火种”,在民族学的规范称谓中,将此生计方式归入“游耕”类型文化。此类文化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兼及狩猎、采集。[9]具体到湘西的土家族和苗族而言,由于深受亚热带低山丘陵、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无论从事何种生产活动,都会打上相应的生态烙印。与此同时,改善后的生态系统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清康熙年间编纂的《红苗归流图》中,便绘有“刀耕火种”的附图,该附图附有如下文字说明:“树载之术,虽苗地未尝无也。镇筸田少山多,所食半食杂粮。苗人相被阳坡,荷锸执锄,披其榛莽,纵火焚之,待其灰烬,而后播种焉。盖以谷种籍暖气,易与于萌蘖也。谓之‘刀耕火种’。”[10]240-241文中提及的“镇筸”,指的是湘西凤凰县境内。文中所提此地“田少山多”,准确记载了当地的自然背景特点,进而指出,当地少数民族通过刀耕火种所获的粮食,是汉族眼中的“杂粮”。
《红苗归流图》中还载有“赶墟交易”图,该图附有如下文字记载:“(苗人)土物则有可纪者。食物则薏苡、崖蜜、洞茶、烘笋,山材则杉木、水丝木、红洲木、黄杨木,药材则黄连、血藤、五倍子、油桐、金刚藤、丹砂、雄黄,服饰则洞锦、洞被、洞巾、柳条绣、稜衣,畜产则山马。凡此皆足货鬻远方,有集场于民苗接壤处,日中为市。苗人男女负载而至,与民交易,以通有无。所重惟盐为重。”[10]242-243文中所提及的内容,是外来作物引入前湘西地区“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基本产出。
苗族通过对所处生态环境进行加工、改造和利用,使其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能够耦合运行、和谐共荣。生物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足以保证当地民族的衣食住行,所出产品除了自用以外,还有富足产品用以销售。这幅图画所载内容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中得与失的体现,因受环境的限制,无法产盐,所以必须从其他民族中购买。所以即使生物物种多样性水平极高,引发生态灾变的风险也很小。
即使是改土归流后的乾隆时期,刀耕火种仍是湘西土家族的主要生计方式。(乾隆)《永顺府志》载:“土民于二三月间,雉草伐木,纵火焚之,暴雨锄草撒种。熟时,摘穗而归”。[11]卷十·风俗文中提及的“熟时,摘穗而归”,大有深意。当代田野调查表明,之所以只收取小米、糁子的谷穗,而不要杆,是因为农田收割后要改作牧场使用。留在地里的作物杆和自然长出的杂草灌丛,都是放牧马、牛、羊、猪、鸡等牲畜的饲料,牲畜排放的粪便不借助人力也可以为耕地施肥。因而,呈现为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相互耦合的稳定延续状态。又载:“土籍重耕农,……喜渔猎,……刀耕火种,日食杂粮,以小米糁子为食,稻谷甚少。”[11]卷十·物产刀耕火种之余,渔猎和采集在湘西地区土家族居民的生活中也占据较高的比例。由此看来,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依然得到一定的保持,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生态灾变隐而不显。类似的情况直到今天的田野调查中,土家族乡民还记忆犹新。[12]
“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适应生态环境而形成的重要生计方式,不仅投入量少产出量高,且森林更新速度也非常快,对维护生态环境最为有利。刀耕火种中不使用铁锄和犁进行耕作,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利用,还可避免伤害树根,被砍的树木也能迅速萌发再生形成新的植株。[1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生计方式下,木材也是重要的产品。因此,当地民族不会轻易乱砍滥伐森林,否则不仅是经济损失,连打猎的场所也会受到影响。从生态民族学的文化生态综合分析方法出发,不难看出,即使实施刀耕火种,对生态环境也不会造成巨大破坏。
首先,刀耕火种通常是在山脊区段进行,这里森林并不茂密,主要以草本植物为主,草本植物易砍伐、易焚烧,且植被的恢复速度也较快。其次,刀耕火种主要种植小米、糁子等耐旱植物,在山脊区段能够快速生长,烧毁后的土壤呈碱性,更能支持小米、糁子等适应碱性土壤作物的生长。因而,刀耕火种是能够适应山脊疏树草地生态系统的合理耕作办法。还需要注意,森林其实也是当地民族的“农田”之一。据清代湘西的方志记载,他们会在森林中种植相关的藤蔓植物,如芋头、板脚薯、葛根等。在清朝时期,这些块根植物仍占据当地土家族、苗族食物消费量的一半以上。[14]因而,在刀耕火种生计方式下,不仅种植的作物种类繁多,而且耕地不固定,农田、森林、牧场、湿地都要轮歇交替利用。这乃是民族学家将这样的文化归属于游耕类型文化的理由所在。
三、外来作物引入与文化生态失衡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15]人类社会要维持,就必须确保其成员有充分的食物保障,而食物的来源又主要仰仗于植物。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一旦形成就会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16]一个民族对一种植物的驯化和利用,往往与该民族所处的生态系统息息相关,故而会形成稳定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从而得以稳态延续和传承。而历史上受某些特殊时段和某些政策因素的冲击,通常会使一种植物从一个生态系统传播到另一生态系统,相关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也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失衡,日积月累酿成生态灾变。
明清以前,湘西地区一直被视为“化外”之地。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湘西苗疆逐渐由“化外”变为“内地”。[17]在湘西各县志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开始编修的《泸溪县志》最早记载了玉米,称为“包谷米”。[18]可见,苗疆开发之时,将外来作物带入湘西地区已成为事实。但当时的人们,对玉米引入的生态负作用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反而将其视为珍稀作物接纳。
改土归流后,朝廷在湘西境内大力推行外来作物与汉族耕种技术,并鼓励汉人移民于此,导致人口逐渐增多。据统计,仅永顺县而言,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10 082户44 024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就增至34 187户,185 023人;乾州厅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1 090户4 116人,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增至2 594户,14 106人。[19]湘西山多田少,为了种植外来作物和接纳外来人口,不得不大量毁林开荒,改种旱地作物,使得“外来移民和本地汉人侵占了苗族人的家园——湘西山区。”[20]
至同治年间,清政府都还在颁发告示鼓励开垦土地。(同治)《保靖县志》载:“为劝民开垦荒地,以裕产业事:
照得力田勤亩,无不衣食丰足。踰闲荡检,必至饥寒,莫告示以农居在四民工商之先尔。民须当勤於田畴,以资家计。保邑虽居万山之中,尚属沃腴之地,何得本地所产不敷本地所用?皆因抛荒者多,成熟者少。本县每事乡间,目覩大峡、坪冲、坦易、坡畸,尽有可耕之地,弃置于荆棘榛莽之中,深为尔民可惜。合行出示劝谕,为此示。仰该都乡保居民人等知悉,即将该都荒地查明,某系某户祖业,某系某户自置,或系无主,或系官地,尽数查报。如系该民祖业自置者,勒限砍伐自行开种;如系无主官地,有人承认开垦,本县给与印照,即与为业;倘有穷乏无力,该乡保邻人出具。素实诚谨之人,本县借给工种,俱限于一年内开垦成熟。如有开垦百亩以上,本县重加奖赏,以示鼓励。”[21]卷十二·告示
对于告示内容,应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所属民族的文化生态观去加以认识。汉族官员将当地民族所种杂粮的“耕地”误解为“荒地”,殊不知当地民族在这些“荒地”里种植的是葛根、芋头等作物。因而,鼓励人们去开垦出来种植外来作物,“遇有溪泉之处,便开垦成田。”[22]土地开垦活动成为常态。于朝廷而言,种植外来作物利国利民。而对当地民族来说,大量种植则使本土粮食作物种类减少。大量毁林开荒,藤蔓植物被铲除,使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受到剧烈干扰,为生态灾变埋下了隐患。
玉米在湘西地区种植最为普遍,(同治)《保靖县志》载:“玉蜀黍,保邑地土瘠薄,乡民率多垦山播种,收期有早、中、晚之分。舂簸以炊,色白味甘,且耐饥,邑中甚多。”[21]卷三物产说明至同治年间,玉米已成当地主粮,并部分地置换了传统的作物。正因为玉米种植规模很大,所引起的生态负作用也十分明显。
(道光)《凤凰厅志》载:“玉蜀黍,今厅境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以代米(稻米)。由是家岁倚之,以供半年之粮。其汁(玉米的)浓厚,饲猪易肥。肩挑舟运,达于四境,酤者购以酿酒;又有研粉为粢者,以粉揉之,入汤成饼、或团子,为利甚普。故数十年来,种之者日甚多。茎似蔗,味甘可啖。”[23]卷十八物产这表明,玉米传入湘西后,很快就得以普遍种植和多层次利用。既导致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又丰富了各民族的生活,还从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在这一范畴内,玉米引种发挥的是正面作用。
湖广总督开泰曾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向朝廷的报告中这样评价玉米:“……至山田硗瘠之区,乃种杂粮,内有所谓‘包谷’者,即京中之玉米也。其性不畏旱涝,高原下隰,以及屋侧墙边,凡有隙地皆可栽植,甚为省力。成熟之时,可以拌米作饭,并为汤饼之用,兼可酿酒,价值与谷(稻谷)相等。贮之于仓,能历数岁。其梗叶可以代薪,糠粃可以饲畜。”[24]据此可知,时任官员对玉米的认知,以其价值巨大,耐储存的特性能为朝廷税收提供保障,也能作为供养马匹的官方饲料去加以普遍利用。
但当时却无法预料到,大量种植该作物给生态带来的负作用。韩昭庆认为,人们任意开辟森林和灌木丛来种殖玉米,使喀斯特山区表层土壤流失殆尽,岩石裸露在外,便产生石漠化现象。同时,玉米栽培要进行点播栽种,上下并不成行,为了排水方便,上下还要开沟,一旦下暴雨,这些水沟就会变成严重的冲刷沟。并且(汉族居民)还要对玉米进行中耕除草,次数越多表土越松,极易被雨水冲走,从而导致水土流失严重。[3]同样位于喀斯特山区的湘西地区,也难逃石漠化与水土流失的灾难,大量毁林种植玉米,无意间加剧了湘西地区生态灾害的出现。对生态而言,地表的藤蔓植物被清除,土层直接暴露在外,使得地表的蓄水能力降低,一遇暴雨就容易冲刷土壤层,从而引发水土流失。
据记载,康熙年间,“泸溪、辰溪四月淫雨弥月,大水暴发,山崩沙拥,田土冲塌成溪,秋收时有山鼠食禾,黔阳城内水深三尺。”[25]28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保靖县“六月二十五日起,天降大雨数日,洪水横流,田土皆成湖泽,禾苗被淹或被冲坏过半,秋收无望。”[25]65对玉米收成而言,由于玉米是高杆作物,稍遇狂风暴雨,就无法获得丰收。如1950年,桑植县冲毁稻田二百亩,损失稻谷二百零八石,包谷六千一百二十一石,红薯十石。[25]67可见,玉米受灾程度最大。又玉米容易受玉米螟虫害,“叶苗尽槁不实,且有螟虫损稼,当地(大庸)谓之‘地火’。”[25]27因此,也易受灾。据统计,仅民国时期(1912-1949年)湘西地区的洪灾就达97次之多,[26]这与玉米的种植应当存在直接的关系。
玉米种植所隐含的生态问题,可以通过民族文化的手段进行调适。如若将玉米与藤蔓植物、豆科植物进行复合种植,使地表不裸露在外,遇到暴雨冲刷便会减少土壤的流失。笔者所见苗族地区,就喜于将玉米与南瓜、番薯等藤蔓植物和黄豆等豆科植物套种在一起,此法虽减少了玉米的产量,但却能确保食物的多样性,兼及维护生态安全。这样的耕作体制使得土壤的覆盖率高,翻耕强度低,以至于毁林开荒引种玉米,其生态负效应也表现得比汉族耕作方式轻。
马铃薯是与玉米、番薯相继引入的作物。但马铃薯喜低温高海拔气候,湘西地区气候潮湿多雨,对于马铃薯的生长极为不利。不仅结的块根小,且容易染病,种植起来非常不划算,以至湘西地区引种马铃薯均以失败而告终。故而在清代湘西方志中,几乎找不到引种马铃薯的可凭记载。
但在四川羌族和彝族地区,马铃薯的引种却非常成功。因为四川羌区山势陡峭,河谷深邃,气温的垂直变化相当急剧。[6]这对马铃薯的种植非常有利,因为川西羌族和彝族地区与马铃薯原产地安第斯山高海拔区段的自然环境极为相似,以致于马铃薯引种到川西后,其生物性适应能够很快完成。因而马铃薯引种后,产量极高,有时亩产量可以超过4000公斤,这意味着种植马铃薯,通过换算的产量甚至比当代杂交水稻产量还高。[27]这是马铃薯引种后正面效应值得充分肯定的巨大成功。反之,湘西的马铃薯引种则显得比较失败。其原因便是同一作物的种植会因不同生态系统和不同民族文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差异。
番薯在湘西境内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同治)《保靖县志》载:“(番薯)邑多种之”。[21]卷三物产道光《凤凰厅志》载:“薯形圆长,紫皮白肉,味甚甘美,裨益脾胃。可生食、蒸食、煮食。可作粉,酿酒养人。与米谷(玉米)同来自海外。俗名番薯,因其色红又名红薯。种法或用藤插入地,或切薯片栽之,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口之家便足一年之食。叶可作菜,藤收干可饲牲畜。其性耐旱,又不畏蝗。种之易生,一岁两熟。今厅境亦种之。”[23]卷十八物产其易活、高产、耐旱、生态适应性强的特点使之能在湘西地区顺利推广。它的藤蔓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尤其是种植在山坡地带,可以很好的覆盖土壤层,减少地表受暴雨的冲刷。但该作物引种的不足是,非常容易引发黑斑病,一旦引发就不堪食用。为了防治储存期患病,就需要建立储存设施。而外来作物引入前,湘西地区各民族通常都“无盖藏”。[28]引进甘薯后,进行规模性种植,就不得不挖掘地窖储存红薯,因而在无意中引发了土家族、苗族的文化变迁。
除了粮食作物外,经济作物的引入也不容忽视。湘西地区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烟草。(同治)《保靖县志》载:“淡芭菰,俗名菸草,一名相思草。……邑多种之。”[21]卷三物产可知清代后期,烟叶在湘西地区也得到了普遍种植。又据(同治)《龙山县志》载:“蔫叶,名淡芭菰,……邑正南壩出者最佳。”[29]卷十二物产淡芭菰的种植,对当地的原生物种会构成威胁,烟叶自身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其留下的农药残留物和化肥对土壤的破坏作用巨大。但种植烟草,在短期内却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以至于当地乡民为了获取经济报偿而大片种植。
(道光)《凤凰厅志》载:“棉布,各乡村多莳棉花,男妇并织,精粗不一。”又厅志“草之属”:“木棉,厅近多种者。凡山地稍平处皆宜。盖木棉不择地之肥瘠,惟视人功之勤惰,以验丰歉。勤于薅者则收必多。”[23]卷十八物产文中所提木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木棉,而是指今熟知的“草棉”,因而才将这一条目归入“草之属”。
事实上,棉花原产于印度、巴基斯坦,宋元时期才经海路传入海南岛,并在当地得到推广利用。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30]一书中,由于没有了解它与木棉不是同一种植物,仅是从其效用都能提取纤维,就将“草棉”误称为“吉贝”,从而种下了误用名称以讹传讹的恶果。元明之交,黄道婆将此植物带到长江下游,在中国才大范围推广。清初,清廷出于满足人们衣着的考虑,出台相关政策才将棉花推广到了湘西,其间的得失利弊也由此而发生。棉花传入湘西,除了丰富衣料品种之外,还冲击了当地传统的葛布生产。棉花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种植才能获得丰收,较种葛藤相比,实则是投入量大,收获量小。加之湘西地区过于潮湿,特别是到了棉花采收的季节,连天阴雨会导致棉花霉烂,使得种植棉花的风险极大。此外,种植棉花还需频繁除草。其间的得失参半,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国内衣料风格市场的巨变,湘西地区种植棉花其实是弊大于利。这也是进入民国后,棉花在湘西地区停止种植的原因所在。
蔬菜作物的引进,也是清代的一大普遍事实。道光《凤凰厅志》载:“南瓜,种出南番,俗呼饭瓜,一名伏瓜。一蔓四五丈,叶如蜀葵,大如荷。……其形长者,俗呼牛腿瓜。”[23]卷十八物产由于南瓜在形态上与当地种植的葛藤极为相似,对土壤的覆盖度很高,因而引种这种作物,即使部分置换了葛藤,也不会引发明显的生态灾变。反而使得湘西民众获得了实惠。加之其种植规模不如玉米和番薯大,对生态的影响较小。因而,湘西地区种植南瓜利大于弊。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物引入湘西地区,如蔬之属,“蕹菜、葵菜”,蓏之属“金瓜、茄、辣椒”,草之属“蓖麻”等。[21]卷三物产这些多是蔬果类作物,在生活中主要充当副食。因而种植面积都不会很大,引发的生态问题也隐而不显,引种这些作物也表现为利大于弊。值得一提的是金瓜和辣椒,文中所涉及的金瓜其实不是瓜,而是西红柿。如(同治)《保靖县志》载:“金瓜,又名西番柿。形如南瓜,大不过四五寸。色赤黄,光亮如金,故名。”[21]卷三物产鉴于(同治)《保靖县志》问世的时间已经到了清末,因此,该植物大致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在湘西得到推广种植。与此相似的还有辣椒,(嘉庆)《龙山县志》载:“茄椒,一名海椒,一名地胡椒。垂实枝间,状如新月,黄色淡青。老则深红,一荚十余子,圆而扁,性极辣,故龙人呼为辣子。用以代胡椒,嗜之者,多青红,皆并其壳切以和食品;或以酱醋香油菹之。”[31]卷八物产在此之前,湘西地区只有花椒和胡椒。但辣椒在湘西得到推广种植后,当地居民饮食习惯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引发的文化变迁也非常巨大。
就这一意义上说,一种作物的引进,只要取得成功,所引起的文化重构也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这些作物做为蔬菜引进,其种植规模不大,又能与当地的土著作物相伴生,因而引发生态负作用的风险很小,仅表现为番茄的品种容易退化,辣椒规模种植后,虫害和草害比较严重。而一旦利用农药,就会引发次生的环境污染,这是当代生态建设需要借鉴的重大问题。
四、结论与延伸
对清代湘西地区引进外来作物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随着跨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传统文化生态区引进外来作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实。而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会引发怎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则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即使是科学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要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也无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今天的生态建设而言,归纳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和参考价值。外来作物的引种理当成为当代生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如下经验与教训,或许能在当代生态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引进作物的原生地来看。引入地的空间距离越远,被引入地历史上被隔绝得越严密,外来作物所构成的生态后果和文化后果风险就越大。清代引进湘西地区的作物,其原生地主要是美洲,空间距离如此之远,以至于这些作物引种后,会引发各式各样难以预测的生态问题,就显得不足为奇。对此,当今仍需引起高度的警惕。
从引进作物的目的和功用来看。外来作物种植面越广,规模越大,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影响越明显,生态风险也越大。立足于湘西地区,作为高产农作物引进的玉米和作为经济作物引入的烟草,之所以引起的负作用大,与引进后的规模存在密切关系。特别是当时政策极力推广,使这些作物能获得丰收和盈利,就导致了大量的推广种植,其引发的生态后果和文化后果也愈加明显。相比之下,作为蔬菜引进的作物,所引发的生态风险就低得多。茄子、南瓜几乎没有引起巨大的生态风险,就可为此提供证据。
从被引入地的自然与生态结构来看。被引入地与原生地的自然与生态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引进后的安全系数也就越高。反之,风险就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具体到湘西地区而言,由于这一地区炎热潮湿,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与马铃薯的原产地——安第斯山高海拔区段疏树草地生态系统反差太大,以至于马铃薯引进湘西地区后,犯病率太高,结出的块根会日益退化变小,从而使得引进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就是一个有利的佐证。烟草和玉米的原生地环境与湘西地区的反差也很大,湘西地区地表崎岖不平,水土流失的风险本身就较大,大量引种玉米规模性种植后,会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甚至是石漠化灾变。烟草引进后,对当地的原有物种会构成威胁,其发病率偏高也可以为此作证。
从耕作体制上看。在种植的作物结构中,生物物种的构成越复杂,引发生态风险和文化风险的几率越低。具体到湘西而言,由于这里的苗族和土家族在接纳外来作物时,基本上还属于游耕类型文化,农事耕作中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使得外来作物引种后,在苗族和土家族的分布区所引发的生态和文化负效应,都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湘西地区的原有耕作体制中,大量种植块根植物作为粮食,以至于甘薯的负作用隐而不显,这显然与此前已有类似作物普遍种植有关联。而湘西汉族移民的村寨则相反,由于在种植玉米、烟草时,实施了汉族传统的精耕细作农耕体制,将杂草都加以严格清除,使得在这样的耕作区内,贴近地表的伴生植物非常有限,以至于遭到水土流失风险的几率便在无意中被放大。在湘西地区,引种的烟草、马铃薯和番茄因不适应环境,生物自身的退化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从作物的生物属性来看。外来作物的引种必然要面对严峻的环境适应挑战,要获得新的适应能力,不仅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磨合,相关民族还要付出巨大的智力和劳力投入,这是作物引种中必须要面对的事实。[32]因而,任何意义上的外来作物引种,都需要有充分的思想、物质、制度准备,切勿过分看重短期经济效应,而忽视了长期的生态效应,否则将会引发难以预测的生态和文化后果。当今若要进行外来作物引种,必须牢记作物的生物属性和环境的差异绝非人力可以改变。因而,必须以史为镜,吸取清代外来作物引进所留下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