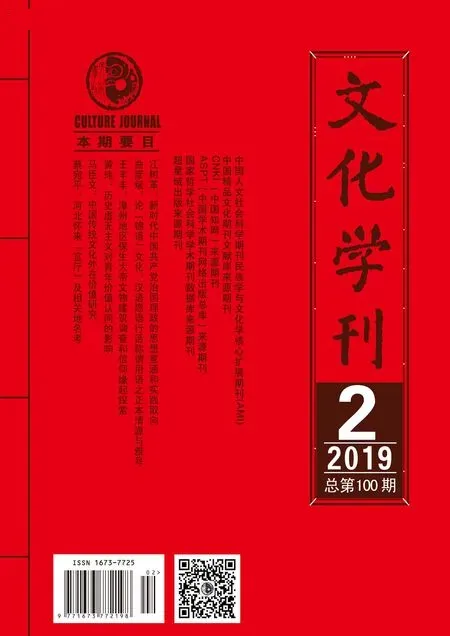李白任侠精神之内核
苑宇轩
隋唐时期,中原文化与胡文化相结合,刚健尚武的思想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侠文化大盛于世,咏侠诗歌的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唐代咏侠诗题材广泛,气魄不凡,且深受文人热爱。卢照邻、王维、李白、杜甫等诗人都曾创作过咏侠主题的作品。在这其中,尤以李白诗歌中所展现的任侠精神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盛唐之社会风气。李白的任侠精神之内核有三点特殊之处:其一,任侠是李白自我内蕴人格的真实写照;其二,李白将任侠精神上升为用世之态度;其三,李白的任侠具备极强的家国情怀。这三个方面相互交融影响,使任侠成为李白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也使李白成为侠客精神的践行者。
一、李白的自我人格——现实中的“侠”
李白有着“诗仙”之称,其作品往往带有飘逸灵动的仙气,杜甫称李白为“谪仙人”,正体现出李白性格中的豪放洒脱,不拘尘俗。这种性格的根源在于李白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侠气。与一般文人士大夫不同的是,李白是一个真正的侠客[1]。唐代诗人刘全白为李白作《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在其中说到:“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这表明,自少年时代开始,李白的任侠之气就成了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李白的成长过程中,勤学苦读、增长文化知识从来不是他唯一重视的事情,在“观百家”之外,是李白高深的武学造诣与丰富的实战经验。深受陇西文化影响的李白成了“文武不殊途”的全才。
在李白所有的诗歌作品中,“剑”作为意象出现了107次,分布在106首作品中,约占李白诗歌总数的10%。李白如此热衷于“剑”意象的使用,在实际历史中,他的剑术也颇为出名。“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2]按李白的说法,他在十五岁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击剑之术,这正是他能够作为一名侠士的立身之本。他在诗中写道:“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结客少年场行》)白猿公是先秦时代一位剑术大师,后人多以“白猿公”泛指善剑法之人,而李白自信自己的剑术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剑术大师,虽不免有一些夸饰之意,但这也从侧面看出,李白对于击剑之道确实有一定的造诣,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这使得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有了自我内蕴的人格基础,而不是仅靠虚幻想象来描摹。李白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位侠者,他的侠士形象多来自于自我内蕴人格的高度升华,如“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李白诗中的少年侠客形象,其原型来源于李白自身,其任侠精神不需要借助外部客观形象得以表达。故李白的咏侠诗更显磊落雄豪之气、快意恩仇之感。“侠”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审美范畴,与李白的自我人格融合在了一起,彰显了李白的本色,使其作品具有了独有的、强烈的感染力。
二、用世态度——不卑不亢,平交王侯
李白的思想相当驳杂,侠作为李白内蕴人格的一种,被李白上升为用世态度之一,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李白人生哲学的一部分。李白的任侠之风,极具责任感与同情心。重义气,守诚信;不卑不亢,平交王侯,是其用世态度的具体体现[3]。
李白的家境比较殷实富足,但这并没有使其养成飞扬跋扈的习惯;相反,他在游侠生活的过程中,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散金三十余万,用来接济落魄之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正是李白一生践行之事。“这些侠肝义胆,是对世态炎凉的封建社会世风的否定和补充。既是封建下层社会小生产弱小者的愿望和需求,又是以浪游为生涯的诗人李白的精神寄托和需要。”[4]李白的任侠之风中,时刻透露出渴望平等的意愿,他不希望因为出身的卑微与低下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李白的心中,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社会等级的限制与束缚。所谓“有力者疾以助人”,李白不仅自己具有“不屈人”的傲骨,更希望这种精神影响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使每一个人在人格尊严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基于此,李白极其看中“义气”与诚信的作用。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李白的义利观正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为了道义和信诺,即使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在《侠客行》中对朱亥与侯赢的事迹高度赞赏:“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赞扬他们二人可以为了信陵君救赵献出自己的生命,所求不为名利,只是因为当时的承诺。侠者一诺千金,义字当头,李白对这样高尚的人格境界不断追逐,重义轻利成为了李白的处事原则之一[5]。当他的友人死后,他用对待自己亲人的礼节对待死去的挚友,哪怕当时李白已经身无分文,却仍然用乞讨得来的钱财将朋友安葬。对待与自己深交的人,李白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他人的事业,他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李白义气为先的价值观的实质就是把“义”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尺,摒除世间一切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尔虞我诈,直击人的心灵深处,达到人与人灵魂之间最直白、最纯净的交流。因此,李白得以“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三、入仕之途——英雄主义情怀
李白是一位解人之难,言必信、行必果之人。然而,李白的任侠精神不止于哥们儿义气,更上升到了家国层面。只不过,李白渴望报效国家的方式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仕宦之路,而是充满了李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他高远的志向与任侠思想相结合,使李白积极入世的同时也游离于常规统治体系之外。
李白渴求建功立业,他在诗文中不止一次表达过求取功名之心。如:
“看取眼前富贵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少年行》)
“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
李白虽然热切地拥抱大唐盛世,却不屑于用寻常儒生入仕的手段博取功业,他对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充满了蔑视。李白对腐儒的鄙弃,与他对侠客的礼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体现了李白的个性,而且显示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李白希望寻找一条捷径,从而快速完成自己的雄伟抱负,这来源于李白对个人能力的极度自信。他在渴求得遇明君的同时,也认为即使身无长物,不担任官职,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李白的家国情怀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三不朽”,也超越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体系。李白对于入仕的态度,已经上升为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突破,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具备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对李白而言,高官厚禄固然重要,可没有这些,自己依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为国家作出贡献,他的胸中自有丘壑,富有四海,心怀天下。
四、结语
李白希望自己成为救世的英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是抛开一切身份与地位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侠”文化正是极致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当时局危困之际,“侠”便被世人赋予一种“超能力”。人们渴望成为扶危济困的盖世英雄,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侠”的崇拜,多是来自于对现实种种困阻的无可奈何。现实的重重打击往往使李白陷入苦闷与孤独,但李白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也正是他的这种精神,唱出了盛唐的最强音,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心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