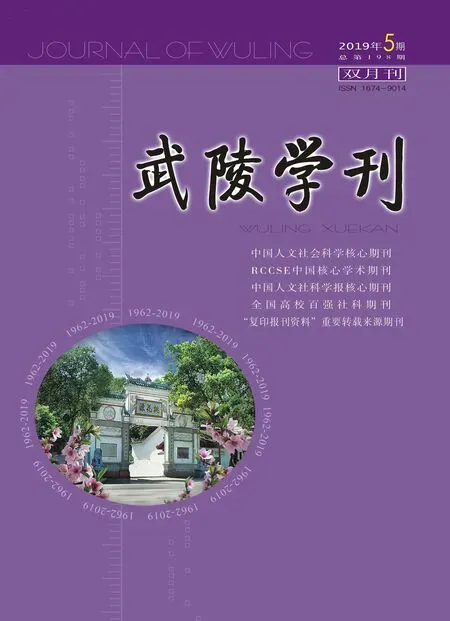法文化视域下的《易经》探源
桑东辉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一,历来被奉为“群经之首”“三玄之冠”。《易经》是对中华文明滋养最厚、对中华民族精神影响最深、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经典。但有关《易经》的成书性质,几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从《易传》产生时起,人们就已无法确知《易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根本性问题。笔者不揣拙陋,拟从法文化的视角对《易经》一书的性质进行探研,以就教于方家。
一、多维文化视域下的《易经》源头考索
从易学史的角度看,根据研究路径的不同,易学主要有义理易与象数易之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又出现了科学易(包括天文、历法、建筑、中医、音乐等领域)与人文易的分野。为了便于把握《易经》的成书性质,我们综合历代易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大体归纳了对《易经》性质研判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卜筮说
通常人们是将《易经》作为卜筮工具来使用的。《周礼·春官宗伯·大卜》明确大卜的职责是“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易经》乃三种卜卦的方法之一。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易赞》中也重申“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进一步指出了“三易”乃夏、商、周三代各自适用的筮占方法。夏、商两代的筮书今天已无法窥其全貌,从古籍的零星记述中我们只能知道夏代的《连山》乃首艮之卦,殷代的《归藏》乃首坤次乾。而首乾次坤的《易经》作为周代的筮书流传至今,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用《易经》进行占卜吉凶、预测决疑的记载。《左传》《国语》中出现过22则用《易经》占问的筮例。汉代随着京房、焦循、孟喜等象数学派的生发,《易经》的卜筮理论日益完善,到了宋代邵雍创制了“梅花易数”,《易经》在卜筮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即便在今天,不仅易学家刘大均等坚持卜筮说,而且民间大众通常也把《易经》作为一本算卦书来看待。
(二)哲理说
此说是对象数派的反动。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的说法。但自汉初以来,象数易学一统天下,京房、孟氏相继列于学官。象数、卦气、爻位、阴阳灾异等成为阐释《易经》的主流话语和官方意志。最初的义理派出现在民间,主要是以费直为代表的费氏易学,费氏坚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易》上、下经。到了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易兴起,义理派始得真正创立。义理派不讲卜筮和占验,而是偏重于研究《易经》及《易传》中的哲理内涵。后来,则有象数和义理合流的倾向。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指出:“郑(指郑玄)则多参天象,王(指王弼)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并兼采郑注、王注。宋易进一步融合象数、义理两派,如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中说:“易本为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于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认为理,而不认为卜筮,亦非。”义理派在把《易经》作为哲理书来解读时,又进一步分为哲学派和伦理派。哲学派认为《易经》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研,提出了天道宇宙观、本体论、形上说等哲学范畴的问题。伦理派认为《易经》通过对夫妇、人伦、义利、人性等问题的占问,实际是要阐释“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说卦传》)的义理,故又有《易经》乃“穷理尽性之书”一说。今人黄寿祺、金景芳等也都持哲理说。
(三)史书说
用《易经》来研究历史,古已有之。司马迁将《史记》定位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历代也不乏有以殷周之际史事解易者,但把《易经》中的一些卦爻作为史事来进行系统探究还是近现代的事。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学的传入,研究者开始从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视角研究古代历史和上古经典,《易经》研究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当时,沈竹礽、章太炎等皆倡《易经》古史说。《古史辨》的作者顾颉刚受王国维甲骨文研究成果的启发,认为大壮卦和旅卦中的“丧羊于易”“丧牛于易”,说的乃是殷商先君王亥与有易部落之间的事。进而顾颉刚又论证了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康侯用锡马蕃庶、箕子之明夷等故事在《易经》中的反映[1]。胡朴安著有《周易古史观》一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再度活跃,《易经》古史派也不乏新成果,如杭州大学黎子耀的《周易秘义》就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奴婢起义史”。北京大学李大用继承乃父李世繁遗志著成《周易新探》,认为《易经》是周人记述从周文王到周成王这段历史的史书。20世纪末,民间学者黄凡利用统计学方法,考之古籍,将《易经》六十四卦推定为周文王受命七年五月丁未日到周公摄政三年四月丙午日共2 880天的史筮记录,而写出了《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此外,香港学者谢宝笙在《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等系列著作中,认为《易经》是周初大臣南宫括记载周兴殷亡历史的史书[2]。
(四)政书说(或经纶说)
余敦康坚持“《易》为拨乱反正之书”,认为《易经》主要是讲拨乱反正、安邦定国的经纶之道的。有学者从《易经》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的角度,认为《易经》是上古政治决疑方面的咨询、建议。“《周易》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换言之,上古社会(或曰青铜时代)的政治,需要占卜来决疑吉凶,运用占卜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并引证《左传》等史籍,指出先秦时期王朝及诸侯往往“以《周易》的筮占来决定国家的嗣位、建侯等大事,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吉凶都纳入《周易》的统摄之中”[4]。更有论者从管理学的视角把《易经》看做是讲管理的书,认为易道是中国管理艺术的价值之源。“《周易》八卦这种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论,都是极其古老的文化符号,在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以及管理变革中,仍然有显著的现实意义。”[5]还有学者认为《周易》是“我国古代科层制管理的萌芽”[6]。
(五)古歌说
对《易经》中若干卦爻的诗歌形式问题,古人论述的较少,倒是现代特别是当代的研究者对此多有阐发。20世纪初,郭沫若先生就对《易经》中的诗歌进行了研究。他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明确指出:“《易》经文的爻辞多半是韵文,而且有不少是很有诗意的。”[7]并以有关爻辞为例,从韵脚、内容、意境等方面对《易经》中的古歌进行了发掘。如他把屯卦六二的“屯如膏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描绘成原始时代男子的求亲诗;把归妹卦上六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描绘成一幅年青牧羊夫妇剪羊毛的田园牧歌般的场景。李镜池先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郭沫若没有纳入古歌研究范围的若干爻辞,并将这些爻辞称之为“诗歌式的句子”,断定《易经》的“卦爻辞中有两种体制不同的文字——散体的筮辞和韵文的诗歌”[8]。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亨先生从训诂学的角度对《易经》古歌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易经》卦爻辞在先秦文献中称为“繇”,并进而论定“繇”为“谣”。“因筮书之卦爻辞及卜书之兆辞,大抵为简短之韵语,有似歌谣,故谓之谣”,直接将《易经》中的有关爻辞断为古代歌谣,并按照赋、比、兴、寓言四类将《易经》歌谣分为四类[9]。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善文、傅道彬、黄玉顺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踵事增华,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发。张善文在《周易与文学》中从《易经》卦爻辞中辑出古歌151首[10]。傅道彬则力争还原《易经》古歌所反映的内容,比如他将乾卦爻辞与苍龙星座形态、坤卦爻辞与秋天的大地景色、离卦爻辞与宏大的战争场面等具象联系起来,同时将剥卦爻辞与阶级差别、咸卦爻辞与粗犷野性的原始恋情等抽象内容联系起来[11]。黄玉顺则将每一卦都解释为一首古诗,有的一卦中还含有一首以上的古诗,共辑出68首古歌[12]。张剑对《易经》卦爻进行整理,共得105首古歌,相当于《诗经》的三分之一强,并据此断言“《周易》中隐含着一部比《诗经》更早更古老的歌谣总集”[13]。
(六)百科全书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之以入易,故易说至繁。”这一认识也为后世学者所普遍认同,即便是持上述成书性质之一的学者也不否认《易经》中所蕴涵的其它方面的知识样态,承认《易经》的含弘广大,认为“《易经》是被宗教巫术大氅包裹着的人类孩提时代的百科全书;它相当广泛地展现了中国上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审美意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14]。
以上各说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而外,还有根据《易经》中所蕴涵的军事、数学、天文学、中医学、农学等内容,从不同的学科分野来生发《易经》的相关理论含量的。由于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不一一赘述。
二、《易经》卦爻辞中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内涵
《易经》就像一座宝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如果一个人拿着探测金矿的工具进去,就会掘出金矿;如果带着探测银矿的工具进去,也一样会挖出银矿。同理,从文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不同文化维度看,《易经》的卦爻辞确实包含着丰富的相关文化视域中的宝贵资源。同样,从法文化维度挖掘,也不难发现,《易经》卦爻辞包含丰富的法文化资源和上古神判以及判例的遗存,体现了上古巫术与司法审判同源的原始习俗。从某种程度上讲,《易经》的部分卦爻辞记载了上古一些司法判例和习惯法的内容,是将卜筮与司法判例相结合的法例集篡。下面就撷取一些有关法律判例和习惯法的卦爻辞进行简要分析。
(一)负乘致寇——有关防范盗寇的法律规制
《易经》成书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围绕财产的占有、争夺,出现了“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尚书·康诰》)等刑事犯罪。《易经》卦爻辞中多次出现“利御寇”“不利为寇”等爻辞,“富以其邻”“不富以其邻”也是出现频次较高的爻辞,显见邻近部落之间的寇攘行为频仍,甚至还出现了抢婚与寇攘的混淆。《易经》中屡见“匪寇婚媾”的爻辞,如《易·睽·上九》记载“见矢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同脱)之弧。匪寇婚媾”的虚惊一场,这些都说明当时部落之间的寇攘行为是非常频繁的。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易经》提示人们要加强对暴力犯罪的防范,提高自力救济能力。除了加强“御寇”的必要措施,从财产所有者的角度也要增强财产保护意识,以防止由炫耀财物而刺激他人的犯罪欲望,使人见财起意。“无妄之灾”就是源于《易经》。所谓“无妄之灾”系指由于保管不当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在《易经》中,不仅无妄卦六三爻所记载的“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乃无妄之灾,否卦九五爻辞所谓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也意在提醒因保管财物疏忽大意而容易造成损失,强调要加强对财物的严格保管,即遯卦六二爻辞所强调的“系之以黄牛之革,莫之胜说(同脱)”以及坤卦六四爻的“括囊,无咎无誉”和蒙卦九二爻的“包蒙,吉”等。反之,如果一个人背着财物、坐着车,招摇过市,则必然招致盗寇。这就是“负且乘,致寇至”(《易·解·六三》)的警示意义之所在。
(二)丧马勿逐——有关遗失物的法律规制
遗失物的追索是私有制产生后的必然。对遗失物的处置,早在上古就已经有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如《左传·昭公七年》有云:“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形成了捕捉逃奴、牲畜的惯例。周武王伐纣灭商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指责商纣王窝藏各诸侯国的逃犯,所谓“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尚书·牧誓》)。《尚书·费誓》亦一再重申“马牛其风,臣妾逋逃,无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的习惯法准则。此外,春秋时,楚国在制定仆区之法时,也明确提出:“盗所隐器,与盗同罪。”(《左传·昭公七年》)从这些习惯法来看,在我国上古时代确实存在返还遗失物的相关法律制度,如明确规定不得私自藏匿拾到的走失牲畜和逃亡奴隶,而要按照规定送还原主。后世不乏怀疑《尚书》乃伪作的,并对上古是否有关于遗失物返还的政策也产生了怀疑。而《易经》中则多见“丧马勿逐”,“利牝马之贞,利东南不利西北,先迷而后得主”,“亿丧贝,勿逐,七日来复”,“妇丧其茀,勿逐,七日来复”等,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在上古时代已经出现了关于遗失物拾得和返还的法律制度。从遗失物品的种类看,以马、牛等大牲畜居多,其次是货币和生活用品。根据涉及遗失物的各卦爻辞中多主张“勿逐”失物看,当时存在拾得人返还他人遗失物的制度或习惯。而且这种返还是有时限要求的,即“七日来复”,最迟不能过10日。《周礼·秋官·司寇》记载有朝士一职,并明确其负有甄别并确权遗失物的职能,如“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也就是说,有人拾到无主遗失物后要公示10天(即“旬日”),如果过了10天仍没有人出来主张权利,则贵重物品要充公,而非贵重物品可依法归拾得人所有。《周礼》的这个规定大体与《易经》《尚书》《左传》相同。如《易·丰·初九》曰:“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也就是说遇到了失主,虽然过了10天,前往归还拾得物仍被认为是高尚的行为。反之,过了10天还不归还则要受到法律的惩处。故而《易·丰·初九·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三)旅丧童仆——有关交易风险的法律规制
上古时期就出现了“日中而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传下》)的交换行为,也出现了“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泰·九三》)的交易原则①和“亿丧贝”(《易·震·六二》)、“丧其资斧”(《易·巽·上九》)、“得其资斧”(《易·旅·九四》)、“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易·坤》)的记载。卦爻辞中的龟、朋、贝、资、斧等都是上古货币形式,甚至还出现了“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易·复·象》)等有关上古商贸交易习俗的原始禁忌。这些都说明早在《易经》成书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频繁的物品交易,与之相适应,也必然出现有关法律规定。《周礼》有司市、质人、贾师、司稽等专门负责市场管理的官职,还出现了傅别、质剂、圭质、盟诅等信用保证措施。《易经》的旅卦则描述了一个商人的交易过程。譬如,旅卦六二爻的“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说的是商人支付对价购买奴仆的交易;九三爻的“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则描写了商人所住的旅店失火,导致刚刚买到的奴仆被烧死(或逃掉)的情况,表明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有关交易风险的法律规范,其核心内容大致是在买方给付对价取得动产物权后,标的物灭失这一风险责任相应地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有关商品交易的法律实务不仅在《易经》中有所记载,陆续出土的金文资料也提供了相关佐证。金文法律史的研究专家胡留元、冯卓慧在《长安文物与古代法制》中分析指出,西周时已经出现了较为频繁的交易和债的流转问题。如《卫盉》反映的是田、物交易,《五祀卫鼎》反映的是田、田交易,《曶鼎》则是对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买五个奴隶的交易纠纷的判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法存在民刑不分的现象,“把本来属于民事法律规范方面的田土、马牛等争讼,用刑事手段去解决”[15]。《易传》的作者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指出交易与刑罚密切相关。在追溯噬嗑卦产生的渊源时,将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传下》)的原始市场交易作为噬嗑卦的立卦基础。对于《系辞传》对噬嗑卦的这一阐析路径,历来宿儒多不得其详,而往往曲解之。难得的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虞翻一针见血地指出:“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饮食之道,故取诸此。”虞翻将噬嗑与饮食联系起来,进而通过生发《序卦传》“饮食必有讼”的思想,将噬嗑与有关交易的法律制度联系起来,为后人梳理了《易传》的法律思想。无独有偶,专讲商旅之卦的旅卦《大象传》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这些都说明饮食会产生交易、交易容易引起讼争,讼争如果不能息讼和解则可能有刑狱之灾。这种法律发生逻辑在今天看来虽然并不科学,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是由来已久。
(四)归妹愆期——有关婚姻制度的法律规制
《易经》中涉及婚姻和家庭的卦爻辞很多,仅以婚姻为例,就有“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易·屯·六二》)、“女壮,勿用取女”(《易·姤》)、“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易·蒙·六三》)、“纳妇吉”(《易·蒙·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易·大过·九二》)、“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易·大过·九五》)、“得妾以其子”(《易·鼎·初九》) 等诸多爻占。此外,还有专门讲婚姻的卦,如《易经》下经的前两卦咸卦和恒卦就是分别讲男女交感、夫妇之道的,渐卦是对原始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嬗变的描述,而归妹卦则是对媵婚制度的记录。媵婚制是商周时代出现的一种贵族婚姻形式。《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实际上,媵婚制是在一夫一妻制基础上的诸侯婚姻制度。一个诸侯在娶异姓为妻的同时,被娶者的同姓女弟和侄女要作为媵妾陪嫁。所以,归妹初九曰:“归妹以娣。”这个娣就是作为媵妾陪嫁的正妻的女弟。按照媵婚制的惯例,姐姐是不能作为妹妹的媵妾陪嫁的,所以归妹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对于须字,宿儒多不得其解。《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须,需也。”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取“须,女之贱者”之意,皆差强人意。金景芳先生以《离骚》中的“女媭”之“媭”来解须,释须为姊,认为“姊姊可嫁与人作嫡”[16],这是极富启发性的。这爻可解为用姐姐作为媵妾来陪嫁不合礼法,故遣返之,而以其妹为娣来陪嫁。九四爻的“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则进一步说明由于六三爻的返归迟延,造成了愆期。上六爻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则表明在媵婚制中媵妾的地位是低下的,没有资格与夫一起祭祀祖先,只有嫡夫人才有资格与丈夫一起祭祖。此卦的女主角都是陪嫁的媵妾,所以这里说的承筐无实的主体也一定是媵妾,这样违背礼制的行为必然是“承筐无实”“刲羊无血”,祖先得不到血食,其“无攸利”的结果也是必然的[17]。
(五)井收勿幕——有关公共设施管理和使用的法律规制
《易经》中蕴涵着大量的和谐理念,不仅含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而且还非常注意人与自然和谐,讲求“王用三驱失前禽”(《比·九五》),反对涸泽而渔。同时在制度设计上明确了“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屯·六三》)的狩猎规定,要求人们严格遵守虞人引导和监督配合下的狩猎规定。此外,《易经》还十分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和管理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井卦就是对公共设施维护、使用的一个专门的制度遗存。井是原始先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有关井的维护和使用不仅是一个部落、一个氏族内部管理的重要事项,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井的规定也是当时人们所应普遍遵守的公德。即便是在战争中也不能毁弃对方的井,“井堙木刊”是有违战争道德和公共伦理的,是受到公共舆论谴责的行为。这在《易经》中也有所体现,那就是井卦所说的“改邑不改井”(《易·井》)。同时,井是为人们提供水资源的公共设施,所谓“往来井井”(《易·井》),乃至于即便整个部落都迁徙走了,原来的城邑聚落被废弃了,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井填埋毁坏。“井收勿幕”(《易·井·上六》),用完了井,也不要盖死,要方便他人使用。对长期废弃而导致淤泥堆积的旧井,要及时清理,以防止出现蛤蟆泛滥井底的“井谷射鲋”(指蛤蟆)(《易·井·九二》)情况,避免由此而造成的“井泥不食”(《易·井·初六》)和“井渫不食”(《易·井·九三》)的状况。此外,对井的配套设施,《易经》也有相关规定,如要保护好汲水用的瓦罐,一旦汲水器皿破损则无以汲水。“瓮敝漏”(《易·井·九二》)、“羸其瓶,凶”(《易·井》)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六)利涉大川——原始神判的遗迹
过去人们对《周易》卦辞频见的“利涉大川”多从字面上解释,认为其意指适合去渡大河。有学者认为《易经》中的“不利涉大川”“利涉大川”“或跃于渊”等卦爻辞具有“水神”裁判的原始神判意蕴,并以景颇族的“闷水”裁决(当事人双方各沿一竹竿潜入水中,以在水中停留时间最长者为胜)和南洋尼亚士族的沉水神判(纠纷双方均沉于水中,最久者得胜,淹死者即有罪,死是神对他的惩罚)等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资料来佐证[18]。我们倾向于将“涉大川”等卦爻辞看做是水审判的神判形式,并进而认为《易经》中除了水神判形式外,还有獬豸审判(见解卦)、神虎审判(见履卦)、神羊审判(见大壮卦)、神龙审判(见乾卦)、日神审判(见丰卦)、月神审判(见归妹卦)、雷震审判(见震卦)、血液审判(见需卦)、毒审判(见蛊卦)、决斗审判(见晋卦)等不同形式的原始神判模式。对于《易经》中的上述神判形式,一些学者进行过考释②。
限于篇幅,以上仅仅是从刑事犯罪、物权、经济、婚姻、公共环境、司法审判等几个方面各撷取一、二来概要说明《易经》中蕴涵的丰富法律判例和法律思想。其实,像这样的法律类卦爻辞例在《易经》中还有很多。另外,《易经》中还有很多专门记录法律类象的专卦,如专门讲诉讼的讼卦、专门讲刑罚的噬嗑卦、专门讲监狱制度的困卦、专门讲捕逃的遯卦(遯者,遁也)、有关法律起源的“师出以律”(《易·师·初六》)、兵刑合一的师卦、专门讲对童蒙等因法律认知不足引起的犯罪“用说(同脱)桎梏”(《易·蒙·初六》)、予以赦宥的蒙卦以及“刑罚清而民服”(《易·豫·象》)、“无敢折狱”(《贲·象》)、“赦过宥罪”(《易·解·象》)、“折狱致刑”(《易·丰·象》)、“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易·旅·象》)、“议狱缓死”(《易·中孚·象》) 等法律特征明显的卦爻,更有许多以不同形式体现了法律文化内涵的卦爻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卦都与法律问题有关。
三、解释学视域下《易传》对《易经》法律内涵的解读
以《易经》文本来自证其成书性质固然重要,通过古人解易书来破译《易经》密码亦不乏给人启发。在浩如烟海的解易书中,《易传》是目前最古老、最权威的解释《易经》的典籍。从解释学理论看,越接近被解释事物的时代,其解释越具有信据力。尽管《易传》作者距《易经》产生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乃至于《系辞传下》也只能小心地推断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但综观易学史,毕竟《易传》作者还是最接近《易经》产生的时代,其对《易经》的解释和阐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易经》的原旨。因此,研究《易传》对解开《易经》成书之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取象比类与先秦司法惯例
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系辞传上》)短短数语道破了《易经》的主旨。对于由阴爻和阳爻的基本符号构成的《易经》,《易传》对其解释的理路也是从阴阳、天地、尊卑、动静、刚柔等对立统一角度入手的。在《易传》作者看来,《易经》的主旨就是通过对自然界各种现象和运行规律的取法,来分门别类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来化解冲突,断吉凶,定秩序。取象比类蕴涵着重要的法律内涵。先说取象。取象的象,一是指卦象。如噬嗑卦为下震上离,象口中有物,要咬合。这个咬合就是法律规制的内容,故噬嗑卦乃是“利用狱”之卦。二是指取象制器的对象。如《易·系辞传下》中的“盖取诸×”等圣人制器尚象之类。尽管《易传》中对器具产生的推断不一定都符合实际,但这种取象制器的方法对《易经》来说却非常重要,《易传》正是通过将相关器物与《易经》中的具体卦象进行联系和附会,才为相关卦的卦意,特别是理解卦的法理意义提供了依据。有学者指出,《易传》所提出的“观象制器”体现了法象自然的法律观。“观象制器”的“器”指法律制度和刑法原则[19]。再说比类。比是比较、比附的意思。《易经》中有比卦,武树臣认为,比卦说的就是对同类案件比较的判例法原则。类的概念在《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典籍中多有出现,他们的类观念是受到《易经》的启发和影响的。而《易经》的类推思想具有原始的逻辑思维色彩。“拔茅茹,以其汇征”(《易·泰·初九》)已然是对相同或相似事物之间的联系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是对一类事物具有共同规律性东西的归纳和总结,并提出指导人们处理同类事物的办法。因此,《周易》的取象说的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和规范原则(包括法律规范、礼制规范、习俗规范等),这个象也类似将成文法典“悬之象阙”的做法,是象魏之象。比类则说的是在对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中按照不同类别施行不同的判例,是后世廷行事和决事比的先河。“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易·系辞传上》)《易经》六十四卦就是在八卦基础上触类旁通,按照八经卦的基本原则处理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个人的各类事物。而在八卦中的离、坎、兑、震等卦则多与刑狱有关,故八卦相荡而成的六十四卦中有相当数量的司法判例。从取象比类的情况看,《易经》中有武树臣所谓的法典法和判例法兼用的混合法形态[20]。
(二)观象玩辞与司法训练和实践
《易·系辞传上》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里的君子指的是统治者,具体到司法实践中指的是具有裁决权的君主、司寇等司法官员,也即卦中所言的“见大人”之大人。要做到遵循法律原则、按照先例判案必须积累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这个积累就是要经常地观察易象,体会卦爻辞所包含的先例中的判案原则和宗旨。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系辞传上》)。只有明吉凶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变化而适时进行占验,并做出遵循先例的判决或因时变易地创制新判例。首先,要遵循先例。“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易·恒·彖》)因此,在司法审判中要做到恒,即遵循先例。“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易·恒·象》)“恒,亨,无咎。”(《易·恒》)反之,如果不能恒定地遵循先例,则“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易·恒·九三》)。其次,在遵循先例的同时,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所改易。“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易·恒·彖》)在把握法律原则的大方向下,随着情况变化而及时创设新的判例也是十分必要的。《易传》反复颂赞《易经》重时,多处谓其“×之时义大矣哉”,主要是肯定了《易经》的变易观。《易传》还从革卦、鼎卦等卦义中发掘出革故鼎新、天命更易的革命观。这些都是对先例的否弃,并假托天命所归而创制新的判例。“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易·系辞传上》),就是指明《易经》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先例的掌握、了解,根据现实的变化,对新发生的案例进行因时而易的处理、变通,与时偕行。“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易·豫·彖》)随着时代发展而变更先例的目的就在于刑罚清明,使当事人心服口服,维护社会安定。
(三)《易传》所生发的法律义理
《易传》在解释《易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潜藏在卦爻辞下面的法律义理,除了讼、噬嗑、困等显性的法律卦义外,还指出丰、解、贲、豫、旅、中孚等卦的法律本质,并断言“作《易》者其知盗乎?”(《易·系辞传上》)认为《易经》的作者是犯罪学方面的专家。而且犹为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易传》通过对《易经》义理的生发,完善了其明德慎罚的思想,并成为后世儒家礼法治国的滥觞。具体而言,《易传》是坚持德刑兼施,礼法并用的。一方面《易传》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基调,并将一些卦定义为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易·系辞传下》有言:“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贲·象》也强调“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另一方面,《易传》也主张对犯罪采取必要的规制手段,强调“明罚敕法”(《易·噬嗑·象》)。具体而言,就是针对触法犯禁者,要根据具体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相应地处以“屦校灭趾”“屦校灭耳”等或轻或重的刑罚。但刑罚的总原则仍然是以德为主,即坚持“议狱缓死”“赦过宥罪”“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等刑事处罚原则。并且根据“上慢下暴”(《易·系辞传上》)的反面教训,指出只有君子才能折狱,体现了“惟良折狱”的法官伦理要求。由此可见,《易传》希望通过德政教化和刑政规制两手抓,来实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易·大有·象》)的治世理想。在刑罚方面,《周易》总体上是强调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法律观,主张慎刑和宽宥,反对刑罚过中,强调刑罚尚中[21]。比卦中有“王用三驱失前禽”的爻占,而《易传》则把狩猎中的三驱之法引申到为政治国上,把为政比喻成猎人狩猎,指出在国家管理上要恩威并重、德刑兼施,既要施行德政,注意教化人民,使其知止不犯,反对不教而杀的罔民行为,特别是对懵懂不开的童蒙之人和愚昏老人,要网开一面,以仁德为主,使其“用说桎梏”,对那些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顺民则适当宽纵,又要对那些不顾罗网、非眚惟终的人进行坚决镇压。《易传》在阐释上古诉讼案例的讼卦义理基础上,提出了“讼不可长”(《易·讼·初六·象》)的儒家无讼、息讼思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讲求“春秋决狱”,其实《周易》的法理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指导精神。不仅《易传》对《易经》的解析成为古代判案的基本准则,此后的一些解释《易经》的易学著述也不乏上升为司法判案原则的。如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所蕴含的法律思想和刑罚适用原则就与《唐律疏议》基本一致,二者相得益彰,体现了《周易》法律思想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22]。
结 语
如前所述,《易经》中包含了大量的法律信息,有的是具体的案例,有的是司法原则,有的是法律思维。总之,如果一卦一卦的剖析,都能发现其中的法律内涵。但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对于《易经》的法律内涵,最早阐释《易经》的“十翼”已有所发现和阐发,但后世研易者多从象数、义理两径入手,于义理又多集中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对法律领域鲜有涉猎。到了现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杨鸿烈、瞿同祖等法史学先驱进行了若干的探研,但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直到20世纪末,武树臣、从希斌等学者对《周易》中的法律现象从法律史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才真正开创了法学易的研究。但在上个世纪,由于学界主流对《周易》与法文化的关系缺乏足够认识,导致相关研究不为法学界所接受,甚至一些研究《周易》与古代法制的论文难以发表。本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易》学研究的多视角、跨学科的延展,有关《周易》的法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课题[23]。黄震在《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上撰文《20世纪的〈周易〉法律文化研究》,对从法律角度进行的《周易》研究做了综述,进一步证明了法学易作为一个学派的可能。近年来,从法律视角研究《周易》的论著日渐增多,壮大了法学易的研究队伍,丰富了法学易的研究成果。
回到《易经》起源问题上,笔者认为从法文化的视角看,《易经》具有鲜明的法学特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习惯法和法律判例的篡集。武树臣对《易经》的法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判例法,《易经》比卦就“专门记录了适用判例的方法和原则”[24],并大胆断言:“《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神明判例集’。”[25]笔者认为,尽管中华法系以法典为主,但判例法的形态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律是成文法典,那么廷行事、比等就是具有判例的意义,例则是具有判例色彩的制定法。”[26]而不论是秦代的廷行事还是汉代的决事比,这种按照类推原理比附断罪的判例法的传统其源头就在先秦,并可在《易经》中大量地发现它的痕迹。但鉴于中西法律传统的差异和古今法律概念的变迁,笔者对先秦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武树臣所说的普通法系的判例法形态持审慎态度,并认为尚不宜遽断《易经》就是一部“神明判例集”,但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包含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传统习惯法的上古司法裁判的法例集篡当不为妄断。
注 释:
①按照武树臣的解释:“平:议也,指契约;陂,借为贩,移予也,指把财物从此地迁至彼地。往、复,指货物、货币的交换往来。”(见武树臣著《〈易经〉与我国古代法制(上)》,载《中国法学》1987年第4期)
②详见武树臣著《〈易经〉与我国古代法制(上、下)》,载《中国法学》1987年第4期、第5期;从希斌著《从〈易经〉看西周时期的司法制度》,载《法学家》1995年第3期;桑东辉著《司法审判的〈易经〉探源——革卦新解》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桑东辉著《司法审判的〈易经〉探源(二)——解卦新解》,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等。
③关于《易经》中的法律类项,不同学者梳理的路径不同。如连邵名按照刑、狱、幽人、讼、寇五类,对困、豫、睽、鼎、丰、坎、蒙、解、归妹、讼等十余卦进行法律解析(见连邵名著《〈周易〉所见古代法律》,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武树臣在《〈易经〉与古代法律文化》中从财产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审判司法制度、婚姻制度与习俗四个方面对《易经》的法律内容进行梳理(见武树臣著《儒家法律传统》第177-189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