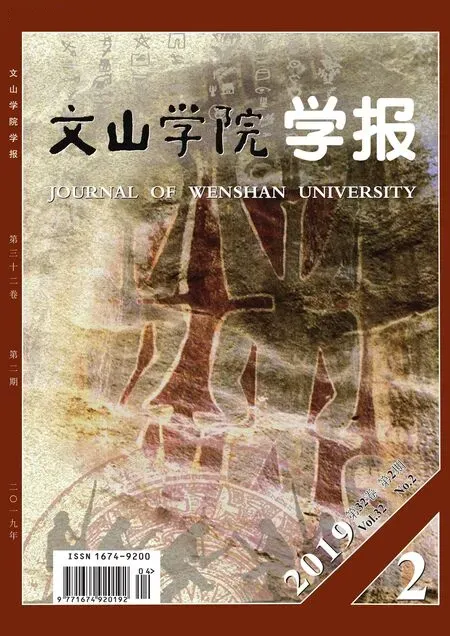由“离合”到“索隐”文学批评方法考证
赖晓琳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一
“离合”,就其渊源来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谶纬之学中文字结构的离析分合,后逐渐应用于其他文体创作之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离合之发,则明(唐写本作“萌”)于图谶”[1]此论主要立足于“离合”的形制而言。图谶起源于河图洛书的传说,是巫师、方士附会某种征兆用以传达天意而制作的隐语和预言。图谶中许多都是利用离合字的形式来附会的,这种图谶被称为字谶。东汉时期,各种谶语层出不穷,不仅限于保存在史书中的文字记载,如《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2]还有流传于口头的看似天真无邪实则暗含某种天意的童谣,如《新唐书·裴度传》谣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3]这种具有神秘性的文字记载或童谣之言,往往隐藏着某种政治意图。
随后,“离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逐渐被应用于文学领域。离合字体,以成诗章,在体制、思维方式等方面独具特色,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离合诗。如东汉袁康、吴平所著《越绝书》,魏伯阳著《参同契》,均隐籍贯姓名于后序中,特知之者鲜耳。离合诗格,须先离后合,二著虽不似孔氏《离合诗》整齐之貌,但始备离合之雏形。在孔融作《离合作郡姓名诗》之后,众多离合诗作鱼贯而出,且离合体制逐渐演变而趋于成熟,自成一套创作体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对离合诗的体制进行过专门的论述:“按离合诗有四体:其一,离一字偏旁为两句,而四句凑合为一字;其二,亦离一字偏旁为两句,而六句凑合为一字;其三,离一字偏旁于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续为一字;其四,不离偏旁,但以一物二字离于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续为一物。”[4]从这段评述中可看出,离合诗体制经四句凑一字到六句凑一字、首尾相续为一字,再到首尾相续为一物,其离合形式、规则更趋多样化。在这体制变化过程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皮陆二人的唱和之作。
怀鹿门县名离合诗
皮日休
山瘦更培秋后桂,
溪澄闲数晚来鱼。
台前过雁盈千百,
泉石无情不寄书。
(桂溪、鱼台、百泉均县名)
和袭美怀鹿门县名离合诗
陆龟蒙
云容覆枕无非白,
水色侵矶直是蓝。
田种紫芝餐可寿,
春来何事恋江南。
(白水、蓝田、寿春)
六朝人作药名、县名诗,均嵌其名于一句中,而皮陆二人以与离合相杂,自成一体,篇章特富,并造新体,斯又欲于模拟中出新意者也[5]560。另外,离合诗在雅润和文约意广,以及思想意蕴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宋孝武帝刘骏所作骚体离合:
霏云起兮泛滥,雨霭昏而不消。意气悄以无乐,音尘寂而莫交。(悲)守边境以临敌,寸心厉于戎昭。阁盈图记,门满宾僚。(客)仲秋始戒,中园初凋。池育秋莲,水灭寒漂。(他)旨归涂以易感,日月逝而难要。分中心而谁寄,人怀念而必谣。(方)[5]549
此诗离合“悲客他方”四字,然诗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将表面的文字与思想上的深层意蕴两相结合。由此可知,实则内容丰富,情感激烈,意蕴深广,富有真趣之美。
“离合”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已逐渐渗透到诗歌以外的其他文体中,如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献帝践祚之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暗指董卓以臣陵君,不得生。杂剧中也有颇多出于避忌讳,免粗俗不雅而采用离合手法的例子。如元代关汉卿《四春院》第二折:(外郎云)非衣两把火,人贼是我。(裴)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西厢待月等得更阑,着你跳东墙女字边干。(奸)由此可见,“离合”这种创作方式已广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二
与“离合”这种创作方法相对应的,从“离合”角度对文本进行关照也随之出现。除前文所述徐师曾于《文体明辨》中从宏观上对“离合诗”的体制进行整体归纳总结外,还有许多文论家对具体的离合诗作进行细致的解读与评鉴。如孔融之《离合作郡姓名诗》,叶梦得便从“离合”的角度对此诗进行详细地分析。其《石林诗话》曰:“古诗有离合体,近人多不解。此体始于孔北海,余读《文类》,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渔公屈节,水潜匿方……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篇离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徐而考之,诗二十四句,每四句离合一字。殆古人好奇之过,欲以文字示其巧也。”[6]此论从反面批驳了“离合诗”仅是古人把玩文字之机巧,持此同论的还有严羽《沧浪诗话》:“离合(字相折合成文,孔融‘渔父屈节’之诗是也。)虽不关诗之重,轻其体制亦古……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之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7]客观来讲,确实存在一些离合诗歌有玩弄文字游戏之嫌,如南宋时期《苕溪集》中记载一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乃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詠黄鹤,志士心不已。”诗中将拆离的偏旁与合成的汉字同时罗列于诗句之中,毫无思想性、文学性,食之寡淡无味。然随后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孔融离合体,窦韬妻回文体,鲍照十数体……魏晋以降,多务纤巧,此变之变也。”从诗体演变的角度看,谢榛将孔融之离合体列于众诗体之首,可见孔融之《离合作郡姓名诗》并非只是诗人出于对文字游戏的热衷,而是作为各种杂体诗之源头,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对离合诗体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
从“离合”视角对具体文本进行阐释,还可以考察诗中深微隐幽之处。潘岳作《离合》离“思杨容姬难堪”六字,考据《潘安仁集》载:岳娶杨肇女,卒,有《悼亡诗》,容姬或是其妻名也。可知安仁其诗所传达的情感对象不是友人或某个红颜知己,而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亡妻。且此诗已经开始脱离简单的文字桎梏,转而凸显诗人内心情感的抒发,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妻子的深切思念。又如通过解读权德舆、张荐之离合诗作,后世可以了解到当时同僚继赓过程中文人们的相互交往。总之,无论是关乎政治的字谶、童谣,还是文学创作领域中所涉及的“离合”,其背后都暗藏着作者不可明言的深层意蕴。那么,从“离合”的角度对相应的文本进行关照,即犹如拨云见日,使幽微之处得以显现。创作者对汉字进行离合以便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读者在解读文本时对汉字进行拆解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诗歌中所隐藏的种种玄机,这对于研究诗人的生平、文学风格、政治立场,以及史学意义上的史实考证都大有益处。
三
然而,赵宋以降,其离合体式微,而唐代索隐批评开始发微。“离合”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效果正与“索隐”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第一部以“索隐”命名的批评著作是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索隐”即是要超越文本的字面意义,索解其文字背后的“本事”和“微义”,而“离合”则是通过解读诗句间的诗意,通过对诗句中汉字的拆解从而明确诗人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离合诗”这类隐喻性文学作品的产生,才使得读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对文本进行细致精微地索隐。
如索隐批评自唐代发微,在柳宗元研究中就存有大量的“索隐研究”,为了将柳宗元打造为一个反皇帝形象,有心人便千方百计地从作品中搜取相应对象,联系官场生态,再结合一贬再贬的经历,描绘出一幅幅诋毁君王、歌颂志士的英勇画面。并将其所作《咏史》《咏三良》《河间传》统统解释为具有影射意义的作品,但经史实考据,柳宗元非但没有诋毁抱怨其君主之意,反而充满了对唐宪宗的臣服与依赖。元明之际又兴起对戏曲小说的索隐批评,如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对众多戏曲作品的讥讪寓意的分析,体现出人们对故事原型与作家创作的具体意图的普遍关注。小说批评更是如此,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也同样受到索隐者们的猜疑,袁中道、屠本畯、宋起凤等人均对其提出过相应观点。《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尖刻地讽刺道:“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8]索隐派也正因对作品过分的解读而受到后世的极力反对和诟病。
即使反对者对其进行不遗余力的讨伐,“索隐”批评还是以极强的生命力留存于戏曲、小说研究之中,并形成了相应的批评流派,例如红学的索隐派。同时,对文本的解读方式也更趋多样化,既可以使用“拆字”“谐音”“解谶语”等猜笨谜式的方式,又可以根据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旁人对文本的批注,探索出文字背后的“本事”和作者的创作动机。如盛行于清代的红学索隐派对《红楼梦》的解读,由于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象征和谶语,以及叙事者本人声称的“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极大地唤起了某些接受者的索隐热情。所以不少索隐者们凭借自身所搜集的资料,把《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与现实生活相互比附,从而探索出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茅盾曾评论说:“平心论之,索隐派着眼于探索《红楼梦》里政治、社会的意义,还是看对了。”[9]可见“索隐”作为一种专门的文学批评方式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对小说、戏曲等本事的索隐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并为人们认识《红楼梦》的主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索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本的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就其字面意义理解而言,“索隐”即专门研究隐约其辞的文本,对文本中“隐”的内容进行索解,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弦外之音,抉微索隐[10]。同时,索隐批评只是通过考察作品内容以指明作者具体的创作意图或目的,较少将气力放置于研究文本的艺术表现或创作规律,比从汉字“离合”角度分析文本这种方式具有更强的主观臆断性。创作者们对本事的故意隐藏,对内心情感的晦涩表达,为索隐方法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虽然从“离合”角度或“索隐”这一方式对文本进行品鉴可使读者收获意外之惊喜,了解到作者笔墨之下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这是每个读者都拥有的阅读权利,但不能让自身的想象力任意发挥,否则只会是缘木求鱼,从而导致将原著拆解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