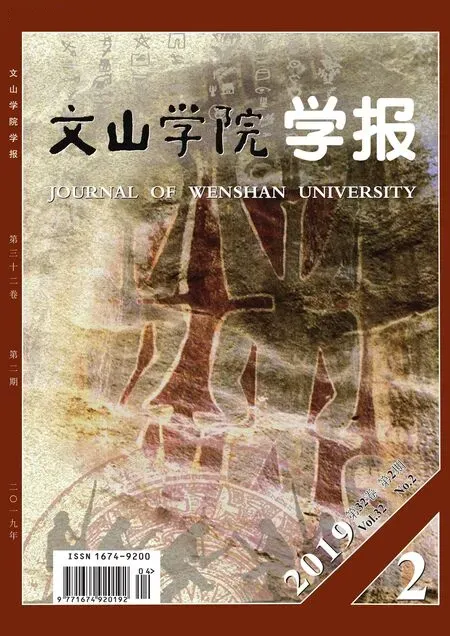“书同文”:对于滇东北次方言苗文通用文字统一使用的反思
叶洪平,汪 倩
(1.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2.云南财经大学 物流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作为文化的象征之一,文字不仅可以记录历史、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也有利于社会的管理、群体的认同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一个民族和群体来说,文字的有无关系到了他们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高低,同时也关系到个体对外交际范围的大小。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由于社会发展与地区地理位置的限制,没有文字的民族尚多。位于滇东北苗族支系的大花苗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大花苗主要分布在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处,在滇中、滇南亦有分布。由于其主体主要聚居在滇东北地区,因而大花苗的语言被称之为“滇东北次方言”。该种苗族方言由于各种原因,在历史上形成了三种文字,即“老苗文”“拉丁新苗文”以及“规范苗文”。
在基督教传入滇东北之前,该地区的苗族社会被视为一个“化外之地”,能识汉字之人极少。直到传教士来到该地区根据苗族衣饰上的花纹并结合当地的方言和拉丁字母以及苗语音调(声母)创制了苗文——“波拉德文字”,即现在的“老苗文”,大花苗才有了自己的文字。随着社会的变迁,政府和当地的知识精英为大花苗先后创制了“拉丁新苗文”和“规范苗文”。由于教会在当地的影响深远、当地的信徒众多,加上基督教在传教和布道过程中对于“老苗文”的使用颇为重视,因此“老苗文”在苗族地区的使用范围广,运用的人数多并且影响久远。时至今日,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滇东北地区的大花苗群体中仍然广泛使用这种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拉丁新苗文”和“规范苗文”也同时在大花苗中推行。这三种苗族文字的并行使用造成了该群体中对于文字运用的茫然,究竟该如何对苗文进行统一以及使用哪一种或者如何融合这三种苗文形式值得考虑。本文的出发点即在于此,笔者在文中将结合中国文字上的“书同文”的推行及影响从“认同”的方面给予相应的回应。
一、秦朝“书同文”的实施与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文字运动,秦代所施行的“书同文”政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及团结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的文字历史甚为久远,在“书同文”之前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字,如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时代的文字、六国文字以及秦系文字[1]40。即使每一个统一的朝代都有数种不同并行使用的文字,但在全国统一使用的字体却极少出现。商代所用的文字主要有甲骨文与金文。虽说这两种文字同时在商代流行使用但二者在“字体上有不同的特点”[1]42,且字体的写作方向也存在差异,甚至相反,不固定[1]45。到了西周春秋时代,字体的使用情况仍然如此。此时虽主要流行的文字是金文,但甲骨文和盟书仍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的发展与习得依靠于社会剩余资源的支持,战国之前社会物质产量普遍低下,中下层社会居民大都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文字的使用自然仅限于上层贵族。到战国时,社会有了相应的发展,社会资源的剩余情况较以前提升了许多,因而个体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机会也随之增大,民间使用文字的范围也逐渐有所扩展。
众所周知,文字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对于那些在行政和社会管控上有独立行使权力的国家区域中也是一样。东周战国时期随着各个诸侯国的独立发展,出现的正是如此情况。各国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风俗习惯存在差异,因而在字体的写作上差别甚大,流行的字体形式各样,如金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文、简帛文字、秦系文字等形式。即使有几个诸侯国使用一种文字的情况,但是普遍来看仍然存在不同之处。在语言相同的地区,文字的差异性对于民间个体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几乎不大,然而在政治上却形成了极大的困扰。一个在语言上、习俗上以及文字上都存在极大差异的国家,它在政治上的统治与社会管控更是难上加难。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所面临的便是如此一些困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结束了由于诸侯争霸导致的常年动乱的局面。尽管秦始皇在政治和军事上实现了统一,但由于诸侯割裂的时间前后达数百年,因此秦朝各个区域在文化上的隔阂一直存在,即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言的“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社会状况。这种差异并不像政治和军事一样会立刻随着秦朝的统一就实现共融,除非政治上的强制,否则只依赖于民间的流动和诉求,它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作为社会最高管控者的秦始皇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必然要进行文化上的统一。所以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才有如此记载:“一法度衡石丈余,车同轨,书同文字”。在文字的统一方面,自然是值得考虑的事情。
陈梦家先生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字,或为自造的,或为承袭别一民族的。……中国历史的通例,常是武力强盛的异族接受被征服民族的文字,而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较征服民族高。”[2]这一点对于朝代的更迭后统治者在文化的选择上亦是如此。虽然秦国的文化较之于其他诸侯国的文化不一定为优,但秦国统一了全国,成立了政治管理部门,而且这个时期又是处于刚统一之后,对于树立秦朝的权威和认同至关重要。选择秦国自己的文字即隶书(小篆)作为全国的通用文字无疑最为适合。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戌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其他对秦朝“书同文”的记录大抵如此。从中可以看出,为政治服务是秦始皇实现文字一统的原因之一。在完成“书同文”之后,这一政策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等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秦朝的当政者来说,“书同文”使得之前的文字得到简化,易于书写,在民间社会得到普及和传播。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官狱职务繁”,使用不同的文字进行书写过于复杂,因而“书同文”可以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繁琐。使用隶书,其不但字体简易,且便于书写。这极大地提高了当政者的行政效率,同时也使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务时更便利。秦代的“书同文”作为中国汉字规范的最要一步,为后来汉字的逐渐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应该且已经被其他研究者所注意到的。然而,还有一方面需要提及的是“文字”与“认同”之间的关系。
历来研究族群和民族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于“认同”颇为重视。但是他们多以个案的阐述来窥探某一个特殊的群体的认同,对于多元化的民族群体甚少有人注意。中国的民族构成复杂,地域广阔,因而不同地方和民族在语言使用方面多显复杂且各地风俗各异。如果仅仅以语言作为彼此之间的沟通手段和桥梁,恐无进行交际的空间。若以同一种文字作为彼此的交流工具,无论语言的差异如何大,只要书写出来,两个交流的对象之间的沟通便会进行下去。对于个人的认同来说,亦是如此。虽然单元个体对于国家整体的一些方面仅凭借自己的了解可能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但通过文字传递,便能给予相应的认识补充,这对于国家整体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某一个个体,不识汉字,也可以由其他那些懂得自己语言又知晓汉字的人转述。这不但能够使得个体认识不同的世界,也能促进个体认知的提升和视野的扩展,同时使得群体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更加频繁,从而为自己在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
或许“书同文”对于政治治理、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的影响与上述观点相差不远。“滇东北次方言苗文”的创制、发展与统一使用的目的都在于此。然而,“书同文”在当今滇东北次方言苗文的统一是否适用呢?欲回答该问题,必须阐述滇东北次方言苗文的发展历史和几种字体形态及其使用的争议。
二、滇东北次方言苗文的发展与几种形态
作为苗族的一支,大花苗的历史颇为悠久,然而在文字方面一直是其“短处”之一。虽然历史上苗族的其他支系曾出现过文字,但是这些文字是否为苗族自己所创而不是其他群体的借用至今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大花苗来说更是如此。在大量的史籍中至今仍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大花苗存在过相应的文字。许多学者认为大花苗曾经拥有过象形文字,并引用各种县志作为证据[3],然而他们所忽视的是自己所引用的县志多出自于民国时期,此时所记录的大花苗文字即老苗文仍是外国传教士在清末来到该地区后才逐渐形成的一种拉丁拼音文字。
苗族过去虽有文字使用的记载,但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迁徙过于频繁,进而造成散杂的分布格局所致。自从先秦时期开始,苗族就开始从黄河向南大量的迁徙,经过历代的变化使该民族的分布杂乱,彼此之间的联系交往弱,从而造成发展不均衡的局面。所以就算是某一支系的苗族拥有文字也只能在内部甚至本地区使用。
另外,苗族与其他民族相比稍显自闭,“新中国建立前,苗族是不与异族通婚的,否则便认为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4],与异族通婚的苗族会遭到其他人的唾弃,甚至会被赶出寨子。就连吕思勉先生在撰写《中国民族史》的时候都感叹苗族“派别至繁,彼此不同婚姻,故不能团结。其于汉人,有深闭固拒,不肯通婚者;亦有慕与汉人结婚者。然汉人多鄙视之,不愿与通婚姻。今贵州男子,有娶苗女者,犹多为亲族所歧视;甚至毁其宗祠。至汉女嫁苗男者,则可谓绝无矣。以是故,其种类颇纯,迄今不能尽与汉人同化。”[5]加之其“迁入之地,又多是荒僻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阻碍和延缓着生产力的提高”,“居住的分散,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严重地影响着苗族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迁徙使苗族各部之间彼此隔绝,少于交往。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不同,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导致相互间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支系多、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样化的现象。”[6]因此“苗族既难团结,习俗自生相异……半载以外,视如路人。老死不相往来,乡音亦随环境而改。同枝连理,几至判若二族。若是者,非血统之各特殊,实环境所役使”[7]18。以上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苗族文化的相对“落后性”,本民族之间以及与汉族或彝族等等民族交往甚少,文字的出现更是无从谈起,加上“自闭”的性情,“不识字苗民,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以上”[7]39。
较之于整体苗族的上述情况,大花苗更是如此。他们“与他种苗族无婚姻关系,其性格孤僻,不与外界接触,故生活完全形成一种独立形式”[8]。因而该族群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也是如同其他苗族支系一样是在晚近时期。但是,从现有的文献和影响程度上来看,大花苗的文字较之于其他苗族支系则显得更加的突出。
大花苗最早的文字,被称为“老苗文”,是由清末民初传教士和当地的汉族、苗族等一起创造的拉丁文字。由于这套文字是在外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主导之下进行创制并改善的,所以也被称为“柏格理文”或者“波拉德文”。这套文字是创制者“从大花苗的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借助于祖先古歌、故事遗传文字失而复得的神话,(因而)苗民相信这套文字是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识别和恢复出来的。”①加上基督教采用一系列的措施办法在滇黔川等地区进行传播,又着重以学校扩大影响,当地的教会及其势力颇大,学校的分布亦广。据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显示,“计在黔滇境界有三十七所,川境有十五所,共计五十二所,苗夷子弟培植成功为数甚多。”[9]由此可见,“老苗文”在大花苗中的影响久远,同时也获得了大花苗的认同。时至今日,在大花苗社会中仍在广泛使用。
“新苗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考虑到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由国家民委组织了一批专家来为他们创造的文字。“规范苗文”则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滇中地区楚雄武定的部分大花苗知识分子与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为了改善“老苗文”,克服“老苗文”音位符号不准、一音多字的问题而创制出来的“苗文”形式,被称为“滇东北次方言云南改革版苗文”或“楚雄规范苗文”与“滇东北规范苗文”。
以上是现在在滇东北大花苗中使用的三种文字形式及其创制与发展的情况。从其产生和发展来看,不论是“老苗文”或者“规范苗文”还是“新苗文”都有自己特定的意义和社会背景,因而在一些不同的苗族地区在使用“苗文”方面也存在差异。滇东北次方言苗文的三种形式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内由不同的人创制和改善。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和自尊心、自豪感的象征,在不同文字创制的地区都有不同的人在使用。目前的大花苗社会中这样的文字使用状况仍然存在,且情况愈变复杂。
“老苗文”是由中底层群体开始创立的,因而具有极强的群众基础。该套文字的构造与大花苗社会中的生活日常以及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简单易学,同时又在教会中通过教会书籍和教育的宣传,所以在很多大花苗聚居地区都在使用。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屡次遭受到打击,甚至在官方的各种宣传中接近消失,但在大花苗的民间社会中仍然薪火相传。至于“拉丁新苗文”,虽然得到行政力量的推广,但是创制该套文字的人对于大花苗缺乏一些日常生活的体验,加上后来的推广力度不够和时间周期不足,使用的人数较少,至今为止学会和使用的人并不多。“规范苗文”是在“老苗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错误较之于“老苗文”更少,音字之间的联系也更强,但“规范苗文”难学习,且缺少一种如同教会一样具有跨地区的推广力量,因而只能在“规范苗文”的创制和修改地区即楚雄的部分大花苗地区使用。对于那些较为注重文化传统的大花苗来说,他们依然遵守传统的书写和认知范式,即使用“老苗文”来进行自我的认同以及对他人的教学。
三、反思与讨论
前文已经对秦始皇的“书同文”与大花苗各种文字的创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秦始皇“书同文”的前提是秦朝统一之前各个诸侯国都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象形文字,虽然在书写上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字体的构成上大同小异。秦朝的统一、强有力的政治推广和民间的自我需求为“书同文”的实施赋予了更加强有力的政治与群众基础。秦朝的“焚书坑儒”的推行,使得各国文字遭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同时也推动了“书同文”的实现。按照唐兰先生的说法这实际上就是:“新文字的发生,根于事实的需要,因为产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增加了无数的新语言,只用图画文字和引申假借是不够表达的,那时的聪明人就利用旧的合体文字、计数文字、声化文字的方法来创造新文字。这种新文字一发生,就很快的发展起来。”[10]78
苗文(特别是老苗文)的创制和实施与“书同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在“老苗文”创制之前,大花苗是没有文字的,但在大花苗群体中又具有读书识字的需求,因而“老苗文”的推行实际上是大花苗的自我需求的满足,这与“书同文”的前提一致。其次,与隶书和小篆一样,“老苗文”是从苗族社会生活中和神话传说中来进行创制的,简单易写,对于没有文化基础的苗族个体来说学习起来甚是容易。最后,与秦朝利用高效的行政力量推广一样,“老苗文”在教会的组织下进行传播和推广,遍布众多大花苗的聚居区。而且由于“老苗文”创制地区的发展,其文化地域成为“西南地区苗族文化的最高区”,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这对于“老苗文”的推广作用甚大,在民间的使用范围广泛,逐渐成为了大花苗的文化自信与自豪以及自我认同的象征符号之一。正是如此,后来的“新苗文”以及“规范苗文”(即使是在老苗文的基础上改制而成)失去了“老苗文”的传播基础,并没有在大花苗地区广泛的使用,因而这两种文字的影响远远逊于老苗文。甚至在2018年1月在威宁召开的“滇东北次方言苗文通用联席会”会议上将老苗文认定为大花苗的通用文字。
但是值得反思的是,老苗文真的能够如同隶书那样能够在“书同文”的开展下得到统一使用吗?“书同文”的实现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沟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爱国标志,亦成为学人宿儒们的研究方向之一。较之于拼音文字,中文不仅消除了中国各个地区不同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且实现了古今对话的时空交流,这是拉丁文字所不具备的功能。唐兰先生认为:“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学习时虽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10]9
然而,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甚至在近代以降,在中国的许多其他没有文字的民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采用形音一致的拉丁字母来创制少数民族的文字,这无疑在中国的民族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在“新苗文”的创制中早有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全国创制拉丁苗文时,由于不同地区的苗族方言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导致语言学者们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方言来为不同方言区的苗族创造文字,最后形成了多种苗文即“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等并行使用的情况。由于形音一致,因此在不同苗族语言地区不能进行相互的沟通与交流,这也就丧失了“汉字”的跨语言与地域的交流功能,对于苗族支系之间的认同无法起到巩固的作用。
“老苗文”作为目前有直接证据证实的,是由苗族参与创制的文字,它不仅成为了大花苗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对生活在大花苗附近的其他民族亦有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苗文”使得大花苗从以前文化被动的角色中转向了文化传播的主动角色,这对于大花苗的民族自豪感的产生和提高具有关键的作用,自然很多大花苗群体愿意使用它。按照同样的逻辑关系,“规范苗文”是在滇东北地区改善和推广的。该地区的大花苗也同样存在一种文化自豪感,接受和使用都存在合理的一面。然而现在却要使之成为一种文字来使用,其中必定存在相当多的困难。
“滇东北次方言通用文字”既没有如同“书同文”那样的执行效率,也没有像中文那样形音分离的功能。加之上文所分析的文化自豪感在群体中的相互冲击,更加使得“滇东北次方言通用文字”的统一难上加难。若要使得滇东北次方言的文字得到统一,这两点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
注释:
①参见沈红.活在苗寨的字符.载于杨华明编,苗文课本·第一册.未刊稿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