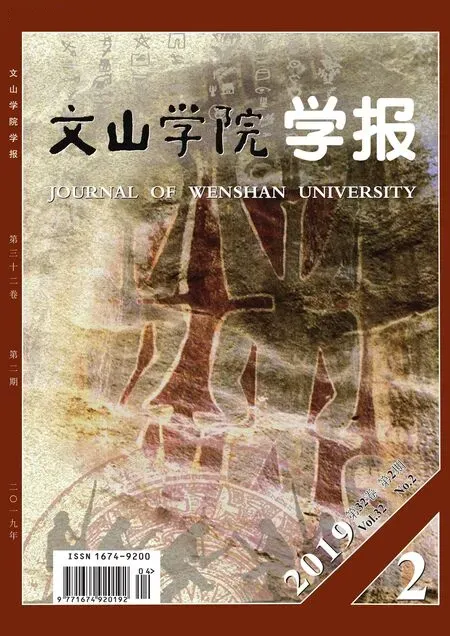清后期西南边疆民族治理的历史审视(1851-1911)
马亚辉,陈逸飞
(1.百色学院 民族研究中心,广西 百色 533000;2.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清朝后期的西南边疆可谓多事之地,仅发生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大规模起义便有两次:一次是咸丰元年在广西金田村暴发并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一次是咸丰六年暴发且遍及整个云南的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此外,滇黔贵三省的各种小规模民族起事和自然灾祸更是数不胜数,连绵不绝。面对西南边疆非常严重的各种民族问题,日渐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治理西南边疆过程中难免显得左支右绌,力不从心。笔者对清末西南边疆的民族问题疑惑颇多,于是利用闲暇查找相关资料,发现已有的关于西南边疆民族治理的论著主要集中在清朝中前期,主要论文有马亚辉、王巧娟的《清前期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动态考察》[1],马亚辉、滕兰花的《乾隆朝的“一视同仁”与西南边疆封建盛世的形成》[2],马亚辉的《“守成”理念下嘉庆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政策探析》[3]等,而有关清朝后期西南边疆民族治理的专门研究是非常少见的,尚待深入。近来检阅史籍,不时提笔,成此小文。现将不成熟的观点予以提出,仅为抛砖引玉。
一、民族起事原因:封建制度下的田产高度兼并
关于清后期民族起义的原因众说纷纭,总的来看主要是清朝政府对百姓剥削过重,而杜文秀领导回民起义的原因则认为是清朝地方政府故意挑拨回汉矛盾所致,这些观点固然有合理成份,但细研史料发现,起事原因貌似别有隐情:即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进入封建时代,内地流民开始大量涌入,少数流民抓住时代转型的契机逐渐演化为地主,开始和原有地主对西南边疆的田产进行高度兼并,造成人地关系紧张,致使大量百姓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中无地可种,无以为生。简析如下:
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后,在曾经的土司辖地推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治理模式,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加速,西南边疆开始全面向封建社会转型,内地民人也开始大量流向西南边疆,是为“流民”;开荒种地,转为“客民”,又称棚户、棚民等;后来少数客民通过土地典当,勾结官府等手段,在一百余年间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曾经的客民转变为“封建地主”,这是一个漫长的土地兼并过程,且汉族地主与少数民族争夺土地的现象在咸丰年间依然存在。咸丰五年,据御史陈庆松奏:“近来云南省永昌腴田,尽归民人,将回子驱逐徼外,失其故业,往往勾结夷人,沿边滋扰。自曲靖至永昌,上下二千余里,民回杂处,回子每思报复。”[4]这则史料的观点显而易见,汉回互斗的根源是田产的归属问题,再说得直白一些,是采用不正当手段,占据大量田产,令回民无地可种,无以谋生,地方官府对此不但无视不管,还与汉民地主沆瀣一气,坦护汉民地主阶层,因而导致回汉时常械斗,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普通汉民与回民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在《腾越回民檄文》中说得很清楚:“回汉在腾,和睦素著;诗书之士,砚席与同;田峻之家,畔耕有让;同心贸易,曾分管鲍之金;把臂订交,只少朱陈之雅,何尝此疆彼界,何尝别户分门!”[5]但是由于汉族地主与官府狼狈为奸,欺压良善,回民生存维艰,被迫揭竿而起,这点在檄文中说得非常清楚。
同治朝统治者开始从高层角度对回民起义的原因曾进行反思,云:“现在云南、陕西回匪,为患甚巨,其始亦起于细微,皆地方官办理不善之所致。”[6]1057又说:“滇陕汉回互斗,即因肇衅之初,该地方官吏不能持平办理所致。”[6]1106后来再次强调:“滇省启衅情形,始于楚雄府属之石羊银厂。有临安人与回众互争,地方官不能妥办,成于省城汉人不分良莠,见回即杀,由此激生事端。”[7]545同治朝统治者的三次言论都是把回民起义的根源归结为地方官员办理不善,其观点显然错谬,真正的原因是清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严重兼并使得大量的少数民族无地可种,百姓无法生存。在漫长的土地兼并过程中,从内地进入边疆的流民通过租种或典当土地等途径转变为客民,一部分客民通过土地典当,把土司与土民的土地据为己有,进而转化为地主阶层,使得众多的回民,大部分客民,边疆的少数民族,以及继续进入边疆的流民无地可种,最终致使官民矛盾激化,发生大规模的民族起义。
回汉矛盾中的汉人是指官僚地主阶层,而非普通汉民,《清穆宗实录》中的一条史料再次很好地诠释了“汉回互斗”中“汉”的指称对象。同治朝统治者说:“云南省自汉回构衅,仇杀日久,汉人之官绅士庶,惨遭杀戮者,为数甚多。”[7]255其中提到被杀戮的人多是“汉人之官绅士庶”,此类人为既得利益者,是当时的官僚和地主阶层,而非贫穷的流民或普通的汉民,说明回民以及各族人民的起义反抗的是西南边疆的官僚和地主,下层的汉民和回民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此杜文秀领导回民起义时,也有许多的汉民参与其中。
田产争端不只是发生在云南,而是遍及整个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这种土地兼并现象在乾隆时期便已出现,嘉庆时期已经十分严重,道光时期达到顶峰,咸丰时期汉族地主与西南边疆各个少数民族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也就不可避免。
二、清朝政府对起事的处置:在偏见中剿抚兼施
道光时期是西南边疆民族起义的酝酿阶段,后期的种种迹象表明,起义已经如箭在弦,蓄势待发,而咸丰和同治时期是民族起义的暴发时期,全国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声势浩大。综览《清文宗实录》和《清穆宗实录》中关于西南边疆的史料,基本就是一部清朝政府镇压西南边疆民族起义的记录。
清朝政府对回民同胞存有偏见。《永昌回民檄文》中如是说:“无如守土官吏歧视回民,不询理之曲直,不思人之众寡,惟恐杀回不力。今为回民者,人人自危矣!”[8]同治朝统治者也曾云:“滇省回汉,酿祸已深,与粤省客土情形,究属尚有区别。滇回异教,本与吾民不类”[9]。早在咸丰时期,为妥善解决回民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御史陈庆松就奏请清文宗“饬滇省大吏抚辑民回,不宜过分畛域”,即不可用偏见的态度来处理回汉问题。清文宗对陈庆松的提议表示赞同,曰:“国家一视同仁,民回皆系赤子,地方官弹压抚绥,本不应过分畛域。”因此,“饬地方官吏,遇有民回斗案,必当秉公审办,固不可宽纵养奸,亦不可偏私激变,总期戢暴安良,弭患未萌,方为妥善”[4]。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思路是正确的,但忽略了西南边疆各个民族与汉人地主之间难以调和的田产矛盾,其一视同仁的治边理念在既得利益的官僚地主面前根本无法付诸实施。此外,自同治以后的三代帝王被慈禧掌控,一生听命于他人,无可奈何而碌碌无为,皇帝的命令等同于空文,因此《清穆宗实录》、《清德宗实录》、《清宣统政纪》中记载之事实际为慈禧统治集团之言行,将慈禧统治集团在不同时期分别称为同治朝统治者、光绪朝统治者、宣统朝统治者更为合适。再加上清末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民族起事只能是武力镇压为主,拉拢安抚为辅。清文宗云:“云南汉回互斗,办理之法,全在分别良莠,不分汉回,剿抚兼用,不可稍存私见。”[10]
清末政府对西南边疆政治形势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偏差。光绪二十二年,奕等人纂修《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丛书》,清德宗为书作序,云:“今滇黔清谧,维彼回、苗以生以养,朕惟抚之安之,俾与编户氓庶敦礼善俗,为我国家不侵不叛之民,永绥于南服,抑朕所以迪耿光而继志事者也。”[11]光绪朝统治者对西南边疆的政局过于乐观,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虽未再发生大型起义,但社会依旧动荡不安,根本谈不上清谧。光绪元年,越南人黄崇英,伙党千余,进入云南开化,经岑毓英檄饬总兵何秀林等剿灭[12]113。同年,中缅边境又发生“马嘉理事件”,后来川滇黔三省接壤地方又有“游勇土匪,勾结滋扰”[12]296,“粤西罗城县三防地方,客土争田,各招滥练械斗”[12]363等。此类动乱贯穿光绪朝之始终,因相关史料过多,本文仅列举一二。光绪四年,“广西贺县、岑溪、藤县、苍梧、博白等处,均有土匪聚集滋事”;光绪十年,贵州遵义县属金盆栏地方,“有川匪朱葓竹、即李麻二纠集匪党,谋为不轨”[13]489。光绪十二年,“贵州近有匪徒拐卖人口”[14]171。光绪十七年,“贵州黎平府属苗寨滋事”[14]1013。光绪二十年,“云南永北厅属鱼硐坡等处匪首丁洪溃等,勾串番夷滋扰”[15]325。光绪二十四年,“以不守营规,革贵州黎平营守备萧庆祺职”,“以假冒官职,革贵州保升游击李荣贵职”[16]417。光绪二十九年,周云祥在云南临安率众起事[17]。光绪三十一年,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滇省镇边厅土民滋扰[18]209。光绪三十二年,云贵总督丁振铎又奏,上年川境巴塘之变,滇省维西厅属僧夷亦因之而动;同年,署贵州巡抚岑春蓂奏报,都匀府属苗民因派捐聚集,闯入府署闹事,旋复分党报复团首,抢杀教民[18]400。以上仅列举边疆民族小型起事之一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很不太平。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问题遍及官场、治安、文教等各个领域。光绪二十年,有大臣奏报贵州盗风日炽,抢案甚多,近则省城竟有明火强劫,伤毙人命之事。光绪朝统治者认为贵州在战乱之后,好多游勇散练,流而为匪,乃势所必然。但讳抢为窃,纵盗殃民,捕务废弛,却殊堪痛恨,因此命潘霨严饬所属,遇有抢劫案件,即行上紧缉拿,不得稍有讳饰[14]92-93。光绪三十三年,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奏“滇省学务腐败已极”[18]613。光绪三十四年,“云南边境猝有匪党勾结生事”[18]812。种种迹象表明,清朝已是行将就木。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动乱”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反抗清朝政府与地主阶层压迫的起事。再如光绪四年,云南临安府属纳楼土族普保极等率领回民起事;光绪七年,广南府属王泽宽与各寨夷民反抗官府压迫等。
光绪朝统治者对民族起事同样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令地方兵练,严密防堵,会合兜剿,务将直司迅速平息,以靖边圉;另一方面晓谕各属土夷人等,各安生业,不得参与起事[19]215。光绪三十年,有起事百姓进入贵州境内,光绪朝统治者在命令军队认真扼剿的同时,还要求“善驭苗民,毋任勾结,致贻后患”[18]110。光绪三十二年,贵州都匀的少数民族起事,光绪朝统治者“分别剿抚解散”[18]542。只要遇有边疆民族起事,光绪朝便派军征剿。光绪十二年,云南盏达土司所属百姓起事,云贵总督岑毓英派军扑灭。所有出力官员,也受到了奖励[14]193-194。宣统二年,云贵总督李经羲奏报思茅厅猛遮叭目召康亮久为边患,于是征集附近土兵进剿。同年,归顺滇边地方又有起事,同样派遣就近营队驰往剿办。宣统三年,李经羲又电奏:“腾越陇川野夷,拒戕弁兵,分别剿抚。”[20]995不难看出,“剿抚兼用”是清末政府解决边疆民族起事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政策,这项政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回民起义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不少起义将士被政府招抚后加入到镇压起义军的行列。
三、光绪朝的休养生息:蠲免赈恤和革除积弊
《清文宗实录》和《清穆宗实录》中的西南史料,基本就是“平匪”实录,鲜见关于西南边疆各族百姓休养生息的记载,而《清德宗实录》中关于西南边疆的史料有所不同,虽然以记录边患为主,但也出现了大量发展经济、治理官吏的史料,因此,浏览这些内容,感觉清朝又回到了乾隆时代,说明清朝政府扑灭西南边疆的回民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后,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开始重视民生问题,但民族政策的内容并未跳出前朝窠臼。
整饬边疆吏治,选贤任能,撤换平庸。一是对在镇压西南边疆各民族起义与平定边疆动乱中出力的官吏给予提拔。光绪三年,云南云州有不法人员张重阳扎踞大寨,四出虏掠,代理知州韦勋承则带领团众平乱,所有出力人员皆得到提拔任用;二是撤换能力不足的官吏。光绪三年十月,云南镇沅厅同知高国鼎、维西通判孙国瑞等人则因年老力衰,才识平庸,人品猥琐,心术不端等原因均被罢免后去充当教职[12]808。教育乃国家要务,有着引导全国民众思想的巨大作用,却由不良之辈来从事教职,清朝江山岌岌可危。与其说清朝覆灭于武力,不如说覆灭于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光绪四年,又有云南盐运使衔补用道李应华,办事颟顸未谙政体,不胜监司之任,著以通判铨选;石膏井提举辛传注,才识平庸,征课不力,著以府经历县丞降补;候补同知黎厚德粗率藐玩,操守平常;补用知县刘永华心地糊涂,行为乖谬;孙绾荣卑鄙狙诈,不守官箴;白盐井大使吴盛琛营私玩公,百端欺伪;试用州判毛华新行止卑污,有玷冠裳;楚雄县教谕尹建中节行有亏,士林訾议。以上人员均被即行革职[19]280-281。黔桂两省官场同样如此。光绪五年,贵州巡抚岑毓英奏:“黔省人员拥挤,流品混杂,请仿前福建巡抚王凯泰条奏,酌量裁遣。”光绪朝统治者下旨云:“该省吏治营伍,即著妥定章程,认真整顿,务须斟酌尽善,实事求是,以期经久可行。”[19]499
光绪朝还遇灾必赈。因广西遭受兵燹多年,光绪四年,因粮食欠收,光绪朝统治者下令“蠲缓广西崇善、左、养利、永康、临桂、恭城、柳城、来宾、淩云、武宣、奉议、永淳、迁江、灵川、兴安、永安、贵、平南、上林十九州县”[19]5的钱粮兵米。光绪七年正月,蠲免贵州贵筑县、兴义府、八寨同知、册亨州同、经管水银等厂历年未征课项[19]821。光绪十一年,广西省城暨梧州府等处,因五月初旬雨水过多,河流骤涨,房屋倒塌,淹毙人口,河流沿岸的灵川、兴安、全州、阳朔、平乐等州县均遇水灾,护抚李秉衡拨款开仓,办理抚恤,光绪朝统治者又“分饬各属确切查勘,认真赈抚,务令实惠均沾,以拯灾黎”[13]965。光绪十三年七月,广西融县南城外市民失火,延烧民房413户,其中贫民126户。光绪朝立刻“饬属详查被灾户口,妥为抚恤,毋任失所”[14]332。光绪十六年,广西灵川等县被火,郁林州等属被水,云南安平蒙化等处被水,广西苍梧等处被水,光绪朝统治者皆给予抚恤[14]860。光绪十八年,蠲免贵州兴义府属水灾地方应完秋粮[15]94。光绪二十五年,蠲缓广西全州被灾田亩兵米钱粮[16]768。蠲免钱粮。宣统三年,缓征云南宜良县属歉收田亩宣统二年应征钱粮,豁免云南恩安县属被灾地方宣统二年应征条粮,永豁云南昆明县属营舍税关购用田地额征钱粮。
此外,光绪朝革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种积弊。光绪七年,云贵总督刘长佑等奏请革除苗疆积弊:“除兵米地段夫役另案议结外,拟禁刑钱专擅,以除土司之弊;拟改粮弁章程,以除屯军之弊;拟增州县经费,以除吏治之弊;拟设义塾,添学额,以除陋俗之弊。”除“添设清江等厅学额之处着礼部议奏”外,其他各条皆得到允许[19]830。光绪十年,有人奏报广西梧州关税加费过多,请饬永远全部裁减,又人奏报广西积弊太深,急宜剔除。光绪朝统治者要求“该省积习相沿,必应严查禁革,著张之洞、潘鼎新按照所奏各条确切查明,将一切弊端,悉行厘剔,毋得有名无实,是为至要”[13]582。
打击贪污腐败,减轻边疆各族百姓的税负。光绪五年,给事中刘曾奏报广西税厘繁多,商民俱困,请饬裁减,“广西梧州府向有额征府税,即该府于正额外,巧立缉捕经费名目,以供馈送上司之用,所余尽饱私囊。厘局众多,弊端更大,局员等蒙混侵吞,差役勒索阻遏,以致物价腾贵。又该省各府州县地丁钱粮,竟敢私自加增。泗城府三属尤甚,纵容书役,朘削百姓,大为民害”[19]563。光绪朝统治者认为粤西地瘠民贫,岂容重征苛敛。所奏如果属实,亟应严行查办,并命人确切查明,如有上述情弊,即行禁止。
西南边疆经过回民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可谓久遭兵燹,地瘠民贫,吏治废弛,地方官吏依然沉湎于积习,一味因循。清穆宗希望西南边疆的官场能有所改变,要求封疆大吏必须“整躬率属,破除情面,随时大加惩创,方足以挽颓风”[21],并重用有能力肯奉献的官吏到边疆任职,但由于皇帝幼年继位,慈禧大权牢握,以致清朝的最后三位帝王始终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清朝官场腐败依然如故。光绪六年,又有一批不良官吏被降职或革职。云南前署寻甸州知州候补知州蓝春田办事颟顸,难膺民社,著降为府经历县丞铨选。禄丰县知县杨逢春居心鄙诈,不守官箴;候补州同秦浚任性妄为,不堪造就;候补县丞申维新藉差需索,肆无忌惮;前署建水县典史补用县丞李炳文贪鄙性成,难期悔改;云龙州吏目刘秀彬举止乖张,声名甚劣;禄劝县典史薛庆祥不知检束,罔协舆情,均著即行革职。元江州吏目黄之容年力就衰,办事迟钝,著勒令休致,以肃官方[19]580-581。同年,广西试用同知元忍容采办土布,浮开价值,置备他物,亦多不实不尽;试用同知黎桢携子入营,纵容舞弊,并有浮开米数,及招摇需索情事,实属居心贪劣,胆大妄为。元忍容、黎桢均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19]604-605。关于清末官场腐败的史料极多,光绪朝尽力整饬,但仍难挽清朝颓败之势。
四、清末的土司治理:改土归流与兴学安边
道光至同治时期西南边疆动乱纷纭,加上皇宫内部勾心斗角,使得清朝统治者对西南边疆的土司无暇治理,直至光绪时期,清朝统治者才得以分出精力来关注土司问题。
光绪朝继续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光绪十一年,广西土田州岑氏“因分党仇杀,土民流离转徙,日不聊生,经刘长佑奏交部议改土归流”。在改流中出现一些问题,据称“该州土民、土目饮憾含悲”,光绪朝统治者要求查找改流未尽事宜,是否有办理不善之处,应否量为变通等[13]1019。光绪十六年,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州土司章天锡,两世私袭,横行无忌,扰害地方,种种不法。政府出兵征剿,最终将章天锡拿获正法。同年又奏请将北胜州土州同属境改土归流[14]810。光绪十七年改流完毕,移设营汛官弁[14]989。光绪三十四年,都察院代递云南耆民等呈称土司暴虐,惨无人理,请求改土归流,以救民生。以前遇到此种情况,清朝政府皆改土归流,但此时“所以不敢轻于举办者,一恐兵力未敷,一恐财力不足”,为今之计,惟有革除汉官规费,慎选守令以清其源,赶紧查请承袭以安其心,严密稽查,防范以伐其谋,并拟整顿防营,开办征兵。庶缓急操纵,得牧控驭之益[18]848。
宣统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川藏交界,主要是对高日、春科、德格等土司改土归流;二是在西南边疆。宣统二年,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请将“永昌府属镇康土州改流,拟请添设知州一缺,巡检二缺,分司治理”。
整顿土属,兴学安边也是清末政府对土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三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整顿土属,必先造就土官”,拟饬就土官子侄中,按年选送四人或六人,来省就学,授以法政一科,使有政治思想,将来各属土官,即以毕业最优者分别承袭。光绪朝统治者将此事下部知之[18]702。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土司学堂在广西桂设立,招收土官子弟,学徨由各辖有土属的府、厅、州督同承审州县,就土官宗族中择年少陪敏粗通文字者按年选送,学费由所管府厅州县各官族筹办,不准摊派土民。辛亥革命后停办[22]。
宣统朝存在三年左右,继续在土司地区推行近代化教育。宣统元年,云贵总督沈秉堃奏:“滇开化较晚,沿边土司,地数千里,往往因语言习尚不同,与内地人民隔阂,非先之以教育不为功。查滇边土目辖境,惟永昌、顺宁、普洱三府,暨镇边直隶厅紧接外域。今以兴学为安边计,自以从三府一厅办起。”但考虑到边境土民混沌未凿,即授以初等小学,恐亦难入,认为开设教人识字的学塾较为适宜。沈秉堃称此为“同化”,云:“既以同化为宗旨,自应以国文为主科。”先之以音读、讲解、习问,继之以钞写、默写,终之缀字、成文;其补助科目,则以习礼、谈话、算数、体操、唱歌、农业六者为限。前三者改良其习惯语言,锻炼其心思脑力,后三者俾其服从规律,陶淑性情,增益智识,而尤在随时觉以尊亲之大义,作巩固国防之用。至身任土目者,虽年长难学,而宗族子弟可教。惟土司族土民其分素严,沿边土民学塾,土目之宗族子弟,必不乐入,不得不另筹办法。省会学堂较外郡规级略备,令其附学,量程度入相当班次,来学则优遇之,毕业归则照章奖励,更奖扁额。附学必置之会垣,俾略瞻军界政界之设施,习闻通人正大之言论,以激发其忠爱。惟学非财不办,沿边土司有限,其宗族子弟来学者,由公家供膳食操衣书籍,甚或增教员,开新班,费属无多。至三府一直隶厅土民学塾,需款甚巨,若责土司就地筹措,势必骚扰,拟照川滇边务大臣关外学务局成案,由司库边防要需项下按年提银二万两,以作经费。宣统朝统治者批曰:“所奏甚是,即当认真筹办。”[22]273据记载,清朝政府就藩库拨银二万两,筹设土民简易识字学塾128所(《云南教育概况》作125所)[23]。
清末政府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治理还涉及到沿边土司。光绪二十年,沿边木邦土司遇到危机,向清朝请求发兵救援,并呈请内附。光绪朝统治者考虑到英国占领印度,侵略缅甸,虽然有土司不服,但力量太弱,无法与英军抗衡。现木邦请求内附,乃其铤而走险之举,实际土司叛服无常,不可相信,因乾隆年间木邦曾经内附,旋复又归于缅甸,加上清朝已与英国刚刚签订最新的不平等条约,“断无为一二土司,另生枝节之理”,因此,光绪朝统治者命令岑毓英再遇有边外土司吁请之事,要“抚以善言,羁糜弗绝。总之驭远之道,因时变通,不拘一格,固不宜显示拒绝,亦不可轻议招怀”[14]99,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怀柔态度,这种态度还表现在对其他一些边疆问题的处理上,为民国时期的领土争端埋下隐患。
五、余论
清末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革,各个阶层都承受着国家和社会被动转型带来的冲击和阵痛,西南边疆外有强敌,内处战乱,清朝政府囿于时代的限制,对世界和全国的时局以及西南边疆的民族问题缺乏清醒深入的认识,不可能制定一套平等完善的民族政策,只能继续“守成”,采取中国历代王朝与清前期历代帝王的剿抚、蠲免、羁縻等传统手段来治理西南边疆民族,同时为了维护西南边疆安全,适度对一些土司改流,并对未改流的土司进行近代化教育,以达到整顿土司,兴土安边的目的。
清末西南边疆的民族问题祸植于清朝前期,其根源在于官僚与地主阶层对田产的高度兼并,这是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天生缺陷。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朝代更替或农民起义,都是在田产高度兼并,农民无地可种,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起义和战争可以消灭许多官僚和地主,使田产得以重新分配,当百姓再次拥有了赖以为生的田产,社会又可趋于稳定,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不断更替的重要原因。当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田产兼并到一定程度,民族问题则变得日益尖锐,但不一定会立刻起事。失去田产的百姓会另寻他路来谋生,比如开矿、经商,甚至偷盗、抢劫等,但无地的百姓过多,当开矿、经商都会成为百姓为了生存而争夺的利益焦点,如果连偷盗、抢劫都不能生存下去的时候,百姓必将起义,通过残酷的战争手段来实现拥有田产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