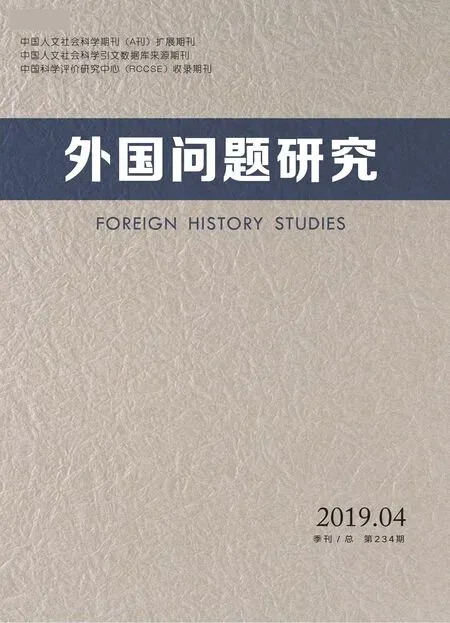“兰普莱希特争论”中的宗教改革史研究
柏 悦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19世纪末,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以文化史(1)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不是狭义上的文化史,其构成比较复杂:从研究对象上看,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集体心理等;从研究方法上看,他秉承实证主义史学,采用了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和生物学等新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新研究方法;从研究领域上看,其文化史是无所不包的,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精神史、艺术史、地方史和普世史等等。的视角探讨了德国近代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闵采尔(Thomas Münzer,1489—1525年)和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年)等宗教改革中活跃的著名人物,开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教改革研究的新视角。但兰普莱希特的宗教史研究很快就受到兰克学派史学家和天主教史学家的严厉批判,成为当时学术热议的焦点,并掀起了“兰普莱希特争论”(2)柏悦:《“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中的一次小高潮。作为串联长达500年的宗教改革史学中的重要一环,研究兰普莱希特以及参与争论的各派史学家的宗教改革史不仅可以从侧面解读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进一步了解德国宗教改革史的新气象,也可以以大见小,窥视19—20世纪之交德国史学界的学术生态。
一、兰普莱希特对宗教改革史的研究
兰普莱希特在19世纪中叶出生于普鲁士邦国耶森镇(Jessen),成长于一个信奉基督教路德宗(Lutheranism)的牧师家庭。耶森镇被视为德意志中部“路德宗信仰的角落”(der lutherische Winkel),小兰普莱希特家中的宗教信仰氛围也十分浓厚,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牧师,上门拜访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兰普莱希特从小就浸润在各种关于神学、哲学和政治的讨论声之中。(3)Luise Schorn-Schütte, Karl Lamprecht, Kultur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4, S.22.新教资产阶级家庭的出身和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父辈权威所传递的新教信仰,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他在之后的研究中对宗教改革时代加以着重刻画。
虽然从兰普莱希特整个学术生涯来看,宗教改革等相关事件和人物作并不是他的研究重心,如他的前期重要著作《11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研究》(1877—1878)、《个体及中世纪德意志的个体认知》(1878)、《8至13世纪大写花体字起首字母装饰品图集》(1881)、《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1885—1886)等都是经济史或艺术史。虽然如此,但他的宏愿一直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写作德国通史,这最终落实在多达12卷、19本的文化史鸿篇巨制《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而宗教改革时代是其中重要的篇章之一。当时已经有学者从文化史角度书写宗教改革,艾伯哈德·戈泰因(Eberhard Gothein,1853—1923年)的《宗教改革前的政治宗教大众运动》(Politisch Religiöse Volksbewegungen vor der Reformation, Breslau 1878)(4)柏悦:《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化史编写状况探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就是极好的先例。但相比前人,兰普莱希特的宗教改革研究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一)“个体主义时代”概念的提出
兰普莱希特认为,宗教改革时代标志着德国历史正式进入了所谓“个体主义时代”(Individualismus)。所谓“个体主义时代”,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78年夏他发表的《个体及中世纪德意志的个体认知》,在这篇论文中兰普莱希特提到了“个体性”(die Individualität),这一概念就是后来他对德国史5个文化时代划分中“个体主义时代”的雏形。按照他的理解,从加洛林王朝到宗教改革前夜德意志民族理念出现,这个过程中个体观念也逐渐形成了。个体在自然经济时期被束缚在氏族和家庭、社团和本性之中,并且备受压迫和限制。随着货币经济的到来,个体获得了较大的自由,逐渐冲破了若干限制因素,并且为新生产关系的系统发展清除了道路。这一观念后来在《德意志史》第五卷(1894—1895)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并且整个德意志文化也被衍生为5个文化时代,但对各个时代的解读分散于12卷内,没有系统总结。(5)Karl Lamprecht, Über die Individualität und das Verständnis für dieselbe im deutschen Mittelalter, in Deutsche Geschichte 12, Berlin: R.Gaertner, 1909, S.3-48.
1897年,兰普莱希特发表论文《什么是文化史》(Was ist Kulturgeschichte?),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化时代”(Kulturzeitaltern)。他认为——德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Zeitsgeist),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二是民族意识的演化也具有周期性特征。就德意志民族来说,历史大体可分为5个文化时代或者说“文化阶段”(Kulturstufen):
1.象征主义时期(Symbolismus):从未知的时代开始到公元350年,经济特征是原始经济时期的渔猎经济,集体占领式的经济;
2.典型主义时期(Typismus):350—1050年,经济特征是中世纪前期共同使用土地的自由农耕,马尔克公社的自然经济经济;
3.传统主义时期(或译为“因循主义”,Konventionalismus):1050—1450年,中世纪后期,经济特征是领主制,大地产制的自然经济;
4.个体主义时期(Individualismus):1450—1700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时代,经济特征是合作社的商业和货币经济;
5.主观主义时期(Subjektivismus):1700年起,浪漫主义时代,经济特征是货币经济,个人贸易和工业。(6)Karl Lamprecht, “Was ist Kulturgeschichte? Beitrag zu einer empirischen Historik,” in Karl Lamprecht. Alternative zu Ranke, Schriften zur Geschichtstheorie, ed. by Hans Schleier(Hrsg.), Leipzig: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 1988, S.252-259.
兰普莱希特强调历史发展历程是由不同的文化时代赓续而成的。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从精神生活单一的原始时代开始,遵循着心理强度逐渐增加原则,一直到一种高度不同的并且带有复杂文化表达的近代大众精神的心理过程。诸文化时代的出现都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经济行为也是心理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对德意志民族和人类历史做出全新的划分定位。其中个体主义时期的时间跨度是1450年到1700年,涵盖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经济特征是合作社的商业和货币经济,是由自然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的重要转折阶段。
(二)《德意志史》中的宗教改革史书写
结合“个体主义时代”的理论定位,兰普莱希特将宗教改革时代安排在1894—1895年出版的《德意志史》第五卷中。该卷的上半部分所记述的时间正处于15世纪末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执政时期,这位皇帝的功绩被作者一带而过,而将更多的笔墨转向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分析,主要描绘了城市和乡村普遍弥漫着的宗教改革和农民运动来临之前的紧张氛围,并将其作为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背景。在城市,货币经济的异常发达、财富和资本的日渐集中,破坏了城市团体的精神和稳固性,酿成了无产者的躁动。而在乡村,兰普莱希特重申了他在《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中的观点,认为社会危机是人口过剩、发展滞后、采邑制度(庄园制度)的没落,以及庄园主的高额赋税和农民贫困等多重因素的产物。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兰普莱希特还记述了教师、学者、艺术家等多个社会阶层的历史状况。以上种种被作者认为是近代早期的前夜并带来“个体主义时代”的降临。(7)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Band 5, 4. Aufl. Berlin, Weidmann, 1911, S.125.
德意志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成为《德意志史》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第一个被作者用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关于路德的论著中,路德个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因素已被阐述得比较充分。兰普莱希特则在自己的“文化阶段”的划分框架下,将路德划分为个体主义时代的杰出代表,认为只有“路德从精神生活最深入的领域为个体主义时代开辟了道路,从宗教上和哲学上,路德把个体的人直接放置到神的原则之前,而同时没有触及神圣的制度。”(8)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Band 5, 4, S.1-7.路德的功绩在于创造性地以一种纯粹德国的方式革新了基督教,路德把新时代的原则延伸到了人类存在的最深入的领域,同时削弱了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而加诸个体身上的束缚。路德发起了这样一场“个人英雄主义的斗争,不仅仅代表他本人,也代表了想要挣脱开罗马教皇枷锁的社会等级,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真理并宣扬路德教教义的正确性。”(9)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Band 5, 4, S.150.路德教教义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其首要原因在于“改革者的个人贡献”。(10)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Band 5, 4, S.272.
《德意志史》第五卷中德国农民战争占了不小的篇幅,兰普莱希特描述了14、15世纪以来农民处境的恶化,他虽然慨叹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层,但是并没有对联合发动起义的被剥削阶级表示同情,他认为农民战争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极端个别的现象,“农民战争中所宣扬的退回到自然经济的社群主义完全是一种反动的思想”。(11)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Band 5, 4, S.349-357.而济金根所代表的落没的骑士阶级起义也仅仅是明日黄花。另外一方面的不协调在于一些宗教极端分子,比如闵采尔,他的个体主义完全否认所有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所以,兰普莱希特认为只有路德才符合历史潮流,“拥有一定的自由但仍旧受到权威的束缚,这才是个体主义最杰出的代表”。(12)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Band 5, 4, S.358.
在第5卷的第二部分,兰普莱希特对直到1648年的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书写却以政治史叙述为主,而且处理地特别仓促,有价值的部分体现在德意志城镇和乡村进一步拉大的发展差距,这也是整个欧洲中部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后果;在德意志乡村,尤其是那些依然信仰天主教的地区经济落后尤为明显,而信仰新教的市镇进入到个体主义时代,享有先进的文化,经济水平也大大超过同时期的信仰天主教的乡村地区。但可惜的是,兰普莱希特对于后宗教改革时代的经济史叙述未能继续深入,反而坠入了他既不擅长也一直反对的政治史迷雾之中。
(三)对受路德教义影响的兰克史学观的批评
“所有的世代都同样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明它的发展是有其道理的,而每一个世代都同样可以同上帝直接联系。道德概念只能在范围上而不能在性质上拓展。要想超出基督教教义之上是不可能的。历史是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神意的显现,”(13)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13页。这是兰克的超验的观念论(Ideelehre)。兰普莱希特认为,这体现了路德新教的影响:人类的历史之上存在着上帝的指令,相信人类的发展是依循未知的法则而进行的,当然这种历史局限了对事物本质的分析。兰普莱希特在1896年《历史学中的新旧方向》(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中认为兰克历史著作中偷偷夹杂着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见解”(14)Karl Lamprecht, “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Karl Lamprecht: Alternative zu Ranke, Schriften zur Geschichtstheorie, ed. by Hans Schleier(Hrsg.), S.199.就脱胎于路德的宗教思想。兰克把历史仅仅看作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一种“神秘的先验精神力量”的闪现,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唯心观念,完全落后于时代。兰克认为“历史的完整进程被视为是一个神圣的秘密,为上帝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所遮蔽。”而兰普莱希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无非就是拿掉这双手,“当我们充满勇气地摘下知识之树上最丰硕的果实,这时我们得以看到所谓上帝的真容。”(15)Karl Lamprecht, “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202.
值得一提的是,兰普莱希特对宗教改革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著作和论文,在教学层面也对宗教改革颇有建树。1908年8月,蔡元培经德国著名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年)介绍来到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求学,期间学习过“兰普来西(Lamprecht)的文明史”(1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自写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8页。,1909年至1911年,蔡元培集中选修了兰普莱希特的7门课程,其中就包括1910年选修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文明 (Lamprecht讲)”。(17)罗兰·费路(Rola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蔡元培研究会编印:《论蔡元培》,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61页。
二、“兰普莱希特争论”中围绕宗教改革史研究的对峙
围绕《德意志史》及其文化史观,德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兰普莱希特争论”(Lamprechtsstreit),传统史学家尤其是兰克学派史学家对兰普莱希特频频发难,如历史学家马克斯·莱曼(Max Lehmann,1845—1929年)在1894年调入莱比锡大学,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为了迎合德罗伊森和兰克,同时为了表明自己与兰普莱希特迥异的立场,他针锋相对地强调意志自由和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在莱曼眼中排在德国历史万神殿中的第一位就是路德。(18)Max Lehmann, “Geschichte und Natur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Kulturgeschichte, Vol.1, 1894, S.245-248.除了莱曼之外,众多学者以宗教改革史为议题,对兰普莱希特大加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因里希·芬克(Heinrich Finke,1855—1938年)和马克斯·伦茨(Max Lenz,1850—1932年)。
(一)芬克与兰普莱希特的争论
海因里希·芬克曾在明斯特大学学习天主教理论和哲学,后留校成为一位正统的天主教神学—教会史家,他一直践行着自己信念,将天主教信仰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芬克将精力几乎都倾注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档案上,尤其关注宗教理事会事宜,被冠以“在档案中耕耘的牛”的美誉。他后来加入了由年轻的天主教学者组成的“格雷斯-社团”(Görres-Gesellschaft),这个社团的宗旨是协调天主教教义和现代学术需求。(19)Christ of Weber, “Heinrich Finke zwischen akademischer Imparität und kirchlichen Antiliberalismus,” Annalen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den Niederrhein,Vol.186, 1983, S.139-165.
芬克1896年出版小册子《兰普莱希特关于中世纪末期教会政治和教会状况的描写》,对《德意志史》第四卷中存在的细节错误进行了严格审查,这一卷所涵盖的时期正是芬克最熟稔的教会史范畴。(20)Heinrich Finke, Die kirchenpolitischen und kirchen Verhältnisse zu Ende des Mittelalters nach der Darstellung K. Lamprechts: Eine Kritik seiner Deutschen Geschichte, Rom: Spithöver [u.a.], 1896, S.96. See 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9—1915),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93, p.217.芬克比菲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1867—1925年)的天主教倾向更为强烈,他不愿意如同拉赫法尔那样,为了赢得学术界的认可而隐瞒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而德国现代学术的基础是由信仰新教的文化资本阶级建立,芬克此举更多的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天主教学者群中的存在感,迎合天主教学术圈的研究旨趣。
芬克批评兰普莱希特“对中世纪的宗教知识一无所知,对天主教仪式也没有任何了解,总而言之根本不懂天主教的深度和魅力,只不过絮絮叨叨了一堆平淡无奇的废话”;(21)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9—1915), p.217.而且兰普莱希特“没有注明出处地引用了阿道夫·哈内克(Adolf Harnack,1851—1930年)著《教义史》第三卷的内容,有愧于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其原创部分也充斥着错误的解读;(22)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9—1915), p.218.并且认为兰普莱希特的社会统计方法只能够解释教会衰落的财政基础,而忽略了到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等。
兰普莱希特并没有及时回应芬克,因为他正忙于和其他批评者的周旋。几个月后兰普莱希特带着新教资本主义史学家的优越感反驳芬克对他的谴责是“宗教狂热”的产物,而芬克的心“根植于两块土地,一块是德国,一块是罗马”,言外之意抨击芬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理念非常淡薄,因而像他这样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并没有写德国史的资格,芬克的批评只体现出他妄图通过“天主教教会的背景、志趣和观念混淆我们国家的历史。他的史学就是中世纪思想的残羹冷炙。”(23)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9—1915), p.218.兰普莱希特与天主教史学家之间的论战体现了进入19世纪后信仰新教与信仰天主教的学者关于德国学术界话语权的争夺,而与芬克同为格雷斯-社团成员的瑞士天主教学者古斯塔夫·施努勒(Gustav Schnürer)则认为在其他新教学者趾高气扬的宗教偏见的衬托下,兰普莱希特对于天主教史学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可见当时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以及新教学者对天主教学者的压制。
(二)伦茨与兰普莱希特的论争
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伦茨出生于一个信仰虔诚的路德教家庭,是路德研究专家,早在1883年就撰写过路德的传记,伦茨认为“从路德到俾斯麦,这两个人搭建起近代德意志历史的两个极点,路德将德意志精神从罗马帝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4)Max Lenz, Von Luther zu Bismarck. Kleine Historische Schriften, 2 Bde., München:R.Oldenbourg, 1920—1922; John L. Herkless, “Ein unerklärtes Element in der Historiographie von Max Lenz,”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222, 1976, S.81-104.
伦茨来到德国学术中心柏林之前,曾在波兰的布雷斯劳(breslau)执教,这里深受德国周边小国所盛行的文化史风潮的浸润。此时伦茨还怀揣一个类似于瑞士著名文化史家布克哈特范式的、主题是宗教改革的文化史书写构想,而来到柏林之后伦茨完全服膺于兰克的学术,成为其头号支持者。即使这样,当他看到兰普莱希特有关文化史的研究层出不穷时,心中还是有所触动,曾经对文化史的热忱让他面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研究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情绪,伦茨对兰普莱希特文化史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25)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1859—1915), p.220.伦茨对于《德意志史》第一卷的评价几乎是毁灭性的,除了历数细节上的失误外,在给友人信中他称“这本书充斥着显而易见的混乱,微不足道的论述,部分行文体现着作者表露无遗的妄自尊大”。(26)Gerhard Oestreich, “Die Fachhistorie und die Anfänge der sozial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208, 1969, S.331-332.“日耳曼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隐喻晦涩难懂;而民族意识显得十分混乱。《中世纪经济生活》已经疑窦丛生,至于《德意志史》第一卷之后就没有继续看下去的必要了,我甚至能想象到格奥尔格·冯·贝洛(Georg von Below,1858—1927年)(27)贝洛是德国历史学家,新兰克学派代表人物,争论中反对兰普莱希特的关键性人物。翻看《德意志史》时浮现在脸上讥讽的微笑。”(28)Gerhard Oestreich, “Die Fachhistorie und die Anfänge der sozial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S.326-327.
1896年伦茨应《历史杂志》主编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年)(29)德国知名历史学学术刊物《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反对兰普莱希特的最主要的阵地,刊物的大量版面刊载来自各学派尤其是兰克学派历史学家抨击兰普莱希特的文章,而对兰普莱希特的文章一律不加采用,只刊载了寥寥几篇回应短评(Erwiedrrung)。的约稿,对《德意志史》第五卷特别是其论述宗教改革前夕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发展部分进行了审查。尽管一贯引用文献甚不规范的兰普莱希特在第五卷里中引用了伦茨关于路德的一些研究成果,而且相对于其他重大人物,他对路德已经算是花费了不少笔墨,但伦茨没有因为“被引用”和赞美路德而“心慈手软”,伦茨直言第五卷的“每一页甚至每一行都可引起争议”(30)Max Lenz, “Lamprechts’s Deutsche Geschichte, 5. Band,”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77, 1896, S.385-447.。
兰普莱希特将宗教改革置于更广阔背景的做法令伦茨反感,而兰普莱希特把农民战争刻画为发生在德意志城市和乡村的“无产者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式动乱”更被认为是十分荒唐的;更严重的是,兰普莱希特将宗教改革史的重点放在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型上,并声称这一过程拉开了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距。在伦茨看来这一阐释不仅充满唯物主义的嫌疑,还体现了兰普莱希特对路德教义理解的浅薄。伦茨认为兰普莱希特的“城镇和乡村之间的二元论”诠释还挑战了一个重要的史学命题,即“正是因为对路德教义的接受,德意志上下各个阶层才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更为普遍的民族经验”。伦茨进一步解释,“从宗教改革一开始路德的教义就广泛传播到德意志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在克服了社会灾难与宗教危机的过程中一直保存至今”。(31)Max Lenz, “Lamprechts’s Deutsche Geschichte, 5. Band,” S.442.伦茨更强调从16世纪20年代初就出现了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联合,而地理的变化和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也模糊了16世纪早期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界限,所谓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穷并没有如同兰普莱希特所描述的那么严重。总之伦茨认为,兰普莱希特所说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城镇的货币经济的二元论“将原来最清楚最确定的历史情况置于一团迷雾之中”(32)Max Lenz, “Lamprechts’s Deutsche Geschichte, 5. Band,” S.410.。
伦茨的观点与之前的学者不同,如贝洛和拉赫法尔,他们将矛头对准《德意志史》是如何处理政治史编纂的,而伦茨审视《德意志史》是如何进行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这正是《德意志史》的特色所在,因而这成为兰普莱希特自争论以来所面对的最严厉的批评。
柏林学界对于伦茨的论文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一开始,兰普莱希特面对伦茨的犀利批判非常胆怯,不愿反击,但在调整心态之后他还是从历史方法与理论的角度回应了伦茨——尽管是从侧面。兰普莱希特认为当时学界的分歧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史”(kollektivistische Kulturgeschichte)与“个体主义的个人史”(individualistische Personengeschichte)之间的抗衡,前者致力于历史结构下行为规律模式的内在动因如何运作,而后者则关注少数精英、个体自由意志,和代代相传的理念动机力量。史学家一旦陷入个体史的视角,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盲视,看到的只是局部压倒整体、个体压倒集体以及规律之外的例外,因为他们的观点既不探寻历史规律和典型,也不研究历史性的群体运动,历史学家没有能力去理解这些现象,更不用说运用批判方法或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解读。(33)Karl Lamprecht,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Probleme der Gegenwart,” Zukunft, Vol.17, 1896, S.306.这是兰普莱希特针对伦茨指责自己“闭眼不见民族国家伟人的重要性”的回应,并进一步指责伦茨对群体运动中的包罗万象的相互联系视而不见,声称伦茨是“个体主义史学家的头号代言人。”(34)Karl Lamprecht,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Probleme der Gegenwart,” S.301.
结 语
兰普莱希特被喻为史学家阵营里的特洛伊木马,(35)Hans-Ulrich Wehler(Hrsg.), Deutsche Historiker, Vol.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3, S.58.他以文化史、经济史为视角,对宗教改革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创新,但分析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兰普莱希特从理论方法的角度对符合路德新教传统的兰克超验的观念论(Ideelehre)提出了批判,认为兰克把历史仅仅看作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一种“神秘的先验精神力量”(36)Karl Lamprecht, “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199-202.是脱胎于路德的宗教思想,局限了对历史本质的分析,完全落后于时代。兰普莱希特强调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了解一个宏阔的集体现象,而个人是所处的特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产物,并非处于一种断裂孤立之中。
但兰普莱希特对宗教改革的创新解读以及他的文化史研究,不仅没有使文化史和社会史在德国成为显学,而且在争论之后文化史和社会史在历史编纂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完全被排斥于德国大学之外了”。(37)Hans-Josef Steinberg, “Karl Lamprecht,” in Deutsche Historiker, ed. by Hans-Ulrich Wehler(Hrsg.), Vol.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3, S. 58.兰普莱希特本人还受到业内同行的敌视和孤立,成了学界边缘人。
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他与宗教史家的辩论中找到一些线索。首先兰普莱希特有关宗教改革史的书写中存在诸如细节上的不准确,年代的错误等等硬伤,这些最基本的史实讹误都受到长年爬梳中世纪档案,并且精通考证的宗教史家一一指摘,如前文提到的伦茨等人;兰普莱希特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参考超出了通常被允许的范围,而且他大量运用二手资料还疏于甄别,这也是传统史家所不能忍受的。故此,尽管兰普莱希特不遗余力地为文化史观提出新的理论原则和体系,在宗教改革史上花费了较多笔墨,但却受到了最猛烈的批评,基本原因就在于他对史料的考证功力不够深厚,导致他在史实这一历史学最基本的支点上有所疏漏,这样一来他的著作就犹如一座建造在空中的楼阁,是难以在深壁固垒的德国史学界立足的。
其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兰普莱希特的理论与实践落差明显,从本质上看他仍然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框囿,在反击芬克的过程中他对天主教史学的抨击亦表明他的学术立场还是传统的新教资本主义史学,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新教资本主义史学家的权威地位,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他对路德形象的探究。
路德是出现在《德意志史》中为数不多的著名人物。虽然兰普莱希特一贯抨击传统史学为伟大人物树碑立传的做法,在《德意志史》中也有意地避免对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国王、政治家大书特书,但读罢《德意志史》第五卷,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路德身上所耗费的笔墨。纵观整套《德意志史》,除了俾斯麦外再也找不到比路德形象更突出的人物:10世纪的统治者“猎禽者”亨利仅仅被他三言两语地总结为“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和城市的庇护人;“红胡子”腓特烈是继查理大帝之后最伟大的人物,而在霍亨斯陶芬王朝倾覆后德意志本就缺少伟大的政治人物,故而在兰普莱希特的书中更不见政治家的踪影。而且兰普莱希特对路德本人及其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赞美有加,完全不同于19世纪下半叶文化史家普遍的否定倾向。如天主教文化史家约翰内斯·杨森(Johannes Janssen,1829—1891年)所著《德意志人民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是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化史最杰出的著作之一,杨森对于主流史学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批判,其中对路德被塑造为民族英雄的形象提出了极大地质疑,(38)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Vol.2, Munich und Salzburg: Brunkmann, 1951, S.33-74.而同样身为文化史家的兰普莱希特将路德冠以“个体主义时代”最杰出代表的美誉,显然,相比于济金根和闵采尔等“不合时宜”之人,只有路德才符合他的“文化时代说”。
但如此一来,兰普莱希特虽然宣称文化史不是历史中某个伟大个体的行为的结果,而是普通人行为的产物;文化史是最重要的“社会化的人的生活形式”的历史,(39)Luise Schorn-Schütte, Karl Lamprecht, Kultur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113.但实质上他与19世纪中叶以来将路德视为“基督教新教民族的新德国的圣卫护士”的史学家并无二致。兰普莱希特的历史叙述与普鲁士学派的绝对权威表述没有根本区别,他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发展周期,“历史研究必须限于研究典型民族的发展。”(40)Karl Lamprech, “Was ist Kulturgeschichte? Beitrag zu Einer Empirischen Historik, in Deutsche Zeitschi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Karl Lamprecht: Alternative zu Ranke, Schriften zur Geschichtstheorie, ed. by Hans Schleier(Hrsg.), S. 271-272.兰普莱希特的德意志史也是从“黑暗的中世纪”的衰落开始,并在路德宗教改革的下,德意志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形成,经过霍亨索伦王朝,最后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中重生。兰普莱希特笔下的路德形象就是兰克模式下的路德形象的“分身”。这正折射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的整体氛围,统一后的德国雄心勃勃,“无论是谁都会一再发现,支持德国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和基础并使之成为一支重要世界力量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新教、宗教改革、路德和他的成就。”(41)孙立新:《关于马丁·路德的种种神话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兰普莱希特的宗教改革研究没能跳脱出固有框架,而他在经济史、文化史层面上研究宗教改革史所做出的创新贡献也因此被冲淡了色彩。
——犀利作者尼基·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