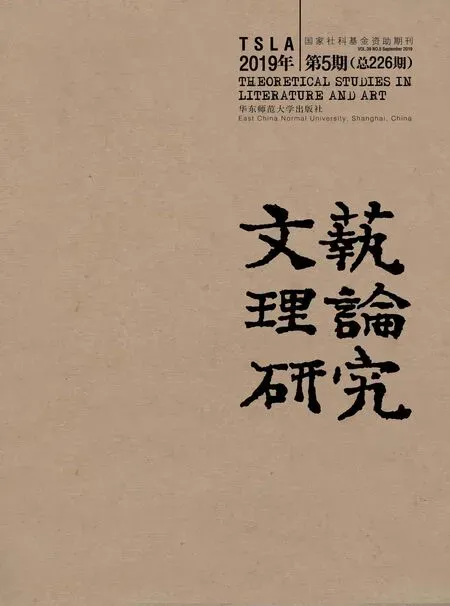图像对语言的僭越与图像批评的生成
——从竹林七贤故事的语图互文关系谈起
张玉勤
引 言
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虽由来已久,却又是当今文艺理论发展必然要面对的一个新话题。语言和图像作为两种媒介,既相互依存、相互交叉,又相互疏离、相互游移,并且“一旦交叉或游弋之后,它们原本的状态和功能都会有所变异”。当前的文学理论关注“语-图”互文问题,必须正视这种媒介新变,以及这种变化背后隐含着的内在机制转换与批评话语生成。
“竹林七贤”故事流传甚久,指的是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七位名士,聚集山林,不拘礼法,倡导清谈,清静无为,饮酒纵歌,恣肆酣畅。“竹林七贤”故事是“触媒”,不断触发和刺激着后代艺术家们的灵感,从而创作出与竹林七贤主旨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诸多图像作品,即“竹林七贤图”。竹林七贤图像所呈现出来的图文特点是“图像模仿语言”,一方面图像源于竹林七贤故事本身和相关语言文本,因文生图,图文唱和,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图像又溢出和游离了源故事和源语言文本,形成了对后者的多重超越甚至僭越。
一、 图像对语言的多重僭越
图像文本与语言文本是“语-图”互文的两个基本单元,或前者模仿后者(即“因文生图”),或后者模仿前者(即“因图生文”)。“竹林七贤图”显然是先有语言文本、后有图像文本,因而“因文生图”是其基本的互文形态。对于“因文生图”来说,图与文的关系有紧密型、松散型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等不同类型。当图像文本与语言文本相距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时,此时的图像就已经远离了“源文本”,从而形成对语言文本的超越和僭越。
历史上出现过诸多“竹林七贤图”,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最早,唐代的孙位,宋末元初的钱选,明代的仇英、陈洪绶,清代的沈宗骞、禹之鼎、改琦、顾鹤庆、彭旸、冷枚,乃至当代画家的范曾等,都绘有这一题材的图像作品。与一般“因文生图”式的“语-图”互文形态不同的是,“竹林七贤图”明显地表现出对竹林七贤故事中原有人和事的疏离与反叛,从而形成图像对语言的僭越。这种僭越大抵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整体呈现对局部摹画的僭越。即对总体性氛围的把握,取代了对原有人和事的局部性描摹和特写式展现。人们对于竹林七贤,既有群体式印象,如不拘权势、任性放达、竹林清谈、纵情醉酒等特征成为这一群体的显著标识,又有个体式印象,如嵇康抚琴、阮籍长啸、刘伶纵酒、王戎忆旧、阮咸弹奏等常常成为这一题材作品中的经典画面。但颇有意味的是,后世对“七贤”的解读与接受充满了诸多解构。就连“竹林七贤”的名号也受到了质疑:“‘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则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万绳楠49—50)既然“竹林”并非真实,“七贤”亦为比附,那么围绕“竹林七贤”所作的图像作品便难以形成固定模式,总体呈现强于细节追求的艺术表现风格的最终形成也就在所难免。如南京博物院藏明代顾绣作品《竹林七贤图》以及李墅、吴昌硕等人创作的《竹林七贤图》,竹林七贤交游的场景已经明显淡化,七贤的个性化呈现也已基本消失,人物和故事的叙事性呈现让位于山水之景的写意化描摹,如果离开画面题字或个别细节,读者很容易将其混同于一般的山水写意画。有学者注意到,即便是早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同样开始透露出这一风格取向,画像中人物的个人身份被淡化,“尽管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刻意表现人物不同的神情与姿态,但是如果没有题记,没有人物手中那些标志性的‘道具’(如阮咸手中的乐器‘阮咸’),我们恐怕很难一一指出他们的姓名。”(郑岩214)
有学者则把这种通过个性化展现让位于整体性传达的手段塑造出的形象概括为“集体式肖像”(collective portrait)和“理想化范型”(ideal-type)(Spiro99)。就此种情况下的“语-图”关系而言,语言文本只是给图像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基本的故事框架。图像文本虽源于语言文本,却又不拘泥于语言文本。换言之,竹林七贤的故事虽然是真实的,但图像却并非取其“实”,而是就其“虚”,故事本身似乎变得并不那么重要,要紧的当是故事背后或故事之外的意义与精彩。这与有的学者看待《洛神赋》与《洛神赋图》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非常神似:“后代图绘《洛神赋》的画家[……]他们所关心的,远非如何解析《洛神赋》的内文,或它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何关系。他们所关注的,在于如何诠释和表现这则美丽而哀伤的恋情和诗意。”(陈葆真27)“竹林七贤”语图关系同样如此。后世的图像作者们所看重的并非竹林七贤在做什么,或者观者能否准确无误地识别出其中的人物角色,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某种观念和文化符号,引导当下的人们从中追寻想要的东西。
二是文化取舍对忠实再现的僭越。即基于某种文化诉求,对故事的原有维度进行适当剪裁与取舍,造成图像表现对语言文本忠实再现的游离。这种僭越又可区分出不同的情形。
一种情形是图像注重呈现竹林七贤故事的唯美性特质,而忽略了其间的复杂性内蕴。应该说,竹林七贤现象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它不仅有光彩照人的一面,如这一群体所彰显的巨大人格力量和清玄高蹈、“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气质,使他们成为后世文人竞相模仿的对象。但在其归隐、放达的光鲜外表下却充满了复杂和变化。如: 七贤在“名教”与“自然”的选择上并非从一而终,最终大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七贤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分化;他们的行为看上去很旷达和潇洒,但骨子里却充斥着无奈和痛楚。恰如有的学者所言:“实际上,阮籍、嵇康、刘伶等人始终没有做到像‘大人先生’和孙登那样超凡脱俗,而是终身陷入一种出与入的矛盾选择的困惑、焦虑和痛苦的折磨之中。”(马良怀113)鲁迅先生更是一语道破了竹林七贤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537)但有意思的是,后代的竹林七贤图像大都取其光彩照人的一面,着意表现这一群体高蹈的气质、潇洒的言行、避世的情结和蔑弃礼法、纵情肆志等特质,而忽略甚至无视其中的复杂与变化。就此种情形下的“语-图”互文关系而言,图像虽是“因文生图”,却是有选择性地入图,其间竹林七贤们内在的苦痛被外表的潇洒所掩盖,群体的复杂被光鲜的表象所遮蔽。
另一种情形是图像作者注重呈现竹林七贤故事的“利己性”一面,而忽略了其客观的内在性表达。也就是说,图像作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竹林七贤故事中对自己有利的情节或画面入图;原有的故事或情节可能只是一种由头,作者的真实意图随着画面荡开,或被隐藏在画面的背后。伯克认为,“如果认为这些艺术家—记者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也就是以为他们的眼光完全是客观的,不带任何期待,也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那也是不明智的。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说,这些素描和绘画都记录了某个‘观点’。”(伯克16)阿拉贡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当我把别人的、已经成型的思考引入我写的作品里,它的价值不在于反映,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和决定性的步骤,目的是推出我的出发点。”(萨莫瓦约27)此处的“观点”和“出发点”其实就是图像作者的观察视角与表达意图。比如禹之鼎绘制的《竹林七贤图》,不仅画出了竹林七贤,更是画出了自己的心声,体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参与意识和文化认同。陈洪绶的《竹林七贤图》更是直接把画家本人画入图中与七贤并置,主体性色彩异常明显。在这种情形下,有一千个画家便会出现一千个不同的竹林七贤图,图像的“利己性”得到充分彰显,与作者意图无关的人物或情节内容则被有意地简化甚至忽略,图文关系出现裂缝,图像以此僭越了语言。
还有一种情形是图像作者注重呈现竹林七贤故事的深层性意蕴,而远离了事件的固有语境与语义。图像的意义不止在于图像符号本身所具有的表面意义,也不止于对语言文本所具有意义的“同声翻译”,而有着更为隐秘的深层意蕴。对于图像的这种深层意蕴,不同的理论家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描述。英加登概括为“形而上的特质”(metaphysical quality),这种特质指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恐怖、震惊、玄奥、丑恶、神圣和悲悯等(童庆炳207)。罗兰·巴特在《显义与晦义》中称为“意指活动层”(或称“晦义”),并认为这层意义“既顽固又琢磨不定,既平滑又逃逸”(44);在《文之悦》中又指出它“越出了对所指主题的复制,迫使人们作讯问式的阅读”,并且这种“讯问明显朝着能指而来,而非所指,朝着阅读,而非概念: 它是一种‘诗性’的把捉”(151)。有的学者透过表象看出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中的“升仙”与“神化”的主题。显然,这一经过挖掘的主题,与竹林七贤的初衷和原有语境已经完全背离了。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透过图像我们可以捕捉到后世对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承和演变中不断涌现出的“规训”色彩与“文人化”倾向。图像的深层意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图像与语言的关系渐行渐远。
三是“以我观物”对“源”文本的僭越。即图像作者在竹林七贤图像中通过时间的挪移、自我的“代入”、移情式的表达等手段,实现新的艺术呈现和艺术传达。后代的竹林七贤图像作者,虽然继续沿用同样的“视觉典故”,但却经过了“以我观物”式的情感过滤。虽然图像表现的是历史故事,却与当下的时代、社会、情感等表意系统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正如伊丽莎白·弗洛伊德所言:“没有任何艺术作品和解释者能够脱离历史、社会或任何其他表意系统而存在。”(67)“只有现在时是被经历的。过去与将来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历史之难写,正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在有关,与我们的现在看问题的方式以及投射将来的方式有关。”(高概7)故而,从李墅《竹林七贤图》所题虞集诗句“糟粕尘世,高纵庄周。我怀古人,遁而违优。安得挥弦,以招湛浮”中,不难看出画家“糟粕尘世”的时局判断、“遁而违优”的高蹈情结和“安得挥弦”的超脱情怀。从陈洪绶《竹林七贤图》中可以读出画家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和落差,读出画家的狂怪趣味与率真性情,读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艺术移情。赵宪章把艺术史中“图像艺术选取同样的文本母题,但却图说着不相同的意义”现象概括为“语图漩涡”。他认为,这漩涡的动能来自“母题要意”和“铺张演绎”的互动,前者是“向心力”,后者是“离心力”,正是二者之间的张力驱动了语图符号的旋转多姿。但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以我观物”,图像与语言的关系都相距甚远,图像对语言的僭越路线清晰可见。
二、 图像僭越语言的三重动因
后世的竹林七贤图像,以整体呈现对局部摹画的僭越、文化取舍对忠实再现的僭越、“以我观物”对“源”文本的僭越三种方式,在外部形态上实现了对语言文本的超越和僭越。但有一个问题无法绕开: 竹林七贤图像何以成功实现对语言文本的僭越?从深层动因来看,图像对语言的这种僭越,主要缘于图像自身所具有的符号属性、言说属性和蕴藉属性。
(一) 图像的符号属性
“语-图”互文离不开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之间的互相模仿。无论是图像到语言,还是语言到图像,“转换”不等于“等值”,“同构”不等于“同步”,势必存在意义的增值或衰减。加达默尔便指出,“模仿的认识意义就是再认识”,就是“比起已经认识的东西来说有更多的东西被认识”,且“谁要模仿,谁就必须删去一些东西和突出一些东西”(146—49)。郑板桥把“眼中之竹”和“胸中之竹”变为“手中之竹”时,同样不是符号之间的等值交换,而是作了“倏作变相”的艺术处理。历史上的竹林七贤图像作为对语言文本的模仿,同样会在模仿过程中出现两种符号信息之间的裂缝和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现象,主要是由语言和图像原本属于不同性质的符号序列所造成的。
苏珊·朗格曾把符号区分为“推论性”符号(如语言)和“表现性”符号(如艺术品)两种,“运用语言可以表达出那些不可触摸的和无有形体的东西,亦即被我们称之为观念的东西;还可以表达出我们所知觉的世界中那些隐蔽的、被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而艺术品则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征兆性的东西或是一种诉诸推理能力的东西”(20—24)。语言与图像虽然可以实现异质同构,但它们毕竟属于不同性质的符号序列。对于竹林七贤图像而言,从语言文本到图像文本,在符号转译的过程中势必会带来信息的遗漏、衰减或增值,因而图像对语言的僭越成为可能。
其实,由于语言与图像两种符号之间的异质性所导致的图像对语言的僭越,还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符号关联。无论是图像文本转化为语言文本,还是语言文本转化为图像文本,其中存在着两个主体,一个是把旧文本转化为新文本的“作者”,一个是新文本的未来接受者。当读者面对由图像文本转化而来的语言文本时,由于语言对意义所持有的固定性与稳定性,因而在理解上并不存在较大困难,很容易领会作者的意图。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实指性”和“强势性”优势充分彰显,“语-图”互文后的意图和意义相对固定明确,语言对图像即便存在僭越也往往比较单纯地局限于作者维度,而较少涉及读者维度。但当读者面对由语言文本转化而来的图像文本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图像文本往往具有意义上的歧义性和模糊性,所以读者的理解往往会与作者意图产生隔阂与裂缝,甚至也会与源语言文本存在误差和断裂,如此一来便造成图像对语言的僭越。在这种情况下,图像对语言的僭越往往是双重的,一是图像作者“化语为图”时形成的图像僭越,我们不妨称之为“原发性僭越”;二是图像观者“化图为语”时形成的图像僭越,我们不妨称之为“叠加式僭越”或“继发性僭越”。不过,无论哪种形式的僭越,从本质上说都是由于语言与图像这两种符号的根本属性不同所致。
(二) 图像的言说属性
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并非直接实现,即由语言直接进入图像或由图像直接进入语言,而是要经过一定的中介。如果说图像模仿语言即“由文及图”,依靠的是“语象”,那么把图像再转化成文字即“由图及文”,则需依靠“像语”。对于后世的竹林七贤图像而言,其之所以能够形成对语言的僭越,主要依靠的正是“像语”,即图像的言说特性。
“像语”,即图像如同语言一样也在说话,只不过语言是有声的,图像是无声的。中国古代所谓的“画是有形诗”,说的其实正是“像语”,即“以图言说”。对于“像语”的形成和图像的言说属性,图像学家米歇尔曾用“可视的语言”和“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等概念加以描述。在他看来,“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的最狭隘意义,即‘给无声的艺术以声音’,或提供‘一件艺术品的修辞描述’”,在此情况下,“形象/文本之间的分化被克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缝合的、综合的形式,一个语言图像或形象文本”(140—41)。
对于“语-图”互文来说,如果说“由文及图”经历了从“听觉语象”进入“内在心象”,再投射到“视觉图像”的“言—意—象”过程,那么“由图及文”则经历了“符号敞开——心象凝结——像语生成——意义释放”的“像—意—言”过程。
“符号敞开”是“以图言说”的第一步。当经由语言文本转化而来的图像作品面向读者时,读者首先面对的便是图像中的一个个符号单元。按照潘诺夫斯基的视觉艺术理论,符号的意义是一步步向读者敞开的,即先进入“基本的或自然的题材,又分为事实性或表现性题材”,然后再进入“从属性的或约定俗成的题材”,最后进入“内在含义或内容”(34—36)。
“心象凝结”是“以图言说”的第二步。图像并不能直接言说,必然要经过读者的心理过滤,把视觉符号凝结成“心象”或“意象”,然后以“心象”或“意象”的方式进入图像的意义生产。如果说“符号敞开”是“眼中之竹”阶段,那么“心象凝结”则是“胸中之竹”阶段。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代表某样东西,即它的对象。它不是在所有方面,而是通过指称某种观念来代表那个对象的。”(丁尔苏58—59)按照皮尔斯的理解,符号并非直接产生意义和指称事物,而是通过“指称某种观念”(即“解释项”)来实现。人们之所以能够读懂众多的竹林七贤图像,并不是直接“望图生义”,而是依靠这些图像在读者心目中形成的“某种观念”即“心象”。没有“心象凝结”,读者不可能真正进入竹林七贤图像的意义世界,所谓的“语-图”互文和图像对语言的僭越便不可能真正实现。
“像语生成”是“以图言说”的第三步。“心象”在读者内心深处凝结而成后,有一个从模糊向清晰转化的过程,按照郑板桥的说法即是“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此时,“心象”慢慢趋于稳定和成熟,并带动图像不断地向外部释放信息,于是“像语”得以生成。原先静止的图像开始跃动起来,并试图不断地与其他时刻产生的“像语”产生互动和联接,形成更大范围的“像语群”。此时,图像才真正向读者打开。历史上众多的竹林七贤图像之所以能够引起历代读者的注意和情感认同,依靠的正是诸多的视觉符号在读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像语”和“像语群”。
“意义释放”是“以图言说”的真正完成。“像语”和“像语群”的形成,便意味着图像意义与接受主体的联结和互动,图像言说和意义释放便已开始。“像语”实现意义释放的路径和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有时是依靠“图解”,即图像符号自身所具有的意义传达的基本功能,如“七贤图”中的竹子自然成为七贤肆意放达的场所,人物手中的“阮咸”分明代表着现实中的阮咸。有时依靠的是“惯例”,即由习俗、传统等形成的艺术惯例,恰如迪基所言“艺术是一定时代人们的习俗所规定的”(799)。有时依靠的是对文本的“深度耕犁”,因为图像的这些意义往往不是直观呈现的,而是要靠“通过弄清那些能够反映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阶级、一种宗教或哲学信仰之基本态度的根本原则而领悟的”(潘诺夫斯基36)。有时依靠的则是“阐释”,即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阅读体验、认知模式等,对作品作出理解和判断。不管依靠哪一种意义释放模式,图像只有开始言说,图像僭越语言的通道才真正打开。不过,图像的言说与文字不同:“图像并不直接以‘说’、‘云’、‘曰’的形式表达其中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时直露在那些‘可见的’(即视觉的)形象的表面,有时又隐藏在形象的背后。”(郑岩288)但不管是直露还是隐藏,都需要读者去仔细鉴别和体味。当然,打开这个通道只是僭越的开始,要真正实现对语言的僭越,还需要更多其他的条件与可能性。
(三) 图像的蕴藉属性
图像能够言说,但不止于言说,它可以发挥自身特有的符号属性,让这种言说功能充分彰显。图像虽是虚指的、弱势的,却成为意义的凝结体和蕴藉物,因而始终处于言说的不断生成与意义的无限延宕中,图像得以在此过程中更深一层地走向对语言的僭越。
语言与图像作为两种符号,各有优劣势:“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两种符号,‘实指’和‘虚指’是它们的基本属性。语言是实指符号,因而是强势的;图像是虚指符号,所以是弱势的。”语言虽是实指的、强势的,却不是万能的,“如纳尔森·古德曼所说,无论多少描写的总和都构不成描画”(米歇尔188),“图像的唤起能力优于语言”,“图像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传达无法用其他代码表示的信息”(范景中107—110)。图像符号虽然是直观可视的,表面看来是容易把握和理解的,但它所蕴含的多义性又使得这种把握和理解有时变得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罗兰·巴特在《图像修辞学》中提出,“所有图像都是多义的。在图像的能指后面,隐含着一条所指的‘浮动链’,读者可以从中选择某些能指而忽略其他。”(265)瓦尔特·舒里安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图像总是比话语或想法更概括、更复杂。图像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浓缩了的方式传输现实状况。因而,图像当然也让人感到某种程度的迷糊不清。”(268)
正是缘于这种蕴藉性质,图像始终包含着意义解读的无限可能性。也就是说,就符号的表情达意功能而言,图像丝毫不亚于语言,图像对意义的“包孕”能力与“唤起”能力同样突出。从这一意义上加以审视,历史上的竹林七贤图像之所以能够僭越语言,不仅在于这些图像能够无声地言说,还取决于其背后“能指链”的丰富与说话者的“意向性”,因为“话语秩序的理由并不都藏在它背后,藏在结构中,其中一部分在说话者的意向性中,这正是指称的主观方面”(利奥塔83)。人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关乎竹林七贤本身的“外延”讯息,还可以通过对背后“内涵”讯息的把握,实现多种意义的叠加。
三、 图像僭越语言成为批评形态和表意工具
何谓批评?希普莱认为,批评就是“对文学作品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揭示作品所包含的原则和理论,并运用这些原则和理论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对作品进行判断和鉴别”(王先霈 王又平179)。纵观历史上的竹林七贤图,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图像大都没有止步于对竹林七贤语言叙事的客观转译(即图式化),其中蕴含着图像作者大量的“判断”与“描述、解释和评价”。如此一来,图像不仅仅是一种言说方式,还上升为一种批评形态,从而把对语言的僭越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后世的竹林七贤图像之所以构成一种批评形态,大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是图像的画面选择彰显作者的立场观点。各种竹林七贤图像虽然依据的都是竹林七贤故事,但选择什么样的场景入图,如何巧妙地把“题外之意”置入画面之中,都能看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伯克的“观点”和阿拉贡的“出发点”,说的都是作者的观察视角与价值立场。当竹林七贤图的作者们把画笔聚焦于这一群体的闲适、畅谈与雅趣,而把他们“越名教”的本性和不与官场合作的“任性”置之度外时,其内心深处的态度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同样,当画家们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如《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甚至画家本人(如陈洪绶《竹林七贤图》)“同图而语”的时候,在画家的视界里,“竹林七贤”已俨然成为一种人格崇拜或神仙信仰,或引导墓主人走向升仙和步入永恒,或成为“晚明偏好个人主义人士所酷爱的人物典范”(高居翰218)。在谢赫看来,图绘具有“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批图可鉴”的艺术功能。高居翰则认为,“当人们有意识地选择风格时,这种选择就带有附加的意义,其特殊价值归属于各种风格。它们包括地望、社会地位、甚至思想或政治倾向。风格于是就有了超出绘画界限的各种含义。”(洪再辛162)不管怎样,此时的图像显然已经超越了语言文本,走向一种深层次的话语批评。
二是视觉符号的运用彰显作者的“弦外之音”。后世的竹林七贤图像,从视觉符号上看是历史上关于竹林七贤的人和事,但对于许多作品来说,表现竹林七贤并不是最终目的,追求画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才是终极旨归。有的作品以直接功利追求为目标,如《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是以引导墓主升仙为实用目的;有的作品是以间接抒情达意为宗旨,如李墅《竹林七贤图》旨在表达“糟粕尘世,高纵庄周。我怀古人,遁而违优。安得挥弦,以招湛浮”的旷世情怀;有的作品则是以深层借题发挥为追求,或抒发忆旧思古之情,或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如陈洪绶的《竹林七贤图》可谓“发思古之幽情的作品”,不免“夹带着一种怀旧或温和嘲讽的气息”(高居翰205)。此时的语言文本其实只是由头,或图像作者只是把语言文本作为借题发挥的对象,其真实意图是隐匿在画面背后的,一旦达到“立象尽意”的目的,便可以“得意忘言”了。当语言处于“被拋”的境地时,图像对语言的僭越便得以形成。

受到政治高压和内心痛楚的双重折磨,到了后期竹林七贤们自身也开始慢慢出现分化,除了嵇康外,大都在“名教”与“自然”、“内圣”与“外王”之间找到了平衡。就是清谈风气本身到了后来也渐渐失去了对抗色彩:“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万绳楠45)受此影响,后期竹林七贤图中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化,文人清玩的成分越来越多,甚至与一般的“文人画”并无多少区别。如改琦的《竹林七贤图》与吴伟的《词林雅集图》极为相像;李士达的《竹林七贤图》和他本人创作的《西园雅集图》更是出现了相同的“视觉典故”;沈宗骞的《竹林七贤图》,已经涵盖了琴棋书画的模式,展现的是文人雅趣;康熙年间青花竹林七贤图炉与竹林七贤图碗,图中文人题壁的场景非常明显,与刘松年《西园雅集图》中出现的文人“题壁”如出一辙;元代的“刘伶银槎杯”塑造的刘伶,醉酒之态开始被读书的形象所取代。早期竹林七贤图中的麈尾和如意已经不复存在,醉酒和清谈遭到了消解,抚琴长啸、反弹琵琶等高士形象也逐渐被双翅帽、书籍、笔墨纸砚等文人形象所替代。

竹林七贤图像所构成的诸种批评形态表明,图像不只是语言的“图式化外观”,还是意义的“自足体”。它不仅能够“言说”,而且能够“隐匿”意义;它不仅能够表情达意,还能够构成判断和批评。至此,图像的僭越性已经非常明晰。

注释[Notes]
① 赵宪章:“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江西社会科学》9(2007): 11。
② 此为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参见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第五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27页。
③ 此为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参见嵇康: 《嵇康集译注》,夏明钊译注(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④ 日本学者町田章认为,“这不外乎是把作为实在的隐士的竹林七贤,改变为理想境界的隐士和方士。这一阶段,壁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对神仙的礼赞。”参见町田章:“南齐帝陵考”,劳继译,《东南文化》1(1986): 51。赵超提出,“有迹象表明,‘竹林七贤’由于其秉承老庄,宣扬玄学,加上世人的渲染,道教的流行,使得他们已经有所神化,成为具有道教意义的宗教偶像。”参见赵超:“从南京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壁画谈开去”,《中国典籍与文化》3(2000): 8。郑岩认为,古代将历史人物神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不管这个人物原来的面目如何,一经神化,便脱离了原来的身份,人们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向他祈风请雨。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通往仙界的媒介,甚至本身就是神仙。参见郑岩: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28—29页。
⑤ 所谓“规训”,指的是后世人们对待竹林七贤已不仅仅停留于任性放诞、远离政治等“魏晋风度”的展现与膜拜,相反“不守礼节”“反礼教”的一面被不断放大,竹林七贤被不断纳入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规训的进程中。与“规训”相关联的便是后世竹林七贤图像的不断文人化。这一问题将在后文作进一步论述。
⑥ 朱良志把视觉艺术中使用的典故称为“视觉典故”,并提出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视觉艺术中直接使用语言文献典故(如文学典故、历史典故、文化传说典故等),二是图像典故的使用主要指对视觉艺术中主题的运用(如“渔父”“待渡”等)。参见朱良志:“论唐寅的‘视觉典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12): 40。
⑦ 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文艺研究》9(2014): 25。
⑧ 赵宪章认为,“无论就声音能指还是就话语活动而言,我们都可以将语言看作是‘包含一种形体面貌的符号’。这符号所包含的‘形体面貌’,其实就是维姆萨特所说的‘语象’。语音是语象的物性载体,语象则是意义的话语表征;意义蕴藉于语象就像盐在水中,语象对于意义如影随形。唯此,语言所指示的意义才可能‘对我变得明显起来’,意义交流才可能成为有效的传达”,“语象肉身作为语义所寓居的话语形体,它的显现就是语言表意的自我生成;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表意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语象活动”。参见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文艺研究》9(2014): 21—22。
⑨ 宋代张舜民在《跋百之诗画》中提出。参见《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册(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48页。
⑩ 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3(2011): 18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罗兰·巴特: 《显义与晦义——批评文集之三》,怀宇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Barthes, Roland.The
Obvious
and
the
Obscure
. Trans. Huai Yu.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 Trans. Tu Youxia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图像修辞学》,方尔平译,《语言学研究》(第6辑)。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61—72。
[- - -. “Rhetoric of Image.” Trans. Fang Erping.Linguistic
Studies
. Vol.6.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8.261-72.]彼得·伯克: 《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Burke, Peter.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 Trans. Yang Y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高居翰: 《山外山》。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Cahill, James.The
Distant
Mountains
.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3.]陈葆真: 《〈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Chen, Baozhen.The
Goddess
of
the
Lo
River
and
Ancient
Chinese
Narrative
Handscrolls
.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2.]让-克罗德·高概: 《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Coquet, Jean-Claude.Discourse
Semiotics
. Ed. and Trans. Wang Dongl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乔治·迪基: 《艺术界》,《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三卷,李钧主编。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Dickie, Gorge.Art
Worlds
.Classical
Texts
of
Western
Aesthetic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 Vol.3. Ed. Li Ju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1.]丁尔苏: 《语言的符号性》。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Ding, Ersu.The
Sign
-Character
of
Language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范景中选编: 《贡布里希论设计》。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Fan, Jingzhong, ed.Gombrich
on
Design
.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1.]伊丽莎白·弗洛伊德: 《读者反应理论批评》,陈燕谷译。台北: 骆驼出版社,1994年。
[Freund, Elizabeth.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 Trans. Chen Yangu. Taipei: Camel Publishing House, 1994.]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Gadamer, Hans-Georg.Truth
and
Method
. Trans. Hong Hand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洪再辛: 《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Hong, Zaixin.Anthologies
of
Overseas
Studies
on
Chinese
Painting
(1950-1987
).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2.]苏珊·朗格: 《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Langer, Susanne K.Problems
of
Art
. Trans. Teng Shouyao and Zhu Jiangy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3.]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话语,图形》,谢晶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Lyotard, Jean-François.Discourse
,Figure
. Trans. Xie J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鲁迅: 《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 Vol.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马良怀: 《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Ma, Lianghuai.A
Study
of
the
Demeanor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3.]W.J.T.米歇尔: 《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Mitchell, William John Thomas.Picture
Theory
. Trans. Chen Yongguo and Hu Wenzh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欧文·潘诺夫斯基: 《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Panofsky, Erwin.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 Trans. Fu Zhiqiang.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Samoyault, Tiphaine.Intertextuality
. Trans. Shao Wei.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瓦尔特·舒里安: 《作为经验的艺术》,罗悌伦译。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Schurian, Walter.Art
as
Experience
. Trans. Luo Tilun.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5.]Spiro, Audrey.Contemplating
the
Ancients
:Aesthetic
and
Social
Issues
in
Early
Chinese
Portraiture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Tong, Qingbing.The
Course
of
Literary
Theory
.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 黄山书社,1987年。
[Wan, Shengnan.Chen
Yinque
’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1987.]王先霈 王又平: 《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Wang, Xianpei, and Wang Youping.A
Glossary
of
Terms
in
Critical
Theory
.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郑岩: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2年。
[Zheng, Yan.A
Study
of
Mural
Tomb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