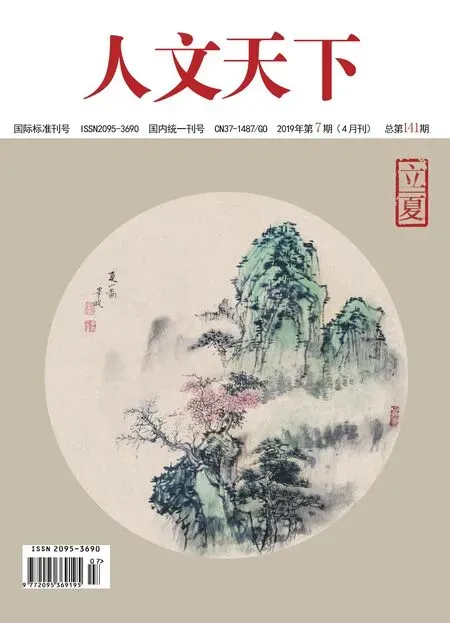试议几点邹鲁文化价值内涵
曹巍巍
传统文化积淀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和人文观念,凝聚着一个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道德向往和价值取向,代表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和载体,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和崛起的不竭动力。
“邹鲁之风”在汉代以后的两千余年里,已经成为“儒风”及传统文明之风的代称。《唐代拾遗》卷四十五载《文宗御注孝经赋》言:“万门翕集,清传邹鲁之风;万室雍熙,普咏文明之德。”将“邹鲁之风”和“文明之德”相联系,不难发现对“邹鲁之风”的仰慕和推崇。
邹鲁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文化的标识,与其早期的文化渊源和后来邹鲁文化融合后形成的风气有着重要的联系。相较于后来通称的邹鲁,邹与鲁早期其实是两支渊源不同的文化脉络。在春秋以前,鲁为周之封国,邹为周之土著附属国。在“兴灭国,继绝世”的周礼文化生态环境下,邹、鲁两国主要传承着各自的部族文化。邹为土著东夷古国,保留和传承着东夷土著文化的诸多特色;鲁为周文化在东方的代表,传承着以周礼为核心的周礼文化传统。两国和平关系的维持主要表现为邾(邹)以礼朝鲁、尊鲁;鲁以礼安邾,关系平稳,各承传统。春秋末到战国中期,邹、鲁两国文化受儒家学派影响,演进到融二为一的完成期,并逐渐出现了“邹鲁之士”的称呼。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在邹鲁之士的大力推动下,尊孔读经的儒风和崇尚道德教化之风逐渐汇聚成邹鲁之风,后随着儒家学派思想的影响和扩大,邹鲁之风影响随之不断扩大,许多地区都以“邹鲁”作为传承儒家文化的重要标识。
今天我们谈的邹鲁文化,在史料中并没有准确的记载,主要是今人的概括和提炼,既可以包括从孔子到孟子一脉相承的儒家学说思想,也应该包括邹鲁早期保留的文化传统。从地域上看,邹鲁之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古代圣贤,创立发展了儒家学派,奠定了早期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华文化的精神走向,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尚和合、求大同的世界观
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如果说“和合”如同儒家的仁义君子一样,传递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谦和,那么大同则是儒家君子所追求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好奋斗光景。
和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其内涵。一是自己内心的平和。儒家一直讲君子的修养之道,非常注重对内心“自得”“真乐”的探寻,如颜回之乐、曾点之乐,是一种如同内心照见鸢飞鱼跃的洒脱与真乐,那种由内而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平和,心有所安,方不为所动。二是个人与社会的和合。不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亦或是“入则孝,出则弟”,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对自我不当行为的约束,对正义、真理的坚持,对家庭和社会的忠义。和合里面保有的是仁爱的温度,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担当。如同《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是一种从内而外、从小到大的和谐,是“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和合。三是个人与自然、宇宙的和合。在儒家传统思想里,“天人合一”一直是矢志不渝的追求趋向。《周易》里提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把合天地的德放在了首要位置,就是要实现人德与天德的统一,实现自我道德修养、精神境界与天地自然的统一。人德主要体现在儒家对仁的追求,通过求内在仁(德性)来实现外合于天道(德)。
大同世界同样是儒家知识分子所期许的。《礼记》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如果说孔子为我们所描绘的是人人彬彬有礼、处处尊卑有序的礼乐大同的话,那么“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孟子则是通过他的仁政、民本思想为我们阐释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不难看出,追崇和谐稳定一直是孔孟代表的邹鲁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
厚德载物、兼收并蓄、和而不同正不断熔铸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更激发着我们不断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担负更大的责任。
二、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
所谓民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邹鲁文化自古以来就包含着浓厚的民本意识,邾文公卜迁于绎的故事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左传》记载,邾文公为了迁都到绎地而占卦问吉凶,结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面对这一结果感叹道:如果对民众有利,也就是对我有利,上天为民众设立君主,就是为了给他们利益,民众百姓既然能得到利益,我就必然会这样做,我的天命就是养育民众。只要迁都对民有利,就是自己劳累至死也再所不惜,因此邾文公被儒家经典《左传》赞之为“知命”,也就是知天命。这说明诞生在邹鲁大地的这种浓厚的人本、民本意识被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理念。
孔子关于民本思想有着明确论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指出了百姓是安邦定国的社会基础,只有爱惜百姓,尊重百姓的意愿,为百姓服务,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主张仁政,从小民的土地宅园,到家庭的基本温饱以及老人的赡养,他的仁政思想建构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发展纲略。孟子认为,民生关乎百姓的生命、生活,治理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生问题,即“民事不可缓也”,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才能安静下来接受礼乐教化。正是因为把百姓的利益看得最重要,孟子才极力反对杀伐战争,因为杀伐违背了百姓心存的道义,战争应该顺应民义,违背百姓民义战争的都是无义战。国君好仁,便能天下无敌,“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孔孟文化的历史地位奠定了邹鲁文化的整体基调,确定了邹鲁文化在后世影响的历史地位,仁政、民本的思想更成为历朝历代学习的治国方略,为后世儒家知识分子注入了兼济天下的理论渊源和思想情怀,使他们能在为官时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感召。这种高扬人性、注重爱民的思潮,在当今社会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聚万众一心的中国梦、提升广大领导干部执政爱民、永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青春活力而言,依然是很好的理论归处和学习蓝本。
三、为仁由己、下学上达的进取精神
孔孟之道“一以贯之”,孔子、孟子倾尽一生,传道授业,躬身践行,以求达道的精神,为历代后世树立了圣王的楷模。孔子主张行仁复礼、仁者爱人,推行“仁”的思想,以期建立一个充满仁爱和礼治的国家。孟子言性善、倡四端,养浩然正气,筑大丈夫品格,兼济天下,推行仁政,以期建立一个和合大同、天下太平的美好世界。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颇为相近,“战乱割据,礼崩乐坏,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身处复杂的环境,心中存留的是仁、民本、天下,而个人的衣食荣辱、富贵爵位在推行的大道面前变得微乎其微。以一人之力肩负天下安危的抱负,不仅赢得了世人的推崇和尊敬,更奠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气节和精神品格。“天不生孔子,万古长如夜”“孔子之后,惟孟子知道”,他们从修身做起,崇尚道德教化,宣扬修身养性之风。孟子讲:“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孟子认为仁者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环境下,大力弘扬传统美德,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种使命担当精神和下学上达的进取路径,时至今日,仍振聋发聩,砥砺人心。
四、涵养道德理性的人性论
东夷文化有个传统习俗就是夷俗仁,其风俗仁厚淳朴,对鲁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而邾(邹)则保留很多周礼的礼乐教化的内容。《汉书·地理志》记载鲁国的情况:“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这充分表明,对礼义道德的崇尚是邹鲁文化的一贯传统。正是在这一传统的熏陶下,邹鲁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高尚的圣贤之士:孔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孟子有道德胜于王者之乐。这种超越时空的心神怡乐,正是源自高尚的道德信念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在这些邹鲁先贤的努力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才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几千年前,世人认知相对蒙昧的时代,信仰的归处尽在“天”,人们将信仰的归处、将命运归结为“天道”。孔子却能极力主张“为仁求己”,极力宣扬人自我的精神价值,极力塑造培养人内在的德行修养,这便是后来儒家知识分子宣扬的“内圣”“修己以敬”的学问。“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内修自己,合乎义,忠乎礼,反求诸己,求于内在仁,便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凶,与日月合其明”的天、地、人三才并立的境界,这样就不用再把遥不可测的时命寄托给天。这种高扬自我主体的精神,在儒家思想创立之初,就与佛道两家思想区别开来,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价值导向。
孟子进一步把“仁”铺张开来,孟子言必称尧舜,因为尧舜能达德故能近于道;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世人应该内求于己,不断扩充自己的本心,便能养浩然之气,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可成就大丈夫的人格,就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便会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情怀,更进一步便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情。由性善铺张开来,去尽性(养内在善端),便可知命(了解自己的时命),以知天(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孟子讲,人生有三乐,其中之一就是“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地”,因为内在的道义才是天地间认同的价值,是人生应该追求的乐趣,才能达到“能仕则仕,能止则止”“不怨天,不忧人”的境界。“内圣外王”由自己内在修身达到一定程度,便会有兼济天下的担当,必然能入仕为官,做一个身正心安不为私利着想的正直之人,即便是处江湖之远,也会忧其君,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内在德性扩张而出的使命担当就不会变。探本溯源来讲,从孔子到孟子,追求的一直是人世间的道义,为官从政、执政为民,不过是道义开出的使命责任。道义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掌握自我,而精神上失去方向,便会经不起诱惑,没有内在价值归一。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成仁,便是因为追求道义,才能心安,才能无愧立于天地之间。
这种追求自我(内在德性修养)、成就无我(忘记一己之私)的人性论,为乱世之中的生民树立了一道理想的丰碑和进取的价值取向,而孔子、孟子那种身处乱世辗转弘道的情怀,更是赢得了百世的敬仰,无愧于“圣王”“亚圣”之名。
邹鲁文化是先贤伟人们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引导人们当下幸福快乐的风向标识,是鼓励世人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是涵养公民道德理性的重要源泉,是执政安民,兴邦济世的重要法宝,更是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重要写照。让邹鲁文化这株千年古树开出灿烂的新花,成为我们涵养人文价值的源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