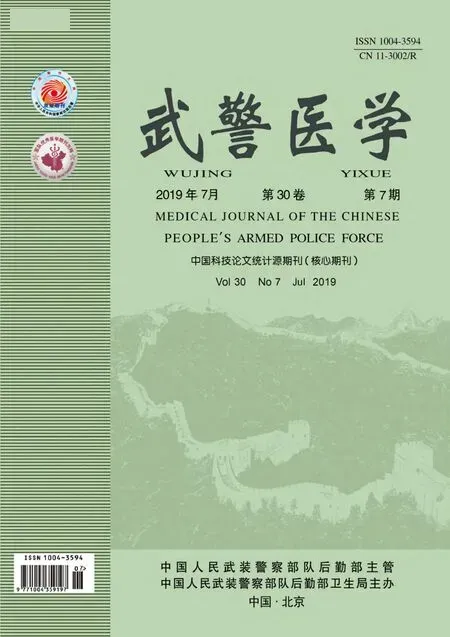创伤性脑损伤基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程世翔
创伤是指机械力能量传导至人体后造成机体结构完整性破坏的损伤,其中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亦称为颅脑创伤)在神经外科学和创伤外科学中均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已成为全球青壮年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急救医学及危重症监护技术的迅速发展,各项救治指南的相继出台和完善,极大促进了TBI临床救治水平的全面提高,救治成功率大幅提升,TBI总体病死率已由50%降至30%,其病理机制和神经再生修复的基础研究也取得可喜成果,为临床救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然而,TBI病死率仍高居各类创伤之首,其中重型TBI(severe TBI,sTBI)患者仍有30%病死率,10%轻型TBI患者会遗留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此外,我国TBI基础研究与发达国家比较严重滞后和不足,国内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差异明显,临床救治水平也参差不齐。基于此,笔者就TBI最新流行病学特点、国内外救治指南进展和基础研究现状进行介绍,并对研究热点和研究新方向加以展望,以期提高我国TBI救治水平。
1 流行病学特点
2016年全球新增TBI 2700万人,发生率为369/10万(比前30年增长3.6%),致残率为111/10万,主要致伤原因是坠落伤和交通伤[1]。全球不同地区TBI发生率差异显著,高发生率地区主要位于中欧(857/10万)、东欧(772/10万)和中亚(495/10万)。2016年我国TBI发生率为313/10万,与美国(333/10万)、日本(263/10万)等国家相比差别不大,但与过去30年比较上升达33.1%,主要是由于交通事故伤(占比53.0%)和坠落伤(占比28.6%)所致[2]。
2 临床救治指南和专家共识
近十余年来,各国神经外科医师和科研人员对TBI的病理生理进程和临床救治方案进行持续探索,陆续颁布和完善了一系列救治指南和规范,主要包括:2007年美国sTBI救治指南(第三版)[3]、2012年日本sTBI救治指南[4]、2012年美国轻型TBI救治指南[5]、2017年美国sTBI救治指南(第四版)[6],以及2018年美国儿童轻型TBI诊断治疗指南[7]。该系列指南逐步健全了全球TBI临床规范化诊治体系。在此期间,我国学者和临床医疗工作者也积极开展了结合我国TBI特点的临床规范化救治技术,陆续于2008年发布《中国颅脑创伤病人脑保护药物治疗指南》以指导合理应用脑保护药物[8],2009年发布《中国颅脑创伤外科手术指南》以规范手术方式[9],2010年发布《神经外科危重昏迷患者肠内营养专家共识》以指导肠内营养支持[10],以及2011-2015年发布的《中国颅脑创伤颅内压监测专家共识》《颅脑创伤去骨瓣减压术中国专家共识》和《颅脑创伤长期昏迷诊治中国专家共识》[11-13],使我国TBI救治取得了长足进展。随着救治指南的不断修订,不同版本的救治标准也不尽相同,这充分表明TBI诊治的复杂性,我们只有对最新指南进行充分理解和合理应用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工作。
3 研究热点与发展方向
基础研究是开展临床工作的试金石或是风向标,临床工作的不断进步与完善离不开相关基础研究提供的理论和实验证据,因此了解TBI基础理论研究热点和动态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外在脑科学尤其是TBI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研究方向涉及模式动物TBI模型建立、病理学分析、细胞与代谢变化、基因及其基因组学改变、蛋白质及其蛋白质组学改变等多个方面,期盼能获得可喜的成果,开拓TBI的研究新思路。
3.1 基于体液生物标志物的TBI诊断和治疗新靶点研究 临床上诊断TBI严重程度和预后指标主要包括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及临床症状等,然而这些指标的评价标准相对简单,与患者自身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主观判断会造成诊断的偏倚,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是对客观评价TBI的重要补充方式[14]。目前TBI体液生物标志物的样本类型主要包括:(1)脑脊液,可直接反映脑内生化改变,但获得途径为腰大池引流或脑室外引流,属于有创检测;(2)血液,优点在于较脑脊液更易于获取,但存在浓度较低、受高丰度蛋白干扰、中枢神经系统(CNS)特异性低等缺点;(3)其他体液(唾液、尿液、泪液等),有研究指出,部分CNS来源的蛋白(例如,神经突触核蛋白-α)可能最终分泌入唾液[15],但浓度与TBI病理生理进程的关联性及其具体机制还知之甚少。
目前已知的某些生物标志物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TBI患者损伤程度及预后康复等情况,例如:S100β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可评估sTBI患者预后,但对轻型TBI预后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不高[16];TBI后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水平的升高与颅内压增高、GOS评分低、脑灌注减少等相关[17];髓磷脂碱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MBP)、Tau蛋白等血清学指标均在TBI的动物及临床实验中被研究,对预后的判断也有一定指导意义[18, 19]。然而,上述生物标志物均为针对某一类神经细胞(神经元、神经轴突、少突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等)损伤或TBI的某一种病理生理进程(血脑屏障通透性破坏、神经炎性反应等),目前尚无任何一个体液生物标志物被很好地应用于临床,依然缺乏大规模、系统化的研究与验证。
3.2 基于炎性反应和可控性坏死的TBI致伤新机制研究 TBI急性期CNS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分子事件,其中神经炎性反应是继发性脑损伤病理改变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既往研究认为TBI后受损脑组织通过释放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等炎性因子加重神经细胞继发性损伤,而TBI患者脑内小胶质细胞通过表达C-C趋化因子(C-C chemokine)募集外周循环中的炎性细胞,后者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入脑参与TBI后的炎性反应,加重神经功能损伤。然而,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性反应在促进神经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阐明和揭示TBI后炎性反应的具体分子机制对临床诊断、预后评判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研究表明,TBI通过激活细胞死亡信号通路,加剧神经细胞死亡、炎性反应和神经功能损害。如何减少细胞死亡进而保留更多的神经元,以获得更好的神经功能预后是TBI的研究重点之一。传统观念认为,细胞凋亡是调控细胞死亡的主要方式,细胞坏死不可被调控。然而,可控性坏死及其调控通路的发现和确认,为逆转细胞死亡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潜在的治疗途径。近期研究发现,可控性坏死是TBI早期细胞死亡的主要形式,具有可逆转、能延迟的特性,能够扩大TBI治疗时间窗,其中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3,RIP3)是调控炎性反应和可控性坏死的关键蛋白,通过RIP3/TNF-α信号通路募集下游底物MLKL并使其磷酸化,破坏细胞膜完整性,导致细胞膜破裂和炎性反应[21]。TBI后24 h内给予RIP3特异性阻滞剂Nec-1干预可明显降低TBI小鼠坏死细胞数目,发挥明确的神经保护作用[22],但可控性坏死和炎性反应的相互作用关系目前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深入研究可控性坏死的分子调控机制,有望为TBI治疗提供更多的潜在新靶点。
3.3 基于定量蛋白质组学的TBI检测新技术研究 自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完成后,生命科学的研究进入后基因组时代,其中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以其高通量、高覆盖和高精度特性成为蛋白功能研究的利器。在此基础上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系统发现某种疾病中改变或失调的信号通路,可阐释该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由于CNS的复杂性导致其系统性研究受到很大阻碍,而包括蛋白质组在内的多种组学技术正在快速推进神经科学研究相关领域的发展[23]。在TBI研究中,通过应用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iTRAQ)结合质谱定量策略能够对受损细胞或组织蛋白进行精确定量,重塑TBI激活脑内分子的全景细胞网络,并结合表型变化趋势,验证关键调控因子和效应分子的表达丰度变化[24]。然而目前,该技术多应用于TBI细胞模型和动物模型中,但随着该技术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后续蛋白质组学技术有很大机会被应用于临床研究,预计该新技术方法必将加速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筛选,也会在TBI严重程度分类及临床精准治疗方面提供支持。
4 总结与展望
TBI后脑组织和神经细胞经历缺氧、氧化应激、炎性反应、细胞凋亡、组织坏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及其潜在的分子机制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网络。以往的基础研究对TBI病理生理进程有了更加深入地认识,但目前对TBI的临床治疗贡献仍然十分有限。今后的基础研究应更多向临床转化迈进,并且能够以整体观来分析和解决TBI发生、发展及预后问题,更为全面深入地研究TBI后神经细胞坏死、氧化应激损伤、线粒体损伤、生物标志物等诸多问题,同时也要重视干细胞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相信在未来,基础研究的成果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和提高TBI临床救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