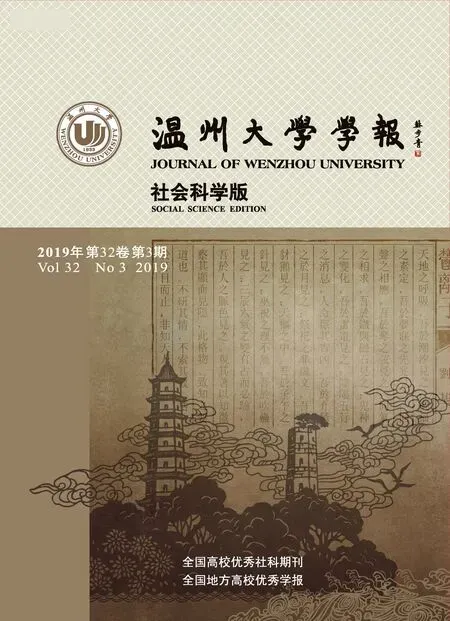夏承焘先生所编词选二种叙录
陶 然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温州夏承焘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词学家,以“一代词宗”之名享誉学林。夏先生词学之深厚宏阔,学者所论甚多。其实,夏先生著述的体例也是很丰富的。有集大成式的古籍整理著作如《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有开创词人谱牒之学的《唐宋词人年谱》,有专题论集如《月轮山词论集》《唐宋词论丛》等,有日记体的记事论学之作如《天风阁学词日记》,有论词绝句组诗如《瞿髯论词绝句》。此外,夏先生还编选了多种类型的词选,其中如《唐宋词选》《金元明清词选》略带普及性质,《宋词系》则有专门的针对性和时代特点。相比之下,《永嘉词徵》和《域外词选》两部选本,特色尤为鲜明,但前者唯有钞本流传,寓目者不多;后者涉及域外词,虽曾出版,然关注者亦尠。兹就此二选本,略加叙录,谨作新版弁言,以供读者参证。
一、《永嘉词徵》
《永嘉词徵》,又名《温州词徵》,是夏承焘先生早期所编的一部乡邦文献选录。作为温州本地人,夏先生的学术活动肇始于此,瑞安孙诒让玉海楼的藏书及其学术、温州重视实学的传统、温州师范期间的学词经历等,都造就了夏先生对温州的浓厚的乡邦之情。直到晚年居京时,虽他仍然时常怀念雁荡山水、永嘉故人。这部《永嘉词徵》虽是夏先生早年所编选,但数十年间他不断增补,未曾忘怀,从中可以体会到他深厚的故土之思。
编选一地之古今词作,为某地“词徵”,这在晚清至民国时期颇为流行。如朱孝臧《湖州词徵》、叶申芗《闽词徵》,乃其著名者。而如周庆云《浔溪词徵》、薛钟斗《东瓯词徵》等,虽稀见而不彰,但也往往颇具地方文献价值。而且这些郡邑性的作品汇编,往往也成为创作群体的汇集动因甚至文学流派的形成要素之一。温州地区自明清以来向来就有重视乡邦文献的传统。从明王朝佐《东嘉先哲录》、陈挺《东瓯乡贤赞》、姜准《东嘉人物志》,到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孙衣言《永嘉丛书》18种、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14种、黄群《敬乡楼丛书》38种等,一脉相承,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文献自觉性。夏承焘先生编《永嘉词徵》就是一部宋代至清代、近代温州地区文人词作的汇辑词选。
在夏承焘《永嘉词徵》前,欲为历代温州地区词作进行汇辑的有薛钟斗于1916年至1918年间所编之《东瓯词徵》10卷,收80家682篇作品,以及1921年陈闳慧、郑猷拟议编撰之《瓯括词综》[1]。但前者体例不周,后者未曾成书。据夏承焘先生日记所载,辑录《永嘉词徵》之拟议始于 1935年,夏先生最初欲将该书分为内外编,“内编登地人,外编登外人有关永嘉之作。前拟作《浙东词徵》,犹嫌范围过大也”[2]379(1935年4月6日日记)。不过现存《永嘉词徵》稿本,并无所谓“外人有关永嘉之作”,在夏先生后来的日记中,也没有提及另有所谓“外编”。其编撰工作主要在1936年。兹将该年日记中涉及此书编撰者,条列于左:
二月廿二日:作冷生复,告欲作《永嘉学年谱》,倡议为《永嘉词徵》。托提遗著会征众意。[2]426
七月廿五日:午后三时往中山公园开乡哲遗著委员会,晤乐清高性朴先生及许蟠云专员,委会本年底结束,同人推予辑《永嘉词徵》亦须年内结束。[2]455
八月一日:著手选《永嘉词徵》,体例一仿《湖州词徵》(宋元明辑、清人选)。
八月三日:午与孟晋合宴诸师友,到刘次饶老,刘贞晦丈、子植、天五、笃仁、介夫、伯、冷生。宴散至中山公园选《词徵》,得潘自、陈虬、张铭、林培厚等数家。[2]456
八月四日:午后与孟晋、天五往图书馆,借《宋元名家词》二册,《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一册,《平阳志》《温州府志》各二册,选《词徵》。[2]457
八月十二日:札《词徵》,阅《平阳志》。
八月十三日:札《词徵》。
八月十五日:早过冷生取书作《词徵》。
八月卅一日:校《永嘉词徵》。[2]460
九月一日:早校《词徵》。
九月二日:校《词徵》。
九月五日:校《词徵》。
九月六日:钞《词徵》。
九月八日:早订《词徵》。[2]461
九月十日:校《词徵》。
九月十一日:抄章元应词完,连《省愆词》及《永嘉词徵》明人各词,寄还叔雍。
九月十二日:抄徐班侯词入《词徵》,即送还冷生。[2]462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夏先生编撰此书是应所谓“乡哲遗著委员会”所托。按该委员会全称为“浙江省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其背景是1932年5月,浙江省民政厅通令各县市政府设文献委员会,“以征存境内方志图书古物照片等,记载要事,藉为异日修志之甄采”。永嘉区遂成立第三特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后改名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以保存乡先哲遗著、发扬乡土文化为宗旨”,初由瑞安沈权出席第三特区行政会议时提议组织,于 1935年4月5日召开成立会。遗著会函聘夏承焘、陈谧、宋慈抱、陈仲陶、孙师觉诸人为特约编辑。考用的六位缮写员是永嘉徐志良(万里)、李作宇(佐武)、夏书(辛农)、曾羽中(字号不详),瑞安胡铮民、张樨竹①以上关于永嘉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之记载,引自卢礼阳《〈征辑乡先哲遗著事〉补谈》,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4683490102ve1g.html,2015-3-26。。由于该会将于1936年底结束,故夏先生编撰此书始著手于8月1日,至9月中旬即基本成稿。体例则仿照朱孝臧《湖州词徵》。其后从1937年至1948年,在夏先生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处提到《永嘉词徵》的记载,如:
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审计工作面临的环境和形势都非常复杂,只有结合实际,从健全制度、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和人才队伍建设等角度着手,提高专业化、连续性审计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审计工作应有的功能,有效规范商业银行经营行为,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二日:过冷生家看破书,得郑蕙《素心阁集》,有一词可入《词徵》。[3]21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孟晋送来《小三吾亭词》一册,鹤亭夫人黄瓯碧(曾葵),有词六首,可入《词徵》。[3]23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早,贞晦翁、孟晋来,贞晦翁欲注苏辛词,允为予序《永嘉词徵》。[3]38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五日:冷生从陈穆厂处抄得孙蕖田先生《盘阿草堂词》一卷来。词仅八首,在梅溪、草窗间,首首可选。其女杨晨跋,谓黄宪清《续国朝词综》曾选先生词,不知即此九首否也。冷生属录入《永嘉词徵》。[3]153
一九四零年二月四日:吴雯来,共晚饭。托其抄《五峰词》,入永嘉词徵。②本条原书有误,今据浙江大学所藏夏承焘日记手迹订正。另它条有与手迹略不同者,亦径据手迹订正。
一九四零年二月九日:早佩秋先生来,与商量《永嘉词徵》体例,求为一序。[3]176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廿七日:以《绝妙好词》校《永嘉词徵》。[3]249
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早雨农翁来招午宴,同席许蟠云、萧冀勉副军长,粤人、贞翁、冷生,蟠云欲为予印《词徵》,不见七八年矣。③此条原书无,今据浙江大学所藏夏承焘日记手迹补。
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发叶遐庵上海函,谢其赠书画集,告将录出《永嘉词徵》中乡人词入其《清词抄》。[3]642
在这十余年间,夏先生不断补充完善这部著作,但一直藏于箧中,未及面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还提及:“午后胡福疇(永嘉教育局)来,取去《永嘉詞徵》稿,云永嘉近编乡土教材,需此取材。”[4]又1973年8月23日夏先生开列了《月轮楼词学丛书》的拟目,其中《温州词徵》列于“未出版”的第6部,并注云:“已成。”①据夏承焘日记手迹。可见直到夏先生晚年,对于这部著作仍然是十分重视的。
今存《永嘉词徵》稿本②夏承焘.永嘉词徵.稿本.共4册:
第一册注“宋元人专集”,收录夏元鼎《蓬莱鼓吹》、卢祖皋《蒲江词稿》、林正大《风雅遗音》、李孝光《五峰词》。
第二册注“宋元明”,所录有甄龙友、王自中、王十朋、许及之、叶适、蔡幼学、徐照、赵师秀、薛师石、赵汝回、戴栩、赵汝迕、赵希迈、曹豳、徐俨夫、薛梦桂、潘希白、薛嵎、曹穞孙、赵处澹、无名氏、郑僖、吴氏女、张著、史伯璿、姜伟、黄淮、虞原璩、章纶、章玄(元)应、朱谏、王瓒、王叔杲、林占春,计三十四家。
第三册注“清”,所录有张子容、张铭、徐丙乙、林培厚、黄朝珪、康应薰、徐德元、顾讷、张梦璜、祝学贤、苏椿、潘自疆、潘福纶、张凤慧、潘其祝、叶芝寿、谷培宸、管甡、陈越英、赵钧、孙衣言、孙锵鸣、黄体立、黄绍箕、黄瓯碧、项瑻、张硕、孙诒让、宋衡、钱蕙纕、谢香塘、郑蕙、洪炳文、王岳崧、陈虬、徐定超、陈寿宸、陈祖绶、黄曾葵、薛钟斗、曾廷贤,计四十一家。
第四册注“附录、存疑、题跋、待访”。其中附录三家:蒋淑英、黄淮、黄中;存疑七家:释道济、张惠、释超智、周长濬、陆进、任文仪、诸定远;题跋有孙应时《蒲江诗稿序》等数十篇。所谓“待访”则未见。
原稿第一册封面记云:“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装于西湖。瞿禅。”全书为誊清稿,抄于“浙江省永嘉区徵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专用稿笺上。其中第一册李孝光《五峰词》旁注:“此数页,无闻一九四一年抄于上海。”可知这六页为夏夫人吴无闻先生所抄,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专用稿笺上。但书中眉批、补注等笔迹,明显出自夏先生之手。事实上,原稿中亦有缺页,如第2册第3页辑自《全芳备祖》之《暗香梅》词前,显有漏简。书中亦有错简处,如第二册薛师石小传前后两见等。但夏先生所作眉批、校订、考证等按语或说明,却颇有研究价值。这也是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的用意所在,以保存原稿原貌,可供研究者进一步参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原题为《永嘉词徵》,但旁有钢笔批注云“改名《温州词徵》”,大概是夏先生晚年拟将书名由旧称之永嘉改为温州。考虑到该书在 1936年即已基本成形,这次影印出版,仍名之为《永嘉词徵》。
二、《域外词选》
隋唐以来,燕乐盛行,声诗与曲子词成为唐代遍及天下的音乐文艺形式。这种盛况和文人填词的热情互相激发,遂促成了从中晚唐开始的词的繁荣时代。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文艺,词沟通了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群体和以市井民众为代表的流行文化群体,涵盖了宫廷教坊和青楼北里,活跃于酒楼歌肆和瓦舍勾栏,传唱在山程水驿和闺阁孤馆,构成了唐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词也是唐宋时代文化输出的主要内容。东亚大陆的中原王朝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的密切文化交流和汉字文化圈的影响,使得词也和中国传统的诗文经史一样,远播至域外。词在这些域外邻邦的流衍,促使其文人仿效操觚,留下了数量颇丰、成就不低的域外词。
域外词史的开端几乎与中国词同样久远。号称“唐词之宗主”的张志和《渔歌子》约作于唐代宗大历九年至十二年间(774-777),而仅仅不到50年之后,日本平安时代的嵯峨天皇在弘仁十四年(823)即写下了唱和张志和的《渔歌子》词 5首,同时之有智子亲王、滋野贞主奉和亦作有《渔歌子》7首,后收入滋野贞主所编《经国集》中。日本兼明亲王(914-987)作《忆龟山》2阕,效白居易《忆江南》,其距离白居易的时代也不过数十年。这都说明中国的文人词在兴盛之初,很快就能渡海而东传,并引发域外词人的模仿,这种交流的速度,以“桴鼓相应”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又北宋雍熙三年(986),匡越禅师吴真流写出了第一首越南词作《王郎归》,其后的日本五山时代(1192-1602),日本词进入了沉寂期,越南词坛也长期静默无声。然而在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却开始接受宋词的影响,由此开启了高丽朝鲜词的兴盛时代,域外词的重心也由日本列岛转移至了朝鲜半岛。《高丽史》卷10《宣宗世家》载宣宗六年(1089),高丽宣宗王运制《贺圣朝》词(实为《添声杨柳枝》),此为现存所见高丽填词之始。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颁大晟乐,三年之后即赐大晟乐与高丽,还专门派遣乐工歌伎带上新乐器和新乐谱赴高丽教习传授音乐。《高丽史》的《乐志》中所记录的数十阕词,其中就有许多传播至高丽的柳永、欧阳修、苏轼等著名中国词人的作品。正是这样频繁而深入的音乐文艺交流,使得高丽出现了后期填词的繁盛局面。尤其是至元朝,与高丽国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后,大批高丽文人赴中原游历甚至应举,浸淫于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其所接触的又往往是中原第一流的文坛巨匠,遂能涵养出李齐贤这样号称“东方一人”的伟大词人。高丽之后的朝鲜时代,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为紧密,许筠、金烋、曹友仁、赵冕镐等文人登上词坛,或清朗超迈,或绮丽柔媚,均显现出中国词对朝鲜词的巨大影响力。清朝建立后,朝鲜虽仍居藩属国的地位,但在文化层面却长期对清朝有拒斥感,同时韩字创制后,用韩字吟咏的时调歌辞渐趋流行,这使得朝鲜词的发展渐趋衰落。然而此时正值日本的江户时代,日本词却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域外词的重心又回到了日本。从林罗山家族到德川光国、从关西的田能村竹田到关东的野村篁园、日下部梦香,他们笔下的词,在词调的丰富性、分韵咏物的熟练度、唱和雅集的频繁以及词作艺术水准的提高等方面,均有长足进步。至日本明治时代,森槐南、高野竹隐和森川竹磎等大词人的出现,更将日本词推进至空前的高度,其中如森槐南在其父森鲁直的影响下,词尤为杰出,其被黄遵宪称为“首屈一指”的“东京才子”,而到 19世纪越南词坛上也出现了阮绵审、黎碧梧、陶梦梅等代表了越南词繁荣的大词人,阮绵审即白毫子,他的《鼓枻集》几乎就占据了越南词的半壁江山。
夏承焘先生《域外词选》就是最早的一部以上述域外词为编选对象的词选。夏先生在《前言》中对于该选本的编选缘起和意图有明确说明:“予往年泛览词籍,见自唐、五代以来,词之流传,广及海外,如东邻日本、北邻朝鲜、南邻越南各邦的文人学士,他们克服文字隔阂的困难,奋笔填词,斐然成章,不禁为之欢欣鼓舞。爰于披阅之际,选其尤精者,共得一百余首,名之曰《域外词选》,目的在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5]这部词选分四个部分,分别选录了日本词 8家 74首、朝鲜词1家53首、越南词1家14首以及作为附录的李珣(世居中国的波斯人后裔)词54首,夏先生在《前言》中还移录了其自作的7首论域外词人的论词绝句,以见品评之意,其中日本词部分由张珍怀注释,朝鲜、越南词及李珣词部分由胡树淼注释。自该书初版近四十年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早有定论。今日视之仍然堪称经典之选。对普通读者而言,书中选录之精当、注释之明瞭恰切,令人披阅之际,既富趣味,又可增强鉴赏能力,而对于专业研究而言,这部词选在在学术上的启示意义是尤为巨大的。
清人词话中,已有部分关于朝鲜词人的记载与评述,20世纪初朱孝臧《彊村丛书》中就收录了高丽李齐贤的《益斋长短句》,这是高丽词集在中国成规模地传播之始,使得中国的词学研究者开始对高丽词人有所了解,但直至 80年代夏先生的这部《域外词选》问世,才标志着治词学者开始正式注意域外词这一研究领域,从而在传统词学研究疆域之外开辟了新的天地,甚至域外词这一概念亦可谓启始于此书。现在的研究者所能掌握的文献当然远远多于当年夏先生编撰此书之时,如高丽朝鲜词目前已知的就有一两千阕,除李齐贤之外的优秀词人也颇为不少,越南词的存世数量也超过了两百阕,但正是这部《域外词选》启发了学者思考域外词的意义与定位,思考域外词的多重价值。域外词既是中国文学之域外影响的直接表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强大辐射性;同时又是中国词的重要参照系,生动地体现出域外词对中国词或反射或折射、或吸纳或拒斥的复杂性。域外词的研究和中国词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域外词选》的经典启示性还体现为引发学者关注不同地区域外词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对于中国词,域外词当然有其整体共性,但不同地域的域外词之间,因与中国的不同关系以及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音乐、文学、礼俗甚至语音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上还是有极大差异的。《域外词选》首次将日本、朝鲜、越南并列作为域外词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书中对于越南词的选录,揭示出中国词的传播方向从东亚地区涵盖至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存在。又如书中附录了五代词人李珣的词作,李珣是波斯胡人的后裔,但世居中国,接受汉文化教育,其文字水准与中国优秀文人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作品早已选入《花间集》,是居于中国的域外人的词。大约因其所作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域外词,故阑入附录。实际上到金元时代,来自域外其他民族的词人如色目词人等并不稀见,他们和李珣一样,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域外词与中国词的连接点。不同地区的域外词,其繁盛程度和创作水平固有高低,但在宏观层面却反映了历史上以东亚为核心的亚洲地区的文化交流之结构和方向。这就要求学者不能仅仅孤立地考察某一地区的域外词,而应将域外词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又要充分认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
以夏先生的《域外词选》为基础,实际上还有不少研究工作是可以继续推进的。如广泛搜辑域外词的所有作品,详加校订、笺释、编年、考证,纂为《域外词全编》;完整汇辑域外词评词论序跋等相关文献,纂为《域外词学资料汇编》;研究中国词与域外词的交流传播、域外词的若干核心问题,撰为《域外词通论》;研究域外词的发展沿革,考察域外音乐文艺的流变、分析域外词的文学特质等,撰为《域外词史》。这些方面,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及之,论著也在不断涌现,相信《域外词选》所引发或启示的这些研究方向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继承夏承焘先生在该书中所体现的精审眼光、弘阔格局,进一步结出坚实而丰硕的学术成果,是后学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