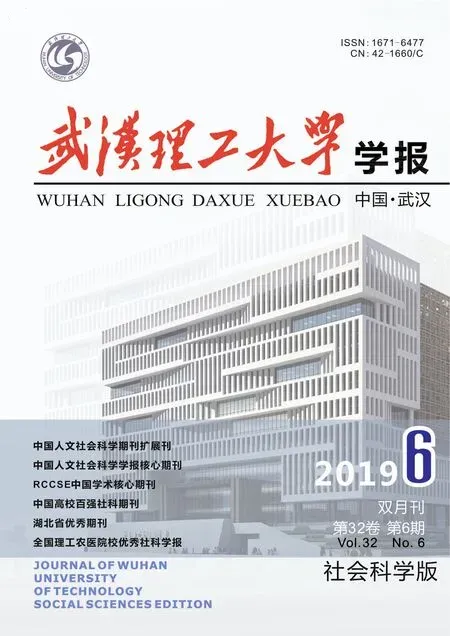中外文化对话中的中国声音:2014-2018年《外国文学研究》“中外学者访谈”话语解读
甘文平, 唐一凡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019年2月,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的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此前三卷已与中国读者见面,只有最新的一卷(第4卷)未被译成中文。正如该书的扉页所言:“‘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后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①无独有偶,“中外学者访谈”是世界文学杂志《外国文学研究》中持续而富有特色的栏目②,它也是国内同类刊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栏目,其理论性和跨学科性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它与《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交相辉映,为读者呈现了两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精彩学术话语。本文收集了5年来《外国文学研究》中“中外学者访谈”的全文,总结并简要分析了其中“中国声音”的三个主要特征——高阶性与国际性、宽广性与集中性、时代感与穿透力。本文最后针对进一步认知这一特殊文学话语提出了几点建议,供广大同仁们思考。
一、 “中国声音”的高阶性和国际性
“中外学者访谈”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声音”的高阶性和国际性,形成了一曲中外学者同台演出的响亮“二重唱”。从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类学术期刊来看,2004-2013年的10年间,《当代外国文学》刊登了31篇“访谈”,这对于一个季刊杂志来说实属不易,但是2014-2018年的5年间,《当代外国文学》只有8篇“访谈”。2004-2013年的10年间,《外国文学》只刊登3篇“访谈”,2014年-2018年的5年间《外国文学》共有4篇“访谈”。2004年至今,《外国文学》只在2007年和2008年开设了此栏目,共刊载了12篇,形成了短期的高峰,但此后就没有了。2004-2013年的10年间,《外国文学动态》共发表了31篇“访谈”,很是壮观,但此后的5年共发表了10篇。2004年至今,《外国文学评论》从未开设此栏目。与以上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期刊相比,自2004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开办的“中外学者访谈”栏目几乎从未中断过中外学者对话的报道和刊文,这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十分惹眼,当属唯一。比如,2004-2013年的10年间,《外国文学研究》共发表了50篇“访谈”,平均每期(一年六期)将近1篇,在2014-2018年的5年间,它共发表了30篇“访谈”,即每年6篇,平均每期稳达1篇。
“中外学者访谈”栏目所体现出的“中国声音”高阶性和国际性特征的表现之一是5年来“访谈”的访谈者一方都是高职称和高学历的拥有者。据统计,这些“访谈”文章的作者来自全国23所高校,覆盖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5大地区。访谈者都是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具有博士(或者在读博士)学位,且大多是某个学术领域的骨干,或者是某个学科里的领军人物。此外,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或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主持人,几乎都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这些访谈者学术功底扎实,学术成果丰富,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得到接受访谈的外国学者的认同。
“中外学者访谈”栏目所体现出的“中国声音”高阶性和国际性特征的表现之二是受访者大多是国际学术高地的占领者以及学术权威话语的发出者。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挪威、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丹麦、匈牙利等国家,都是各个领域享誉国际的知名学者,并且大多在世界著名的学术刊物担任重要职务,或者是洲际院士/皇家学会成员以及重要协会负责人、重大理论的创始人或者研究专家,在世界高水平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的受访者还身兼数职。其中,部分受访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部分受访者身兼多种学术头衔,如,彼得·海居教授是匈牙利佩奇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A&HCI收录)》主编,尤里·塔尔维特教授是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世界文学教授、世界文学学科主持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协会副主席,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比蒂教授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阿卡迪亚国际文学文化学刊》主编,伊恩·邓肯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苏格兰文学研究协会副主席、爱丁堡皇家学会成员、A&HCI知名杂志《表述》的编委。中国学者与他们进行学术对话,既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开放心态与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积极态度。
二、 “中国声音”的宽广性与聚焦性
“中外学者访谈”的第二个特征是“中国声音”的宽广性与聚焦性。纵观《外国文学研究》5年来刊发的30篇“访谈”,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发出的“声音”涉及面十分广泛,他们提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国别与区域文学、族裔文学与儿童文学,以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传记、书信等)、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文学流派、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政治、文学与伦理、文学与经济、文学与音乐、文学与视觉艺术、语言学、叙事学、文学与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与自然、文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等。这些问题既有很强的理论性,也有很强的实践性。它们之间有时相互交叉,彼此勾连,形成了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辐条式”的广义维度的学术“轮圈共同体”,极大地拓宽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视野。
与此同时,“中国声音”兼顾了话题的集中性和探讨的深入性。第一,从单个“访谈”的角度看,以下3篇“访谈”颇值得外国文学研究同行关注。第一篇是《儿童文学研究的现状、趋势和热点——玛丽娅·尼古拉耶娃教授访谈录》。尼古拉耶娃教授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成人作家和儿童读者之间那种不平等的社会与认知地位;不管是为成人还是为儿童创作的所有伟大艺术,都因其有关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知识而具有教育性,但因儿童的认知能力比成人弱,所以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更具有教诲价值”[1]。该“访谈”对一直不太受重视的儿童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第二篇和第三篇分别是《迪兰·托马斯诗歌的威尔士性与过程诗学:约翰·古德比教授访谈录》和《苏珊·桑塔格的作品的艺术、风格及现代性意识:利兰·伯格访谈录》,它们都是中外学者在集中讨论“第三方”,这种现象几乎不会出现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在《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外学者访谈”栏目中也不多见。这两篇“访谈”选题高端,主题集中,理论性强,实践性强,是中外学者研究以上两位作家的必读文献。本文以为,以上两种“声音”是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的。
第二,从“访谈”的整体内容来看,“访谈”主题的集中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对“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以及与之相关话题的关注上。30篇“访谈”中有8篇与该话题有关,受访者来自匈牙利、美国、爱沙尼亚、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可见该主题已是世界学者共同关心的焦点之一。郝岚教授向哈佛大学的达姆罗什教授提出如何“重振世界文学”时,达姆罗什认为必须视野开阔,放眼各洲和各国,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更广泛地学习和思考以及教学和科研同步走[2]。匈牙利佩奇大学海居教授在回答张甜博士关于比较文学的“死亡与再生(death and rebirth)”的问题时说道:“学科之死”实际上是一种建议,即学者们应该采用包含一切研究方法——特别重视以前被忽视的领域和语言、特别重视地球上所有文化相互之间的联系、特别重视为受压迫者辩护的道德上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多国合作研究的大时代。”[3]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比比教授对类似的问题发表了如下看法:雷内·韦勒克写到的“比较文学危机”是把比较简化为影响研究,变成一种“借记系统”——强化而不是解构语言之间的传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统治语言边界巡查的“跨越”时代[4]。以上三例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同时关注比较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外国学者在认同中国学者的“声音”的同时提出要打破传统的二元模式,开拓学习和研究视野,注重学科之间的融合等建设性的建议。以上问题是当下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研究的前沿话题和热点话题。
三、 “中国声音”的时代感与穿透力
“中外文学访谈”中“中国声音”的第三个特征是“中国声音”的时代感与穿透力。中国学者能够敏感地抓住外国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切中问题的要害,共同直面问题本身,把握问题的实质。
中国学者就创伤理论的相关争议性话题访谈了当今创伤理论的权威学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凯茜·克鲁斯教授是当今西方最杰出的创伤理论专家之一,她的《创伤:探索记忆》等专著是我们了解创伤理论和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创伤主题的必读书目。在被问到“美国的创伤研究现状”时,克鲁斯说:“我不喜欢‘创伤研究’这个词语。我的理解是:它用于描述某种研究和实践或者询问形式时是有用的。但是创伤有某种力量,某种表演和文学力量。它是不可捉摸的……尽管‘创伤研究’可能是不能避免的,但它的问题是当它和其他许多理论结合在一起时就变成了一个概念……创伤肯定具有一种穿越不同文本、不同人物个体、不同文化的力量。研究文学和科学创伤的最好作品总是令人吃惊的,总是叙说你以前不知道的新东西,尽管它与你认为的创伤有某种交叉”[5]。克鲁斯区别了“创伤研究”和“创伤”的不同含义:前者是一个概念,带有共性特点;后者是一个特殊力量的个体,具有特殊性和不可言明性等特征。这对我们厘清相关的概念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此外,克鲁斯还就当下学界关于“创伤理论”中的“表征性”与“反-表征性”之争以及“消失的历史”的内涵作了独特的阐释。总之,该篇“访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时代气息,是“中国声音”话语体系中的佼佼者。
同样地,中国学者就以上相同话题从不同视角与欧洲知名学者对话。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讲席教授弗拉基米尔·比蒂则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回答了中国学者关于创伤理论研究的现状与面临的新问题。他不完全赞同中国学者提出的创伤理论经历了四个阶段——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创伤理论、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创伤理论、种族/性别创伤理论、文化创伤理论。他认为,创伤研究历史悠久,我们已经将创伤概念与类似于奴隶制和大屠杀的重大创伤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犹太人或非洲人经历的创伤往往成为创伤研究的中心。如此庄严的精神或心理创伤概念很自然地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发展的力量变化和经济的不对称导致传统的创伤概念让位于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创伤经历[6]。这个论断很有启发性。在谈到现今创伤理论的重大转向时,比蒂教授认为,创伤的叙事表达成为新的研究焦点。他接着发问:谁在表达创伤?他或她如何表达创伤?谁是创伤经历的携带者?谁是创伤话语的携带者?这个新焦点就是创伤政治,因为“携带者群体”必须将创伤政治化才能使之得到认同[6]。此外,比蒂教授表达与克鲁斯类似的观点,即创伤具有逃避性和不可表征性的特点。如果克鲁斯教授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表达了对创伤以及创伤研究的新思考,那么,比蒂教授似乎是从认识论视角提出创伤和创伤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二者的观点同样具有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中国学者在上述两篇“访谈”中起到了很好的话题引导作用。
“中国声音”的“时代感”还体现在“中国声音”穿透时代的主旋律——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促使外国学者了解外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声音”和中国立场。第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青年长江学者傅其林博士与欧洲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加林·提哈诺夫教授关于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话。该“访谈”别具一格,首先由提哈诺夫教授向傅其林博士提问。所提的问题是:傅其林博士为何研究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妮斯·赫勒。傅博士认为,赫勒是布达佩斯学派最重要的人物,她在20世纪60年代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指导下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撰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文学和艺术的著述,提出了许多令人兴奋且很少被西方和中国学者讨论的观点。接着,傅博士向对方提出“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的问题。提哈诺夫教授简要地梳理了20世纪以来以当时苏联为例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即以20世纪60年代分界线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为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时期、每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其中,提哈诺夫教授重点提到卢卡奇及其作品的重要性。这种“素描”式的评论既简洁又清晰。最后,傅博士向对方介绍了他的文章《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引起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话的兴趣。提哈诺夫教授对此同样感兴趣,并希望傅博士向他引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和美学方面的译作[7]。在统计的30篇“访谈”中,以上“访谈”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令人耳目一新,充分说明“中国声音”对西方学者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第二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讨论西方学者的热议话题——就西方学者眼中的“毛主义”与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之一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展开对话。杰姆逊解释“许多西方学者对‘毛主义’感兴趣”的原因在于:“毛主义”是共产主义仍然存在的一个标志,“毛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革新。他认为“毛主义”的两个特征对西方具有吸引力。第一个特征是“毛主义”坚持将农民阶层作为一个历史的主体,这是“毛主义”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平民主义,西方学者站在各自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他们自己的“平民主义”观点。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杰姆逊在回答所有问题上几乎同时强调了“历史情境”的重要性。这似乎表明杰姆逊秉持根植他内心深处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杰姆逊不同意“有些美国学者认为‘毛主义’已经过时了”的说法。他觉得“毛主义”中的“某些时刻仍然非常重要……它们仍然各有可资借鉴的经验”[8]。最后,访谈的双方还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功能等问题。总之,以上两个“访谈”的双方既不回避敏感问题,也不隐藏内心的真实想法,交流坦诚,思想丰富,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四、 结 语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扉页上写到:“一次访谈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上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③该评价很好地概括了“访谈”这一特殊文学话语的主要特征。本文以为,上述话语也可以应用于评价《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外学者访谈”。笔者最后在相信《外国文学研究》会继续将“中外学者访谈”作为刊物“座上客”的同时,向该刊物和广大读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大洲国家学者对话的视野;第二,展开对“文学访谈”这一特殊文学话语——本体论/认识论文本、开放/封闭文本、真实/虚构文本④、形式/内容文本、主体/客体文本、理论/实践文本等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第三,欧内斯特·海明威说:“每期《巴黎评论》我都有,我非常喜欢上面的访谈。如果把它们编成书,那将是伟大的书,对《巴黎评论》本身也很有益。”海明威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笔者相信,我们广大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一样,都持有与海明威类似的想法。
注释:
① ③以上两段话同时出现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三卷中文译本的扉页上。它们的译者不同,出版社也不同。参见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黄昱宁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仲召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杨向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② 国内外国文学刊物发表第一篇外国学者访谈录的信息如下:余一中的《阿斯塔菲耶夫访谈录》,载《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3期第143-147页。未名的《Ч.艾特玛托夫访谈录》,载《国外文学》1994年第1期第105-106页。生安锋的《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和少数人化——霍米·巴巴访谈录》,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第56-61页。朱刚、刘雪岚的《琳达·哈钦访谈录》,载《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第124-128页。查尔斯·鲁阿斯与斯默的《托尼·莫里森访谈录(一)》,载《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1期第8-15页。王晓路的《贝克教授访谈录》,载《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25-30页。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外国文学研究》刊载外国学者访谈录的文章出现最晚,但自设立该栏目以来,它的刊载频率却最高。具体数据参见该文的第一部分。
④ 西方学者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讨论“文学访谈”的类属问题,参见David Neal Miller.“IsaacBashevisSinger:TheInterviewasFictionalGenre,”ContemporaryLiterature1984 (25):187-204.Bruce Bawer.“Talk Show:The Rise of the Literary Interview,”AmericanScholar,Summer,1988:42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