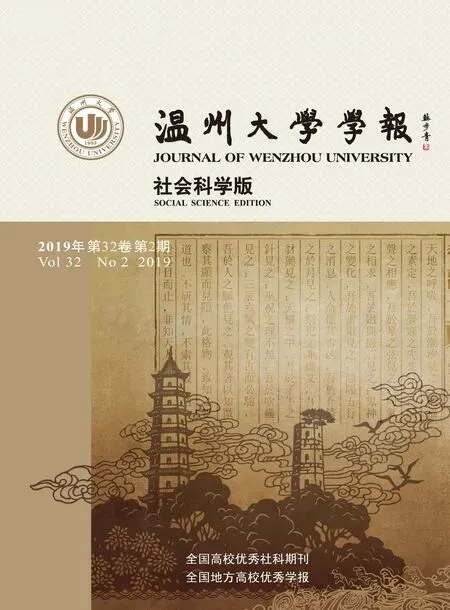从马克思“类本质”视角看孟子的“性善论”
闫 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51)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类本质问题做了充分的理论分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解“人性论”问题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所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是对哲学“人性论”问题的批判性发展,突破了西方“人本主义”的旧传统,创造性地将“人性论”问题的关注点引向现实世界与社会实存。马克思“类本质”理论所引发的这一转向与孟子“性善论”的现实关切与内在超越,在逻辑前提、理论内容和思想趣向等方面颇具一致性。
一、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的人
马克思“类本质”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性”问题首先是一个“存在”问题。这与孟子是不谋而合的。“人性”问题是对“人何以为人”之根本可能性的追问。传统欧洲哲学的回答方式是设定一个抽象的人的“本质”,并将其建构为终结性存在,作为人之为人的合法性来源。但在马克思哲学与孟子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能诉诸抽象“本质”规定性,反而要落实在人天然的存在中,理解人性的前提在于先在地理解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发问为“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与孟子共同给出的答案是“类”:人是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的人。“人”并非以个体存在者的方式而存在的“个体的人”,人从本质上来说首先是“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类”是人最本真、最原初的存在方式,“人之为人”的关键要向“类存在”中去挖掘,要追问“类”维持自身实现的内在可能性。马克思的回答是“类本质”,孟子的回答是“心所同然”,用词虽然不同,但所指并无二致。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都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95。从“类存在物”的立场出发,对“人性论”问题的讨论必须首先从“类”的意义上进行。
关于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孟子也有相似的表述。孟子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2]孟子以类比和举证的方式从身体性、审美性与道德性等方面给出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论证,并且从“类存在”的角度指出了圣人与凡人是“同类”。
对此,孟子进一步阐发:“有若曰:‘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3]孟子通过引述孔子门人有若的话,再一次强调了人是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的,圣人概莫能外,只不过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者,是“类存在物”中最为灵秀的那一部分。而圣人超越于凡人之处,就在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就是说,在“类”的意义上理解人性,孟子认为“圣人”率先实现了自身人之为人的“类本质”。
二、“类本质”是现实具体的生命存在活动
“人性论”问题向“类存在”问题的上溯直接引出了“类何以可能”的问题,“类本质”和“心所同然”是对这一问题异名而同质的回答。就是说,“类本质”和“心所同然”是“类”对其自身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它就是现实具体的生命活动。马克思说:“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1]96人作为“类存在”而展开什么样的生产生命活动,直接地就成全什么样的“类本质”。人的生命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他说:“人则是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4]273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成就人的类本质,构成人与动物的区别:“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96
孟子解释“心所同然”的方式与马克思如出一辙。在孟子这里,“心所同然”的那个东西无非是“良知良能”“孝亲敬长”,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活动,而非存在着的某种东西,是人之大本,但并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
关于先秦儒学对“本”的附意,《论语·学而》以有子的话做了十分有意义的说明:“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7《论语》以“亲亲敬长”为“本”,便是以本源生活情境中的情感活动为人初生之质,这是就情感作为人本真的生命存在方式而言的。“本”字表明,在一种最为原初的意义上来说,孝悌之情是先于任何存在者的,甚至在“孝悌”之先“人”都是未成的。人之为人的类本质皆在于这个大本大源的生命存在活动,有子正是以此为人性论的立论之基。对“性”的情感化处理化解了它固化为抽象本质的危险,将它推进到一个更为基础的层面。孟子继承了这种方式,并进一步以“仁义礼智”细化、丰富这一本质。孟子曰[6]2691:
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将“良知良能”具体分说为“仁义礼智”,并将“仁义”作为核心,“礼智”只是就“仁义”上做文章:“礼之实”在孟子那里是“节文斯二者”,是对“仁义”的恰当安排;“智”是“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是对“仁义”的坚持。“仁义”在《孟子》中出现凡数十例,涵义十分丰富,但大致上又可以作如下归纳。
关于“仁”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仁”究其基本意义而言,表达一种基于生命间感通谐行的同情。“仁”的此类涵义可以上推至《论语》“仁者爱人”的“爱人之心”,具体到《孟子》文本中的“不忍人之心”与“怵惕恻隐之心”。孟子谈“仁心”,以齐宣王“不忍见牛之觳觫”事和“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事进行说明,点出了“仁”作为一种生命体所固有的本性,一旦有所见,则当下呈现,不思不虑,“沛然莫之能御”。
第二,孟子言说“四端”中的“仁”包含着一种由内向外的推扩,即推其所为于其所不为。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不忍”即同情之心起处,向外流行而至于其所未见之处,此是“仁”中内涵的意蕴。譬如孟子判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前者王见牛过堂下,恻隐之心一动,刹那间流行于禽兽;然而犹有未足之处,故而未至于百姓。孟子称之为“不为”,那么孟子所要求的就是推其所为于其所不为。戴震《孟子字义疏正》解“仁”曰:“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即言此意。
第三,“仁”在孟子这里获得了一种德性的内在“心性之本”的地位和意义。孟子直言“仁,人心也”,这里绝非在一种庸俗意义上使用“心”,而是用以代指“安宅”,天然性命之所安顿处。由此“仁”便构成了人成就自身天然性命的内在依据。
孟子说仁:“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6]2773通常,我们将这句话理解为儒家向外推扩的思路,即是第二义,由内向外的呈现。进一步看,这种向外的推扩之所以得以可能乃在于生命本源状态下相互间的感通,这就引出了“仁”的第一义。同情从何而来,如果依汉儒的说法,来自同类间的相感。这自然可以解释孟子“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中的“恻隐之心”。但“孟子见齐宣王章”,宣王“不忍见其觳觫”的同情又从何而来?孟子虽然与告子辩“牛之性”与“人之性”的分疏,但也清晰地认识到人与牛之间生命本源情感上的通性,这是万类生命之间的感通,而不仅仅局限于同类。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2771这里面“亲亲”是“仁”,“仁民”是“仁”,“爱物”也是“仁”。尽管有差等,但“仁”确实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到的。也唯有如此,才可能求得“反身而诚”。若“仁”只限于同类中,于万物有不到处,又怎么可能“万物皆备于我”?此是就“仁”之感通义上言说。这种感通首先是人本源性存在活动的自在呈现,真实无伪,具有最高的先在性,以此为奠基人之德性才能为可能。这就是“仁”的第三义。
“义”在《孟子》文本中是与“仁”最为紧密的概念。孟子关于“义”的用法可概括为两种。
第一种“道义”或“仁义”合称,代指全德。譬如《公孙丑上》第二章“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此处是“道义”合称。《梁惠王上》第一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处是以“仁义”合称。
第二种与“仁”正好相反,是由外而内的裁制。如果说“仁”意味着由内向外的扩充,当仁不让,推其所为于其所不为;那么“义”正好相反,意味着由外向内,推其所不为至于其所为,给予人的存在活动以自限。孟子视义为“羞恶之心”,按朱子解,内有所“羞”,外有所“恶”,所“羞恶”者即人所不为。孟子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6]2726,又言“仲尼不为已甚者”,皆是谈此意义。
孟子以亲亲、敬长、人心、人路来喻说仁义。“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6]2765此种“亲亲”之要在于“爱”与“养”,乃是生命感通的充实,是“自反而缩”的有所为,故而是“仁”。“从兄”之要在于“敬”,在于谨守界限,不逾越规矩,是有所不为,故而是义。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6]2752这里面明确将“义”与“仁”相对而言,“仁”是正向的言说根源处的感通,“义”则是反向言说生命自在自为的自限。由此可知,“义”虽有两层涵义,但第一种只是一种泛化的用法,其要旨只在于“无穿逾之心”的生命的自限。
孟子讲“仁义”的实质是感通与自限,正是生命最天然的关于其自身的存在活动,故而可以与马克思“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相对应。当然,这种对应只是逻辑结构与叙事方式上的对应,实际上马克思关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具体的说法,与孟子又有所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活动是一种辩证活动、生产活动。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生产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319并且马克思最终将这种活动解释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这与孟子哲学的意味和趣向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这样理解:将“人性”在“类本质”的意义上作一种“活动”化的处理,从而避免其固化、抽象化,由此确证人性的真实与现实,这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与孟子是高度契合的。
三、类本质天然地趋向于实现自身的自觉与自由
由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成就的“类本质”,在马克思那里是最真实的、普遍的,因而最终也一定是自由的。“类”之所以是普遍的,根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自身内在地、天然地所具备的能动性使得它能够通过对象化活动而把人自身当作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在理论和实践上确信并塑造它的普遍性。换句话说,人作为“类存在”的普遍性是由它自身所生产出来的,这是自我生产自我的自觉。这样,自由与自觉在马克思这里便是“类本质”最终所一定要实现的趣向。
孟子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他并没有讨论关于实践、生产、辩证这样的问题,但他同样确信“人性”必将带来自身的全面实现与自由。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养心”,或者叫“存心养性”,即通过内向性的精神反思与外向性的实践工夫互相发明,从而使得“心所同然”的人性得到完全的实现。在孟子看来,“存心养性”最终可以臻至通达天命的境界,实现天人之间的真实不虚、贯通无二,由此实现终极意义上的精神自由,“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具体地说,所谓“存心养性”就是“存心”“正心”,使人的存在始终维持一种有“良知”的存在方式,端正不偏,湛然不昧。其紧要关节之处在于“去蔽”,即克服“良知良能”当体呈现之时由于心物错置而蒙昧昏聩的危险,保持“良知”在刹那间所发所用若合符节。孟子的讲法叫做:“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6]2779这里所说的“欲”不是我们日常意义上的生活需求,而是心物交接之际生出虚妄心而对“良知”造成的“遮蔽”。“良知”一旦从人的生命存在活动中隐去,人也就不可能以它独特的方式而存在,由此人的存在活动也就丧失了真实性与现实性意义。故而孟子讲要“寡欲”:自隔阂有蔽的后天困境中透析出感通相谐的先天本真的生命存在状态。
这里就要回到孔子说的“忘”来讲明这个道理,只有通过它,才可能返于人真实无妄的生命存在活动。《论语》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5]270
孔子一生矢志于恢复周文礼乐,但在“老之将至”的时候,他却在这里谈到了“忘”。其实,孔子这里所谈“忘”的意指与孟子“养心寡欲”是一致的。孔子讲君子要“文质彬彬”,“文”即“礼乐教化”,“质”即天性“仁心”,以“仁”言“礼”就是以“质”救“文”的路子。那么,如何复“质”呢?这就需要通过“忘”而消解掉虚妄分别心带来的“欲”的遮蔽,“寡欲”以“养心”,回复到生命真实的存在状态中,“质”才当体呈现、从容自得。
夫子谈“忘”是在重建周文、继而损益周文的过程中,破除掉对“礼乐”的偏执,忘却“意必固我”,最终超越周文名位限制,复归到“不虑而得”“不勉而中”的从容中行,是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在人文化成中的保持。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之“矩”是礼乐兴起之文,“从心所欲”是当体呈现,是生命初生之质。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战战兢兢、端正自持;二是率性无伪。前者是人为工夫,即孟子所说“心勿忘”;后者是天然禀赋,即孟子所说“勿助长”。少了前者则流于道家玄谈,放浪形骸;少了后者则礼乐教化无处施展,流于空疏支离。只有实现二者的相合,人的生命既在礼乐德性之中得到发现与尊重,也在天然纯真之中得到安顿与成全,最终的自觉自由才得以实现。
颜回境界最近孔子,虽然“具体而微”,尚有未尽处,但“已具圣人之全体”。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5]226颜回的精神气象和修养工夫与孔子如出一辙,皆是以“忘忧”成全圆融自在的“乐”,从而臻至于生命最高意义的自由。
孟子正是要传下来“孔颜乐处”的“忘忧”。此“忘”与佛老不同,绝非教人“忘”到空无,它只作为一种作工夫的方法途径而归旨于“乐”。一旦进入到“尽心知性知天”“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高度精神自由境界中去,本真的生命存在刹那充实起来,不仅只有孔子“乐以忘忧”、颜子“回也不改其乐”,还可以有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闵子骞“吾必在汶上矣”。其形象虽然分疏,但其要旨是统一的。
由“寡欲”“去蔽”而复致生命本真的存在,是为“存心养性”的工夫。自此而进,真实的生命存在活动激发出“人”与“天”贯通无二的“诚”,人才得以紧紧地扣在天地之中,反于妙本,应于大通,始终保持其活泼泼的整全生命力,实现“万物皆备于我”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孟子所确立的人的生命是完全真实的、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