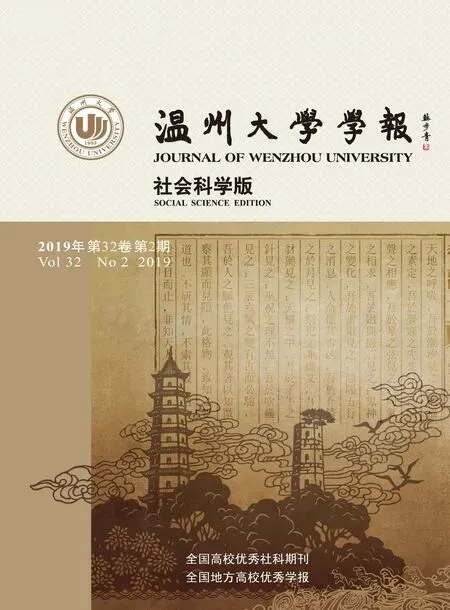章学诚史学史观中的“史意说”
崔 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章学诚论史标榜“史意”,他提出的“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1]887,以及“刘言史法,吾言史意”[1]817等论断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所谓“得史意”与“言史意”,主要是针对古人的撰述行为来说的,所“得”与“言”者也大多指“古人之意”,即古人著书的旨趣①目前学界研究章学诚“史意”的成果很多,但经常出现脱离与刘知幾进行比较之语境,甚至置章学诚“言意”文本于不顾的现象,致使诠释出现偏差。实际上,在《文史通义》中可以找出许多体现刘、章论史之不同的例证,有力凸显出“言史意”与“言史法”的治学异趣。如《书教上》篇:“刘知幾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后世之空言”指后人对《尚书》“记言”体例的认知;刘知幾以后人认识来讥讽前代史书义例不纯的做法,在《史通》中俯拾皆是。这一点在《书教下》篇中被进一步总结为:“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这完全可以视作对刘知幾史学批评方式的高度概括。从中我们可清晰地分辨出两种不同的论史方式:一是以后世之成法,来批评前人;一是舍弃后世成法,转而探求古人著述之旨,以理解古人的变通。前者大致就是“言史法”,后者即为“言史意”。“史意”的含义也因此而明了,即“古人著书之旨”。。《〈和州志·志隅〉自序》文中说:“诚得如刘知幾、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1]887围绕“古人之意”,章学诚文本中有许多可供讨论的话题,例如古人之“初意”“深意”与“微意”“遗意”,“知其意”“得其意”与“无其意”“失其意”,“经世之意”“谨严之意”“褒贬之意”,《尚书》之意、官礼之意、《春秋》之意,等等。其中,对“古人之遗意”的体察是章学诚讨论史学的重要方面,亦为一独特切入视角,体现了其浓重的史学史意识[2]。本文即着眼于此,对章学诚有关中国史学演进的论述加以分析和概括。
一、“六经”到“三史”之演进
“六经”指儒家的六部经典,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始见《庄子·天运》篇。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六经”一称广为流传。“三史”的称谓出现且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至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成为“三史”之一[3]。正如章学诚所说,“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1]229,它们是学者追溯中国传统学术而必至的源头。司马迁撰《史记》,在《太史公自序》中隐晦道出其与孔子《春秋》的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将《太史公书》归于《春秋》之下。这都暗含着一种对史学渊源的理解。唐初,刘知幾撰《史通》,则明确将“六经”同“三史”一道纳入史学演变的历史中去①刘知幾《史通》中蕴含有“五经皆史”的观念,而不仅《六家》篇中《尚书》、《春秋》以及《左传》这种史学色彩浓厚的儒家经典被认作史书处理,《诗》、《易》也同样被看作“史籍”,所谓:“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参见:刘知幾.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69。。所撰《六家》与《摸拟》两篇,即分别从史书体裁体例与文字表述两个方面来揭示和探讨史学继承的现象,得出一些规律性见解。其“摸拟之体”,分为“貌同心异”与“貌异心同”两种:所谓“貌同心异”是指后来者对于经典的僵化模仿,只追求表面的相似,好像“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专袭形迹,而不顾实际情况,最终导致似是而非;“貌异心同”则要求去体会先贤文字表述的用意,学习其手法而非强求外在的相似,所相似的地方在于“道术相会,义理玄同”。他还进一步归纳得出,不同阶段的“摸拟”具有不同特点,即“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4]158-161。刘知几将六经与三史并列叙述,指出它们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却未涉及从“六经”到“三史”的历时演变过程。
章学诚补刘氏之不足,从史学义例之因袭变化的角度,对“六经”到“三史”之演变过程提出自己的见解。需要指出的是,其辨析“古人之遗意”的审视路径很可能是对刘知幾论“摸拟之体”时“貌”“心”分途方式的继承[5]。章学诚说[1]36: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章学诚首先建立起中国古代史学从《尚书》到《左传》,从《左传》到《史记》,从《史记》到《汉书》的三个演变环节,其中四种史书各有其义例,呈现出一幅历时蜕变的画面。如下表1。
所谓“经世”“纬经”“搜逸”“示包括”诸义,在章氏看来都是随时代变迁而对历史撰述提出的不同要求,例以义起,故这种种蜕变实是“势使然”的“不得不然”。随后,章氏从“形貌”和“精微”两种视角出发,着重分析《左传》《史记》《汉书》三部对后世影响最为显著的史书。从形貌上看,《左传》为一类,史记》《汉书》为一类,前者为编年之祖,后者为纪传之祖。这是常人之常识,更是为刘知幾《史通·二体》篇所揭示的。章氏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往往能突破常规的束缚,直窥精微之妙处。他指出,《史记》与《左传》相近,得《尚书》之遗意;《汉书》与《史记》却远,得《官礼》之遗意。这样,他就从继承古人之遗意的角度,构建起史学从六经到三史之蜕变的历程。
章氏认为《尚书》与《官礼》是“撰述”和“记注”两种史书形态的范本:《尚书》“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其宗旨在于“经世”;《官礼》则相反,“纤悉委备”,具有一成之法,其宗旨在于最大限度地、最有条理地保存史料[1]21。基于此,章学诚指出,《史记》“不拘拘于题目”,虽“以名姓标题”,却常常以意命篇,自有其用意与宗旨,虽名为列传,却时时因事命篇,“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这种体圆用神、不拘成例的做法,“犹有《尚书》之遗者”。而《汉书》则不同,它虽然也“有圆而神者以为之裁制”,不失为一家之撰述,但置其于“六经三史”的比较场域中,这种品质表现得很不明显。后人所见是班固继承司马迁首创之纪传体,通过整修使具备一定之体例,形成“近于方以智”的“体”和“用”。因此,《汉书》被认为“多得《官礼》之意”也就理所应当了。
此外,章学诚以其特有的感悟力和想象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探寻到另一种从“六经”到“三史”的演进路径。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指出:“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1]828他借“或问”之口将这种演变过程归结为:“六经演而为三史。”从师法“古人之遗意”的角度来说,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纪传正史,乃《春秋》家学,师《春秋》之遗意;刘秩《政典》、杜佑《通典》为代表的掌故典要,法《官礼》之遗意;吕祖谦《文鉴》、苏天爵《文类》为代表的文征诸选,则承《风诗》之遗意。这三种师法古人遗意的著述,并非同时产生,而是先后相继,章学诚进一步总结道:“获麟绝笔以来,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至积久然后渐推以著也。”[1]827-828这揭示出一种有关“认识”的规律,与乾嘉汉学“汉人去古未远”的观念恰恰相反,章氏认为距离古人越远就越有可能洞察古人言论的真谛。所谓“积久”“渐推”,说的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从而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与乾嘉汉学完全相悖的认识理论,其核心在于摆脱注疏的磕绊而直接从“遗意”的角度来审视古代经典、把握学术流变。
二、“诸子之遗意”与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对“诸子”具有特殊感情和独特认知,其思想、学术与之紧密相系。其尝撰《诸子》一文,虽然已经亡佚[1]47,但从散布于其他文章的相关言论依然可以考见“诸子”对其史学的重要意义。章氏受刘歆、班固以及《庄子·天下》篇影响很大,其中对刘歆“诸子出于王官”说最为服膺。他说:“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由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1]912通过借鉴这种解释方式,章学诚进一步考察了诸子学兴起的过程和背景。他认为,诸子之学出于周官典守,其兴起是“官失其守”后的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的结果。和“官师合一”时代的“大道备于六经”相比,诸子之学虽然“不衷大道”,但也并非对“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是能够通过“得道之一端”以树立“一家之言”的[1]17,45。于是,章学诚将诸子之学作为“一家之言”的源头和典范,所谓“诸子一家之宗旨”[1]222,“诸子著书,承用文字,各有主义”[1]227,“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1]61一类的言论遍及其文集之中。那么,在章学诚看来,后世之效法“诸子之遗意”,就表现为对“一家之言”的追求,这一点从其学术批评中可见一斑。如其评价两汉辞赋与文章说:“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1]60,“贾生奏议……相如辞赋……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1]318。
对于史学而言,师法“诸子之遗意”即要求史家撰述能够具备其“宗旨”与“主义”,从而使所撰之史具备“一家之言”的特质。如章学诚评价郑樵《通志》,“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又称“《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1]237-240《通志》的“事实”多沿袭“旧录”,考核常有粗疏,但这不能掩盖其师诸子遗意而成一家之言的光芒。郑樵只是章氏从其所谓“史学失传”的时代中发掘出来的个例,真正继承“诸子之遗意”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时代出现在汉唐之间。他指出:“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1]249,又有“马、班而后,家学渐衰……特立名家之学起……六代以还,名家复歇,而集众修书之法行”[2]985-986。可见,在章氏的观念里,汉唐之间“一家之言”的史学形态存在马班“家学”与魏晋六朝“特立名家之学”的区分,二者前后相继。他曾定义“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体现了在“家”的确立方式上的不同。但实际上,在对“一家之言”的追求,亦即继承“诸子之遗意”方面并无差别,有些地方这两个阶段被并称为“家自为学”的时期[1]441。
章学诚从继承“诸子之遗意”的视角,揭示两汉魏晋史学的“一家之言”特点,还鲜明体现在对曾巩《南齐书目录序》的删订中。曾巩指出,两汉之前,执笔撰史者都是圣人之徒、天下之士,所撰史书往往能够揭示出“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作为鉴戒,从而成为至上之史。但他对后世诸史的看法颇为严苛,《南齐书目录序》原文记载:“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6]这是认为,包括司马迁在内的“为史者”都与古之良史相去甚远,而所谓“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则更是不值一提。章学诚赞许曾巩对三代史学的评价,而对其有关后世史学的批评则持保留态度,遂将上引曾巩这段文字删订为:“获麟绝笔以还,左氏不免诬夸,史迁是非不能无谬于圣。……盖圣贤之高致,左马有不能会心于微,而显示于后者矣。后世之史,其视左马之见奇而生色,已如九天,况敢议其他乎?然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约《宋》收《魏》之书,虽难语于中人而上,第就其所得,尚足成一家言。”[1]525-527章氏一方面认为孔子之后修史者确实存在不足,他们所修史书也必然存在缺失,甚至指出左丘明与司马迁的“不免诬夸”“不能无谬于圣”;但另一方面,他又总能洞察到常人无法视及的地方,提出后史“非竟无所得”“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第就其所得,尚足成一家言”的见解。这种分析方式和用语,与其对诸子百家“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1]17的阐述如出一辙。
此外,章学诚通过对战国时期著述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发现了另一种继承“诸子之遗意”的现象。他说:“子史不分,诸子立言,往往述事;史家命意,亦兼子风。”[1]355前半句论诸子何以具有“史”的性质,后半句论史家如何具备“子”的兴味。上文所述史家对“成一家言”的追求,即述史而“兼子风”的做法;而“述事”以“立言”的方式,在后世学术演进中也不乏效仿者。章学诚论“浙东学术”,称其“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121,可谓从“立言往往述事”的角度探寻“诸子遗意”继承者的最大发现。
章学诚在阐扬师法“诸子之遗意”史学的过程中,还以“豪杰之士”的名称来称呼这些史家群体。他讲:“马、班而后,家学渐衰,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1]985-986又如:“文集者,诸子衰而后起也。然气运既开,势必不能反文集而为诸子,惟豪杰之士,能以诸子家数行于文集之中,则文体万变而主裁惟一,可谓成一家言者矣。”[1]785“豪杰之士”总是出现在学风“既衰”“渐衰”之后,带有逆境之中力挽狂澜之孤胆英雄的色彩。章学诚说:“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1]709将历史上和当下的这些能够“自得师于古人”的人称作“豪杰之士”,这种做法与当时驱逐风尚、缺乏自主的学术风气息息相关。“豪杰之士”语出《孟子·尽心上》:“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7]章学诚曾用这句话来激励他在清漳书院的弟子们,并简化为“豪杰之士,虽无所待犹兴”[1]605,意在提倡一种学术上的寂寞之途,提倡继承“诸子之遗意”的“一家之言”。这不仅体现了章氏的学术理想,而且反映出其针砭时弊的现实关怀。
三、“失班史之意”与史学之衰落
《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也是历代史家争相效仿的典范。章学诚认为,《史记》无定法,《汉书》有成例;无一定之法,所以难于模拟,有一成之例,所以容易遵循,因此班固《汉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更大。对于这种影响,章氏用“后史失班史之意”一语加以概括,体现了他一贯的视角。“失意”主要是指,后世史家不知经由《汉书》“遗法”来推求班固“遗意”以获取编撰史书的灵感,从而根据撰史之“义”来灵活确定“例”的形态,而只知道“拘守成法”,“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1]37。从章学诚的论史文字中,大致可以将后人对班固《汉书》的误解归纳为以下几点:
对《汉书·古今人表》的误解。《古今人表》是班固《汉书》中最受争议的一篇,他将汉代以前的人物分为九等列入表中。刘知幾在《史通》中曾批评这不符合《汉书》的整体断限,即选人范围上自伏羲下至秦嬴,没有涉及汉代史事,却编入了《汉书》,这无异于“鸠居鹊巢,茑施松上”,可谓“附生疣赘,不知翦截”[4]49。章学诚十分清楚《古今人表》“为世垢厉”“至今史家以为疮病”的历史境遇,不无失望地指出“史识如刘知幾,乃亦从而非之”。他认为,“人表”一体并非班固的私创,而是对《春秋》家学的继承,对司马迁《史记》疏忽的补充,《古今人表》应该与《地理志》《艺文志》诸篇共同作为史氏“要典”;但事实是,后世史家不仅不知阐发绝学,反而“随声附和而诋毁之”,导致后世正史的列传“日出日繁而不可简料”[1]510。这种观点他还在同顾炎武“表废而列传遂繁”观点的商榷中,作出了进一步说明:“昔亭林顾先生之论史……谓表废而列传遂繁,其言良允。然顾氏……未尝知人表之陷于众谤,宜急为昭雪,而当推为史家之法守也。充顾氏之所议……唐、宋、金、元诸史,俱有年表,何以列传之繁,反比范、陈、沈、魏无表之书增至数倍?则顾氏表废传繁之说,不足以为笃论,而小子争复人表之说,非好为异论矣!”[1]764清初史家马骕撰有纪传体史书《绎史》,书中用人表例,但章学诚认为该书仅可称作“纂类”,不能成为“著作”,并推测作者的用意不过是因为“三代去今日久,事文杂出,茫无端绪”,所列的人表也不过是一部“经传姓名考”,与班固“人表”之“意”相差甚远[1]995。
对《汉书》诸志本“诸子之遗意”的误解。前文已述,师“诸子之遗意”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要著成一家之言。章学诚认为司马迁和班固所作的书志“略存诸子之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是“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得读者能够“推验一朝梗概”,并能与纪传“互相发明”。而对于“名物器数”,则因为“别有专书”,所以“不求全备”,就好像“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1]1001。然而,后代史家并没有继承司马迁和班固撰述书志的用意,章氏指出,自范晔、沈约以来,“讨论”的旨趣逐渐淡化,而关于“器数”的记载却越来越多。如欧阳修《新唐书》的志成书至五十卷,分十三名目,“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1]1001,《宋史》、《金史》和《元史》更加繁芜,可谓“盈床叠几,难窥统要”,这就好像将“《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1]1001。
对《汉书·艺文志》的误解。班固《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章学诚说:“《周官》三百六十,皆守其书,而存师法者也。秦火而后,书失传而师法亦绝……所赖存什一于千百者,向、歆父子之术业耳。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叙六艺百家,悉惟本于古人官守……其书虽佚,而班史《艺文》独存……其叙例犹可推寻。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1]648他认为班固《艺文志》的旨趣在于保存师法、纲维学术,在《校雠通义》中又进一步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8]。而后世学者却逐渐失去班志之遗意,章氏梳理了这个过程,指出“著录之舛”始于南朝梁阮孝绪之《七录》,此后唐初修《五代史志·经籍志》因袭七录中的经典、纪传、子兵、文集四录,改为经、史、子、集,遂使“千余年来,奉为科律……未有觉其非者”[1]319,649。章学诚还具体评价了唐代以后的多种艺文志,如认为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删去叙录,好似“书贾簿籍”,致使无从知晓其著录义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论校雠为天下至论,但部次著录“不能自掩其言”;钱大昕补撰的《元史·艺文志》则在方法上存在不当的地方[1]648-649。除正史艺文志之外,他还注意到,后世学者在编纂方志“艺文书”时更是远离了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旨趣,将“艺文志”做成了“诗文选集”[1]857。
对《汉书》“文苑致文采之实迹”的误解。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班固《汉书·扬雄列传》均详载传主所作长篇赋作,这一做法受到后人众多非议,所谓“自刘知幾已还,从而诋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但章学诚没有从众,认为那些“诋排非笑者”都不“知言”;他从中体察到“文苑传”的撰述原则和宗旨,并指出后世“失班史之意”而带来的不足:“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1]60-61
对《汉书·叙传》的误解。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自序》篇,班固《汉书》有《叙传》篇,是作者自叙家世、生平的传记。章学诚认为司马迁与班固叙述司马谈和班彪的业绩,有的简略,有的详实,但“既非有意为略”,“亦非好为其详”,而是“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于书,必肖其亲之平日,而身之所际不与也”[1]182。后世学者不得二人叙亲之意,章氏指出两种现象,其一为“侈陈己之功绩,累牍不能自休,而曲终奏雅,则曰吾先人之教也”,其二为“敷张己之荣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赋卒为乱,则曰吾先德之报也”。这两类学者的做法都是典型的“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1]182。
对《汉书》“子卷之法”的误解。子卷之法,是班固在竹素并行时代的一种创造。“竹”指竹简,“素”指缣素,都是古代纸张尚未流行之前的书写材料。根据材料的不同,产生了统计著述时的不同量词,所谓“篇从竹简,卷从缣素”。章学诚认为“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带短长”,如果一篇之起讫超过一卷的容量,则可分子卷,这就是“子卷之法”。章氏对这种方法十分赞赏,因为可以使篇数和卷数保持相当,“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班固《汉书》中的《五行志》《元后传》《王莽传》就是如此。但后世史家并没有沿袭这种篇长则分子卷的做法,而是“割篇循卷”。始作俑者是司马彪,他将《续汉志》八篇分为三十卷,自此“开割篇循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1]328。其后欧阳修《新唐书》志五十卷,其实只有十三志,年表十五卷,其实止有四表。《宋史》列传有二百五十五卷,其实不过是一百九十余传[1]329。可谓愈演愈烈,距班史之意渐行渐远。
以上就是章学诚所谓“后史失班史之意”的具体表现。包括陈寿、范晔等“或得或失”“粗足名家”的六朝史家在内,“后史”或拘守班固“成法”而不得其“意”,或因不得其“意”而摒弃其“法”,最终致使史体芜杂、“事文皆晦”。至唐初设立史局,集众修书,本应“谨守绳墨”以成一代之“记注”,却偏偏效仿前人“亦名其书为一史”,史学以此失传[1]250。
四、结 语
张舜徽先生曾言:“昔人论史每为‘史源于经’一念所桎梏,必谓某体出于《尚书》,某体出于《春秋》,某体源自官礼,某体源自《尔雅》,则自汉以下史部群书,但有因而无创,二千年间乌得有所谓史学乎?此其说必不可通也。章氏论史,盖不免于斯累。”[9]张先生此语道出了中国古代史家探究学术源流的弊病,章学诚自然不能独免。但这不能抹杀章氏论史的卓越之处,即辨章学术非但探究“体”之所出,而且体察“意”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其对“意”(包括经意在内)的理解,并不指向某种道德判断、伦理法则,而重在探寻历史编纂的本源与灵感。章学诚从继承“古人之遗意”的视角大体完成对中国史学之演进历程的梳理:三代为史学的“黄金时代”,“六经”是史学的源头和最理想的典范,也是“古人之遗意”的最主要发起点;汉魏六朝为继承“诸子之遗意”以“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时期;魏晋以降,史家不断失去“班史之意”,以唐初开局设监为标志,史学中绝。总之,章学诚始终强调“古人之遗意”在史学传承中的核心位置,其有关史学演进历史的叙述与构建,不仅展现出“言史意”的治学追求和特点,而且寄寓了通过回归六经、回归诸子以及回归班史之初意以革新史体的学术理想。而这种回归,不应被视作单纯的复古,它是一种以本源而济末流的手段,是一种跳出常例禁锢而寻求变通之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