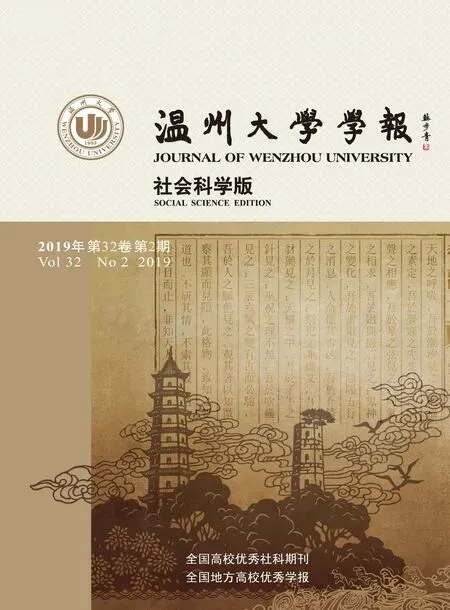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青楼文化书写探析
王 凡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高罗佩(1910 - 1967),荷兰著名汉学家。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高罗佩虽辗转亚洲多国任职,但毕生痴迷于中国文化的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汉学研究,著述颇丰,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推理探案小说集《大唐狄公案》。这部由20余个故事篇章构成的小说作品主要表现了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除奸去恶的传奇经历。青楼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维度,一直以来都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大唐狄公案》在展现中国古代的丰富生活画卷之际,也对古代青楼文化进行了细腻描绘,这不仅投射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对这位汉学家的潜在影响,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感受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风貌的特殊视角。
一、古代青楼文化的多元化呈现
《大唐狄公案》中的《红阁子》《黄金案》《铜钟案》《湖滨案》《黑狐狸》《广州案》《断指记》《莲池蛙声》等多个故事篇章都涉及了“青楼”内容。这些篇章在展现腾挪顿挫、峰回路转的推理、断案情节之时,也为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多方面地呈现了古代中国的青楼文化风貌,从而让读者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认识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
(一)青楼风月之貌的生动展现。在《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多次表现了名震一方的青楼妓馆,如《湖滨案》《莲池蛙声》中的“杨柳坞”、《跛腿乞丐》的“乐春坊”,《红阁子》更是展现了“金山乐苑”及在其内的“藏春阁”“海棠院”“逍遥宫”。不仅如此,高罗佩亦不吝笔墨地对上述风月之所进行了介绍,如《红阁子》就通过狄仁杰之口向读者展现了“金山乐苑”:
这乐苑大有声名,内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弹丝。漫说是这金华县的风流渊薮,它就占了绝大风光,便是杭、台、温、衢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也都麋集到这里图欢销魂,认它是纸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1]146
而《湖滨案》也对“杨柳坞”进行了介绍:
这“杨柳坞”坐落在汉源东郊湖滨曲隅,最是汉源的风月渊薮。院内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起舞,大多色艺俱佳。[2]189
可以说,《红阁子》《湖滨案》对于“金山乐苑”及“杨柳坞”总体概况的叙述与这些故事篇章中罪案突发后,狄仁杰抽丝剥茧、破解疑团的情节主线并无紧密联系,但实际上,作品在通过对行院妓馆的描绘来进行社会、文化背景的必要性铺垫之际,也使西方读者感受到中国古代青楼会所经营活动的基本面貌,并由此领略中国古代市井文化的独特风韵。
(二)冶游狎妓行为的别样呈现。《大唐狄公案》在展现青楼妓馆的同时,更多次表现了男性的冶游狎妓活动,譬如《黄金案》中乔泰、马荣随卜凯在花船上与群妓嬉戏,《湖滨案》中韩咏南、刘飞波等人狎妓之行,《红阁子》则表现了冯岱年、温文元等人在白鹤楼宴请狄仁杰时,也邀请了名妓秋月、银仙。对于自己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这一特殊文化现象,高罗佩曾指出:
官吏、文人、艺术家和商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家外的酒楼、寺庙、妓馆或风景区进行。这类聚会不仅是在同伙中消愁解闷的主要手段,也是官方和商业事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热衷于保住或晋升职位的官员总要频繁不断地宴请他的同事、上司和下属;每个阔绰的商人也要在宴会上洽谈和议定重要的买卖。唐代,妻妾是可以参加这种聚会的,但真正无拘无束的气氛只有靠专业艺伎才能创造出来。一个官员只要能给他的上司或某个有势力的政客引见精心物色的艺伎便可确保升迁,一个商人也可用同样的手段获得急需的贷款和重要订货。显然自己的女眷是不宜为这种隐秘的目的服务的。[3]175
由此可见,官吏商贾宴饮欢娱之时的狎妓行为表面看似是男性一种放浪形骸之举,但实际上这一行为更承载着男性官场交涉、商业接洽等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功能。《红阁子》中里长冯岱年、温文元等人在白鹤楼宴请当地县令并同邀“花魁娘子”秋月,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变相逢迎作为上司的当地行政长官,以使自己日后行事更为方便,而《黄金案》《湖滨案》中的冶游嬉戏也同样是官商之间拉近关系的某种社交手段。
不可忽视的是,上层社会群体这类带有狎妓色彩的聚会欢宴,除了特殊的社交功用外,实际上更附着了某些富于“集体无意识”色彩的社会个体内在心理诉求,对于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颇具建树的高罗佩对此也进行了精辟的阐释:
那些能够结交艺伎的人至少属于中上阶层,因此在家中也有妻妾多人。既然如前所述,他们有义务给妻妾以性满足,那就很难期望一个正常的男人竟是因性欲的驱动而与外面的女人发生性交。当然人们会有调换口味的愿望,但这只能算是偶然的胡来,并不足以说明他们与职业艺伎整天厮混的动机。浏览描写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你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必须遵守某种既定的社会习俗之外,男人常与艺伎往来,多半是为了逃避性爱,但愿能够逃避家里的沉闷空气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原因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并不一定发生性关系。[3]177
正因如此,在《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虽多次展现官吏、巨贾的宴饮狎妓场景,但却很少言及这些男性与青楼女子有过床笫之欢。以此观之,高罗佩通过作品中的狎妓描写所欲揭示的是唐代的中上阶层的在外狎妓之行虽不免有社交方面的考虑,但亦不乏有放松身心、舒解家庭婚姻规制与夫妻生活道德所带来的精神压力的潜在功能,而这在儒生士子和青楼女子的交往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陶慕宁先生曾就这类人群的狎妓行为指出:
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是中世纪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宫高捷,仕路亨通,要向妓女们炫耀;宦途偃蹇,怫郁不舒,也要到妓女们那里排遣。其间那种浅酌低唱、莺语间关的氛围确有荡涤利禄、排愁遣闷的审美功能,而那些风尘“尤物”的目挑心许、娇容冶态较之自家“糟糠”的板滞端敛当然也更饶风情,更富于刺激,因而已更易引起回味。[4]
儒生士子和青楼女子的交往绝非单纯的男女狎昵行为,而是前者邀炫成就、展露才情或排遣抑郁、舒荡心绪的重要方式,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也对儒生士子的青楼活动进行了一定的描写,如《红阁子》就写到举人李链在死前几日曾多次狎妓。这种“柏拉图式”的两性关系的展现也为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男女两性关系的一个特殊认知视角。可以说,这种青楼士妓关系既非西方“他者”视野中原始蒙昧的纯粹肉欲关系,亦非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作品中那种绝对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式的理想爱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士人阶层游离于家庭伦理规制和社会功用理念、寻求摆脱世俗利欲束缚,继而实现精神世界短暂舒张和自我情感片刻纵任的特殊途径。
(三)青楼女子生存状态的细腻描摹。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展现了一副丰富多姿的女性人物画卷,其中既有气度高雅的名媛闺淑,如《红阁子》中的冯玉环、《湖滨案》中的韩垂柳,也有机警聪慧的布衣之女,如《玉珠串》中的紫茜、《紫光寺》中的春云,甚至还不乏《玉珠串》中三公主那样的皇室之女及《迷宫案》之紫兰小姐、《柳园图》之蓝白这样的侠女。在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谱系中,青楼女子同样不可小觑,作者在多个篇章中都塑造了这类独特的女性人物,并展现了她们相对真实的生存状态。
在中国古代社会,许多女性往往因家贫或其他缘故而在秦楼楚馆谋生,她们以人前卖笑甚或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了此余生,这种沦落风尘的生活境遇其背后的苦楚和辛酸无疑是不言而喻的。她们最终或是被人赎出甚至自赎其身,或是在人老珠黄、容貌不再后终老妓馆,前者较之后者看似是一个更好的归宿,然而在赎身成功、嫁为良妇甚或成为豪门富家的妻妾后,其生活前景亦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大唐狄公案》不仅表现了青楼女子迎客卖笑的常态生活,更着重展现了这一女性群体在脱籍从良前后不同的命运归宿,由此辐射了青楼中人相对真实的生存状态。《铜钟案》中被狄仁杰赎身的碧桃、黄杏因助其勘破普慈寺淫僧案有功而被赐予普慈寺庙产的一部分来作嫁妆,并予以择良婚配。《迷宫案》中的胡妓吐尔贝虽难与碧桃、黄杏百事无忧、皆大欢喜的结局相比,但其也因马荣的救助得以从良,并嫁夫生子、经营酒肆。与碧桃、黄杏及吐尔贝回归正途、乐享生活相比,《莲池蛙声》中的名妓史玉娘虽被诗人孟岚赎身,这对老夫少妻婚后也是相敬如宾,然而天不佑人的是,玉娘之弟史晓鸣因与奸商沆瀣一气、盗取黄金而不仅令自己死于非命,更致姐丈孟岚被害身亡。新婚丧夫、孤苦伶仃的史玉娘也因此未能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跛腿乞丐》中的名妓梁文文在自赎其身后欲攀高官,但最终她不仅嫁入高门的愿望成为南柯一梦,更因自己杀人弃尸而身陷囹圄。除了展现青楼女子赎身从良的人生希冀外,《大唐狄公案》也表现了这类女性在赎身之外的其他生活出路。青楼女子无不渴望自己能够尽早摆脱人前卖笑甚或出卖肉体的凄楚境遇,但她们却并非都能如愿从良,更多的女子只能终老妓馆,在朱颜尽褪的年老之时被迫通过其它途径来维持生计。对此,高罗佩也认识到:“每个艺伎的最终目标是被一个爱她的男人赎出,但那些找不到丈夫的艺妓照例也得养起来,当她们年老色衰不能接客时,便留在妓院中,靠给年轻姑娘教音乐舞蹈为生。”[3]176他同样也对这方面进行了文学书写,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红阁子》中的凌仙姑,凌仙姑在其年轻时曾为“金山乐苑”中的“花魁娘子”,其当时的姿色、地位与作为后起之秀的秋月可谓一般无二,然而年老后的她,不仅花容月貌早已不复当年,而且眼盲丑陋、身染沉疴,为此,她不得不以向银仙等年轻女子教授吹弹歌舞来聊度残生。可以说,通过凌仙姑的老年境况,高罗佩为读者细腻展现了未获赎身的青楼女子凄凉悲苦的命运归宿。
在为西方读者生动揭示中国古代青楼女子多变难料的命运归宿,并由此折射底层女性的坎坷人生和令人唏嘘的炎凉世态时,高罗佩亦借篇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这些女子的人道主义关怀,这在《红阁子》中秋月这一形象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波伏瓦曾指出:“从低级妓女到高级妓女,有很多等级。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以女人纯粹的一般性来做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悲惨的生活水平,而后者竭力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承认,如果她成功了,她就能期待高贵的命运。”[5]751美国学者贺萧则认为:“高等妓女在性的方面表现得妩媚、优雅、含蓄,没有一点淫荡之意,在想必是十分枯燥无味、单调郁闷的中国生活中提供了绚丽多彩的插曲,因此高等妓女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构件”[6]。从李师师到李香君,再到赛金花,这些名妓都可以说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而秋月亦属这类地位较高、身份特殊的青楼女子,作为“花魁娘子”的她有着美如冠玉般的容貌,其不仅拥有一般妓女无法相比的特殊地位,更是男性垂青的主要对象,正因如此,她俾倪骄慢、刚愎自用、胸襟狭小,并对有人为她殉情无动于衷,在嫁给罗宽冲之愿化为泡影后,她又不惜向狄仁杰投怀送抱、自荐枕席。可以说,这一侍仗美貌、自命不凡的浅薄狭隘之女既难与《铜钟案》中帮助狄仁杰破案的碧桃、黄杏等量齐观,更不具备《黄金案》中因提供线索而为歹人所害的玉珠那样的人性光辉,然而高罗佩仍对其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理解之情。为此,作品表现了面对横死红阁子的秋月,“狄公心中油然升起一阵伤感之情。在这么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一个女子要站得住脚跟,谈何容易!可怜秋月机关算尽,劫数难逃。”[1]180此后更是借陶德之口直接表达了对秋月之死的惋惜以及对其本人的包容:
我见她浅薄气狭,喜怒无常,又自命不凡,言语尖刻,早知不是长寿之人。也可怜她一个弱女子,在人欲横流的环境里立身处世,何等不易。她周旋于一群人面虎狼间,内里苦痛,也不尽言。故而一心念也想找个相匹配的赎她出去,更担虑明日珠黄,门前冷落。[1]209-210
乔治·巴塔耶曾说:“从来不乏同情之人为妓女的不幸鸣不平,但是他们的呼喊掩盖了一种普遍的虚伪。”[7]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大唐狄公案》对以秋月、凌仙姑、史玉娘等青楼女子的细腻刻画及其渴求通过赎身婚嫁走上正常生活来看,高罗佩在作品中无疑寄寓了对中国古代青楼女子生存艰难的境遇和曲折不幸命运的由衷理解和同情。
通过《红阁子》《铜钟案》《莲池蛙声》等故事篇章,高罗佩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呈现了古代中国青楼文化的诸多方面。虽然通过这样一部以推理断案为核心元素的作品实难为西方读者展现中国古代青楼文化的整体面貌,然而高罗佩这一凭借通俗文学形式来展现异国社会文化的艺术尝试却无疑是难能可贵而又独具创意的,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青楼妓馆以及青楼中人的生存状态形成某种初步印象和基本认知的创作初衷也可以说已基本实现。正因如此,西方读者在阅读《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实现了两个层次的审美体验:一方面是西方侦探推理文学所提供的罪案告破、案犯落网后的审美愉悦,另一方面,无形之中通过青楼文化完成了一次东方异国的市井文化之旅。这也鲜明地反映了高罗佩通过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人物形象所建构的推理小说,来进行客观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图景的这一文学创作理念。
二、青楼女子塑造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塑造了众多青楼女子,这些身份特殊的女性人物不仅多次出现,而且性格多样、形象鲜明。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妓女形象成为一种隐喻,一种表达思想意识、建构社会性别身份的媒介”[8],而高罗佩笔下的青楼女性不再是男性人物的陪衬与虚饰,而是通过其形象“集中发挥了宣扬男女平等、赞扬妇女的才智和胆识、肯定妇女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的现代性因素”[9],这在凸显高罗佩创作思想旨归的独特追求之际,更投射出其“与传统公案小说创作者殊异的女性主义人文色彩”[10]170。
(一)才貌兼具的形象彰显。《大唐狄公案》在塑造众多青楼女子的过程中,时常有意彰显这些女性独有的美貌,如史玉娘初次登场时,作品就通过狄仁杰的视角生动展现了其不俗的容颜:
狄公抬头,果见一年轻美貌的女子,娉娉婷婷,轻移莲步从内屋走了出来。那女子雪肤花容,乌云不整,凤眉下一对大眼,深明透亮,颊上闪着几滴泪珠。朱唇外朗,皓齿内鲜,狐眉清秀,柳腰摇摆。虽淡妆素裹,总不掩其窈窕妩媚之态。[11]
作为新寡孀妇的史玉娘虽是略施粉黛,亦未披红戴绿,但却依然难掩美貌。与素雅之中愈显娇容的史玉娘相比,“花魁娘子”秋月更可谓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秋月身穿满月一天星杭绸百裥罗裙,银光闪闪。满头乌云高高螺旋盘起,一只金雀钗贯穿其间,金雀钗头嵌镶一粒大红宝石。两片似白玉雕出般的耳朵各垂下一叶翡翠明珰。后髻间插一凤凰展翅玉搔头。行步来摇曳闪光,嫣然动人,真是花妖转世,压了满苑众芳。[1]169
通过上述描写,秋月犹如仙姝转世般艳盖群芳的动人容颜已跃然纸上。除此之外,“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窈窕”[2]179的杏花、“纤腰袅娜,风姿翩翩”[1]15的梁文文也都可谓是绝代红颜、倾城佳丽。
在凸显青楼女子非凡容貌的同时,高罗佩更彰显了她们的独特才情,这种艺术才情首先表现在她们的能歌善舞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善于歌舞演奏和有表演才艺的妓女,一般是高价赠品,或被呈送宫中或被赠送达官贵人,许多集聚在皇宫里或在有权有势人的手中”[12]45。《红阁子》中的银仙即为这类女子,她在初次登场时,自弹自唱、轻放歌喉,其歌声如莺声燕语,婉转动听,而教授银仙歌舞技艺的凌仙姑同样在这方面是技艺精熟。日本学者斋藤茂曾说:“总体上来看,妓女的交往对象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但是流传最多的是与文人雅士的交往”[12]78,正因如此,高罗佩也在《大唐狄公案》中彰显了青楼女子在与诗人文士交往过程中所独有的文学才情,《黑狐狸》中以鱼玄机为艺术原型的玉兰就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创作理念。家道中落的玉兰年少时被父亲卖入行院,身在青楼的她结识了众多文人墨客,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其更兼自身的颖悟聪慧,她很快就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非凡的造诣,而受邀参加翠玉崖诗会时的即兴作诗便是其诗情文采最为鲜活的写照,高罗佩对这一极富文思雅趣的情节也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刻:
玉兰小姐呷了一口酒,借着酒兴,索来笔砚,便走近一根红漆亭柱,命丫鬟一个捧砚一个擎烛。但见她略一思索,润了润笔,拣了柱上平滑无疤的一面,嗖嗖题了一绝。其辞云: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为怨情。知郎朝朝逐新欢,寄词自叹妾薄命。邵樊文、张岚波、如意法师、狄公、罗宽冲一并走近亭柱,轻轻吟哦,不由频频叹息,心中称许。[13]
这段情节表现了玉兰与诗友进行唱和时即兴作诗的整个过程,其所作的这首闺怨诗不仅对仗工整、情景交融,且又哀而不戚,怨而不怒。正如严羽所言:“诗者,吟咏性情也。”[14]陆时雍亦言:“体物著情,寄怀感兴,诗之为用,如此已矣。”[15]122可以说,玉兰在诗作中将自己虽为人弃、却旧情难舍的一腔愁苦曲折委婉地吐露了出来,从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才思敏捷、饱富诗情的形象侧面。同时高罗佩还表现了邵樊文、张岚波等诗会参与者在吟读这首“披情著性”[15]122之作后对该诗叹为观止而又自感不如的由衷赞许,由此其也从侧面折射出玉兰不可多得的文学才华。更为重要的是,与歌舞技艺多用于男性主导的欢宴聚会不同,玉兰的行诗作赋打上了女性主义的文化烙印。玉兰在与众多男性诗人吟诗作对的过程中,其诗作水准不输甚至超出了男性诗人的诗作,这实际上是《大唐狄公案》中男女两性之间平等文化交流的潜在表述,也是高罗佩在其作品中舒张女性文化话语权的无形投射。
(二)提供破案线索,襄助狄公办案。作为《大唐狄公案》这部作品中的核心人物,狄仁杰冷静睿智、缜密推理、屡破奇案,而女性对其成功破案亦不乏有重要贡献。如《紫光寺》中狄仁杰就曾在狄夫人的提示下成功找到失窃的朝廷御金,《铁钉案》中在女典狱郭夫人的提示下,狄仁杰才得以探知陈宝珍铁钉杀夫的隐秘玄机,《广州案》中盲女兰莉及其所豢养的蛐蛐为狄仁杰勘破钦差柳道远遇害案提供了线索。这种女性提供线索,帮助狄仁杰破案的情节模式同样反映在青楼女子身上,《黄金案》中玉珠将蓬莱前任县令托付与她、存有犯罪物证的木匣转交于马荣,为狄仁杰侦办王县令遇害案和黄金走私案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湖滨案》中杏花暗中将浦阳城中将有阴谋巨变的讯息传递与狄仁杰,《铜钟案》中,被狄仁杰赎身脱籍的碧桃、黄杏更是直接帮助狄仁杰破获了普慈寺淫僧案,而《红阁子》中的银仙亦助狄仁杰找到凌仙姑,继而使红阁子连环凶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在为狄仁杰提供线索、助其破案的过程,杏花、玉珠还为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通过上述情节描写,高罗佩不仅凸显了青楼女子所具有诗文、歌舞之才,更以义助破案的情节突出了她们纯洁善良、不畏奸邪的精神品格,这无疑在突出其饱富才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升华了其作为女性所透射出的人性光辉。
(三)追求婚姻自主的独立人格。“妓女们往往会在风尘岁月中留意寻找一个爱自己而又较可靠的狎客,争取让他把自己娶去。这种‘从良’的结局,常被看成是上等妓女最好的下场。”[16]秋月、史玉娘、碧桃等人无论结局如何,其都渴求并最终实现了赎身从良,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红阁子》中的银仙虽也希望脱离苦海,但其并未将赎身之愿寄托于显宦巨贾,而是渴求被心仪之人所救。她虽身陷风尘,但与秀才贾玉波却是两情相悦、暗结鸳盟,贾玉波本欲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银仙赎身,却未能如愿。银仙更是早已抱定如若自己为他人捷足先登、赎身而去,便与爱人以死殉情的决心。《断指记》中的沈云虽与其兄颠沛流离、生活无着,但当痴恋于她的富商万茂才提出要娶其为妾时,她却一再婉拒,而对万茂才所赠金银,她也从未接受,她所渴望的只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银仙、沈云虽对普通女性的正常自由生活十分向往,但这一愿望却淡化了利用自身条件攀金附贵、以求富足生活的利欲色调,而凸显出青楼女子掌控命运、自主婚姻的独立人格精神。
波伏瓦曾指出:“每个作家在界定女人的时候,也界定了他的一般伦理观和他对自身的特殊看法,他往往在她的身上记录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自恋的梦想之间存在的差距。”[5]336高罗佩亦不例外,其虽在《大唐狄公案》中塑造了多位具有独立人格色彩的女性人物,诸如《玉珠串》中为摆脱不幸婚姻而与相爱之人相约私奔的魏夫人,《柳园图》中不畏强暴、矢志复仇的侠女蓝白,但与之相较,作为游离于社会道德规范之外的特殊群体,青楼女子地位低下,倍尝人世的冷暖辛酸,因而但凡有财势者向其伸出婚娶的橄榄枝,她们为摆脱自身的现状和地位,便很可能会轻许于人,所以比之一般的高门名媛、闺淑良妇,其更易产生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依附心理,其独立人格的养成和命运自主的追求也更显不易。为此,青楼女子在表现出才貌兼备的形象特征、婚姻自主的思想意识以及襄助破案的智慧胆识之际,其所折射的男女平等思维和独立人格特征较之魏夫人、蓝白等女子更为显著,这更为鲜明地昭示了高罗佩在作品中所秉持的女性主义人文意识。
三、青楼女子犯罪形象的人性化关照
《大唐狄公案》在塑造众多女性人物的过程中,也展现了一些犯罪女性的特殊艺术形象。难能可贵的是,高罗佩并未对其形象加以矮化或贬抑,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将涉案女性还原为有丰满心理活动和正常人生要求的社会群体”[10]169,而这在梅柳氏、玉兰等青楼女子的身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柳园图》中本是青楼名妓的梅柳氏虽与助其从良的何朋情投意合,但却因后者家败而未能与之举案齐眉、比翼双飞。与之相对的是,虽然梅柳氏在嫁与梅亮后,过着饫甘餍肥、奢华安逸的生活,梅亮对她也十分关爱,甚至对她的通奸行为也宽忍待之,但梅柳氏却在与其相处中难觅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正如福柯所言:“对于夫妻双方,婚姻艺术并非简单地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即每一方根据双方确认的和共同参与的目的来行事,而且是一种二合一的生活方式。婚姻所要求的行为风格就是,配偶双方都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种两人生活,他们一起形成了一种共同生活。”“对方的存在、面对面和共同生活不仅是义务,而且是让夫妻团聚的婚姻关系所特有的期望。他们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作用;他们无法彼此忘怀。”[17]正是由于所嫁之人实非所爱之人,这一爱情与婚姻的错位才导致了梅柳氏杀夫被捕、庭审病亡的悲剧性结局。而在《黑狐狸》中,原本沦落风尘的玉兰在邂逅邵樊文后,与之痴心相恋,邵亦助其脱离风尘,但二人终因邵家的反对未能结合。由于情感的挫折和经济的拮据,玉兰再陷青楼,苟且偷生,并罹患重疾,后虽为人所救,但其始终难忘对邵之情,因而她虽详知邵樊文构陷他人、杀人灭口的内情,却不仅未将其告发,反而一味替其遮掩,甚至还不惜承揽罪责。《广州案》中的番邦妓女珠木奴也同样是因情犯罪,年轻貌美而又命途多舛的她在与钦差柳道远相爱后,为了将其留在身边,而暗自将一种须按期服用解药的毒酒为即将回京的柳道远饮下,后者终因未能如期返回,以致毒发身亡。
梅柳氏、玉兰、珠木奴这三位青楼女子虽然分别处于不同的故事篇章,其生活环境也不尽相同,甚至还不乏胡、汉之别,然而她们却同为历经情感挫折和人生坎坷的痴情女子。她们执着于刻骨铭心的往日之情,甚至还为之不惜触犯律法。格里耶曾说:“作家的传统任务就是挖掘本质,深化本质,以便达到越来越内在的深层,最后把一种令人目眩的秘密的碎片公诸于世。他一直走到人类情感的深渊中去。”[18]可以说,高罗佩通过表现梅柳氏、玉兰、珠木奴等三人的恋情很好地践行了作家反映人之深层情感的传统理念。她们并非为声名利禄或个人仇怨铤而走险,而是在复杂情感的支配下做出了后悔莫及之事,其杀害亲夫或旧爱的非理性之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对过往情感痴心所导致的心理畸变和精神异化。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一个人的性格不可能是单一的,它的每种性格表现,其实都是很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是系统质的总和显现。他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善的行为,事实上都包含着另一种潜在的恶的可能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极不简单”[19]。这种人之善恶的辩证认识在这些女性身上有着鲜明的表现,梅柳氏、玉兰、珠木奴三人因情犯罪,一方面触犯了国家法度,必将受到刑律的制裁,更在未能挽回过往之情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所爱之人的永远消逝;另一方面,这种执着甚至偏激的情感诉求也投射出这些有着青楼生活经历的女性渴求过上普通市井平民生活,继而能“与君便是鸳鸯侣,休向人间觅往还”[20]的强烈愿望,而在爱人背叛或旧情难复之后,失落绝望的她们也无疑是值得同情的情感受害者和生活无助者。由此,高罗佩将为爱痴迷、迷失自我、实施犯罪与思慕真爱、渴望摆脱世俗名利纠扰、以求过上正常生活,这种富于两面色彩的思想、行为特征集中于这些青楼女子身上。由此观之,这类独特女性形象的人性化描刻,不仅投射出高罗佩对命途多艰的风尘女子表露出浓郁的人道意识和人文关怀,亦使其笔下的青楼女子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圆形人物”[21]的审美特质,进而映照出他本人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艺术努力。
四、结 语
青楼文化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方面,在《大唐狄公案》中通过青楼妓馆、狎妓行为以及青楼女子等不同层面得到了多元化的生动呈现。与此同时,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通过青楼女子才华卓群、婚恋自由、机智勇敢等形象特征,不仅在青楼女子和男性人物平等交流的潜在表述中舒张了女性文化话语权,更由此赋予了这些特殊的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和鲜明的自主意识,而对犯罪青楼女子复杂的情感世界和特殊犯罪因由的生动揭示,则既投射出高罗佩的人道意识,更体现出他本人在塑造这些艺术形象时,力图展现出复杂真实人性的创作希冀。可以说,通过青楼文化的总体性展现,高罗佩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认识、审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文化视角,这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斑驳陆离的特殊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也同时传输了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两性关系文化的独特思考和认知。青楼女性的形象塑造以及由此透射出的女性主义色彩和复杂的人性审视则凸显出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的高罗佩所具有的理性反思精神,二者的相得益彰投射出了其在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中所秉持一种取道东西、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基本理念,这也成为《大唐狄公案》这部巨著能够风靡于东西方的重要缘由。因此,青楼文化书写对于全面探究《大唐狄公案》及高罗佩本人丰富广博的汉学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