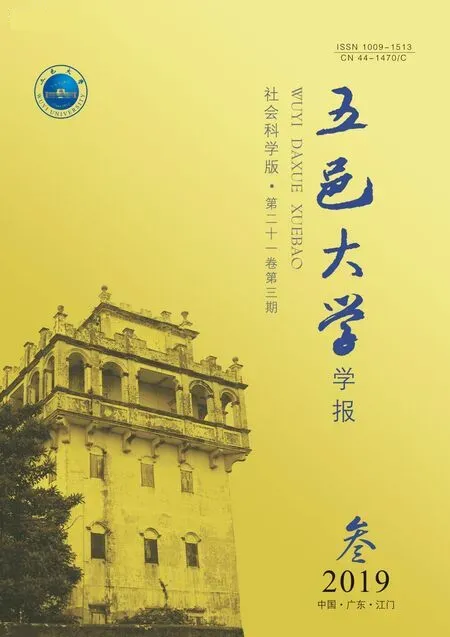论斯皮瓦克异质伦理翻译思想与实践
周庭华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194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翻译理论家。她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德里达 《论文字学》的成功翻译和介绍。作为一个身处世界文化中心的印度人,斯皮瓦克对语言的跨界始终保持研究的热情,撰写了一系列讨论翻译的名文,如 《翻译的政治》《想象的地图·译者序跋》《属下的文学再现: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文本》《关于翻译的问答:游移》等。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思考主要体现在探讨翻译所反映的不同文化和种族间的关系,揭示主流文化对他者文化的遮蔽机制,并尝试为他者文化发声的途径。美国学者Tat-siong Liew指出斯皮瓦克认为只有爱才能补偿翻译中不可避免的 “丢失 (losses)”,只有爱才能“认识到每一次相遇的 ‘伦理独特性'”。[1]美国斯皮瓦克研究专家桑吉特·瑞 (Sangeeta Ray)认为斯皮瓦克著作阐述的主要是 “阅读他者可能性相关的伦理问题”。[2]国内学者研究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通常采用两种路径:要么依据某一文学或文化理论(如后殖民主义或者属下研究)解读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政治诉求;①要么综合斯皮瓦克在不同文本中关于翻译的论述或者对斯皮瓦克某一篇文章中的翻译论点作详尽的阐发。②前一种研究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便于深入挖掘,但由于斯皮瓦克理论来源多元,其翻译思想远非某一理论所能涵盖,因此把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简单归于某一理论,有削足适履、管中窥豹之感。后一种研究貌似全面,但读后却让人不得要领,因为和德里达一样,斯皮瓦克使用的理论术语不断滑动,难以固定。③那么是否还有别的研究路径呢?本文作者认为,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始终以异质伦理思想为归旨,在她众多翻译理论文本和文学译作中,斯皮瓦克不断尝试如何通过修辞手段解除逻辑的控制接近原文难以表达的异质性。下面将从语言观、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等三个方面对斯皮瓦克的翻译伦理观做系统梳理。
一、斯皮瓦克的三层次语言观
作为跨种族跨学科的理论大师,斯皮瓦克庞杂艰深的著作常常让研究者感到如深陷迷宫,不得要领。其实斯皮瓦克的学术生涯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他者的伦理考察。桑吉特·瑞在其新著中敏锐地指出:“各个时期,宏观上看异质伦理一直是斯皮瓦克作品关注的中心,即使有时并未明确表述。”[3]异质伦理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1906-1995)伦理学的中心理念。与西方传统伦理观不同,列维纳斯伦理学强调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中他者的绝对异质性,即不能被自我意愿包含或主体的概念和语言再现的他者性。列维纳斯认为他者先于自我存在,他者的异质性是哲学的第一性。在 《意义与感知》一文中,列维纳斯写道:“我面对的他者不能尽为语言表述所包含,……他既不是文化符码也不是简单的给定,……他者的显现是他自己的意义生成过程,独立于外部世界给定的意义之外。”[4]如果说列维纳斯从认识论上强调他者的异质性,斯皮瓦克则侧重通过文学想象靠近他者。她说:“绝对异质性——完全他者——必须通过文学形象加以想象。人自打出生就得面向他者。对人的诠释以他者的异质性为前提。这是伦理关系中的人的底线。”[5]斯皮瓦克特别强调他者异质性是伦理关系中的人的底线,斯皮瓦克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思考语言问题。
斯皮瓦克对语言问题的考察重点不在语言自身,而是试图揭开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特别是他者的声音如何被意识形态的网络滤除。这是斯皮瓦克对异质伦理思考在语言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说她所思考的语言问题实质是语言所反映的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问题。在 《翻译的政治》一文中,斯皮瓦克指出人是在语言运用中构建自我身份的,这个过程不是封闭的自说自话 (identity as self-meaning),而是首先指向他者并向他者开放的交流过程。[6]179斯皮瓦克进而依据语言中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提出 “三层次的语言观”(three-tiered notion oflanguage): 逻辑、 修辞和静默。[6]181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符号系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符号本身。静默是语言交流的反面,是言语的缺位和交流的缺失,通常不能进入语言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斯皮瓦克对语言所分的三个层次中,静默处于最核心的位置。斯皮瓦克对语言的关注溢出了语言学通常的研究范围,因为她关注的重点不是语言交流而恰恰是语言交流的障碍。斯皮瓦克对静默的研究并非要揭示语言运行机制自身的障碍或者缺陷。她始终关注的是话语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他者消音。斯皮瓦克最有代表性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探讨的就是属下女性如何被主流话语消音。文中讲述了一个印度革命女青年因无法完成革命团体委派的暗杀任务而选择自杀的故事。她特意选在月经期自杀,以避免被误认为殉情而亡。但她以自己生命书写的信息经过主流话语的过滤而变得面目全非,即使在她亲人眼里,她也是因未婚怀孕蒙羞而死。而她真实的死亡动因则被主流话语抹除。斯皮瓦克从这个事例中看出,静默是语言的权力机制运作的结果,语言的缺位反映的正是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在场。斯皮瓦克继而从这个事例推演开来,发现静默并非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而是语言的内在特征,其根源在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对等,也就是列维纳斯所阐述的他者绝对异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皮瓦克强调语言不被理解的可能性或是 “没有意义的可能性”[6]181。
修辞通常被认为是语言的特殊用法。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发现修辞是语言的本质特性,只是人们对语言表达习以为常后,它的修辞性被遗忘了。解构大师保罗·德曼 (Paul de Man)从语言的修辞性找到了解构文本的切入点,而斯皮瓦克则把修辞看做克服他者绝对异质性的语言策略。“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修辞系统通过把这作为在语言之外总可能存在的危险空间而加以控制。”[7]279斯皮瓦克设想人类与太空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智能生物的交流场景,为了让交流成为可能,“绝对异质性或者他性被延异为与我们相似并能与我们交流的另一个自我。”[6]181通过修辞, 绝对他者被转化成另一个自我。斯皮瓦克将修辞转化过程描述为 “修辞则必须在言词之间及言词周围的静默中活动,试探怎样才起作用,效力有多大。”[7]280她认为修辞的基本机制是将处于理解疆界外的绝对他者置于自我范畴之下,她称之为 “修辞内在的对静默的暴力”(the founding violence of the silence at work within rhetoric)。[6]181我们仔细分析, 不难发现修辞过程存在一个内在的悖论。一方面,绝对异质性只能经由修辞过程才能走出静默,实现交流;然而经过修辞过程的转化,绝对异质性也就无法保留。也就是说,修辞并不能取消静默,因为静默正是修辞转化过程中所遗漏或者压抑的信息。
在斯皮瓦克对语言的分层中,处于最底端的是逻辑。斯皮瓦克对逻辑一词的使用有别于我们对逻辑的通常理解。逻辑学上的逻辑指的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或者思维的内在联系。斯皮瓦克是从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考察语言,她认为 “逻辑使我们得以依据明确表明的连接把言词串联起来”。[7]180与作为客观规律和内在联系的逻辑不同,斯皮瓦克强调逻辑是由外部强加的 “明确表明的连接”,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从他者角度看,逻辑是严密排他的网络,清晰明确的逻辑彻底清除了异质的声音,体现的是主流话语权力意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斯皮瓦克对语言所分的三个层次反映了语言所体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逻辑是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静默是被意识形态网络压抑和滤除的信息,而修辞是意识形态滤除他者信息的运行机制。依照列维纳斯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描述,我们可以将斯皮瓦克对语言所分的三个层次的关系表述为:静默代表绝对他者,逻辑是自我的体现,修辞是自我与他者的中间地带,是沟通自我与他者的纽带。斯皮瓦克一方面考察他者如何被意识形态消音,一方面探索他者发声的可能性。以此语言观为基础,斯皮瓦克对翻译的研究强调对他者的想象,也就是通过修辞的运用,打破逻辑的禁锢,尽可能靠近静默的他者。
二、翻译是爱的交流和阅读
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思考着眼于在全球化语境下保存弱势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性。在英语几乎一统天下的网络时代,边缘文化只有经过翻译才能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但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原文的独特语言和文化表达常常会被滤除。在斯皮瓦克看来,丧失了原文文化特性的翻译不是真正的翻译。斯皮瓦克探讨在翻译中保存原文文化特性的可行途径。她特别关注翻译过程的伦理层面,强调要在目标语中重建源语原有的语言的三层次的关系。她指出:“修辞和逻辑之间、获得认知的条件和获得认知的效应之间的不协调的关系,就是为能动者构建她的世界的关系,如此能动者才可能有伦理的行径、政治的行径、日常生活的行径;如此能动者才可在世上以人的方式生存。除非能至少为那另一种语言建构起这样一个模式,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翻译可言。”[7]280逻辑和修辞在翻译中的转换不难理解。但静默作为在原文中被主流意识形态滤除的信息又如何能译呢?国内有学者认为直译即可。“直译通过危险地接近这种修辞性,使得原文语言编织物整齐紧密的织边遭到磨损、变得松散脱落,从而释放出原文以逻辑方式逃避、限制和压抑的静默。”[8]对此疑问,斯皮瓦克并没有在技术上给予解答。与德里达相似,斯皮瓦克主要是从哲学和伦理的层面思考翻译。缘于此,她把翻译定义为 “把对他者在自我之中的痕迹的感应活演出来”,“在爱意中及有关爱的交流和阅读”,并将翻译者的任务界定为 “促进原文及其影子之间的爱,让散佚发生,免受译者的能动机制和她想像的或真实的读者对她的要求的牵制。”[7]278-79斯皮瓦克界定翻译的术语表明她思考的伦理维度,即他者异质性。无论是 “他者痕迹”还是 “爱的交流和阅读”都强调的是在翻译时面对异质文本所应保持的谦恭姿态,即翻译不是将原文的语言文化特性在目标语中化于无形,而是要 “译者必须完全贴服于原文。她必须在文本中苦苦求索,穷其语言尽处,因为那修辞作用的一面会指向文本的静默,在那里语言不受限制地散佚开,而文本则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去防止它的发生。”[7]283也就是说, “只有本着对人类的爱,对原文和原语的爱,那些 ‘具备对原语言场地的鉴别能力'的译者在 ‘贴服于原文的修辞作用'的过程中才能更接近翻译的伦理目标”[9]。
斯皮瓦克以自己翻译18世纪的孟加拉诗歌的经历为例,说明翻译如何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静默。“我翻译的时候贴服于文本。这些歌在我记事前就以家庭合唱的形式日复一日地演唱,让我感到特别亲切。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和贴服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我得以从记忆中的他者痕迹进入到自我最私密的深处。”[6]180这段话看似平常, 谈的也只是翻译的个人体悟,因此没有引起国内翻译学界的注意。然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翻译路径却不同寻常,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思想。斯皮瓦克强调在翻译中借由他者的痕迹进入自我,她首先突出的是他者的异质性,这就从翻译层面呼应了列维纳斯将他者作为第一性的伦理思想。斯皮瓦克在 《翻译的政治》一文进一步阐发了突出他者异质性的翻译,并归纳出 “作为译者的读者”(Reader as Translator或RAT)的概念。陈永国教授对这个概念做了深入阐释,形象说明了翻译要如何才能进入他者:“他/她 (译者)不仅要弄懂每一个字、词、句,还要身不由己地、本能地、自发地被文本慑服,被一种特殊的语境、文化、语言所慑服。在这种被慑服的状态中,主体与客体、源语言与目标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瞬间消失了,于是,译者在距离自我最近的地方跨越了他者的踪迹”[10]。
斯皮瓦克把 “贴服”视为向他者开放的伦理行为,尽管他者的异质性超越了理解的视域。她说:“作为伦理的能动主体,我们不能够倾尽全力去想象他者性或者异质性。我们只能将他者转变成和自我相近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伦理关系。翻译时的贴服爱欲的关系多于伦理的关系。……为了赢得这份友谊的权利或放下我的执著,为了明白只要你投入到文本中它的修辞作用就会给你展示语言的尽处,你必须与语言——而不仅与特定的文本——建立起不同的关系”[6]183。
就技术层面而言,贴服于源文文本的翻译就是要放弃符合目标语语言规范的 “安全”翻译,而要能体现源语语言异质性。[6]182所谓 “安全” 翻译指的是牺牲源语修辞特性的意义传递,也就是说对目标语的破坏被降低到最低值。而斯皮瓦克关注的不仅仅是传递源语的语言信息,她更强调保持源语的特定表达习惯和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信息。她因而主张尽可能直译,因为直译会打破目标语的逻辑关系和修辞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直译是对目标语的一次暴力。它能将处于静默中的源语最大程度地释放到目标语,带来异质的表达方式、材料和观念。斯皮瓦克强调翻译要贴服于原文,着眼点就是要保持对他者异质性的开放,目的是要让原文的异质性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得到保留。由此可见,斯皮瓦克的翻译策略体现的是她的异质伦理思想,即对他者绝对异质性的开放。斯皮瓦克的翻译实践始终以尽可能保留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第三世界的语言和文化特性为归旨。我们在此举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马哈斯维塔·德维 (Mahasweta Devi,1926—)是当代印度著名的政治小说家。她有一篇名为的“Stanadayini”的孟加拉语短篇小说,第一个英文译本将标题译为 《奶妈》 (“The Wet-nurse”)。英文 “奶妈”一词虽然表明了女主人公的社会身份,但却没法传递原文所暗含的 “将女性乳房视为商品劳动力的器官和将乳房作为将他者视为物品的隐喻物件。”[6]187斯皮瓦克在她的译本中自创了一个新词“乳房供应者”(Breast Giver),这个词巧妙地表现了主人公作为家庭和雇主的性工具和物品的价值。小说女主人公靠哺育主人家的儿女来养家,后来凄凉地死于乳腺癌,死时乳房胀裂。如果说 “奶妈”是英语的安全译法,“乳房供应者”则尽可能地保留了孟加拉语原文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打破了英文的习惯表达和英文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给目标语带来了弱势文化的异质信息,斯皮瓦克将之称为对目标语的 “社会逻辑,社会合理性和社会实践中的修辞性的破坏力”。[6]187斯皮瓦克强调翻译对目标语力的破坏是为了保留源语 (第三世界的弱势语言)的异质性。
三、翻译德维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仅仅要实现信息在语言间的转化,还要处理源语的修辞如何在目标语中转化和呈现。然而在从第三世界边缘语言到西方主流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修辞问题却常常被忽视。边缘语言和主流语言之间翻译的不平衡性最直接地体现在对译者的要求上。斯皮瓦克发现对以主流语言为源语的译者要求很高,例如对玛丽安·穆尔 (Marianne Moore)和艾米丽·迪金森 (Emily Dickinson)这些英语诗人的译者,既要求在语言上完全掌握目标语和源语,还要求精通诗歌;然而对以第三世界语言为源语的译者标准却降低到 “能够以源语交流的人”。[6]188结果导致 “所有第三世界文学翻译过来都有一股翻译腔,以至于一个巴基斯坦女性作家的作品行文风格和一个台湾男作家的类似。”[6]182也就是说边缘语言在被译入主流语言的过程中,其语言特点及其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被滤除了。这样的翻译是牺牲源语的修辞特性以适应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体现了主流语言的强势和霸权。无怪乎,斯皮瓦克称这类翻译为 “自恋的翻译”和“缺乏亲密的翻译。”[6]184那如何才能做到亲密的翻译呢?除了 “个人生活细节里所体验的对正确文化政治的深刻认同,……语言的历史、作家所处的历史时刻、以及翻译中和用于翻译的语言的历史,也必须予以玩味。”[7]288斯皮瓦克对以边缘语言为源语的译者所提出的要求,包含语言、文化、历史以及情感等诸多方面,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在翻译中保存边缘语言的异质性。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文学翻译者提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翻译马哈斯维塔·德维的经验总结。
斯皮瓦克早期翻译德维的作品时,常常为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改变甚至抹除孟加拉的特殊表达。如在 《德罗巴蒂》一文,她以直白的日常英语译出孟加拉部落人的口语。斯皮瓦克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总结了自己翻译时选择语言风格的策略:“我曾在翻译部落人说的特定的孟加拉语时遇到 ‘译者的难题'。总体上,受教育的西孟加拉人对部落人的口语有种族主义的歧视……。而用劳伦斯的 ‘大众'英语或者福克纳的黑人英语又让人尴尬。再说语言的独特性无关宏旨。我选择使用‘直白英语'。”[11]斯皮瓦克所说的 “译者的难题”主要是指在翻译中如何选择语言风格。语言的风格是语言使用者的阶级和种族的重要标志。劳伦斯小说中工人用语粗俗不堪,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口语不合英语表达规范,读者阅读他们的作品有不小的难度。而德维笔下的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部落人的用语自然更会让英语读者望而却步。初涉文学翻译的斯皮瓦克于是选择使用 “直白英语”翻译部落人的日常用语,这无疑降低了英文读者的阅读难度。但因为斯皮瓦克没能在翻译中保存或者体现部落孟加拉语的独特性,源语所鲜明刻画的部落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也就一并抹除了。虽然我们不能以斯皮瓦克自己所批评的 “翻译腔”来贬低这篇英文译文,但它也的确称不上 “亲密的翻译”。
十多年后,斯皮瓦克在翻译德维的长篇小说《蒙达和他的箭》时,采取突出源语独特性的翻译策略。她采用对美国方言昵语的大胆变形,把西孟加拉语的独特节奏和形象以创造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为了表现部落人蒙昧原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斯皮瓦克大量省略单词的元音或者辅音,由此产生的支离破碎的句式冲击了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些词单独看来难以理解,但连在一起读却简单明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句式成功营造了部落人艰辛困苦的生活境遇和在面对压榨剥夺时发声的困难。马克·桑德斯 (Mark Sanders)评论认为斯皮瓦克的翻译 “发明了新的语言。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土语中包含了美国俗语和口语体的词汇和转译的含有英语外来词的孟加拉语。”[12]44以下, 笔者引用一段斯皮瓦克的译文来加以分析:
Why're ye jerkin't'Mundas aroun'at market and takin'cuts?
Who said?
I say.Daroga must be told.If ye cross t'Mundas-takin'cuts again! Understan'? Then Daroga too will hafta answer.Yes,I'll not tease t'Munda People.But e'en t'Gormen don'want new torture and t'Munda roughed up.[13]6
这段充满吞音和词汇变形的对话较为真实地呈现了原文质朴破碎的风格。不规则的拼写,如“gormen” (government), “hafta” (have to) 既体现了口语随意多变的特点,又切合部落人淳朴闭塞的身份,与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口语和劳伦斯的工人口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注意的是,斯皮瓦克的英文变体简洁干脆,没有所谓黑人英语常见的重复拖沓,而有庄严凝炼的质感,如未曾雕琢的璞玉,传达出在种族迫害和资本压榨下挣扎的部落人的尊严。诚如斯皮瓦克在译者前言中所说:“这部小说的最鲜明特色之一是属下对话所营造的氛围,这些属下人并没让人觉得卑贱。就好像是乡绅的话语,只是少了些语法规范而已。我长时间对这个特色的翻译有所担心。……令我欣慰的是,我到达加尔各答,马哈斯维塔·德维一见到我首先提到的就是:‘盖亚特里,我对你译文由衷欣赏,你把方言表现得那么高贵。'”[13]vii与十多年前的译文相比, 斯皮瓦克更加原汁原味地保存或者表现了西孟加拉口语的质朴和简洁,语言的独特性及其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夹杂着西孟加拉语的不规范的英语是斯皮瓦克在翻译时贴服于源语的创造。马克·桑德斯对斯皮瓦克所译方言的伦理意义做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这种口语体所暗含知识精英与部落贱民的某种关联或者关联的缺失, 这正是伦理的标志。”[12]45的确, 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斯皮瓦克找到了一条贴服于源语的亲密翻译之路,从而最大程度地在译文中体现了西孟加拉语的独特性。
四、结 语
在 《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论证了在男权社会和西方文化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属下女性无法自我言说的事实。这只是斯皮瓦克关注的意识形态网络滤除的异质性他者的个例。她一方面用犀利的理论论述破除西方意识形态的藩篱,揭示被主流话语遮蔽的他者异质性,一方面通过翻译德维等第三世界作家的文学作品,把来自异质文化的一个个鲜明形象展现在英语读者眼前。对于翻译德维作品的初衷,斯皮瓦克说道:“阅读她 (德维)的作品我能想象出一个不可能的完整的世界,没有这样的世界便不会有文学。……或许是自不量力,通过与这些独特人物的神交,我试图打开难以企及的社会正义的结构,见证语言、主题和历史的独特性并以这难以实现的全球公正的体验对这个杂合的全球文化的霸权观念加以补充。”[14]斯皮瓦克翻译德维的作品的目的在于描绘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是个完整的世界,他者的异质性得以呈现,多元文化异彩纷呈。正是由于斯皮瓦克对这个理想世界的执着信念,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作品才能在世界各地的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参见陈永国:《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载 《外国文学》2005年第5期,37-43页;袁晓亮;《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翻译——读斯皮瓦克 “翻译的政治”》,载 《中国校外教育 (理论)》2007年第2期,24-25页。
②参见关熔珍:《斯皮瓦克翻译研究初探》,载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62-65页;李红玉:《斯皮瓦克翻译思想探究》,载 《中国翻译》2009年第2期,12-16页;蔡新乐: 《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悖论与修辞误用》,载 《外语教学》2010年第3期,84-87页。
③斯皮瓦克给翻译下了一系列定义:“阅读就是翻译,翻译就是阅读”、“把对他者在自我之中的痕迹的感应活演出来”、“在爱意中及有关爱的交流和阅读””、“文化即翻译”。蔡新乐教授对 《文化即翻译》一文的解读着重揭示了斯皮瓦克观念中的 “悖论”和关键词的修辞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