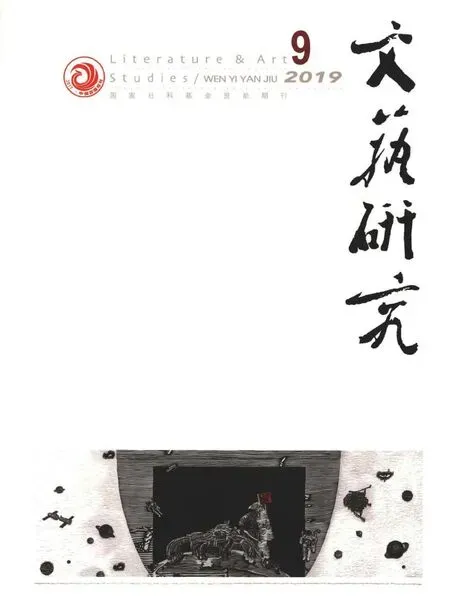成体之道:《文心雕龙》《体性》《风骨》篇关系重估
赵树功
《文心雕龙》一书中《体性》《风骨》二篇的关联,学界已有所关注,或将“风骨”视为《体性》“八体”之外最为理想的艺术风格①,或认为二篇皆与作家志气相关②。若从全书理论体系考量,可以看出,《体性》与《风骨》都是围绕文体展开的。“风”承接“性”,“骨”承接“体”,《风骨》的确属于《体性》的意义深化。《体性》讨论的是才性与文体关系制约下的才性偏宜,而《风骨》则是才性偏宜的文体在具体创作中的落实之道。《体性》对于文体、才性关系的讨论是针对一般可能性而言的,其中涉及的八种基本文体通过后天努力皆可掌握,可称之为“得体”。不过,“得体”并非文体确立的标志,只是文体建构的起步。能否真正“成体”——彰显出一个作家独到的个性,关键还要看作家才力的高下,只有融合风骨并赋予文采的作家才能实现“成体”。因此,《体性》《风骨》的关系可以视为从“得体”至“成体”或者由“共体”至“个体”的确立过程。
一、文体确立的路径:从“得体”至“成体”
自从文体概念进入文学批评,至六朝已形成以下基本指向:由内容倾向而言题材,由形式规范而言体裁(又称体制),由主体才性的贯彻而言体格、体调、风体、风调。《体性》中,刘勰论及了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其一为总括而言的“八体”之“体”,其二为“八体”融合主体才气之后其异如面的创造之“体”。
《体性》从文体与才性的关系展开,但全篇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此。《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理论巨著,而且有着指导创作的直接诉求。从这个角度审视,该篇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醒文人:创作应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③。
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互文见义,是指顺着自己的性情学习和自己的个性比较接近的体格,在形成自我习尚的同时来锻炼或练习自己的才能。这里的“体”,特指“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体”。文人各具才性,诸如“韦、柳隽逸,不宜长篇;苏、黄瘦硬,短于言情”,都是“才力笔性,各有所宜”④。但并非每个文人对此都有客观体认,勉强从事和自己才性并不匹配的创作、追求与自己才性距离较远的体格者大有人在。“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因此成为一种深明我性的艺术智慧。明人“谐情合体,仿性纾才”之论也正由此敷衍而来⑤。只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不仅刘勰所论“摹体”之“体”皆就“八体”而言,《体性》全篇但凡涉及“体”字,其意义大都如此。尽管文中专门论述了才气对于文章体貌的直接影响,但对这种与才气对应的体貌,刘勰自始至终没有以“体”相称。也就是说,《体性》篇论“体”,主要不是从个性风体(或者说从后世所云作家的个体风格)立论,而是锁定在具有超个体意义的“八体”之上。
对于“八体”,刘勰始终是从学习维度关注的,如“体式雅正,鲜有反其习”,“八体屡迁,功以学成”(《体性》)。如上所述,刘勰将“八体”与个人体调分而言之,而个人体调概举之就有十二体。在刘勰眼中,“八体”属于文体的基本类型,是个性化体调创造的起点。基本类型的熟谙与个性的形成在作家成长历程中也许有其先后,但它们必然以统一体的形式出现,即无论如何变化,作家“不同之种种体貌均可归入此八体之中”⑥。文中“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等一节文字,“上句斥其材性,下句证以其人之文体”⑦,如此论述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个人体调与“八体”的统一关系。“八体”的掌握并不说明作家独到艺术体调的形成,这只是作家走向成熟的初阶,可称之为“得体”。
如果说《体性》表达的是体调与才性之间大略对应的基本规律,那么《风骨》核心解决的就是具体创作之际如何实现这种基本对应,或者说,如何将才性贯彻于作品之中。刘勰认为,虽然通过后天之学可以模仿一些类型化体格,但是,只有“风清骨峻”才能成就真正属于自我的体调,是谓“成体”。而“风情骨峻”的根本则离不开性情才气。
《诗经》“六义”以风起始,风、气一体。《风骨》开篇即敷衍其大义:“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从气论文艺思想而言,文本于气,由气而至文,气化赋形,一气相通。而气的显形必赖乎文辞,因此“怊怅述情”(“情”即气的感动)之后继有“沉吟铺辞”,而情辞融合的关键在于“文骨成”“文风清”。先看“文骨成”。“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文辞对于文骨的需要如同身体离不开骨架。文骨成就具体表现为“结言端直”“析辞必精”:“结言端直”就是文字有力,尤其指向直达本义而非氵曰没于采饰造作;“析辞必精”就是文字精确,“捶字坚而难移”。再看“文风清”。“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性情之中包含气质,如同肉体之中鼓荡着自我生气,这里侧重个体气质的昭著,具体表现为“意气骏爽”“述情必显”:意气昂扬、纯真即是“意气骏爽”,根本在于性情意趣源心而发、为我独有;性情意趣显扬、声律谐调宣畅就是“述情必显”,具体呈现为自我性情、情意的鲜明贯通。如此“文骨成”“文风清”则情辞融合,如同个体生命具备了生气与骨肉,文体也便傲然挺立了。
如果说“结言端直”“析辞必精”的“文骨成”尚可以凭依学习锻炼渐趋成就,那么“文风清” 所仰仗的主体性情才气则必赖于禀赋,由此才能实现“风清骨峻”。刘勰在详论“文骨成”“文风清”后笔锋一转,宣言“缀虑裁篇,务盈守气”,集中于主体禀气的颂扬,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风骨》云: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这个“气”就是禀气,当然表现为主体的生命活力,但同时又浑融着作家的性情才气。刘勰这段文字是对作家个性化精神与作品风骨根本关系的直接认定。
《风骨》是以主体的性情才气与文辞风体统一为理想追求的,其赞语所云“情与气偕”的状态得之于“蔚彼风力”的涵养,是才气的陶冶;“辞共体并”的表达源自“严此骨鲠”、析辞必精的磨砺,主要关乎学习。以上才气涵养、学习磨砺兼容了《体性》所言风体建构依托的才气学习,作家“才锋峻立”的素养便在如此天人相合之中得以塑造,偏能之才性获得如此锤炼也便有了“符采克炳”的风体与之相称。可以说,“八体”只有与作家风骨相融,充满生命活力的个性之体才能绽放。从《体性》到《风骨》因此就成为一个从“大体”到“具体”的个人独到文体的塑造过程,是文学的显在形制与作家潜在精神的融合之道,是从“得体”至“成体”的创生之道。
风体的形成(“成体”)意味着作家于艺术殿堂的登堂入室,它是主体才性禀气的艺术赋形,又是文学之士造诣的认证——只有才华卓著者方备此殊荣。体的本义源自生命体,许慎《说文解字》释为“总十二属也”⑧,即首、身、手、足等十二部分的总合,包融着主体的完整形质、气血性质。审美理论言体由此引申而来,其中蕴含着生命的圆活性、系统性、有机性、贯通性。刘勰将作家文体的创造从《体性》的泛论延伸至《风骨》的具象,既是对文体生命性质的贯彻,也是生命性质文体的内在需要。
二、文体创生的关键:从学习入手至才气皈依
从《体性》至《风骨》,刘勰所依托的基本理念就是天人合一。《体性》先后四次论及文体创造必有待于天人合一。一则开篇总论才性与文体的关系:“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才、气本自禀赋自然,属于天的范围;学、习出于后天,归于人力。二则云“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意在提示“八体”尚非个性化的风体,作为类型化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但随之又云:“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意思是说,及至“各师成心”阶段,风体之中便镌刻上了才性印痕,“才力”“情性”在古代都是才性的异名表达。三则云“才有天资,学慎初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论及文体的熟悉与磨砺,也是兼天人而言的。四则在篇尾的“赞”中,先有“才性异区,文辞繁诡”之论,从才性的决定意义对体性关系予以定位;后云“习亦凝真,功沿渐靡”,表现了对于学习师法直接影响文体特征的关注,同样兼言天人。
《风骨》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天人合一系统。其开篇即由“怊怅述情,必始乎风”发论,“风”是气的流行,泛指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情感,是主体性情与本然生命力量的综合,才力也融会其中。这一点刘勰在《体性》中已经明确:“才力居中,肇自血气。”《风骨》论风论气,实则就是从才性才力的源头立论。作家认识自己的才性才力、磨练自己的才性才力、坚守自己的才性才力,就可以实现“意气骏爽”,最终形成独到的“文风”。再看“骨”的内蕴。从字面理解,论“骨”就是从作者的修为立论,如同一个生命体,初时肢体柔弱,无以自立,及至骨节壮大坚实,则成就其间架体格,具有了生长发育的根基。回到创作上,刘勰以“结言端直”“析辞必精”论“文骨成”,其反面例证则为“瘠义肥辞,繁杂失统”。一正一反都表明“文骨”的成就需要两个工夫:一是语言精到,一是体法熟谙。具体学习之中二者不可分解,作家都是在体法的习练临摹之中逐步实现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而体法习练在刘勰看来就是“练骨”的过程。《文心雕龙》一书中,“骨” 与作为文体最基本意义的体裁法度、经典文体范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檄移》:“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章表》:“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奏启》:“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这里的“骨”皆出现在体裁论中,是文辞成章的相应规范。《风骨》“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之“骨”,同样延续了这层意思,而“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之“骨”,则更指向经典的、可以传承的体格法式。以上无论体裁规范抑或经典体式,都可以后天临习追摹,如此一“风”一“骨”,恰是兼言天人两端。
不过《体性》《风骨》虽然皆属天人合一的系统,具体命意却各有所属。《体性》极为重视“才气”,但主旨在于通过才气学习之于文体影响的论述强调“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的重要。无论文体摹习抑或才能训练都立足于创作的启蒙初阶,属于人力范畴。关于这种人力侧重,纪昀早有觉察,在“才有天资,学慎初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数句的批语中,他这样说:“归到慎其先入,指出实地工夫。盖才难勉强,而学可自为,故篇内并衡,而结穴侧注。”⑨正指出篇中才气、学习天人并论,而最终意旨则落实于可为之人力。
与《体性》天人合一而侧注于人(学习)不同,《风骨》恰恰是天人合一而侧注于天(才气)。尽管“风”“骨”不可离析,但《风骨》全篇则以“风”为主。刘勰虽然将“捶字”“结响”之力名之曰“风骨之力”,但对“风骨之力”的阐说则最终归结于曹丕“文以气为主”等文气论。论“风骨”而归于“重气之旨”,这一命意明代曹学佺早已勘破:“‘风骨’二字虽有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⑩刘勰在曹魏前贤论气诸例之后,又列举了禀气不同所产生的两种偏才:或“肌丰而力沉”,有文饰无气力;或“骨劲而气猛”,有气力而乏文采。两种形态最终都被纳入“文章才力,有似于此”的评断。如此而言,《风骨》虽然延续了《体性》在文体建构中对于才气学习的依托,但论述重点则落实在“气”与“才力”之上,其侧注于天的倾向不言而喻⑪。
既然侧重研讨才气对于文体建构的影响,为何又以“风骨”立名呢?除对于才气纵逸心存警惕之外(这一点下文有论),根本原因在于才气属于作家的虚灵范畴,无可诠表,因而刘勰便由表象可鉴者入手——相比才气,“风骨”更便于鉴察感知。以“风骨”论文源自汉魏之际以骨相品人的占察之术,骨相之中潜伏着性情、气质的根脉,孕育着寿夭、成败的症候,具有观其表相可以测度其里的特征。如王右军品祖士少云“风领毛骨”⑫,所谓风气独标于毛骨之间,正是从骨相鉴察人的气韵风度。刘勰将文骨之成、文风之清定位于“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将风骨与文辞、意气统一,正是因为天赋难言,故而就表象可鉴者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界影响较大的“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之说,的确勘察到了“风骨”的用意,但非其本义⑬。
由《体性》偏于人至《风骨》偏于天,体现了刘勰对于文体建构过程中天人合一特征的细致把握:由人力入手,以天赋创构;自学习“得体”,凭才气“成体”。能够“得体”仅仅具备了“成体” 的客观条件,作家是否具备非同寻常的才气才力方为最终能否“成体”的关键,骋才创体是《文心雕龙》的核心理论⑭。由此而言,有学者将“风骨”视为“作家情志、才气在作品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成功之作必备的一种特质”⑮,是极有见识的。如此文体“风”“骨”兼备,其本质就是“格”“调”统一。杨慎评点《风骨》曰:“《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又评“文明以健”云:“诗有格有调,格犹骨也,调犹风也。”⑯“美”是基本标志性的尺度,合乎这一尺度可以纳入美人的行列;但美人各自之美却千姿百态,“艳”便属于其中一种。依照这一譬喻观照“风骨”:“骨”本于文体的共同规范,呈现为共性的、类型化的审美品质,相当于古代文艺理论常言的体格或《体性》所言的“八体”,“风”则出乎才气才性,是主体精神气质的体现,一如六朝之际人伦识鉴所谓的“才调”。只有作家的精神、才调贯注其中,真正美学意义的文体才算最终完成。而这一“风”“骨”完美融合的过程,就是“格”“调”的统一过程。
三、文体完善的保障:从归雅制至防华侈
就文学实践而言,作家“成体”已经是极高的境界,相关问题的讨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刘勰是一位有着浓厚儒家情怀的学者,文艺在他眼里不只是独善之具,更是“经典枝条”(《序志》),是“纬军国”“任栋梁”(《程器》)的媒介。因此,他所确立的文章诸般标准多以经典“六义” 为归趋,在一般的“成体”标准之外,又延伸出了《体性》之中的归于雅制与《风骨》之中的防华约侈,二者可视为作家文体完善的保障。
《体性》所论“八体”,“典雅”居于首位,从渊源而论虽然仅仅指向“镕式经诰,方轨儒门”之体,有别于“馥采典文,经理玄宗”的“远奥”及其他诸体,但“典雅”却是诸体的根本。有关“典雅”的这种根本地位,刘勰通过文体学习之初应当如何选择进行了反复强调:天才不可勉强,文章只有从临摹习练入手,而这个过程需要格外慎重,因为“器成采定,难可翻移”,如同木器斫削与丝织染色,一旦定型定彩,便再也难以复原。“童子雕琢,必先雅制”,自然成为他的核心命意。只有以“典雅”之体为根基,才能“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才能“雅丽黼黻”,继而规避“淫巧朱紫”。刘勰将以上规范纳入了“文之司南”,可见其重视程度。
《风骨》之所以单独立篇,在深化《体性》有关文体创造的论题之外,还为了纠正文坛病弊。南朝文学其时约有二病。其一,忽略传统法度而纵其才气。刘勰重视经典体式与传统法度,这与他文必宗经的志趣相合,所以在《风骨》中提倡“镕冶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经典提供的范式与法度是“骨采圆,风辞练”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个基础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则“虽获巧意,危败亦多”(《风骨》)。所谓“驰骛新作”,就是纵恣才华、不加敛束。这种“空结奇字,纰缪成经”(《风骨》)的危败创作并非刘勰的揣测、假设,而是当时文坛的常态。《风骨》所云“意新” 而“乱”、“辞奇”而“黩”,《定势》所云“近代辞人,率尚诡巧,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通变》所云“宋初讹而新”,《序志》所云“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等等,皆是就此而言。其二,“文滥”而掩蔽自我面目。“文滥”就是言过其实。刘勰以《周书》“辞尚体要”为标准,鉴照出当时文坛“流遁忘反”(《风骨》)、文饰过甚的现状。在其他篇章中,他对类似弊病也屡加指摘,诸如《情采》“为文造情”“体情之制日疏”“淫丽烦滥”,《序志》“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等等。
无论“纵才”还是“文滥”,最终皆可归之于“习华随侈”(《风骨》),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骨》的本旨在于确立才气在文体创造之中的核心地位,这并非意味着学习、师法不重要,而是刘勰从作家“成体”的实际出发、从突破模拟绮靡之风的目的出发做出的必然选择。但刘勰对于才气的纵恣不羁特性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才气讲求过度往往会流于率意,此时对于经典体式规度的倡导也便有了约束才气、谨防逸辙的祈向。《风骨》侧注才气而由“风骨”立论,其间寄寓着对人格涵养的关切,这与刘勰对才气发露特性的警惕不无关联。
以上病弊在刘勰看来都属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序志》)趋势的具体表现,正因为“文体解散”而不成文体,所以对于以上偏蔽的警惕成为作家创作“成体”的必然要求,“风骨”与文采兼美的文体标准因此得以确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惟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骨》)风骨主内,藻采主外,内有生机,外有光泽,内外兼修,作品才能“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肌丰而力沉”的偏文采与“骨劲气猛”的偏风骨都应避免。刘勰的这一思想,与其“贵器用而兼文采”(《程器》)的观点遥相呼应。当然,在他的理论体系内,风骨、文采的地位并不相当,二者兼美需要一个前提:首先必须“练于骨”“深乎风”——风韵鲜明、析辞精要,“兹术或违,无务繁采”(《风骨》)——没有风骨的挺立,藻采的经营毫无意义。
以上思想表达体现了刘勰深刻而清晰的佛教中观思维。对于文体的创造,他既颁布正面的准则——归于雅制与风骨、文采兼美,又揭示反面的病弊——崇尚奇诡与“习华随侈”。对于文体创造的依托,他既论尽才气以见自我风体,又论尽人事以熟谙轨式,尽天尽人皆出于补救偏蔽。天人观照之中,尽我才气方成风调,以此申明人力的限度,但又以骨体骨法约束才气;尽人之学以洞晓情理变化与文体规矩,同时又以不随流俗敦劝。才华运使之中,既期待“才锋峻立”,又提醒“务盈守气”,挥洒与涵蓄必须统一。就风骨与文采的关系而言,刘勰反复宣言风骨不可离开文采,目的在于提醒:风骨虽然重要,但创作不能落入枯质;同时,他又不断强调文采不可离开风骨,矛头直指当时文坛的形式主义风潮。
佛教中观思维促成了刘勰以上细密周全的文体理论建构,但建构理论显然不是刘勰最终的诉求,其最终诉求应当在于推动文学实践走上归于雅制的康庄大道。《体性》对于归雅有着鲜明的论述,《风骨》亦有着同样的意旨。《宗经》有“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之说,“六义”是经典的审美特征、后世文章的高标,而“风骨”恰是“六义”的升华。具体而言,“六义”所谓“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的“风”“情”对应“风骨”之“风”,“风”“情”本来一体,以生命之气的运动为载体,表现为个体才性气质。“六义”后四项皆就“骨”论:《风骨》赞语中明言“辞共体并”,论辞就是论体,因此篇中“结言端直”“析辞必精”“捶字坚而难移”即为“六义”所谓“体约而不芜”;对于风骨、文采兼美的强调即是“文丽而不淫”;主张“镕冶经典”“翔集子史”从而规避“虽获巧意,危败亦多”(《风骨》),便直接关系到“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刘勰既反对“跨略旧规”的“驰骛”,又批判“习华随侈”的“文滥”,其目的在于呼唤作者能够“确乎正式”(《风骨》),“正式” 无他,即与“六义”相合的雅制而已。
四、相关焦点问题反思
从《体性》至《风骨》,是文体建构由“得体”至“成体”的深化。以此审视,《文心雕龙》研究中一些相关阐释也便需要重新估量,其中亟需厘清的就是《体性》“八体屡迁”“会通合数”中“屡迁”与“会通”的本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以“风格的多样性统一”理解中国古代文体思想的合理性问题⑰。
关于“八体屡迁”,学界最基本的理解就是,作家的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能实现这种风格之变,就可视为“会通合数”。具体所指,各家略有差异。詹锳认为,所谓迁变、会通,以如下两端为主:首先,“作家的文章风格可以逐渐变化,繁缛的可以变为精约,新奇的可以变为雅正”,这与黄侃的理解一致;其次,“同在一个作家中,通过思想的修养,艺术的锻炼,风格可以多样化”。当然,变化的根源就在“功以学成”之中⑱。如此理解,“屡迁”与“会通”即是“八体”内部的变化与综合。吴林伯看法与此不同,他指出,所谓“屡迁”指向的不是“八体”,乃是“从八体派生出各种风格”,“会通”由此成为这种迁变之能⑲。
从“八体屡迁”至“会通合数”的理解,又延伸出了中国文体论讲求的“风格的多样性统一” 命题。这一命题的开创者是詹锳。在对“八体屡迁”的解读中,他已经提到,同一个作家“风格可以多样化”。在阐释“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的意蕴时,他又指出:“只要抓住关键,则各种风格就可以形成多样化的统一。”⑳这一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曹顺庆也认为:中国的体与西方的风格论虽然都讲统一,但西方强调的是主观风格、客观风格的统一,而中国更多强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㉑。那么,风格多样性最终要统一到哪里呢?詹锳认为,其一要统一到“主导风格”,比如“典雅”;其二要统一到《定势》所确认的体势所在㉒。
假定风格是多样性的统一这一命题成立,“八体屡迁,功以学成”的偏于人事便与“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的偏于才气、性情产生了抵牾。我们不能不质疑:既然风格乃是功以学成,又何来“才气之大略”的限定呢?能与性情、才气对应者当然是有限甚至有定的,如何可能随机生变、因学而变?如此而言的话,风格的独到性也便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可见,以上理解是有偏误的,举其大者而言,约有二端。
偏误之一,将“功以学成”的“八体”之“体”,与熔铸了作家才气、性情的创造之“体”混为一谈。《体性》至《风骨》,论述的是由“得体”至“成体”的历程,由此着眼,“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至“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一节文字是说:“八体”可以学习、临摹且每有变化,作为一种知识性的存在,它向所有人敞开;随着经验的积累、爱嗜的变异,作家可能多体共得,也可能随时调整,如“八体”内部互相转换,由繁而至约等等,甚至“八体”彼此融合,如壮丽之中兼备新奇等等。这些变化与熟能生巧的技术养成相关,但又无不体现出作家才气、性情的潜在投射——偏长于“八体”之中的哪种体格、所长之体如何运使、相关要素如何组构等等,处处袒露出个性化的选择与手段,与共性相异的个性化风体也便由此形成,这就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如同屠隆对“仙才”的论述:“人但知李青莲仙才,而不知王右丞、李长吉、白香山皆仙才也。青莲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玄冲,长吉仙才而奇丽,香山仙才而闲澹。”㉓作家及乎此,已经达到了“成体”的境界。从“八体屡迁”至“莫非情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前者是讲“八体”可变、因学而得,后面才力血气的引入不是另起炉灶的才性描述,而是讲“八体”虽可变化但其变化并非毫无节限,而是遵循着作者才力血气的程限。可以说,才力血气的引出,是对文体建构之中人力所能的一种约定。
事实上,能够与作家才气大略真正切合的文体是有限的,它发端于主体的才气、性情,依托于“八体”完成、表现。但凡创作,只要从雅制出发,以才性所宜为原则,那么具体表现之中无论远奥、显附抑或精约、繁缛,并无统一的规则,在适宜、需要的地方运用适宜、需要的文体即可,这是作家才力的体现,是为“会通合数”的“合数”。如此说来,作家风格意义的文体不是所谓多样性的统一,而是适配作家才性前提下的多种表现形态的统一。
体派或者体类意义的文体有着较为稳定的类型,刘勰“八体”之外,类似的还有皎然的“辨体一十九字”、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皆可纳入这个范围。这些都属于知识范畴,可以通过后天之学逐步熟悉并多样化地统一于一人。但是要创生真正的自我之体,在以上人力的基础之外,必须以源发于主体血气的才气、性情为根本。在这一点上中、西文论有其相通之处。比如,康德就曾指出,美不是科学,因此没有与科学一样的教学方法,美的传授“只有风格”(modus)。但康德随即做出解释:大师必须示范学生如何面对这些既定的风格,只能以之入门,以之纳入记忆激活想象,只能视之为一种“附带”,却不能成为代替艺术“理想”的“原型”与“模仿范本”,而艺术“理想”的决定者只有“天才”㉔。康德所说的“天才”,与刘勰所讨论的才性或性情大致相当。
偏误之二,以“风格”通解文体之“体”。以风格多样性统一概括古代文体思想特征,虽与八体“屡迁”“会通”以及相关文字的完整理解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以现当代意义的、由西方引进的“风格”直接替代了传统“文体”之“体”㉕。如此格义不仅未得其实,而且也造成了对古代文体理论思想的解构。
作为中西极为重要的文论关键词,文体与风格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差异。中国之体兼具体类体裁、体制架构与体派风格之意,西方的风格论偏重于作家作品;中国体论侧重于主体的才性,西方风格论更为关注作品的语言形式;中国体论追求生命之气、人格精神甚至道德品格的前后贯彻,而西方风格论则体现了鲜明的理性精神,聚焦于主观风格与客观风格的分量协调㉖。
古代文学的创作往往被归结为题材、体裁、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的组构,刘勰将以上要素的有机相融称为“体制”,并在《附会》中申言:“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与《颜氏家训·文章》中“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的论述异曲同工㉗。其中“理致”近“情志”,“气调”即“宫商”,“华丽”实“辞采”,“事义”则二说相同。诸要素的综合,如同一个人内有其骨髓神明、外有其声气肌肤,文体由此成立。而有此文体,则可以“制首以通尾”(《附会》),实现作品的生气贯通,而非尺接寸附。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文体并不玄虚,它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个系统。不同作家以上诸要素的显现形式、程度会各有不同,这种相异的特性综为一体,便形成自己具有一定倾向性的风体。由于古代文体论包容如此复杂,具体批评之中以文体之一端直接名曰文体的现象也便成为常态,就如同才情、才气、才学等等本义为主体之才在情怀、气势、学问上的显现,皆为才用的一维,但习惯用法中则以“用”名“体”,常常以之代言才本身一样。于是,创作之中无论题材体裁还是情志事义、辞采宫商所呈现的独到倾向,也便被视为文体。
由此看来,现当代意义上的“风格”更接近古代文论中的“格调”“体调”或“才调”,仅仅属于古代“文体”之“体”内蕴中的部分内容。不分语境地以“风格”转译“文体”之“体”,节缩了“体”的意蕴,放大了“风格”的应用边界。如此格义,便直接带来以下问题:将得体初阶习练的“八体”与成熟作家成就的“风体”混淆;将学力勤勉可得者与必待卓出天资才力者混淆;以西方主客二分理念阐释中国古代文体,单纯由作品立论研讨风格,忽略了中国古代论体必归于生命性创造这一主客圆融的文化立场。而当一个作家可以将多样风格统于一身之际,也就意味着“风格”概念的失效。刘勰以《体性》《风骨》(甚至可以延伸至《定势》)考察文体的建构,不仅创立了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才性、风体关系理论,而且也提示我们:对于古代文艺理论思想的阐释应该尽量采取文化还原的态度与方法,最大限度减少中西概念格义产生的内涵错位与误读。
①⑩⑯⑱⑳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6页,第1043页,第1045页,第1022页,第1035页。
② 张海明:《文心雕龙〈风骨〉篇释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海明也认为《风骨》所言偏于“才气”,但同时又以为《体性》篇侧重于“气质”,如此区划有将性、能一体的才性分解的嫌疑。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原文皆据此本,文中仅随文标注篇名。
④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⑤ 黄汝亨:《南太史饮酒集杜小序》,陆云龙辑《翠娱阁评选皇明小品十六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⑥ 罗宗强:《读文心雕龙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0页。
⑦ 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306页。
⑧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⑨ 戚良德辑校《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
⑮ 张海明:《文心雕龙〈风骨〉篇释疑》。
⑫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7页。
⑬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1页。
⑭ 参见赵树功《道贯“三才”与骋才创体——论以“才”为核心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载《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
⑰ 詹锳较早通过对《文心雕龙》的《体性》《风骨》《定势》诸篇的分析,系统论及中国传统的文体具有“风格多样性统一”的特征(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詹福瑞、任文京主编《詹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8、70—72页;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1021—1022、1035—1036页)。曹顺庆又在中西比较视域下考察了“体”与“风格”的关系,更为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结论(曹顺庆:《风格与“体”——中西文论比较研究》,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
⑲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㉑ 曹顺庆:《风格与“体”》。
㉒ 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詹锳全集》第4卷,第70—72页。
㉓ 屠隆:《鸿苞节录》卷六,清咸丰七年(1858)屠继烈刊本。
㉔ 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㉕ 陈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可能萌蘖——梁昆〈宋诗派别论〉的学术史意义》(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指出,在西方现代文论“流派”观念的影响下,现代学者往往用“风格”诠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其实后者“统摄性极强,可能指涉体用、体貌、体式、体势、体裁、体类、体制、体法、体性、体律、体度、体要、体格、体气、体致、体理、体统、体韵、体意、体样等等,其内涵远非风格所能囊括”。
㉖ 参见詹福瑞、赵树功《体与文体(Style)》,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㉗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