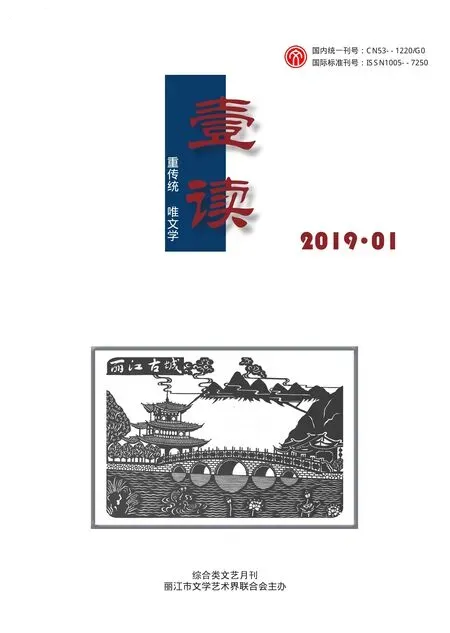往昔少女
◆徐兴正
现在,你开始进入梦境。
一段时间以后,小鲁离开了他原来住过的房子。那房子深陷在小县城乱七八糟的建筑之中。房子是朋友借给他的。房子背后挤满了一大片歪歪斜斜的民房,那些瓦片似乎随时都会滑落下来,——事实上正是如此。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鲁经常听到瓦片下落。那些不计其数(怎么可能)的瓦片,有的像轻飘的树叶或飞鸟的羽毛一样飞舞起来,不管过了多少时光,它们都不会再落到地面;有的落到坚硬而混乱的石头上,摔得粉碎;有的直接掉进井水里,溅起来的水花打湿了断砖头砌成的井壁(这使小鲁激动起来);有的掉在晾衣绳上,晾着的衣物趁机不翼而飞,再也寻找不到,而这类瓦片也偶尔被弹到天空中去,过了多少日子,才在乌云密布中包裹在冰雹里从天而降,说不定就砸在了谁的头上。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男人们弯着腰在房子上拣瓦。妇女和儿童通过搭在屋檐上的木梯子往房顶上搬运瓦片。他们的影子看起来十分哀怨、悲苦。但谁也没有办法。你能阻止瓦片掉下来吗?房子的前面矗立着相对规整的楼房,里面住着许多人,包括借房子给小鲁的那位朋友。房子附近有一个垃圾场,常年累积的垃圾上甚至生长着许多肥嘟嘟、臭气熏天的刺菠萝和蓬草。房子其实是煤屋。云南东北部的冬天并不温暖,不仅冬天,即使在春天和秋天,不少日子都需要生炉火取暖,大多数有条件的市民,都备有专门的煤屋。朋友为了帮助小鲁,把煤屋借给他,蜂窝煤就堆放在住房楼梯口。小鲁好像是结了婚的人,并且有了孩子,两三岁了吧;他妻子好像是乡村教师,他们一家好像长期分居。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房子里塞满了一个家庭必需的那些东西,诸如床、桌子、炊具、沙发、水桶、火炉、纸箱,等等。房子差不多有十个平方吧,它就像一只胀鼓囊囊的旅行袋。
小鲁好像在小县城一个机关工作,他的具体事务好像是草拟文件。小鲁时常抱怨他的工作,他的抱怨不切实际,比如说,他甚至认为,机关依靠文件运转,他还进一步认为文件就像他的房子背后民房上的瓦片,简直着了魔,变着戏法折磨人,即使在梦中也逃不脱。但小鲁并不感到怎么哀怨和悲苦,他的生活与那些在民房上拣瓦的男人不同。
小鲁妻子好像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她有一辆银灰色的单车,一双红雨鞋。她娘家离乡村中学三公里,一条泥巴路,雨水一多就骑不成单车了,穿上红雨鞋,走完那段路程,要花四十分钟。泥巴路边的居民和乡村中学的同事,时不时会观看或议论小鲁的妻子。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过去还追求过她。
好几年前的一个黄昏,校园里的树叶正在秋风和灯光中飘落,一个身穿米黄色长裙的少女出现了。这是小鲁与他后来的妻子第一次见面。米黄色长裙一直在小鲁的睡梦中飘飞,和那些魔法无边的瓦片不同,米黄色长裙轻逸、柔软,伴随着少女的身姿。当时,少女还涂过银灰色唇膏。
小鲁读到了女作家某某的一本叫作《乡村札记》的书,某某拍摄于云南某些村庄的照片精美地编排在整本书里,这本书看起来更像一卷特殊的相册,某某不下四十岁了吧,但她居然穿着米黄色长裙,并且也涂过银灰色唇膏,与当年的少女毫无二致。就像著名的玛丽莲·梦露一样,某某成了小鲁一段时期向往的女性身体符号。
在昭通火车站,小鲁懒散地躺在一张长木椅上,女作家某某的照片在那本此时并不存在的《乡村札记》里,从他眼前一页一页地翻过,他的血液暗流奔腾起来。这情景,就像少女当初从背后突然抱住了他,长时间不放开。当时是19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少女穿着一件紧身衬衣,而他那件陈旧的T恤却宽松得像一条麻袋。少女把两只手臂伸进他的T恤,直接缠住他赤裸的胸膛。小鲁明朗地感受到少女乳房的坚挺与温热。他们站在学校花园里的一个亭子下,亭子用粗糙的水泥支架建造而成,支架上面爬满了长势旺盛的藤蔓,藤蔓尖端的嫩绿叶片散发出一阵模糊、微弱的气息。夜间11:00宿舍熄灯的铃声响过了,11:30关闭宿舍大门的铃声也响起来了。少女松开手,一蹦一跳地站到了小鲁面前,她扬起眉毛、抬起下巴,用一种刚刚才从梦中醒来或者正要进入梦乡的眼神打量着小鲁。到了2003年,小鲁和妻子坐在家里(他们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沙发上,看孙周导演的《周渔的火车》,当演员巩俐所饰的周渔,用与少女如出一辙的姿势和目光,如梦如痴地在铁轨上盯着演员梁家辉所饰的陈青,陈青慌乱地往后退了又退,周渔嘻嘻而笑转身跑开时,小鲁问妻子:
“你知道周渔她这时想干什么吗?”
妻子回答说:“她想让陈青吻她!”
小鲁说:“当时,我也许是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了但又不敢。”
可是妻子她已经记不得少女的那个夏天的晚上了,她说:“你说什么呀?”
周渔那时候还是不是一个少女?
小鲁十分沮丧。
这时,有人在小鲁那张长木椅上坐了下来。因为他是仰躺着的,那个人坐的地方就非常靠近他的头部。小鲁仍然闭着眼睛,他闻到了少女的气息。
少女的气息非常饱满,如同河流涨满河床,犹如阳光普照大地,仿佛山坡开满花朵。少女的气息经常在梦中弥漫、浸润,睡醒的时候,口里还残留着甘甜、芳香,身心感到舒畅和宁静。在夏天,小鲁那房子活像一只大烤箱。实际上,不知始于何时,小鲁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睡眠。在他那房子里的夜晚,梦中从始至终都是瓦片在下落,或者说,瓦片无休无止的下落已经使他不可能以一种正当的方式睡觉。如果在别处,梦中则是米黄色长裙漫无边际地飘飞,就像古代的战旗,漫山遍野,遮天蔽日。因而,小鲁的睡眠显得十分诡怪。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完全、安然入睡,但又都可以睡上一会儿。比如在办公室里,在会场上。别人看完一张报纸的时间,他能断断续续地睡上几觉。况且,他也和别人一样,根据“浏览”的需要,先后多次翻动报纸。开会的时候,小鲁即时性、瞬间式的睡眠,并不妨碍他作记录,他的记录从来没有漏掉过要点。即使是与人交谈,甚至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小鲁也能以别人乃至他自己察觉不到的方式打打盹。你看,小鲁既是一个基本上失去睡眠的人,又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都在)睡眠的人。小鲁为此去过医院,医生给他开过一种白色药片,好像叫疏利通什么的,日用量从2片增至8片时,他就可以一次性睡到3至5小时了。但在睡着的时候会出现幻听,小鲁好像听到:
“跑吧,少女。”
“你把自己丢了,少女!”
“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了使你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她。”
“少女。少女。少女。……”
于是,小鲁中止了用药,不久就恢复了他个人的常态。从某方面讲,小鲁处于一种飘逸状态,就像蝴蝶。少女的气息萦绕着小鲁的生活。蝴蝶与蜜蜂不同,蜜蜂收集花粉,虽说主要是酿蜜,但也靠它维持生命,而据说蝴蝶只要被花朵的气息萦绕着,它们就能活下去。
小鲁睁开眼睛,他吃惊地发现少女正在注视着他,那种神态就像妻子在他无法入睡的时候安慰他。少女同样穿着米黄色长裙,但她涂的唇膏不是银灰色,而是红色。口红让人感到热烈、悲伤。少女的发型是那个时期比较泛滥的碎发,并且染成了浅黄色,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做出一副一见如故的样子。起初,谁也没有说话。小鲁长时间地观察少女,就像电影上那些常见的镜头。小鲁的目光主要停留在少女的脸上。他看到少女脸色苍白,并且有些浮肿,眼角留有泪痕,神情之中,有一种刻意做出的冰冷和自然流露的疲惫。小鲁不着边际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莫非一场初恋结束了?紧接着,一个少女消失了吗?
小鲁抽出已经发麻的手掌,仍然让它们交叉在一起,罩在眼睛上。……小鲁终于吻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姑娘,姑娘十分镇定,而小鲁却害怕(也许是激动吧)得发抖。姑娘把小鲁的头埋在她的乳房之间。少女的气息就像梦境。——花朵在幽深的峡谷里绽放,蝴蝶在花丛中飞舞。闭上眼睛,你能呼吸到世界上最幸福的空气。“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姐姐穿过峡谷和梦境,自由自在地奔跑,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姐姐忘了抓住我的手,她在无拘无束地飞翔,就像一场白日梦。我的身体那时不是由血液、肌肉和骨骼构成的,它好像一大块废铁,是那么沉重,那么没用,不能奔跑,更不可能飞翔。我的身体好像一团可疑的气体,消散在花朵的芬芳和蝴蝶的舞姿之中。姐姐丢下了我。我已不复存在。……姑娘失声痛哭,她的哭声化为有形,比如马匹、羔羊或者蚂蚁、虫子,在幽深的峡谷中徜徉、爬行。姑娘在为少女痛哭。小鲁仰起头来,看着姑娘,他不知所措。姑娘说:“不是你,不是你让我哭泣!”小鲁说:“……是谁?”姑娘说:“是一场恶梦。”小鲁不懂得安慰姑娘。“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小鲁把罩在眼睛上的手掌移开时,少女故作无所谓地对他说:“你能为我买一张火车票吗?”
小鲁伸出右手扶住长木椅坐了起来,并穿上鞋,不怀好意地看了少女一眼。他还把食指伸进嘴巴涮了一下,这是一个挑逗和侮辱女性的动作。小鲁听说过,有一段时间,成都到昆明的卧铺班车,有暗娼陪卧。小鲁问:“你想去哪里?”
也许少女把小鲁的这个动作看成一种孩子气,她爽朗地笑了,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少女的一颗门牙十分碎小,仿佛是从两颗牙齿中间挤进去的,显得淘气和调皮。她的脸上滚下几颗泪珠来,好像是破涕为笑。她回答说:“任何地方。”
小鲁认识过一个少女。离现在还不到一年吧,那之前的一段时间,小鲁差不多完全丧失了睡眠。认识少女期间,他正在服用疏利通这种白色药片,幻听十分厉害。“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了使你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少女几乎每天都给小鲁打来电话:
“昨天晚上什么时候才睡?不该又是一个通夜吧。今晚能早点休息吗?”
“都中午一点过了,你还没有吃早饭。早点也没吃过?”
“你要想办法给你妻子调动工作啊,这样你们才能互相照顾。”
“我想去遛冰,你说可以吗?”
“宿舍里(什么地方的?)很多人,故意在我身边议论我老是给你打电话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前次我受了委屈,对着电话向你大哭一场,你介意了吧。”
“我父亲他老是喝酒。一喝酒就骂人,发脾气。”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伤心不会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这一切也是幻听吗?
小鲁一次接过电话后,对着墙上平时只有妻子才用的那面大镜子,长时间地端详自己。妻子有了警觉,她问小鲁:“你怎么啦?”
妻子带上小鲁的身份证,在电信局打出一张电话清单。同一个号码通话次数超过一半,其中一次通话时间长达3小时。妻子对小鲁说:“我都不用再问你了。”
在火车站,小鲁又出现了幻听,那声音极其遥远,仿佛来自云端,来自天外,那声音不明不白,辨别不清,就像一场梦呓。
小鲁和少女在火车上的座位连在一起。火车开往昆明,大约五小时就能到达。少女带着一只安装着拉杆和轮子的箱子。箱子通过了安检,少女声称“这是一只重要的箱子”,本人不愿意托运,小鲁费尽力气才将它弄进车厢。箱子过大,塞不上行李架上去,只得摆放在座位前边;那里安置着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大概是提供给乘客玩扑克牌的吧,所以倒并不感到有多拥挤,有多不方便。小鲁对箱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箱子用牛皮、铝合金、钢材、橡胶和铜等材料制成,产地好像是上海。这是一只十分普通的箱子,材质和做工倒还不错,估计值几百块至一千块钱吧。
少女始终把一只手搭在箱子拉杆上。小鲁希望她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本川端康成的《雪国》,或者干脆就是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来读。小鲁对少女并不了解,但他却有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愿望。小鲁问:“你早有准备?”
少女说:“你感觉到我是在旅行吗?”
“对,我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为什么呢?”
“你明明带着一只箱子嘛。”
少女开怀一笑,像个男孩似的,她还伸手拍了一下小鲁的肩膀。在其他乘客看来,他们倒像一对恋人。
小鲁问:“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
少女反问道:“你这样问不觉得冒昧吗?”
“我忍不住要问。”
“我不告诉你。你猜猜看吧?”
“怎么猜得着呢?”
“不打算试一下吗?”
“好吧,我试试看。依我看——”小鲁沉思了片刻说,“里面空无一物。或者这样——”他张开十个手指,环绕成球体状,也许是要表示出一个“空”来,接着说,“本来倒装着某种东西,但也无异于一无所有。”
少女佯装不高兴,嘟着嘴巴说:“你这人太自以为是啦。”
小鲁突然觉得没意思,扭头去看窗外。火车发出尖叫,在幽深的峡谷中穿行。那些转瞬即逝的悬崖,就像被晃荡的铁轨弹飞的巨大石头。
三个男人在小鲁和少女前面的桌子旁坐下来,喝着随身携带的啤酒,凶猛地抽烟。啤酒已经剩得不多了,香烟却一只紧接着一只地抽。烟雾一阵一阵地飘过来,把少女和小鲁笼罩起来。
列车员也不在这截车厢,没人管。少女本来想请求他们去厕所里抽烟,别在这里让人受不了,但又害怕他们寻衅滋事,不敢开口。万一真发生了什么事情,小鲁会保护她吗?
小鲁看着窗外,想着《周渔的火车》这部片子。一直困扰着小鲁的问题是:究竟什么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那三个男人总算走开了,其中一个还故意踢了箱子一下。
少女对刚刚回过神来的小鲁说:“我其实可以告诉你,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
小鲁对困扰他的那个问题理出一点点头绪来了,他认为,“背叛”——倒不如说,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活,有了秘密。
少女接着说:“你想不想听?”
小鲁点点头。
少女狡黠地说:“那我告诉你吧。箱子里装着一个——一个——一个秘密。”
小鲁也笑了,他说:“你真是太狡猾了。为什么不说箱子里装着,装着一场空,装着一个人的命运?”
“我不喜欢什么空不空、命运不命运的。开口闭口就是命运,谁懂得一点点呢?”
“是啊,这话倒说得不错。”
说到这里,双方都想不出还有什么话要说,就沉默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毫无疑问,小鲁入睡过若干次,他既不觉得头脑有多清醒,也不感到思绪有多混乱。
少女打了一个哈欠说:“我想对你讲点什么,你有兴趣吗?”
傍晚已经来临,在夜幕下往后奔跑的山岗,犹如火车拖着的阴影。
小鲁说:“你说吧。”夜色显得温柔,稠密,像水在流淌,并且还有一层、两层、无数层涟漪。
少女说:
“我在几个月前认识了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已婚男人。”
小鲁在朦胧的灯光下,看到少女那张普通、明净、年轻的面孔,蒙上了一层梦幻色彩。她的双手收回到胸前,一字一顿地划动着。小鲁问:
“你现在多大了?”
少女显然不喜欢这种审讯的口吻,但在一种倾诉的欲望支配下,她忍不住回答说:
“二十岁,离生日还差十多天呢。”
“你什么身份?”(又是审讯的口吻)小鲁闭上了眼睛。
少女说:“在校大学生。”她把两只手臂缠起来,抱在胸前。
小鲁心头一惊,眼前的少女与他认识的姑娘情况差不多,不,不是差不多,简直——一模一样。他睁开眼睛,不由自主地伸了一个懒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少女的米黄色长裙让小鲁凭空产生一种想拥抱她的强烈愿望。
少女似梦非梦地说:
“然后,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当然你也不会相信,我们的交往主要是说话。说话,如果有机会,我们就找个地方,比如校园,去火车站的路上,他的房子,大街上,小饭馆,冷饮店,无休无止地说,漫无边际地说;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们经常是通电话。我一进IP电话超市就是一两个小时,最长一次达到3小时,那是一段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兴奋、快乐的时光。你根本不明白,我们会有那么多话要说。如果不是生活改变了我们,中断了我们的联系,那么,我们还将继续说下去。我们相识之前的那些年,似乎积存了不计其数的话,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把它们全部说光。我们甚至还准备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光。也就是把双方都全部掏空,这样,我们会感到轻松和快活。除了对方,我们和其他所有人都不想来往,甚至一句话也不想说。我们都把那些话留着。我们既被对方囊括,又被对方充满。少数时候,我们也会一声不响。呆在一起,我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来写;而他呢,随时都带着一本什么书,打开就看。不在一起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汹涌,但我们的生活看得见的部分,却平静得像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我们到底怎么啦?谁也说不清楚。”
小鲁说:“你好像告诉过我,你还在上学。我没有记错吧?“
少女说:“十多天以前,我就打算逃课来坐火车了。“
是啊,小鲁想,就连我也是第一次坐火车。火车跑起来就像在穿越梦境。少女认为第一次坐火车的感觉终生难忘。
小鲁说:
“在火车上,这是你和我——唯一的一次旅行。”
少女没接上小鲁的话茬,自言自语:
“它发生了,我把它讲出来。”
小鲁说:
“那我也给你说点什么吧。”
少女说:
“你说吧。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找一个人说一说。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要说。”
但小鲁这时觉得他们都太饶舌了,不想马上就说。小鲁示意少女一起坐到桌前。少女挪了挪那只箱子,让它斜靠在她的腿上。他们不约而同地托起下巴,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窗外一片漆黑,只听见风在火车上往后刮过去,响声很大。少女不自然地靠近了小鲁。
至少过去了半小时。小鲁说:“喝点什么吧。”他向列车服务员要了饮料。在向饮料罐插吸管时,少女突然问小鲁为什么不要啤酒和香烟。小鲁就要了啤酒。因为火车上不准卖烈性酒,啤酒不够味也只得迁就了。少女又要了香烟,随便什么牌子都行,两包。……少女用一种仪式化的姿势撕开香烟,只抽出一支,点燃,缓慢地吸,一丝一丝地把烟雾吐出来。在朝窗外弹烟灰时,少女发现白色过滤嘴上粘附着鲜艳的口红。它像什么?少女忧伤地想,像月经。她做出一种使坏的表情,用嘴巴直接把香烟嘟出窗外。
打开的啤酒不断冒出气泡,一股马尿和青草的气味逐渐散开。少女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坏?”
小鲁没有回答少女,对着瓶口一口气喝了半瓶啤酒。少女一扬头,也把剩下的啤酒喝了。两个人都趴在桌子上喘粗气,眼睛都开始泛红,也许是被啤酒冲的吧。
少女说:
“在今天以前,其实我也只喝过一次啤酒,抽过一回香烟。啤酒喝了三瓶,香烟抽了两包。就一次。我一直在对你说的那个人,有一天突然来找我,我们见了最后一面。这次见面,我们说话不多。他告诉我,从今以后,我们不能在一起,不能互相问候、通话,不能什么都不能了。因为谁也不会相信,我们是像兄妹一样相处的。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信。他来向我告别。我当然只得接受。我们的相识和交往本来就违背了常理。……我以前到过他那里,我们安静地呆了两天时光。那些时光简直就是童话和梦境。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过了两天。我离开时,由于天气突然变冷,他让我换上他妻子的衣服。可我们一出门就碰上了他妻子——直觉告诉我,她就是他妻子。或许她已经在门外等我们很久了。我知道她在别处工作,一时弄不清楚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她涂着银灰色唇膏,用一种爆发出愤怒和诅咒的目光瞅着我,一脸通红,牙齿咬紧嘴唇,银灰色的唇膏逐渐变乌,十分怕人,她张了张口,一句话也没说,扭头冲进屋去,用整个身体把门撞了过来。我听到一阵呜咽,我猜,她肯定顺着门页滑到墙角里去了。我羞得无地自容,天知道她在怎么想。他也失了神,蹲在门外一动不动。我站了片刻,撒腿跑了,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他妻子的衣服里空无一物,忐忑不安,已经消失。
“我们见最后一面那天晚上,我很难过。分手后,我一个人独自在外边喝酒,醉得不成样子,披头散发回到宿舍,同学们也不想照管我,我总算自己爬到了床上。我的事情她们都知道。她们还加进去了不少想象和推断,认为我道德败坏,丧失理智。她们对我议论纷纷。其中一个平时与我还算要好的同学说:‘她已经不是少女了,一看她走进来的样子我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了。’其他人随着笑了起来。另一个和我经常在一起的同学接着大声地说:‘对呀,我在纸篓里看到,她的月经也没有过去红了!’我躺在床上,摸出剩下的香烟,找出火柴,点燃,抽,我一声不响,一直抽。宿舍熄灯以后,借助烟头的光亮,就能看到几个同学还在盯着我。我有一种无耻的快感。
“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痛,全都是痛。我这个人,我的身体、思想、意识、知觉,一切都不存在,剩下的全都是痛。痛得空无一物、一无是处。”
小鲁抓住一包香烟拍了几下,从烟盒里弹出一支,递给少女,自己也抽了一支。他回想起第一次吻姑娘时的情景。姑娘失声痛哭。(“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说这很美。”)姑娘当时也在痛,从毛发、皮肤一直痛到血液和骨髓。
打开第二瓶啤酒,小鲁把另外三瓶搬到自己面前说:“这些都是我的啦,不准你再喝了。”
“可以,由你安排。”少女摆出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她接着说:“喝啤酒——或是其他任何一种什么酒——都没有用,抽烟也没有用。我们为什么要喝酒、要抽烟呢?它们是生活的背景,舞台的道具,离开它们,我们就会觉得空荡荡的,就会感到表演与游戏的困难,就会无抓无拿,难为情。”
这话对小鲁来说很投机,他感叹道:“是啊,这说明我们不堪一击,假模假样。哎,我问你呀,你什么专业?中文,外语,戏剧,绘画,音乐?”
少女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夹住香烟,在桌面上抖了抖烟灰,这个姿势显得生疏和做作。小鲁这时才注意到她的手指瘦削、苍白。她说:“我们还是不谈这个了——没有必要。”
“好吧,那就谈点别的什么吧。”小鲁说,“你可以谈一谈你们在一起的情景嘛。”
少女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即使我们要坐好几天火车,也不至于找不到什么话说。这次旅途剩下的路程已经不多,我们就随便说点吧。”
小鲁说:“对,我们就挑当时很让自己感动的说。我先说一段。”
少女调皮地把香烟凑过去,让小鲁看抹在白色过滤嘴上的口红。小鲁摆摆手,笑了笑说:“你这样不会让我感动。就说我认识的姑娘吧。姑娘来到我住处的那一天,天气有点冷。大概是秋末冬初吧。云南的东北部不像人们所说的‘南方’那样温暖。姑娘穿着一条牛仔短裙、一件格子衬衣和一双平底皮鞋。即使在我那只有一只旅行袋那样大的房子里,也很难抵御寒冷。她的小腿被冻得泛红,她不停地把本来就不太长的白袜子往上拉,她甚至开始流鼻涕,真是一个小姑娘啊。我当初确实想把她拥入怀抱,不过你知道,我并没有那样做。我犹豫了一下,找来妻子的冬裙和风衣,让她换上。她十分勉强,换好衣服后,她来到我身边,就像在梦中那样转动身体,我差一点就伸过两臂去把她抱住了。她在妻子宽松的冬裙和风衣里,像个稻草人。我是怎样和她认识并来往起来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罪恶感。我知道她为什么会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穿那么一条短裙和一件衬衣到我这儿来。她说过,她特别喜欢‘五·四’时期女学生的打扮,她在让我分享她的美丽,这样能让她感到幸福。”
少女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小鲁问她是不是又难过了,她说不是难过,是伤感。她还说:“这故事发生在我身上,你却把它偷来讲给我听。”
后来,小鲁和少女回到了座位上,那只箱子就放在他们面前。少女把头靠在小鲁的肩上。小鲁抚摸了一下少女的头发,他忧伤地说,不该把头发染成浅黄色——染成任何一种颜色。
少女说:“你应该还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你我痛经,正在痛。你让我立即去医务室开元胡止痛片,吃下去,等着你。不到一个小时,你就赶到了。你带我上医院。”
小鲁说:“你还是再给我讲讲你酗酒的父亲,讲讲你们一家的日子,讲讲你们坐落在一条沟里的村庄吧。如果可能,再讲讲你呆过和将要去的任何地方。说不定我哪一天就去找你了。”
少女不再说话。小鲁的大脑里还是浮现出了一些场景:
——铁路还未铺通,火车站就提前建成了。火车站离昭通也就几公里吧。小鲁和少女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走过多少回了?他们逮住一个话题就无休无止地说下去。公路两侧的土地上,一些民房陷落在玉米地深处。在少女一条沟的村庄,玉米也在生长吧。她的母亲,在村庄的炊烟下,在某间民房的角落里,模糊不清,苍老不堪。一切都是那么悲伤。而小鲁,他却说起他们村庄的一条狗。这条狗是王三家养的。王三在鲁姓村庄独门独姓,势单力薄,为人显得谦和、软弱。他家养的狗也软稀巴拉的,陌生人来到家门口也不敢叫几声。村庄里羞辱人,先是大家都说:“你看你这王三样!”自从王三家养了那条狗,所有人都改口说:“你看你这王三家的狗样!”小鲁还自我作贱地对少女说:“你其实不完全了解我,我也是王三家的那条狗。”王三准备杀狗雪耻,但他恶念过重,没杀,摧残,剁了狗的尾巴和一截腿,狗逃掉了,不敢再回来。一条丧家之犬啊,在村庄里游荡,一见人就跑,但跑不快,一边跑一边呜咽,最后不知死在什么地方了,反正谁也没见着尸体。小鲁怎么会那么说自己呢?
小鲁坐火车去昆明参加笔会。他本来就是冲着女作家某某,那个《乡村札记》的作者去的,渴望在笔会上能一睹她的芳容。笔会一开始就介绍了到场的作家和其他一些人,但当中并没有女作家某某。不过,笔会的议程之一却是研讨《乡村札记》这部书。小鲁可以断言,在场的人,惟独自己认真读过此书,可是作为一个无名小卒,会议不可能安排他发言。笔会期间,他在昆明花了一两天时间到处打听某某。事情渐渐有了眉目,都快要弄清楚女作家在哪里上班、住什么地方了,但这时候,他放弃了。
相比之下,回程火车就太漫长了。和小鲁坐在一起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带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孩子一直在哭。而去的时候呢,小鲁旁边好像坐着一个少女,她好像带着一只箱子;他一路上迷迷糊糊的,待到汽笛声将他从似梦非梦中闹醒,火车已经驶进昆明站,少女不见了,永远消失了。
小鲁在昆明逛了很多地方,准备给妻子买些东西。最后,他好像在一家商场买了一只箱子。这只箱子用牛皮、铝合金、钢材、橡胶和铜等材料制成,安装着拉杆和轮子,产地上海,标价一千块,打八折。对于他们这种收入的人来说,这箱子太贵了,但小鲁还是果断地买下了它,为此,他不得不给一个在昆明的朋友借了点钱。他想,这么好的一只箱子,一定能让妻子喜出望外。和小鲁一起带着一只箱子去旅行,一直是妻子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箱子的锁要使用密码,密码印在精美的用户手册上,好像是6个数字,或者9个,虽然小鲁好像试过,但拿不准。小鲁记得很清楚,用户手册他在火车上反复翻过;翻看用户手册的时候,那只空箱子就放在他的座位旁边,拉杆还靠在他的腿上,他不时扳一下锁扣,并张开手指抚摸箱子的皮革,手感既晦涩又舒畅。可是,现在,用户手册丢了,箱子打不开。小鲁给在昆明的那个朋友打电话,托付他到那家商场去咨询,箱子的密码丢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朋友在电话里好大一会儿都不吱声,小鲁以为线路出了故障,小鲁说:“喂,听到了吗?”
朋友说:“你真在昆明买过一只箱子?”
小鲁一惊:“这还有假!箱子已经带回来了,我妻子还挺喜欢的,但就是密码丢了,打不开了,现在。”
朋友说:“你知道自己在玩一场什么游戏?”
小鲁停了停,开始喘息,然后问:“都这么多年的朋友啦,你什么意思?”小鲁过去就心生疑惑,此人和妻子早年有过某些关系,比如说,前者是后者的初恋情人,或者反过来。小鲁记得明明白白,他向妻子提到这个朋友时,他们刚刚结婚,妻子当时的眼神暴露了一点什么,但隐藏了更多的什么。他问:“你早就认识他?”妻子说:“啊啊,哦哦。”妻子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这个姿势如在梦中。在那个初次见面的黄昏,她转身离去的时候,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他终于吻了她那一回,过了一会儿,她推开他,接着伸出两只手臂扳住他的肩膀,用那种暴露了一点什么,但隐藏了更多的什么的眼神,若有若无、如梦如痴地看着他,然后——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垂下两臂,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她突然之间崩溃了,先是哗啦一下泪流满面,再是失声痛哭,最后,她把他的头埋进自己的胸脯。新婚之夜,在昭通的一个小旅馆,她拉下窗帘,用一种宁静但甚至也是心灰意冷、转眼成空的目光看着他,那一次,她也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前面三次,连起来,一共四次。
朋友说:“告诉你吧,你妻子给我打过电话。不是早就出现了一个女学生了吗?她——我怀疑你的这次昆明之行。”
一回到家,妻子就看到了小鲁手里拖着的箱子。小鲁说:“说过多少次了,这一回就买回来了。”
妻子垂着两只手静静地站在小鲁对面。她的身旁还站着他们的孩子。孩子两三岁了吧。小家伙长期不在父亲身边,对父亲有些陌生、隔离,歪着个小脑袋,无声无息地盯着对面站着的这个人,他的目光很快被那只箱子吸引。小鲁这才想起去了一趟昆明,居然没给儿子买个玩具,比如电动小火车什么的。哎,在昆明,在火车上,连“儿子”这个念头都没有。妻子碰巧穿着米黄色长裙,还涂过银灰色唇膏。她忽然抬起右手,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这是第五次吧。对,五次了。以后还会这样吗?她的眼神依然是那种暴露了一点什么,但隐藏了更多的什么的眼神。
小鲁问朋友:“你们经常打电话吗?”
朋友说:“怎么,你在怀疑我?”
小鲁突然说:“你见过她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吗?”
朋友说:“谁?”
小鲁感到口干舌燥,他咽了咽唾沫,觉得身体的某个地方发出“咔嚓——”一声响,他说:“少女,某个,对,某个少女,比如说,……”
朋友已经把电话挂了。
小鲁到了小县城机关领导办公室,他说:“局长,我准备到昆明看病,来请你给批个假条。”他把假条递上去。
局长说:“小鲁,我看你好不好的,你这把身体,有什么病?”
小鲁有些慌张:“局长,你知道——全机关都知道,我无眠,幻听,服用抗精神分裂的药物都好几年了。”
局长批了假条,吩咐小鲁自己送交办公室,末了,局长说:“那就找个好一点的医院——适合你这种病的医院吧,比如——你去吧。”小鲁猜得到,局长想说的是精神病院。
小鲁一家终于有了他们自己的一套房子。房子很大,由于他们东西不多,也就显得空。小鲁在这套房子里安排出一间书房来。书架还留下几处空格,其中一处放着一个木制相框,里面装着小鲁和妻子刚认识不久的一张简单的黑白合影。这张合影经过了扩冲,做了他们的结婚纪念照。那时候,妻子还是一个少女啊。她穿着米黄色长裙,也许还涂过银灰色唇膏,但黑白照片上看不清楚。样子有些模糊,不过记忆犹新。她的眼神依然是那种暴露了一点什么,但隐藏了更多的什么的眼神。另一处呢,放着一些信件和记事本。全是小鲁妻子和少女的消息。
小鲁给还在乡下的妻子打电话,他们的孩子对着话筒吼道:“爸爸,你在哪里?”小鲁想象得到他的小脸蛋一定绷得通红,他还在小口小口地喘气呢。小鲁感觉到自己快要流泪了,他说:“爸爸在家呀。”孩子说:“家在哪里?”
妻子接过电话:“有事?说吧。”
有一两滴眼泪顺着小鲁的脸颊滑下来。小鲁说:“我想告诉你,我慌称去昆明看病,局长给我批了一周的假。我呆在家里好好整理一下小说,——我给你说过,要参加昆明笔会。”
妻子说:“写小说?对啊,也许,也许能改变你的——我们的生活。”
小鲁说:“生活,改变它?写小说,……”
妻子说:“我也请假过来吧。我们——在一起,多呆几天。”
妻子给小鲁冲了速溶咖啡,盛在一只红色的杯子里,端到书房。据小鲁说,咖啡,可以缓解他的失眠。妻子说:“你的小说写作计划被长期搁置下来了,先写哪一篇?”小鲁说:“我也拿不准啊,试着先写《往昔少女》这一篇吧。”
妻子喃喃地说:“往昔,少女,往昔少女,……”
有一天,在昆明的那个朋友忽然打电话来了,他说:“箱子这问题不好解决,是很麻烦。”
小鲁说:“你就说说看嘛。”
朋友说:“我去过那家商场了。有很多麻烦。一呢,你不一定记得买箱子的具体时间。要记得具体时间,才能在销售档案里查找你这只箱子的货号。但据商场介绍,这种箱子正在热销,情况好的时候每天卖过几百只,很难确定你的是哪一只。二呢,即使确定了货号,还要联系厂家。一般情况下,厂家是不会主动、积极配合的,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不在售后服务的约定范围。在提供客户详细资料和有关证明的前提下,厂家确实有可能会告知你这只箱子的密码,但真正办起来实在不容易呀。所以,依我看就算了吧,不就是一只带密码锁的箱子吗?”
小鲁说:“这只箱子的事情,我自己都已经搞不清楚了。”
朋友说:“真是的!你倒是说说,确实在昆明买过一只箱子吗?”
小鲁说:“前次就问过你了,那件事情——你看见过一个女人,或者少女,对,一个少女,比如我妻子——你与她认识比我还早,在她的少女时代,你看见过她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这个动作、这个姿势、这个梦境、这个管它是什么吗?”
朋友说:“你坐火车来昆明到底干了些什么?还向我借钱,又不见面,让我把钱存在你的卡上,到底在哪个节骨眼上出了,出了,出了什么问题?”
小鲁说:“都说过多少遍了,一只箱子,很值钱,八百块的,是密码锁,可是密码丢了。”
朋友说:“如果真有一只什么密码锁的箱子,还不简单?找个匠人,把锁卸了,重新装。找个手艺好一点的,能装好,就像原装的。”
小鲁说:“我知道简单,比如说,把它毁掉,扔了。但问题是,我,我妻子,我们,都不愿那样干,都想把它完好无损地打开。”
朋友说:“那你们就瞎碰吧,也许能走运。这机率呢,不比买彩票大,也不比买彩票小。再见啦。就这样bye-bye啦。”
小鲁在一天黄昏开始了小说《往昔少女》的写作。几年前的某一天黄昏,小鲁和少女初次见面,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们当时是在校园里,树叶正在秋风和灯光中飘落。少女穿着米黄色长裙,涂过银灰色唇膏。小鲁写道:
“现在,你开始进入梦境。”
写到半夜,小鲁想在妻子怀里躺着。他经受失眠的煎熬时,妻子只要在他身边,就会流着泪安慰他。但这种时候,她从不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暴露了一点什么,但隐藏了更多的什么的眼神。妻子还没睡,一直有意无意地翻着女作家某某的那部《乡村札记》,等着他。她对这部书上女作家仪态万千、风情万种的照片很有热情,她说过,“这人快四十岁了吧?还能给我们带来少女——永远的少女这种感觉。”小鲁的头埋在妻子的乳房中间,他睡着了。这些年来,小鲁一直是这么入睡的。经过哺乳期,妻子的乳房没有少女时代坚挺、圆润了,甚至都有些松弛和不对称了,但小鲁却感到它们无比温暖、体贴、抚慰。没多久,小鲁就醒了过来,他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咔嗒——咔嗒——”的轻微的响动,一辨认,知道是妻子在反复拨动那只箱子的密码锁。小鲁的大脑中一片茫然。天快亮的时候,小鲁再次醒过来,他发现妻子已经彻底睡着了,在朦胧的台灯光下,看到妻子的脸有些憔悴、苍老,但少女的单纯与惊艳还未消失殆尽,这使他一下子热泪盈眶;他也看到了妻子的左手用张开的手指穿过了自己的长发,右手却停留在那只就放在床边的箱子的密码锁上,似乎还在拨动,并且发出了一种“咔嗒——咔嗒——”的轻微的响动。
要是有朝一日,箱子真的好端端地被打开了,或者妻子终于失去了耐心,用锋利的刀刃剖开了它——小鲁的心里空荡荡的,到时候,谁知道里面会装着一些什么呢?
(注:本文反复部分和全部引用了张楚的《姐姐》、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