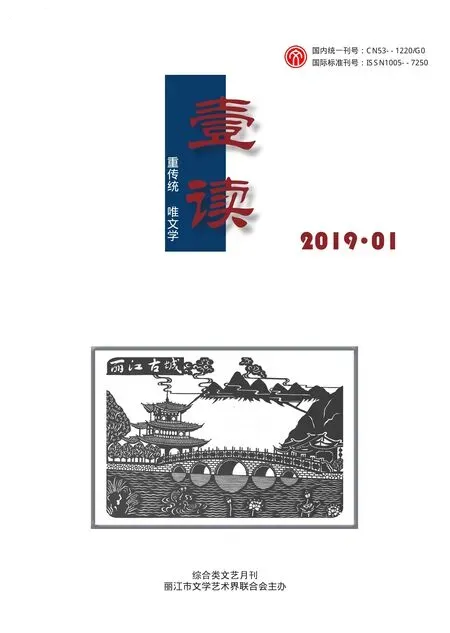王煊不宣
◆杨杰宏
初闻王煊
这是八年前的事了。2010年6月27日,在拉市海观察鹤山庄老板和丽刚先生的组织下,与丽江师专杨林军博士、古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杨金山老师一同考察拉市海到龙蟠乡阿喜的茶马古道,并对阿喜村内的龙潭、龙神祠、古渡口、铺子古村进行了调查。年届七十的严子藩是铺子村人,嗜好诗文,为丽江玉泉诗社成员,现为阿喜诗社顾问,对阿喜地方文化耳熟能详,他带着我们开始了这趟阿喜之行。
铺子村在阿喜龙潭西南边的国道之下,村落民居从公路边一直延伸到江边,层层而下,栉次鳞比,俨然一个小古镇。听村中老人说,阿喜渡口最早是在宏文村,清朝中后期才移至阿喜村,铺子村刚好位于两个新旧渡口的中间,又是七十二道弯铺石茶马古道伸入阿喜的第一村,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成就了铺子村,其名也是源于茶马古道兴盛时期村中广开店铺的历史。
村内至今仍遗留有一段宽约三米、长约两百米的铺石古道,古道两边的民居大多为传统古建筑,大多为传统纳西庭院建筑,有蛮楼、厦子、花厅、两面房等,其中有两栋三层土木结构瓦房是典型的马店,一楼为地楼,为关牲口用,二楼为赶马人休息睡觉用,三楼为贮藏货物。听村中老人讲述,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古道两边房屋都保留着铺店格局,后因铺子功能失去,大多都由墙基取代。现有些房屋仍可辨析出原有店铺格局。
铺子村开铺子历史已经成为陈年旧事,只能从老人口述史中依稀听到当年的一些盛况:一直到解放初期,村中家家开铺子,铺子都朝路边开设,铺子前有长条凳,供过路马帮休息。有些赶短途的人在此休息片刻,买碗酒喝,或买点路上的干粮。走长路的马帮一般在此休息两三天。如果是从藏区回来的,因为回到了丽江地盘,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了,在此休息放松几天,也是对经年累月所付出的风餐露宿、担惊受怕所作的一些心理补偿;如果是往藏区的,离开此地,意味着即将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险途,在此整顿休息,是作最后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铺子里的买卖都是围绕服务马帮而做的,大到货物的接洽、转让,现金大洋的借贷,小到马料、马鞍、货物包装袋等小商品的交易。也有一些来自丽江、石鼓、剑川的小商贩在此以低廉价格批发一些小商品。由此形成一个小型的商品集散地,晚清至民国时期是铺子村兴盛时期。马帮到村后,与店主交待后,马匹一进马圈,藏客们或在店内打酒吃饭,或与店家商谈货物接洽事宜;马帮来自藏区、丽江、鹤庆、剑川等地,其中少不了年青的小伙子,休息期间,有些年轻小伙与村中姑娘谈情说爱,就这样马帮离开时,把姑娘带走了,也有留在村中当了上门女婿。茶马古道深深地嵌入到铺子村的历史之中,可以说是茶马古道成就了铺子村的繁荣,铺子村为茶马古道的兴盛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村中有一口古井,古有围井而聚传统,从现在铺子村格局来看,基本上是以古井为中心的。水井直径约有两米,深四米多。一直到文革前还出水,1996年丽江“二•三地震”后水源枯竭而废。据村中严子藩老人介绍:古有围井而聚的传统,水井可能从村子形成时就有了,但以前没有现在这般大,是民国时期孙渡部队驻防于村中时扩建的。这与1936年红军长征过丽江的历史有关系,当时,孙渡作为龙云的参谋长,兼任蒋介石任命的剿匪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率部追剿红军至丽江。
当时阿喜作为渡口,也是重要防范之地,孙渡一个连队就驻扎于村中。张向斗是铺子村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官至中央陆军121师运输大队中校营长,为孙渡的爱将。孙渡率兵追赶红军时,他因负伤并未随行。孙渡率部抵达阿喜时,红军已经渡江北上,为了防止红军返回,在村中驻扎了近一年多。当时村中驻扎了一个连队,连长为李佐,是张向斗的好友。连队驻村期间做了一些好事,如修缮了村中公路、桥梁,对此古井也作了较大规模的扩建,部队在村中并没有发生鱼肉百姓的事件。
孙渡与丽江有一段情缘。孙渡是著名滇军将领,曾任云南省宪兵司令,龙云的参谋长。抗战时任五十八军军长,1945年初升任第一兵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60军、93军。1948年任热省主席。1949年12月随卢汉宣布起义。孙渡追剿红军到丽江时,与丽江张大老爷家曾孙女张灿琪相识,后送其到昆明读书,并与之缔结秦晋之好。
水井旁有两棵高大楸木,县志中记载已有270年的树龄。树上二米上方有一凹陷处,里有平板。严子藩老人说这原是块清朝时候就钉在树上的一块村规民约,后随着树木长高变粗,此木板也渐渐陷在里面了。
在石板路西侧座落看一个深宅大院,从外观上看,三个大院紧密相连,沿路一字排开,想必是一家大户人家。严子藩老人说这就是阿喜最大的地主王煊故居。王煊?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心里有些陌生。他是个地主老财?还是茶马古道上的巨贾?带着诸多疑惑走进这个深宅大院。
与和万华家院命运相同,解放后他家大院也作为“革命胜利果实”分给贫下中农居住,原来的三个大院分给五户人家,由此原来相互通连的大院分别隔成了三个院子。王煊故居曾占地10余亩,为一进三院,南北两院为三坊一照壁,中院为四合五天井,中院主楼曾为三层结构,被后面住进来的农户改造为两层。王家大院虽外面格局尚存,但里面已经面目全非。细细辨察,仍有一些历史遗迹可寻,尤其是中院主楼的“四季博古”窗雕设计新颖别致,四季花鸟草木雕刻凸显于内窗之上,类似于浮雕风格,画面内容栩栩如生,雅韵犹存,雕刻刀工娴熟高超,不着痕迹。据说是由纳西族著名画家周霖画图,请剑川木匠名师雕刻。后院为花园,花坛石础仍在,长约九米,高约一米,图案精致。严子藩老人说原为东西两个花坛,现只余东边一个。东厢有一水井,以前还出水,水流至花园中的水池,萦绕宅院四周,是为风水。水井旁建有家庙,现已拆毁。
王煊是阿喜村中最大的地主,曾拥有田地近百亩,但发家之初是以村中开铺子、食店、铁器加工、纺织作坊所得收入为资本,民国时期才发展成为大地主。也是这个“大地主”之名使其家产在解放后成为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王煊一个家院分别分给五个家庭,从中也可看出王煊家底殷实程度。
但王煊声名仅限于阿喜一村,扩大一些也就龙蟠境内。这样一个大户人家为何这般低调?他是如何做到守拙如平民百姓家的?王煊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王煊后人已作为地主赶出了家院。听说王煊还有个曾孙仍住在村中,在严子藩老人领路下我们去找王煊后人。王煊曾孙家在公路边,为一座北朝南的三坊一照壁院落,院内树木成荫,瓜果飘香,窗明几净,从中看得出来主人的修养。
王煊的曾孙已经年届六旬,但仍神采奕奕,身体硬朗,看起不过五十有余。但他似乎对自己家世有些避讳,并未谈及曾祖父多少历史,只是说曾祖父在世时,他仍在襁袍中,记忆中没留下多少印象。他也只是听父亲一辈的人说起过,曾祖父王煊一代从丽江古城的新华街黄山下段搬迁至此,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后来有了资本积累后才置田盖房,也就是民国中后期才发达起来。老人的母亲仍在世,已有九十高龄,身体尚可,也不愿多谈。是否六十年前留下的历史伤痕仍心有余悸,毕竟“大地主”那顶大帽子已经戴了那么多年,祖先的光辉业绩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更多的是不可承受的历史之重。
墓碑中的王煊
那次铺子村之行抱憾而归,一直到三个月后才得以第二次之行。2011年8月9日中午,我与刘军又到阿喜村再访。严子藩老人说王煊墓地在铺子村背后的山上,可以考察一下,可查缺补漏。这样三人朝岩肯美居山进发。“岩肯美居”意为悬崖下的山,相传上方有一山洞,是木氏土司的藏金处。山势看起来不高,但一爬起来还是费劲,一则顶着烈日酷热,二是越往上爬,山势愈加陡峭。这座大山的背后就是七十二道弯古道,王煊把墓地选在此地是有深意的。想到当年开辟古道先驱的艰辛,大家也就迎难而上了,一个小时后终于抵达墓地。
王煊家族的墓地依山而建,王煊墓在最高处,与母亲、其弟的墓并排,其下有两排墓地,皆为旧式墓制,但均遭严重破坏,墓碑、拱顶、狮座都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四周。其中有一墓碑尚存,但里面铭文被人为地凿坏,无法辨识,严子藩说这是王煊儿子之墓,在“文革”时为红卫兵所破坏。王煊墓基背后也是被人挖开了,说是盗墓贼所为,因为王煊是附近有名的大财主,盗墓贼频繁光顾,往往是填好一次后不久又挖开了,后来干脆不填了。看来做个财主也不容易,即使入了土也难得安静。从挖开的墓室看,墓坑四壁皆由青石板砌成,外面浇铸了石灰糯米浆。幸亏墓碑仍保存较好,里面铭文仍清晰可察。
墓中铭文如下:
从九寿官显考王化讳煊
前清待赠 合享耄期之寿藏
七品孺人显妣郑氏鹄
右侧铭文为:
原命生于道光三十年腊月吉时受生
大限卒于民国十五年四月初二卯时终寿
丽江县□委员长兼时务总董清附生侄愚和近
圣顿首拜撰
左侧铭文为:
孝男 王文炳,媳 严氏
孙男 运兴
侄男 王文魁、文选、文□、焕东、焕典
侄 孙男 王协中
侄孙女 阿爱、阿合
千秋奉祀
大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上浣日 豰旦 立
王煊墓高近两米,宽三米,进深一米五,墓石上雕绘有龙凤、狮子、麒麟、文官、八卦等物。除了内碑有文字外,其他地方均无铭文。这说明了王煊家族并不是妙明家族那般的诗书人家。有意思的是王煊的碑文是由妙明孙侄和近圣所写。和近圣家族与王家并无姻亲关系,更多是出于对一个乡贤的尊敬。
从墓碑现存文字考察,王煊出生于道光30年(1850),去世于民国15年(1926),享年76岁。据严子藩介绍,王煊父亲死于“乱世十八年”期间,死后尸体也没有找到,所以王煊的父母墓只是单墓。王煊自幼由母亲抚养成人,与母亲感情极深,故死后仍陪伴在母亲旁边。其兄王熙去世于民国二年(1912年),享年77岁。墓碑除了对死者的生死受限、子女情况予以照例说明外,并无更多的记载。虽有妙明家族的两个文士写了碑铭,却无他们家族墓志铭那般丰富,已经简约到极致了。王煊还是不肯宣扬,但这并非意味着真的一无可宣。
王煊的家世
回到村里四处走访,从村民中获得了一些有关王煊的信息,严子藩老人也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口头文本,由此,一直不肯走出历史迷雾的王煊渐渐清晰起来。
王煊祖上为内地汉族移民,明时“洪武调卫”始入云南,后入籍丽江。王氏家族是丽江古城的名门望族,民国时期与习氏、李氏、赖氏同称丽江四大家族。王氏除了经商有名外,也是以书香门第著称。晚清丽江著名诗人王竹淇为家族之翘楚。王煊先辈原居住于大研镇坞古崩(黄山下段),王煊父亲曾到藏区做过生意,成为当时的“藏客”,后死于咸丰、同治年间的“乱世十八年”期间。王煊孤苦伶仃,青年时期四处打工,后迁至雄古一带开了个砖瓦窑,以制作、出售砖瓦、陶器为生,手头有些积蓄后,又迁到铺子村,开设了铺子、打铁铺、纺织铺、陶器铺等手工作坊,并在当地购置田地种植棉花,自己织布、制衣,家底逐渐殷实后,开始置田盖屋,到解放前,家中占有田地九十余亩,同时也是江边一带开设铺子、作坊最多的大户人家。
但这也只是一个大户土财而已。王煊自幼随父外出经商,后定居于铺子村开创基业,备尝艰辛,并没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从他墓碑风格中也可体察到,他更多的是一个实干家,而非吟诗弄墨的文人雅士。但后来他做出了一件那些文人雅士难以企及的大事!
王煊的大事
七十二道弯茶马古道全长近八公里,从江边铺子村一路盘旋而上,直达山顶的蒙古哨,至今仍完整保留了近五公里的石板路。整个古道平均宽度为两米多,峰回路转,行走其间并不感觉在攀爬,且一路林荫,晴不起尘,雨不泥泞。如此保存完整的茶马古道在丽江乃至在滇、川、藏都极为罕见,由此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7月,丽江召开国际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会后最后一天,与会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实地走完了这条古道,并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条古道与王煊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是说这条古道由他开辟,如果算年头,从他家背后盘旋而上的古道比他身世、甚至比他家世的历史还要长。他做的事就是给这条路烂泥滑的古道铺上了石板,拓宽了路基,沿途设置了拦马石、饮水槽,两个马队相遇时的分道。近七公里的七十二道弯因弯道甚多而名,这一古道开拓时间很早,但因年久失修,洪水冲刷,道路破坏严重,一到雨水季节,道路泥泞不堪,过往商旅深受其苦,有些马帮就改道而行。马帮改道,直接影响到了铺子村的生意,这迫使王煊不得不陷入思考。古道不修则意味着家业衰落,要修则耗资巨大,独力难撑。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终于作出了决择:大干,快上!
王煊率先捐献出一部分资产作为修路资金以作为倡议,丽江城内也有多家商户纷纷捐资,但与整个工程所需资金仍有差距。天上不会掉下来金坨坨,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经过一番动员后,他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请石匠打凿石料、搬运石板上,而且最大限度地就地取材,靠山吃山。资金不足部分通过村民的无偿劳力投入,以工代赈方式来弥补,建设期间村民伙食大部分由王煊免费提供,这样保障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工程所需石料大部分出自古道经过的山坡,但仍有需要搬运的地段,尤其离村三公里山路皆为红土,只能靠人力搬运。
王煊带领村中劳力以圆木运石方式硬是把这一段山路全程铺上了石板。有些因经常滑坡、洪水冲涮而倒塌的路段采用了重新设计改道,或用石基加固的方法,达到了百年不坏的质量。原来路段的急弯处、陡坡段道路较狭窄,不利于不同方向的两个马帮同时行进,他们就把这些地段进行拓宽,并在危险地段设置了高达一米的拦马石;在平路段也拓展为中间土基相隔的分道,以利于两个马队互不打扰而行。经过两年多日晒雨淋、风餐露宿的艰苦奋战,从铺子村一直到太安乡蒙古哨的八公里路段全都铺上了石板。这是何等的一个奇迹啊!没有政府投入一分钱,也没有工程师规划设计,全是由这样一伙村民百姓埋头苦干出来的。
王煊从未以这段古道功臣自居,他的身影更多隐没于群体乡民中,与他们一同滚石拉纤,凿石垒基;一同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在暴风骤雨中坚守在工程最险地段;亲手把饭菜舀给村民,在艰难时期相互鼓励打气……他没有留下一块铭刻这项丰功伟绩的石碑,以致到后来的人们也淡忘了当初的古道修拓者。他只是在去世后,静静地躺在了与古道同在的半山腰,就如当初修路时,从山上俯瞰着一路蜿蜒的古道延伸进村里,又从村里延伸到山尽头。他是欣慰的,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件大事,大到何种程度?他也不会去琢磨。他更不会想到他们留下的这个工程会成为茶马古道遗址,与世界文化线路遗产这类国际大事更扯不上了。但正是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创造了茶马古道上的奇迹,这条古道并非只是由藏客、巨商、达官、文人所成就。
仁者王煊
王煊除了修建七十二道弯古道外,也为村里做了不少公益,至今不少村中老人仍感念不已。阿喜村内的兴文桥、兴建龙潭以及龙神祠,王煊率先捐资,并亲任监工,与建筑工人一同参与兴建。兴建龙神祠时,从开挖墙基到盖上最后一片瓦,他从未缺工过一天。同样,这些流惠村民的工程中也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王煊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时处动乱时期,家境清寒,没有机会读书。后来家道中兴后,他在家中办了私塾,从丽江聘请教师来村中教书,除了自己儿子外,村中儿童也可入蒙受学。他对教书先生尊敬有加,除了过年过节置办礼品以表庆贺外,平时教师的伙食也优于家人。
王煊家庙旁有一水井,一年四季有一小股清泉从中汩汩溢出,除了家人饮用外,也让邻里饮用。若有邻居过来挑水时,即使家中要用水,让邻居先舀,并且自己亲自把井水舀到水桶中。
相传村中有一窃贼慕王煊家财富,择一风高月黑夜潜入他家中行窃。窃贼进入王煊卧室时,王煊已觉醒,但未出声,直至窃贼得手而出。王煊于暗中辨出窃贼系村中熟人。第二天,他拿着一些米、肉、钱物送到此人家,说不知家境艰难如此,同为村人,深感有愧。窃贼汗颜,自此洗手,重新做人。
不少村民都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每天拂晓,王煊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一个人,身背一个篮筐,手持一把小铲,沿着古道一路捡拾马粪,直到篮筐满了后才回家,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去世前一个月。
每次经过阿喜,心头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幕场景:那些一路吆喝着,满载货物,浩浩荡荡地从村中经过的马帮,或许对这个佝偻着腰,一脸谦卑的老人不会予以太多的留意,甚至说不定还要喝斥几声,让他赶紧让路。若有人告知背后山上的石板路是这个老人带领下修建而成的,他们或许以为是在讲天方夜谭。其实这也是王煊所期愿的,他不习惯过多的炫耀与喧哗,做个本分的平民百姓,享受着其间的酸甜苦乐就是最大的幸福。甚至我们认为那件了不起的大事,在他心目中也只是尽了本分而已。
王煊不宣,仁者不宣。何谓仁者?常怀爱人之心也。
太子已归苍莽外——太子洞的历史及其他
在“丽江社区”网站上,曾为洛克拍的一张山洞照片争执不休,有的说是大具的,有的说是在藏区,有的说是在白沙,莫衷一是。其实这张照片就是龙蟠太子洞,主要原因是这张照片的英文说明把龙蟠说成了“axi li”,太子洞说成了王子洞。这样把读者蒙晕了。约瑟夫·洛克到太子洞时,当时因还未设龙蟠乡,所以他的书中仍称为阿喜里太子洞。洛克到太子洞的路线是从白沙玉湖村出发,经玉峰寺,绕道背后现在植物园的背后,到文海背后的“海罗谷”(herl loq gu),进入现文海彝族村二队、三队,到雪山脚下的“郭查”(go cha),本海罗山,抵达龙蟠境内的“勒哲郭山”(lee zerq goq),然后下山就到了太子洞。这一线路基本上是沿雪山脚下绕行,一路雪光山容相伴,也是最佳的徒步线路。当然,洛克当年走此线,是带了保镖、马夫、厨师等大队人马。他也不会想到,当年他走的这条线路,现已经成为丽江境内最理想的徒步旅游线路,时常有欧美游客踏上当年洛克走过的这条玉龙雪山到太子洞之旅。
上海有个太子洞
上海名字倒时髦,但实际情形与国际大都市上海十万八千里。这里是整个龙蟠乡交通最为不便的偏远山村。听说“文革”时期分配知青时,有时知青一听这一名字,以为即使不是座大城市,可能也是个经济发达的城镇,就争相报名去上海,不期上路后走不完的山路,越走越心寒,有些女知青到半路就止不住涕泪涟涟。上海是个偏僻小山村,在龙蟠境内位于雪山东北角,新尚村的最北端。上海因太子洞而名。
我们的太子洞之旅,与洛克线路相反,是从龙蟠境内往上爬的。之前准备了好几天,因为一直下雨而未果。如果走路,从龙蟠乡政府到太子洞旁边的上海村,至少要一个小时多,加上到太子洞的行程,来回基本上就一天的路程。所以我们采纳了乡里知情人的建议,直接把车开到上海村,约摸半个多小时就可到达,然后徒步半个多小时可抵达太子洞。刚好那天一直没有下雨,中午十一点半我们就从乡政府出发,车子是一辆老式吉普车,是从乡林管所借过来的,司机是林管站的站长,大家都喊他“蒋师”。因工作性质,蒋师对龙蟠境内的林区状况了如指掌,这条山路不知跑了多少趟,轻车熟路,是最好的向导。
车子是从龙蟠村委会的忠义村拐上山,一路都是陡坡,且多泥路,幸好没有下雨,不然车是开不上去的。一路河水喧哗相伴,林木葱郁,景色旖旎。因前一阵子一直下雨,河水涨了好多,有几个地方几乎与路同平,且河水特别白,似乎放了乳汁。我们还开玩笑说这是最典型的白水河了。听林管所的蒋师介绍,这是来自雪山溶岩水所致。因为雪山半山腰都是风化,一下雨就冲刷下来,汇入河水就把整条河染白了。
上海海拔不算高,也就2200到2400之间,比新尚的长松坪低多了,这从上海可以种植烟草就可看出,但交通状况比长松坪差。听村长介绍,现在的这条路都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修的,直到现在也只是土路,只是在河谷地段修了段近半公里的水泥路。从忠义到上海,全程将近9公里。当年村里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得起锄头的都全体出动,政府也给了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断断续续攻坚了一年多,终于修通了此路。但因雨水季节经常发洪水,时有冲毁道路的事故,加上村里拖拉机对路破坏大,每年修路成为村里的义务劳动。
我们到达上海村口时,村长已经在路边等着了。村长是个40出头的中年人,个头不高,精瘦中透着干练。这几天全村都忙于收烟叶,烤烟叶,也是关系到一年收成的关键时节,村长家也是在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还请了亲戚帮忙烤烟叶。但一听到刘部长的电话后就二话不说答应了与我们相随。
一路上,村长向我们介绍了村的情况,上海是汉名,纳西名为“格得”(ggeq der),意为上面的水塘子,与下边一个水塘相对应。民国时称为“上逢得”(sail fuq der),至今还保留有一颗那个时期的公章。民国时村里有不少人被抽壮丁当兵,后来有些流落到外地,有一个随溃败的国民党部队到了台湾,他们写信回来时,地名都写成“上逢得村”,邮递员因不知此名而把邮件寄了回去。村子现有51户,有杨氏、和氏、李氏三大姓氏,和氏为两个家族,杨氏家族有21户。村中四个家族都从白沙搬迁而来,如杨氏家族从玉湖搬来的,至今已有7代人,与龙蟠大多数移民相似,几乎是在乱世十八年间搬迁过来的,至今村人称玉湖为“堆古”(duq gu)。白沙与龙蟠关系非同一般,笔者在太安、南溪、后山一带田野调查时,了解到那里的住户也是大多从白沙搬迁而来,白沙成了纳西族移民的发源地、根据地。
上海村地处山区,气候湿润,粮食基本上能自保。以前生产队时,因没有通路,只能由马帮驮运到乡里粮站,有时检查不合格,就只能在粮站里晒粮食,回去时就只能摸黑走夜路。整个村子不算富,也不算穷,现在也是处于温饱水平,这几年种烤烟,收入有了明显改善。但村子风气一直很好,从来没有打砸抢、小偷小摸、违法乱纪的事情;村人也很团结,哪家有难,都能互助互济,村里公益事业也不需要动员,一声令下,全体出动。去年修河谷底那段水泥路,就是全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参与,吃住都在路边,一鼓作气修成功的。乡政府也为这种士气所感动,乡领导买了猪头、猪肉去慰问。与之形成对比,有些村即使钱是政府给的,但许多事情因村民组织不起来而不了了之,政府也为此大为头疼。
从上海村到太子洞
吉普车到村尾后不能往前了,一行四人下了车子,徒步上路。原以为这段山路会异常艰难,不期山路只是在半山腰绕,基本上以平路为主。村长说以前四里八乡的民众到太子洞进香都是从这条路上走的,搞生产队时把路拓宽了,可以走胶轮车。只是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没有人护理,加上常年用牛拉木料,整个路况已经破败不堪,但行人倒不成问题。
步行20多分钟,绕过山梁子,就进入了一个狭长的山谷,往上仰望,皑皑玉龙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似乎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似一尊者安详端坐,又如一个调皮的女孩,“千娇面,盈盈伫立。”愈往上攀爬,山势有些陡峭,且苍天古树也蓊蓊郁郁,遮天蔽日。沿途有茂密的白杜鹃树,纳西名为“母个”(muq gel),而再往上的雪线附近的多为红杜鹃,纳西名为“母冷拍”(muq le perq)。还有一种樱桃一样的小红果,一串串地挂在树枝上,阳光照耀下娇艳欲滴,煞惹人馋,村长说可以吃,我们就争相摘吃起来,却满嘴酸涩,都吐了出来。村长说本来名字叫“酸涩夫”,村人以前拿它作酸料,放在凉拌里异常可口。在路边又见一种草药,高约一人,杆粗大拇指,分枝多,叶如小枫叶。村长说此草药名为“生麻”,根可入药,洗净后切成小片,晒干后泡水喝,对重感冒最见效。
这几年搞天保工程,植被恢复了一些,森林里动物也多了起来,黑熊、野猪、狼、旱獭、雉鸡、獐、飞鼠时常出没于深山野林中,前个月,有只黑熊还偷吃了太子洞旁村长家岳父养的蜂蜜。有些小动物还是时常会被捕到,如旱獭,晚上喜欢爬到松树上掰吃松果,这时拿手电直射它的眼睛,它就只会呆呆盯着电筒,人们便可以用石头或汽钉枪打它。旱獭肉无膻味,鲜美异常,且治风湿,视为山珍。心里总觉有些残忍,但山民自古有打猎习俗,单纯从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来讲,是否有些违背了传统?靠山吃山,不吃山只能自己饿死,恐怕也不合人情。只能说取舍有度,适可而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如此,关键是掌握好尺度。
我们在半山腰,就遇到两个村里年青人在砍树,他俩一见到林管所的蒋师,吓得脸色都有些苍白了,村长也在旁说情,只是砍些杂木,是村里通过的,主要是用作烤烟用。蒋师也只是强调了一下不能乱砍滥伐就没再说什么。
那两个青年人倒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山背后的彝族村经常有人到村子山上偷伐木料,尤其是这一段时间,趁着村里忙着烤烟,几乎成群结队地乱砍伐。村长也证实了此说,以前彝族村到他们村护林区是不通路的,这些人专门靠人工开辟了一条马帮道,可从他们村直通林区。前几个月,他们村的人在林区里搭了棚子,吃住在里面,专门盗伐木料。村长闻讯后带了一伙劳力去抓他们,却扑了个空,可能是事先有所发觉而溜走了,当天烧了8个棚子。以一个棚子住四个人计,大致有30多人成天彻夜地盗伐森林。彝族村子所属林区已无木可伐,加上村子除了种几亩洋芋满足吃饭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收入途径,只能靠盗伐林木为生。贫困是根,要根治这类现象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往太子洞的路是在雪山下来的一个山岰中盘旋而上,因属缓坡,行走不甚吃力。原来的老路在靠近东边山脚下,至今仍有石台阶,宽约两米多了;右边是一道石块垒起的石墙,高约一米多,顺着路一直延伸了一公里多。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工程了。村长说此路是当年洞庙中的主持化缘所修,主要是防止路人、坐骑糟蹋庄稼;石墙西边都是田地,是专门供给看护太子洞的和尚田地。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和尚田已了无痕迹,全部被树木荒草湮没,原来的老路完全成了杂木茂盛的小山沟。
约摸40来分钟,走到一个弯子处,村长突然喊了三声“唔……”,把我们吓了一跳!事后村长解释说,相传古时太子洞中有三虎,经常咬死过路之人,但对猎狗却异常害怕,一听到狗吠声就逃离了。所以留下这样一个风俗:只要走到这弯子时,每个人都要高喊三声狗叫声,还有说上一句:“阿祖,肯尼得乎佑!”意为:老祖宗,请等一下猎狗!
从密林中钻出来时,两个大洞昭然在前,一种震慑力油然升起。那黑洞面积之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犹如两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或者是不明怪物的眼睛。这就是有名的太子洞了。两个洞隔了近20米,刚好在我们所站山坡的斜对面,西北边洞更大些,犹如神斧从外头直接砍凿出来似的,洞顶端是平平的,与悬崖山顶只隔了近四五米,洞口高约30多米,一座山的肚子好似被挖空了。
太子洞的前世与今生
大伙顺着山路蜿蜒而行,一会儿就进入了山洞,刚好此时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村长说以前搞集体生产队时砍伐木料,下雨时洞里可躲上百人,但占不到整个洞的三分之一,前方平台上就可满足上百人躲雨所需。洞口宽约十五米,进深20余米,折算长宽不等情况,整个洞占地面积大致有200平方米。
从洞口往里,中间坡度依次抬升,其中有人工搭建的三个石头平台:下方平台宽约2米,长约8米;中台宽约三米,长2米;上台为一米见方。此为主洞,旁边有两个分洞。两个分洞也在大洞内,但因各处左右两边,且洞内有洞,各有特色。左下方的山洞地势平整,有十平方米多,从平地上突兀起十多柱钟乳石,犹如男性生殖器。听说在此位置的洞顶上悬垂下来一个钟乳石更为神似,太子洞也是由此而名,以前民众到此祭拜时,用铜钱投中此石者为吉,尤其已婚未育妇女到此求子者甚众。民间信仰中实用功能是最突出的,“临时抱佛脚”总比不抱要强,至少有个心理安慰,只是在后面的历史演变中,不断有儒释道等宗教内容累积、叠加、附会于上,其本初功能反而遮蔽了。譬如太子本来突出了男性特征,后来与送子观音、皇太子等外来文化相混融,由此也创编出观音现身、太子避难于此的种种传说。
洛克的版本中对太子说表示了怀疑,更倾向于另一个纳西族的民间传说:“在丽江纳西人所崇奉的三个山神中,作为丽江雪山之神的三多是最受崇拜的。与三多有关的神话以及丽江雪山东斜坡上三多寺的历史,到处传扬。相传三多有两个哥哥,第一个名叫阿吴瓦(Aw wuea wuea),住在雪山西斜坡的石灰岩洞里,称为太子洞。这洞以一个皇帝的太子曾来洞里居住而得名,但历史上有关这个太子的具体身份及其父皇的统治时期却无任何记载。三多的第二个哥哥名叫拉吉拉恒(cLa gkyi la khu),他的庙宇在丽江迤西。”
太子洞的祭拜时节分为三种,以二月八的集体祭拜为大,其时四乡八村的民众在此聚会野餐,洞内无法容纳,一直扩大到旁边的草坪地,活动一直延续三天,人们在此烧香拜佛、商品交易、会故识新、听戏游乐,成为民众的狂欢节日。另外两个祭拜日期为不定期的民众祈愿活动,男子36岁、49岁两个生命关口要结伴前来许愿,已婚不育者也要前来求子。神灵与平民、神圣与世俗、庄严与狂欢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太子洞的文化魅力。只是后来,以“科学”的名义,对民众的信仰实行污名化,人为地割裂传统与现实的文化脐带,窒息了信仰空间,使民间文化出现了巨大的黑洞。这也是后来太子洞遭受灭顶之灾的根源所在。
村长介绍说,以前洞内建有庙宇,地点就在太子石柱处,这从洛克图片中也可找到印证。门上方还挂了三块匾额,中间有三个字,模糊不清,旁边两块分别写有“地灵”、“人杰”二字。听说里面还塑有送子观音,观音端坐于莲花宝座上,高约2米多,“文革”破“四旧”时被砸坏,但还没完全砸烂,被一个村民发现后抱回家中,藏于楼上的草料堆中,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惶惶,他害怕受牵连,最后还是偷偷地把这尊观音菩萨从村边的悬崖上丢了下去。那两块匾额也被村民收藏,不幸的是前年有人到村里收购文物,卖了二千元。在右边前方的洞崖上有一突出的乳石,底端如平座,大小如坐椅,民国时上面塑有一尊从上往下俯视的金罗汉,也是破“四旧”时被村民偷走,也有人说是江对岸的林业局的人偷走的,听说卖了此物后发了横财。不知这些人真的能安心吗?毕竟是做了亏心事啊!
大洞右边也有一小洞,其地势在三洞中最高,离平地约有六七米,没有左洞大,但胜在形态,俨然是一个浓缩版的白水台,从地面到台上有小石台阶,离洞顶一米许,就有一个三个梯田形状的华泉台,大小约3、4平方米,但里面没有水,村长说断水只是这几年的事,以前年年都有水涌下来的,这已经从侧面说明了这几年干旱的严重。
太子洞神奇的是这里的水,常年点滴不止,汇聚成洼、成池,有了水气氤氲,洞中气候酷夏如秋,严冬如春。这水方便了人们的聚会野餐,也是这水的多年穿石功才成就了这方大观。隔着此洞往大洞口,地势稍低处又有一洞,此洞也有华泉台,与左边太子庙相对应,但泉台没有前者大,只有两小台,上有清水,晶莹可鉴,喝了一口,清洌甘甜。村长说也可清目,掬了一捧洗了下眼睛,感觉神爽目清。这说法倒与三坝白水台如出一辙了。是这里面的矿物质起作用,还是神在里面起的心理作用都不得而知了。
与阿喜观音洞相似,洞内也有不少题辞,如“古旧佛生成”“仙洞天堂”“别有天地非人间”“景胜名山”等,也有老外留下拉丁字母签名。从题辞质量来看,年代越往前移,品味越高。当代一些游客题辞更多是“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如在玉埂银丘的华泉上,有好事者在光滑的沿壁上硬生生地刻写了“神田”几字,笔法粗陋,简直是暴殄天物。
但更让人叹息的是洞内钟乳石几乎毁于近年来的偷盗者。外村人说是上海本村人砸下来后,在每年棒棒节的市场上便宜出售;村里人说基本上是外地人过来采集为主,尤其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中甸林业局职工最为猖獗,经常是成群结队过来砍砸,或自己做盆景,或外售谋利,洞顶悬垂的钟乳石几乎无一幸免于难,原来千奇百怪的艺术世界现在成了光秃秃的洞顶。十多年前有人在洞内发现硝矿后,实行大规模的采矿,尤其是炸药爆破对洞内破坏最大,最里面的洞壁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甚至把洞顶的石块也炸落下来。我们在洞口地上看到一块写有题辞的巨石,颜体笔法,苍劲有力,应为有学之士所写,内容为:
树映林深久隐烟霞为伴侣,
山清水秀只凭花木记春秋。
癸未孟秋 剑阳刘楷落
村长说这块石头原来在洞顶上,是被炸落下来的。
太子洞成了一个伤心洞!连洞口前的那株百年香柏也在劫难逃,被人拦腰砍断,只剩一截树根杵在那儿默哀。听说以前此树与洞齐高,枝繁叶茂,树影婆娑,几乎把洞口覆盖了。而今树已无,洞虽存,却成了一个空洞,一个巨大的历史伤口。
从大洞出来,顺着洞壁斜坡往南二十余米就到了邻洞,这个洞明显小了许多,高约七、八米,最宽处为十米许,进深仅四、五米,内里又分为两洞,东边洞更小,洞外天然形成一个洞门,大小如一间小房子。当地人称为“尼奴钻”(ni nvq rhual),意为妻房(厢房),据说解放前村民杨海一家居住于此,主要是租种太子洞庙田。里面的大洞为两间房的面积,可容4、5个人在此做饭。洞中还有柜子、火塘、条凳。村长说,他的老岳父在此养蜂,隔段时间就过来看一下,临时在此生火做饭。洞口边上有十多个蜂箱,成群蜜蜂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只是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旁边架设了好多拉线,上面挂着光盘片。村长说老熊嗜吃蜂蜜,时有过来扒蜜吃,老熊怕反射光,就以此来防它。老熊体大皮厚,一般火枪打不死它,它发作时可把人撕成两半,村民发现后也不敢接近,而且现在政府严禁捕杀野兽,猎枪都上交了。
从洞中出来时,雨已停歇,天空放晴,雾气渐渐退回雪峰间。在返回路上,离洞口约半公里处,发现路上露出不少条石,这些条石显然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村长讲了这些条石的来历,以前大家也不知道此处埋有这么多条石,后来村民拖拉木料时常在此经过,时间一长形成了一个土槽,才发现了这一秘密。据村中老人回忆,这些石料都是原来洞中观音庙的住持穆欣和尚为建一大寺而准备的。穆欣原在岩羊山神庙中当庙祝,后受一个汉传佛教高僧指点,说太子洞有佛缘,与玉龙雪山龙脉相接,建寺后可佑一方平安。穆欣听从高僧指点,从山神庙转投太子洞,并身体力行,四处化缘,终于建起了洞中的观音庙,但他认为还不足以实现高僧的宏愿,决定到内地化缘,资金充足后再建大寺。世事难料,穆欣云游四海后一直没有回来,再后来,不但大寺未成,连里面的小庙也不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现在此情此景,穆欣若在天有灵,情何以堪!据村民推测,穆欣出去化缘时也是解放前夕,天变一时,他可能知道已经无力回天,就消了念头,也无颜回来见父老了;抑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成了专政对象。这些都无从得知了。
村长还记得穆欣题在洞中两句诗:
静听岩泉亦雨乐
喜看萤火似星光
诗描述的是自己夜宿洞中,静听岩泉滴答如雨落,看萤火翩翩如星光的情景感受,“雨乐”为“雨落”的谐语,透露出他胸怀大志、乐观豁达之情怀,“星光”隐喻了实现夙愿的信念,这应该是这位僧人出游化缘前心迹的表露。
从太子洞返回,临近村口的一个峰回路转处,金沙江如一条黄色飘带映入眼帘,因雨过初霁,江岸村庄与柳林笼着一层轻纱;远近群山层峦叠嶂,颜色由深绿、靛青、淡蓝依次隐入远方天际。此情此景,极为吻合明朝状元杨慎所写的一幅对联:
一水抱孤城,烟渺有无,主杖僧归苍莽外;
群峰朝叠阁,雨晴浓淡,倚栏人在图画中。
江山依旧,人间几多沧桑,主杖僧已归苍莽外……
太子洞下的风雨苍莽
从太子洞到上海村,天雨流芳,历史与现实也总是风雨相随。
在村长家烤烟炉边,遇到了过来帮忙的几个村民。据一个老者回忆,村中杨氏家族源于白沙乡玉龙村(ddiuq ggv),至今已有七代。老人对太子洞的破坏遭遇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对上天的大不敬。村里民风纯朴,至今没有出过一个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的人,而且村中男丁特别兴旺,与太子洞神灵保佑有关。老人至今对旧时“二月八”节日期间的热闹景象记忆犹新:“二月八会期长达三天,周边四村八乡的人都聚会于此,来来往往的人挤满了村里的山路,那几天也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有些亲戚提前住宿到家中,为的是参加太子洞的节日活动。更多的人是带着帐蓬,住在太子洞旁草坪上。有一家老小的,有达官贵人,有来做生意、摆地摊的,唱戏的,看热闹的更多,最隆重的是穆欣主持的祭佛法事,参加的和尚、道士也很多。集会最多时有上千人,太子洞旁边的平地都住满了,附近村民在家做好了凉粉、豆腐、凉宵、粑粑等小食在这里摆摊,经常是不到下午就卖完了。解放后还搞过一两年,后来就作为封建迷信被禁止了。破坏活动也是那时开始的,但没有‘文革’与现在这般破坏严重。唉,这么好的一个洞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老人的一声叹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说村里人对太子洞还是敬畏的,对洞里古物破坏最大的还是周边的村民。村长说到去年一件事,从新尚村那边过来一伙人,准备到洞中采集钟乳石,村长听闻后,带了几个村民,制止了这种行径。在村中他也多次三令五申,在村规民约中严格规定保护太子洞的相关要求。杨青红老人认为,太子洞遭受破坏是与大时代背景相联系的,“那年头,人都保不住,更不要说一个山洞了。运动一阵接一阵,没完没了,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他说的“人都保不住”是事出有因的。原来村中有个大户人家,户主叫杨自良,读过私塾,有头脑,也曾参加过地下党活动。他家位于往太子洞的必经路口,家中就开了酿酒坊,除了卖给过路的游人外,还批发销售到江边集市上,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买了骡马走茶马古道。但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生意也停止了。土改时划为地主,屡遭批斗,后上吊自杀而死。杨自良对乡里是有贡献的,上海第一所小学是在他手里建立起来的,教学楼是一栋五间楼房,还配套了教师的厨房、宿舍,在当时龙蟠乡内是数一数二的。另外,对村里修路铺桥、动员村民子弟上学等方面也作了不少善事。他家院子是一个四合五天井,当地人又称为“跑马转角楼”,意为可以在院子房内前廊中骑马通行无阻。大院后来作为“胜利果实”遭到拆分,部分分给贫雇农居住,大部分作了生产队的粮场。一个风光一时的大户人家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被村口一座巨石吸引住了。巨石高约四米,长六米多,厚度约四米,背后是一堵百米悬崖,直抵河谷。村民说以前有人曾炸过此石,炸石未成,自己却身负重伤,自此后村里人一直不敢动它。村里老人说,此石与太子洞遥相对望,是灵石,与太子洞一起,保佑着村子的平安。大家想在此辨识一下太子洞的位置,但此时雨又加大了,群山皆隐没于茫茫雨雾中,太子洞已经归于苍莽之外了。
其实归于苍莽之外的何止是太子,还有那位曾经雄心勃勃、云游未归的的穆欣僧人,以及饱受政治风云摧残的杨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