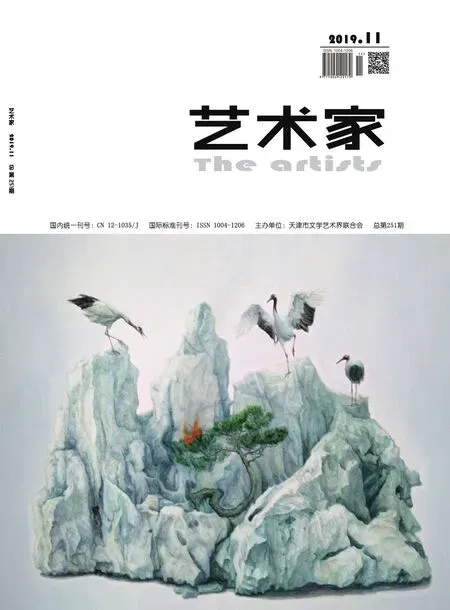《非草书》之新思考
□王晓萌 曲阜师范大学
《非草书》开篇指出,草书上不是仰观天象得之,下不是河洛水所吐之,中不是圣贤所造。赵壹认为,草书起源是“趋急速”产生的结果,作用仅在于“临事从宜”。当人们刻意临摹张芝等人的作品,把他当作一种艺术形式时反而有违文字产生的初衷。当时,人们不以书写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学术,包括朝廷的科举、贤士的招纳和业绩的考核。所以赵壹认为,字写得不好并不妨碍治家治国,认为写好草书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无实质性作用。但当通篇看完《非草书》后,笔者才发现赵壹想表达的还有对当时盲目临习的人的诚恳劝勉,而非实质性反对。
一、赵壹的批评态度
(一)“夕惕不息,仄不暇食”的现象
处于“草书热”时期的人们不分昼夜地疯狂练习,十几天就会将一支毛笔写坏,衣领和袖口全是墨,更夸张的是嘴巴牙齿也是黑的,就算难得有时间和朋友小聚,一边交谈另一边还要用手指在比画写些什么。有的人胳膊磨破,指甲划折,脸颊瘦得凹陷还不分昼夜地练草书。当人们孜孜不倦地临习,自以为可以达到高超境界时,赵壹以这样的姿态提出非难草书的观点也无可厚非。其本意只是想劝勉人们,因为人的筋骨和气血大不相同,心手所表达的疏密姿态也大相径庭。所以,书法不可以仅依靠临摹和效仿而放弃自己本身的思考,更不能扭曲本性而强学某体,否则到最后只是浪费心力,无法取得想要的效果。除此之外,赵壹还重点强调,人由内而外的气质和书法艺术密切相关,草书富有强烈动感,它自由的变化和形状更能表达个人情感。
(二)“凡人各不相同,不可强哉”的劝勉
人因为与生俱来的气质和秉性不同,精力和体质不同。心有粗细之分,手有拙巧之分,所以在写得好坏、写什么书体上,是不能强求的。笔者认为有一点不可否认,我们应大量临摹,但这绝不是在数量上的追求。
所谓书法的个性其实就是心的流露,即心手合一的表达。在《非草书》中赵壹提到,凡是八岁以上的孩子,当时只要进入学堂开始学写字,就是以崔瑗和张芝的字为模范进行临习,所以这些孩子是被灌输而无自我选择的,这不适合刚入学的孩子。崔瑗、张芝等有绝世才华的人都是在有渊博知识的前提下,才能够随手写字,通过书写表达个人情感。书法不能一味依靠效仿和临摹,更重要的是艺术个性的抒发和表达。
《非草书》在最后一段提到,写字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专注自我的人一定会缺失大眼界,只有小志向的人也一定没有什么作为。从起初结绳记事开始,到图形文字,最终到规范化的文字,书法从艺术萌芽到艺术发展再到成熟,始终和文化紧紧相连,这提醒我们在写字过程中还应提升自身文化水平。
二、《非草书》历史影响
(一)重要成就
赵壹在《非草书》中反映了东汉时期草书艺术发展的空前盛况和社会地位,记载了东汉时期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欣赏和对草书的喜爱程度。受社会风气影响,当时草书写得好的人备受世人仰慕和向往,这真实地反映出书法在当时出现了审美意识和自觉。汉代是书法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进而发展成赵壹所记载的“草书热”时期。
(二)对后世学书的影响
书法专业要求学生做到诗书画印四全,虽不求样样精到,但需有所涉猎。这大概是要把书法爱好和书法专业进行明确区分,就如手工劳动者和艺术家的差别,一个是单纯重复一项工作,而另一个需要花费心力脑力通过手来表达。这也正是对赵壹观点强有力的补充和肯定,我们应有广泛的涉猎和专一的研习,但不能一味地做临摹的工匠、字帖的搬运工。我们应开阔眼界,潜心解读书法家想要给表达的情感。我们如果将眼光放在浓厚的历史中,一定会发现唐人的庙堂之气、宋人的尚意之风,也会理解汉代草书之热。笔者发现赵壹在不知不觉中将矛盾制造在笔下,又将思考留给了我们,我们只有和文化贴近时,才有可能有机会在较高的层次上掌握书法这门艺术。
《非草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篇批评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著作。赵壹从某种程度上间接对草书进行了部分质疑,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草书艺术。这是通过人们自觉产生的,也是人们对自然审美的一种追求,至今还影响着书法的发展。
草书的发展离不开赵壹的非难,没有书法自觉就没有草书成熟的结果,也就没有真正的书法艺术。没有赵壹的批评和劝勉,就没有我们现在对书法创作更深层次的情感认识和表达,我们最终追求的应是心与手、脑与笔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