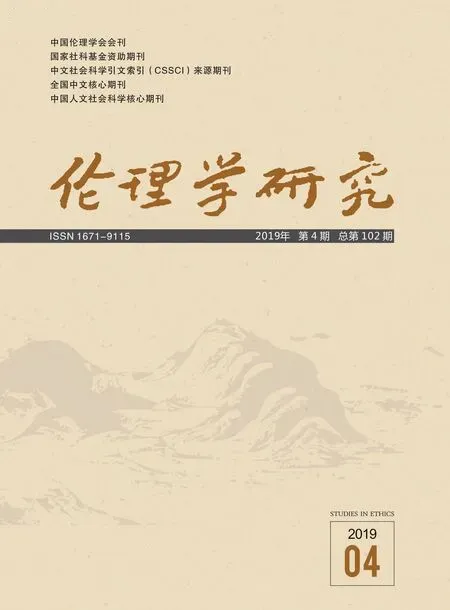人性与德性的两难:利己与利他的悖论解析
刘清平
一、问题的缘起
在西方道德哲学的语境里,长期存在着某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把利己与利他看成是两种在概念上就不兼容而相互排斥的东西,结果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引发了众说纷纭的无谓争议,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主张利己主义“有人性无德性”、利他主义“无人性有德性”的怪诞悖论了。
首先,一些哲学家认为,按照人们的自然本性或所谓的“自然法”,他们只会单向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产生利他的动机。霍布斯便宣称,“人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而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因此,“自然法……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对于保全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以致每个人都会“凭借武力或机诈去控制所有能够控制的人,直到没有强力可以危害自己”,结果走向“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1](P93-97)①。直到今天,所谓的心理利己主义仍然没有摆脱这种观念的深层积淀,从实然性描述的角度特别强调每个人都仅仅关注自己的利益,即便从事利他的行为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作为伦理维度上的一种规范性诉求,利他主义违反了“自然人性”,是“不合理”而无从成立的[2](P87-105)。
与此同时,另一些哲学家又主张,在人类生活中,只有利他的动机以及行为才是有道德的;相比之下,利己的动机以及行为不仅谈不上高尚,而且还潜藏着不道德的倾向。休谟就宣布:“我敬重那些能将自爱以任何方式指向关心他人和服务社会的人,而憎恶或蔑视那些只考虑自己满足和享乐的人。”[3](P149)康德也强调,人们只有基于不包含自己的感性需要或爱好的良善意志,出于理性颁布的普遍义务从事行为,才能具有值得高度推崇的真正道德价值;相比之下,那些仅仅出于利己意图的行为,诸如商人在买卖中为了自己长久赢利做到了童叟无欺之类,即便是符合义务、广受赞许的,也缺乏真正的道德价值[4](P11-14)。叔本华在把“自我保全”的利己欲与“不可害人”的正义德性对立起来的时候更是主张,“利己主义与行为的道德价值是绝对相互排斥的。……道德价值完全取决于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只是为了他人的利益”[5](P143-144)。
于是,一旦将这两种针尖对麦芒的观念放在一起,不仅会在利己与利他之间生出不共戴天的二元对立,仿佛前者在逻辑上已然排斥了后者,而且还会在通常被视为内在统一的人性与德性之间也造成致命的断裂:利己的动机以及行为虽然符合人性,但同时又是缺乏德性的;利他的动机以及行为虽然很有德性,但同时又是违反人性的,从而形成“人性还是德性”的荒唐两难:如果利己符合人性,它怎么会缺失德性?倘若利他具有德性,它为什么不合人性?更简洁些说,要是利己构成了自然人性,利他如何可能有高尚德性?事实上,面对这种两难,如果说利己主义只能是尴尬地努力挽回自己在道德上的不良名声,利他主义的境遇则更为难堪,不得不设法找到自己在人性中的立足根基。
尤为反讽的是,这种两难有时甚至还会凝结在同一个人身上。例如,主张利己主义符合自然人性的霍布斯,内心深处便似乎倾向于认为它有些不道德,所以才在描述了人人开战的丛林状态后感叹说:“自然人性竟然使人们如此分离,相互侵害和毁灭。”[1](P95)他甚至指出:“为他人好的意欲就是惠助、善意或慈爱;如果指向所有人就是善良的自然人性。”[1](P39)再如,叔本华在宣布“不带任何利己的动机就是评判一个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标准”的同时,又明确承认利己欲是人的首要行为动机,甚至与人的本质是合而为一的[5](P131、140)。至于那个以亚当·斯密命名的悖论同样是在这种两难的语境里生成的:一方面,人们主要是凭借自爱的利己欲在经济领域从事谋利的行为,其动机只是想为自己赚钱而不是对他人施惠;另一方面,人们只有凭借利他的同情心才能在伦理领域从事有道德的行为,摆脱利己欲的偏见而生成正义和公平的良知[6](P14)[7](P96-113)。这样一来自然会引发下面的质疑:既然如此,经济生活岂不是就缺失了正义的德性,而道德生活则会扼杀了利己的人性吗?事实上,尽管两百年来许多论者试图从各个角度消解二者的张力,其结果好像都不怎么成功。例如,斯密自己提出的一种解释是:虽然人们从事经济行为的主观动机只是为了利己,但这些行为的“客观”后果往往是利他的。[8](P27)可是,他在此通过神秘的“看不见之手”展示的这种“主客观统一”似乎还是难以解开一个魔咒:本来不道德的利己欲难道能够单凭产生了利他后果的飞身一跃,就让经济行为转化成基于同情心的有道德行为吗?众所周知,这个不仅把人性与德性,而且把经济与道德也弄得水火不容的理论两难,迄今还是一个让西方学界伤透脑筋的深度悖论。
与西方学界以二元对立架构为前提展开的上述理论努力不同,本文试图依据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日常体验,通过辨析“自利”人性内在包含的“利己”与“利他”两种因素之间既和谐又冲突的互动关系,主要从元价值学的实然性视角出发,破解西方学界制造的人性与德性的怪诞悖论,论证下面的见解: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不仅同样符合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而且同样具有复杂纠结的道德属性,无法一刀切地贴上不道德或有道德的片面标签。
二、自利本性中的利己与利他动机
匪夷所思的是,与另外某些在理论上引起了长期困扰的千古之谜相似,导致西方学界在利己和利他问题上陷入悖论难以自拔的一个主要原因,居然是它未能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深入辨析人生在世趋善避恶的自利意愿的丰富内涵,结果只是单纯强调了它的利己一面,却将它实际包含的利他一面排除在外了。
本来,从元价值学视角看,最广泛意义上的“趋善避恶(趋利避害)”可以说确实构成了人人拥有的自然本性,因为一个人只会通过从事各种行为,追求他认为是有利于自己因而值得意欲的好东西,避免他认为是有害于自己因而觉得讨厌的坏东西,以满足他的需要,弥补他的缺失,维系他的存在,实现他的自由,却不可能南辕北辙地追求他认为是有害于自己,因而觉得讨厌的坏东西,避免他认为是有利于自己,因而值得意欲的好东西。其实,哪怕一个人昨天还因为反感榴莲的味道避之不及,今天就因为了解了榴莲的丰富营养趋之如骛,也是由于他昨天把榴莲视为可厌之恶、今天却视为可欲之善的缘故。所以,尽管他在规范性层面上昨天避之不及和今天趋之如骛的是同一个东西,貌似陷入了自相矛盾,但在元价值学层面上却始终恪守着“人性逻辑”的同一条原则: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善,想要避免自己讨厌的恶。至于人们经常指责对方“趋恶避善”“为非作歹”,则可以溯源到不同的人在规范性层面上持有的歧异性善恶标准那里:你一直对榴莲的味道深恶痛绝,当然会觉得我钟爱榴莲是在“趋恶避善”了。
不幸的是,或许由于望文生义的缘故,西方学界往往把这种“趋于对自己有利的好东西,避免对自己有害的坏东西”的自利意愿片面地曲解成了只利己不利他,结果潜在预设了“自利在本性上就排斥利他”的前提。例如,霍布斯曾把“善和恶”界定成“表示我们意欲和厌恶的语词”,并将“自然权益”说成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欲、运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本性的自由”[1](97、121),已经相当清晰地指认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趋善避恶的自利意愿。但如前所述,他同时又将元价值学维度上的这种人性逻辑扭曲为规范性维度上的利己主义,把“按照自己的意欲保护自己的本性自由”说成是“做自己认为对于保全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认为“保全自己生命”总是与“做有利于他人之事”相互对立的,结果将利他的动机排斥在“人人自利”的“自然法”之外了。至于心理利己主义否定利他主义的种种论证,并没有从霍布斯落入的这个陷阱里走出来,所以才依然建立在“人人只关注自己利益”的基点之上。
然而,直面现实很容易看出,这类曲解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在遵循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从事行为的时候,既能把那些只是单纯对自己有利而与他人没有直接关联的好东西当成自己意欲的善来追求,也能把那些对他人有利的好东西当成对自己也有利因此自己也意欲的善来追求——或者说把对他人的好(满足他人的某些需要)也当成对自己的好(满足自己的利他需要)来意欲,从而在自利(self-interested)意愿中互不排斥地将利己(selfish)与利他(altruistic)这两种指向不同的行为动机兼收并蓄。换言之,元价值学意义上的自利人性本来就是把利己之善与利他之善一并当成“自我利益”来意欲的,根本没有在它们之间设置某种势不两立的二元架构。无论如何,像下面这类蕴含在自利意愿中的利他动机及其引发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生在世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现象了:我觉得榴莲好吃,因而希望身为朋友的你也能享受它的美味,于是出于这一动机(并非为了卖掉自己的积压货物)鼓励你品尝它,甚至不惜自己花钱买一个送给你,并且没有打算想要得到你的对等回报,从而体现出连霍布斯也承认的“为他人好”这种“善良的自然人性”。
细究起来,导致西方学者面对如此简单的人生现象犯下如此低级的逻辑失误的一个直接原因,可能是他们未能在最广泛意义上理解人性逻辑的自利之“利”,而倾向于将其限定于自己在实利领域里意欲的“单纯对自己有利”,却把自己在道德领域里同样意欲的“对他人有利”排除在外了。例如,与休谟相似,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处曾指认了利他之心是普遍性地包含在自利意愿中的:“无论我们假定人是怎样地自私,在其自然本性中都明显有某些原则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把他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虽然除了看到他人的幸福感到高兴之外自己一无所得。……即使最残忍的恶棍和最冷酷的罪犯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感觉。”[7](P5)可是,大概是由于把“利”狭隘地理解成了实利,斯密并没有将“看到他人的幸福感到高兴”的利他因素也看成是一种与“因为自己的幸福感到高兴”的利己因素相似的自利意愿,反倒基于前者除了让自己高兴之外“一无所得”的理由把它排除在自利的意愿之外,未能意识到“看到他人的幸福感到高兴”正是利他之心构成自利意愿的内在要素的直接体现:一个人把他人的幸福也当成了自己同样意欲、实现后同样能让自己快乐的好东西来追求(为他人的幸福感到高兴),至于自己在实利领域的一无所得并不会因此就把这种道德领域的快乐之“利”化为乌有。就此而言,斯密可以说是在已经触摸到事实真相的那一刻,又在二元对立架构的影响下,让事实的真相在概念不清中从手边溜走了。
那么,人们在自利的意愿中为什么会形成利他的动机呢?只要如实理解了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抛弃了片面扭曲的二元对立架构,回答这个貌似棘手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其形成机制与利己动机的形成机制根本一致:如同人们在一己性的个体生活中会产生利己的需要一样,他们在人际性的社会生活中也会产生利他的需要,从而或者基于生理的本能或者源自后天的教化或者凭借两者的结合产生利他的动机,以维系自己与他人在各个领域尤其是道德领域的共同存在。例如,父母对子女的“为你好”的利他性关爱,既可以上溯到许多动物养育幼仔的生理模式那里,又受到了人类文明的教化熏陶。再如,基于利己性自爱以及利他性亲子之爱的延伸扩展,人们同样也会产生爱友邻、爱同胞、爱人类的更广泛动机,甚至最终结晶成“让世界充满爱”的理念。
有鉴于此,哪怕考虑到被利之他做出回应的复杂程度(如你因为极度厌恶榴莲味道的缘故,觉得我的推荐是“好心办坏事”等),我们也没有理由像霍布斯那样以走极端的口吻断言,人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欲去做对自己有利事情的自然法必然导致“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只有基于利己的动机签订了转让自然权益的理性契约,才能防止毁灭性的丛林状态。相反,由于利他动机同样构成了自利意愿的组成部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在包含无可否认的冲突一面的同时(霍布斯的学说主要彰显了这一面),还包含着无可否认的和谐一面:不仅我有可能从事有利于你满足需要、维系存在的行为,你同样有可能从事有利于我满足需要、维系存在的行为。所以,人生在世在不断发生“许多人对许多人的战争”的同时,也会存在“许多人对许多人的关爱”,绝无可能形成“每个人对每个人像狼”的局面——其实就是在自然丛林(而非人们构想)的狼群里,每只狼虽然对猎物很“残暴”,彼此间却依然会维系某种协同互助的团结友谊。严格说来,指出了人也有“为他人好”的“善良人性”的霍布斯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坦率承认:“就具体个人而言,人人相互开战的状态任何时候都不存在。”[1](P96)不过,或许是想要维持理论上的自洽一贯,他既没有指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符合自然法的“反常”现象的原因,也没有察觉到他自己从自然法到契约论的推演因此留下了怎样的逻辑漏洞。更遗憾的是,西方主流学界似乎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霍布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依据所谓“自然法”指认的只利己不利他的“自然人性”,实际上既不“自然”也非“人性”,反倒包含着基于“文明”的严重扭曲。
综上所述,利他动机在人类生活中的实然性存在其实是无法否认的。相反,一旦打破了那种子虚乌有的二元对立架构,我们很容易发现:利他的动机与其说是和自利的人性背道而驰的,不如说如同利己的动机一样也是顺性而为的。
三、利己与利他的冲突和权衡
在肯定了利他动机与利己动机在自利意愿中的共同存在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实然性描述的视角辨析二者之间既冲突又和谐的复杂关系,由此揭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生成机制了。
比较而言,二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要简单一些,集中表现在:人们能够互不妨碍地实现自己意欲的利己之善和利他之善,在许多情况下达成了某种善还会有助于达成另一种善。例如,我对你的尊重惠助得到了你的善意回报,让我也在某些方面获益匪浅;你基于利己的赚钱动机获得了大笔财富,能够让你积极实现利他的慈善意图等。再如,斯密在把经济行为解释成单纯基于主观利己动机而只是出乎意料地达成了客观利他后果的时候,就忽视了经济行为可以具有伦理德性的关键一点:经营者虽然受到了发财致富的利己动机的支配,但同时也怀有积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利他动机,并且在两者的和谐统一中凭借利他之善的工具效应,实现了利己之善的最终目的。同时,如同人际关系中的类似情况一样,虽然我们不应当像霍布斯那样在理论上一笔勾销这种和谐关系的实然性存在,在实践中却的确没有必要为它操心费神,因为它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麻烦。不管怎样,倘若利他与利己之间不相抵触,没有谁会想要放弃其中的任何一种善:鉴于两种好东西统统属于可欲之善的自我利益,既然可以兼得,何乐而不为呢?
人们在这方面遇到的实践和理论上的麻烦,主要来自利己与利他之间不可兼得的张力冲突:虽然二者对人们来说都是可欲之善,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法同时实现,比方说你在把利他的动机变成利他的行为时,就要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或金钱,从而造成你自己的损失;要是我在竞争中为他人提供了赢利的机会,我自己就可能会失去赢利的机会等等。就此而言,利己与利他这两种自利之善之间的张力冲突,构成了一己个体通常遇到的“诸善冲突”的典型表现(在道德领域里尤为突出),并且因此会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有得必有失”的取舍选择,结果生成所谓“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要是为了利他放弃利己,就会在让他人获益的同时导致不想受害的自己遭受损害;要是为了利己放弃利他,又会在让自己获益的同时导致自己不想加害的他人遭受损害,从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说穿了,人生在世的所有不顺心之事,都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冲突而非和谐的原因造成的:“既要……又要”的圆满愿景无疑是十分浪漫,实现了更属于心想事成的美梦成真,但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注定了只能是乌托邦式的镜花水月。
在这类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冲突情况下,人性逻辑的另一条原则“取主舍次”就将发挥效应了:面对两种好东西不可兼得的局面,人们会把哪一种善看得更重要,以致为了防止失去它势必生成的不可接受之恶,不惜放弃另一种次要善并且因此忍受对应的次要恶呢?[9]例如,要是在权衡比较了两种好东西在质上的主次轻重之后(并非西方学界所强调的在量上的大小多少),我认为利己之善的重要性超过了利他之善,我就会做出为了利己放弃利他的选择,亦即为了不让自己遭受损害而让他人付出遭受损害的代价;相反,倘若你觉得利他之善的重要性超过了利己之善,你则会做出为了利他放弃利己的选择,亦即为了不让他人遭受损害而让自己付出遭受损害的代价。不错,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远为复杂,像许多时候人们的权衡比较并非总是凭借工具理性的清醒计算展开的,也有可能是在人生理念积淀下的一时冲动中完成的;张三在对待李四的时候把利他置于了利己之上,在对待王五的时候又把利己置于了利他之上,等等。但不管具体的场景如何纠结变化,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总是贯穿其中的,就像它在一个人面临当下偏好与长远利益、感性欲情与理性目标的类似冲突时也会起作用一个样。
表面上看,为了利己放弃利他的自利选择似乎比较容易理解;相比之下,要澄清为了利他放弃利己的自利机制,却好像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这样的取舍不仅仅是利他,而且同时还包含着“害己”的因素,在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他人的情况下尤其会陷入某种自相矛盾:要是你连自然法特别看重的自己生命都失去了,怎么还能谈得上是“自利”的呢?但深究起来,这种困惑仍然受到了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没有看到人们在做出后一类选择的时候,只不过是把自己意欲的利他之善置于了自己虽然同样意欲、地位却不如前者那么重要的利己之善乃至生命之善之上,所以根本没有违反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自利人性:他们把利他看成是比利己或生命更重要的自我利益。事实上,在单纯基于利己动机从事的行为中也会出现类似的自相矛盾:人们在酗酒抽烟或深山探险的时候,也是在冒着失去自己生命的危险,但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的这类行为因此就违反了自然人性而不再是基于自利意愿的了;毋宁说,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意欲的酗酒抽烟或深山探险之善看得比单纯维系生命之善更重要罢了。从这个角度看,霍布斯主张“自然法……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对于保全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已经包含着“自己生命至高无上”的规范性片面扭曲了。
进一步看,撇开现实中也存在的“害他”动机不谈,严格意义上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不会在单纯基于利己动机从事行为或利己与利他保持和谐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单纯基于利己动机从事行为而不涉及他人的情况下,不管一个人是把酗酒抽烟看得更重要还是把身体健康看得更重要,他的行为都只是单纯“利己”的,谈不上与“利他”的对立冲突,因此也没有以“利己”为“主义”的内涵;在利己与利他保持和谐的情况下,一个人从事的行为则总是呈现出鲜明的“互利主义”特征。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只会在两种动机相互冲突的时候产生:在无法兼得的两难困境中,人们再去期盼美美与共的“圆满之好”就没有意义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考虑如何达成“正当之对”的问题,试图按照“放弃次要善以确保重要善(基本善)、忍受次要恶以防止严重恶(基本恶)”的行为底线克服二者的张力,最终得出利己与利他哪一种善才是自己认同的为“主”之“义”(“主要义务”)的不同结论:为了利己放弃利他自然就是利己主义,为了利他放弃利己则无疑是利他主义。换言之,按照利己主义的行为底线,以利己压倒利他是可以接受的,以利他压倒利己是不可接受的,而按照利他主义的行为底线却截然相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如同利己与利他的动机一样,不管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都完全符合元价值学意义上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因此也都是可能的。心理利己主义指责利他主义违反了“自然人性”无法成立,仅仅是因为它执着于二元对立架构将利他的动机排除在自利的意愿之外了,没有看到像为了救助他人不惜舍弃自己生命这样的激进利他主义得以立足的前提依然在于:人们完全可能依据自己的人生理念,在冲突情况下把自利意愿中的利他动机凌驾于利己动机乃至自己的生命之上,从而以利他主义的方式遵循自然人性的内在逻辑实现自己的自利意愿。
应该承认,二元对立架构也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利己与利他的现实冲突,因为假如两者之间总能保持和谐统一的话,它压根就不会产生了。但问题在于,这种架构又把二者之间具体的现实冲突扭曲成了抽象的概念对立(逻辑上就不兼容而相互排斥),断言自利的意愿中只有利己的动机没有利他的动机,结果反倒严重遮蔽甚至干脆否定了这种现实的冲突,在抽去自己立足的现实基础的同时走进了理论上自败的死胡同,无法揭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为什么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关键机制。限于篇幅,在此仅仅简要地分析一下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美国作家安·兰德。她为了提倡“理性的自私”,明确主张“理性的人们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因为只有不会造成冲突的才是理性客观的善。由此出发她宣称,理性的人们可以只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不会伤害到他人,亦即“既不能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也不能为了自己牺牲他人”,甚至认为像人们在危急时刻冒着一定风险救助陌生人这类明显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也属于利己主义的范畴[10](P17-21、36-46)。毋庸讳言,凭借这种混淆概念、漏洞百出的论证,当然可以让自私或利己主义升华成某种德性了;但问题在于,假如为了陌生人的利益不惜让自己冒风险的做法也有资格算是利己主义的话,人生在世哪里还可能存在她指责的那种应当贴上“道德食人主义”的骇人标签的利他主义呢?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他曾试图凭借分析哲学的严谨方式,通过与审慎德性的类比以论证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但奇怪的是,他不仅在讨论审慎德性的时候很少深入探究当下偏好与长远利益的冲突,而且在讨论利他主义的时候也很少深入探究利己与利他的冲突,反倒声明自己在考察“利他的理由体系”时,“把所有涉及到分配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相互权衡的问题放在了一边”。结果,在二元对立架构的积淀性影响下,内格尔也将自利与利己混为一谈,一方面把利己主义片面地定义成“行为理由的唯一来源在于行为者的利益”,没有看到利他的动机也能构成“行为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空泛地宣称:作为行为的理性要求,利他主义可以从“不涉及他人利益就能说明的形式化原则”中推演出来,主要“依赖于对他人实在性的全面认识”,却与行为者的利益等感性的欲望情感没有多少关联[11](P86-96)。就此而言,内格尔其实只是笼统地指认了利他动机是怎样从“自己和他人都是人”的形式化理性认知之中生成的,并没有深入揭示与利己主义相对而言的利他主义如何可能的真正理据:人们在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现实冲突中,基于自利的本性展开了权衡比较,最终赋予了利他的动机比利己的动机更重要的“权重”。
因此,单从这两个案例已经可以看出,一旦执着于二元对立架构而不愿正视利己与利他的张力冲突以及权衡比较,很容易把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人人都应当更看重利己或利他之善)等同于利己或利他的动机本身(人人都有利己或利他的自利意愿),结果不仅扭曲了利己与利他动机的互动关系,而且也难以揭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产生根源和实质诉求。
四、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属性
既然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同样符合元价值学层面的人性逻辑,它们在有没有人性方面的二元对立可以说就不复存在了。那么,从实然性描述的角度看,它们在有没有德性方面的二元对立是不是有根有据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本来,假如利己与利他能够维系完美的和谐状态,彼此间不存在任何冲突,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它们在道德领域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将只有正面价值,没有负面效应了。但这样一来,道德自身也就变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人们在这样的和谐状态中不会产生道德方面的任何需要:既然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是不道德的,干嘛还要劳神费力去追求有道德呢?所以,撇开现实中存在的害他动机不谈,只有当利己和利他在冲突情况下产生了害己或害他的悖论性后果时,它们才可能在不道德的负面反衬下呈现出有道德的正面价值。就此而言,抓住利己与利他在诸善冲突以及人际冲突的状态下对于主体和他人分别具有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效应,构成了我们如实揭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复杂道德属性的关键;相比之下,西方学界恰恰又是由于凭借抽象概念上的二元对立否定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冲突的缘故,分别给利己与利他贴上了不道德与有道德的僵化标签,才扭曲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具有复杂道德属性的本来面目。
先来看利己主义的情况:一个人如果在冲突中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他自己一般会认为这样做是合乎道德的,否则他也不会在权衡比较之后依然想要从事这个利己主义的行为了。不过,受到这个行为伤害的人以及许多奉行利他主义原则的人,却通常会认为它是不道德的。更有反讽意味的是,要是就受害之他这方面看,如果他们也奉行利己主义的原则,肯定会凭借自己受害的理据对于这个利己主义行为做出否定性的评判(虽然他们对于自己从事的伤害他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不会做出这样的评判);相比之下,倘若他们持有利他主义的态度,反倒有可能容忍这个行为对自己的伤害,不对它做出否定性的评判,有时还会以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态,认可甚至赞许这个行为对自己的伤害。就此而言,恰恰由于现实冲突所导致的悖论性交织的缘故,同一个利己主义的行为对于不同的人也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道德属性,没法得出一刀切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看,像安·兰德那样声称利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德性,只能建立在一个错谬的前提上:以无视冲突的方式声称利己主义行为根本不会导致“为了自己牺牲他人”的后果。然而,当德里克·帕菲特把利己主义界定成“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应当赋予自己的利益以至高无上的权重,其他人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足惜”的时候[12](P281),他已经指出了关键的一点:利己主义行为在实现主体自己的利益时肯定会让他人付出受害的代价,而这也正是利己主义者们在奉行同一条伦理原则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彼此开战处于丛林状态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像休谟等人那样断言利己的行为根本缺乏道德价值或违反了正义,也是片面的。问题在于,倘若我们把他们不约而同地指认的“不可害人”原则看成是一条适用于每个人的正义标准的话,那么,一个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应得利益不受他人侵害的举动,虽然在元伦理学层面上也属于将利己凌驾于利他之上的利己主义行为,并且还会妨碍实施侵害行为的那个(他)人达成其不应得的利益,以致有可能被某些人特别是施害之他贬斥为只利己不利他的不道德,但如果从尊重人权的规范性视角看,却是完全正义和符合道德的。例如,张三在禁烟场所出面制止李四抽烟以保护自己的健康,虽然也是一种阻碍了李四满足自己抽烟的需要或利益的利己主义(而非利他主义)举动,但同时又是捍卫自己正当权益的正义行为,并不会因为具有“损(他)人利己”的元伦理学特征就失去了积极正面的规范性道德价值。再如,商人为了自己长久赢利做到了童叟无欺,不仅在当下偏好与长远利益的冲突中克制(而非放纵)了利己的动机,同时也在自己致富与尊重他人的冲突中守住(而非突破)了不可坑蒙拐骗的正义底线,因此具有不容否认的真正道德价值。事实上,康德断言这类利己的行为尽管值得称赞,却又缺乏道德价值,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倘若它们原本不具有“不会伤害任何人还帮助了某些人”的正面价值,人们凭什么要在道德上称赞它们呢?难道人们在道德上称赞它们的头号理据,不就是因为它们符合康德自己特别强调的“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吗?从中不难看出,一旦受到了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就连康德这样严谨的思想家也会像安·兰德那样陷入莫名其妙的逻辑错谬之中。
再来看利他主义的情况:一个人如果在冲突中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不仅他自己和被利之他,而且其他许多人(包括某些自己不愿从事利他主义行为的利己主义者),通常都会认为这种宁肯害己也不害他的做法在道德上是高尚的。这也是“舍己为(他)人”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受到广泛赞许的机制所在,以致就连把利他主义贬为“道德食人主义”的安·兰德也不敢与人们的这种日常直觉正面对抗,而不得不把冒险帮助陌生人的行为划归利己主义的范畴给予肯定。不过,撇开另一些利己主义者很可能嘲讽利他主义行为属于犯傻的现象不谈,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其他许多人同样会对这类行为做出歧异性的伦理评判,从而展现出利他主义在人际冲突中具有的复杂道德属性,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像休谟等人那样,一概而论地断言它们总是高尚优越的有德性行为。
第一,倘若被利之他并不认为某个利他主义行为的后果对于自己具有可欲之善的价值,那么,在他看来这个行为就不见得是有道德的,相反还可能是不道德的。像子女有时会反感父母出于“为你好”的动机从事的关爱举动,就折射出了利他主义“好心办坏事”的这种悖论性特征。
第二,倘若一个人的利他主义行为让自己受到了严重伤害,哪怕他自己认为这样做具有“舍己为(他)人”的优越德性,也还是有可能被另外某些人视为不道德的。例如,张三对李四百依百顺到了甘愿受虐的地步,从元伦理学视角看当然也可以说是利他主义的:自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也要让李四感到满意;可是,许多旁观者却会觉得张三的这种利他主义行为类似于放弃人格尊严的奴才。刚才提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现象,不妨也作如是观。
第三,倘若一个人的利他主义行为在有利于某些他人的同时又伤害了另一些他人,更是会因为这种“利此损彼”的悖论性特征在道德属性上发生致命的断裂:一方面被利之他会认为这个行为是有道德的,另一方面受害之他却会认为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以斯密举出的恶棍和罪犯为例:他们对于自己团伙中人的无私奉献、倾情关爱当然会受到后者的赞许,但遭受这些团伙不义侵害的其他人,对于这类“盗亦有道”的利他主义举动却很可能做出相反的评判。
无需细说,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远比刚才辨析的几种类型复杂纠结得多。不过,撇开其中的哪一种具体评判更能得到证成的应然性话题不谈,上面的讨论足以提醒我们:无论在实然性描述的维度上,还是在规范性诉求的维度上,我们都没法给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贴上某种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伦理标签,断言它们单纯因为利己或利他的特征本身就是不道德或有道德的。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在利己与利他问题上的致命失误在于,由于没有仔细辨析自利的内涵而将它混同于利己却将利他排除在自利之外,结果在强调利己与利他之间子虚乌有的概念对立的同时,又遮蔽了二者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无从回避而且意义重大的现实冲突,最终通过这种把不可兼得的现实冲突扭曲成互不兼容的概念对立的逻辑谬误,制造了利己主义“有人性无德性”而利他主义“无人性有德性”的怪诞悖论。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打碎在人性和德性维度上都不存在的二元对立架构,另一方面正视利己与利他之间复杂纠结的现实冲突,才有可能克服这些理论上的怪诞悖论,澄清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产生根源和实质诉求。事实上,不仅在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事实与价值、善与正当、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都能发现类似的情况:西方主流学界由于执着于抽象概念的二元对立架构,无法澄清它们的语义内涵,往往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难理解的日常现象神秘化,结果将它们变成了众说纷纭的千古之谜。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打破对于西方哲学的盲目崇拜,凭借严谨细致的学术批判,深入揭示西方著名哲学大师也免不了会陷入的种种悖论,找到这些千古之谜的谜底,为人类哲学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贡献。
[注 释]
①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在引用西方译著时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有所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