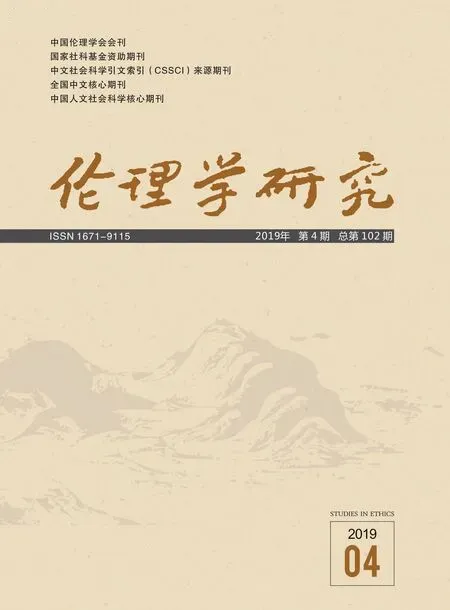论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
聂文军
一、什么是个人偏好
个人偏好或个体偏好(individual preferences)是个体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呈显出来的、对某些事物或某种活动的喜爱或喜好。“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罗卜白菜所有所爱”,由此可见个人偏好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或时代都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源越来越丰裕,消费者的各种非经济偏好如审美偏好、情感偏好、道德偏好等就会越强烈。”[1]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个人偏好不仅在其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消费偏好、投资偏好、风险偏好等)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且在个体参与的政治生活中也得到了较明显的体现(被称为政治偏好、选举偏好、政策偏好等);在文化、体育、娱乐和休闲生活中更是呈现出了不同个人对不同事物的各自偏好。
个人偏好是个体差异性——由个体认识与情感喜好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一种表现。在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变化和发展缓慢以及社会流动性缺乏的历史条件下,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简单、内容贫乏,人们只能在极其有限的选择范围内作出选择,从而使得个人之间的偏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不是十分明显。进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近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日益突破传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限制,使得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或加深。人们进行选择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以及做出选择的对象范围都大大拓展,在个人主义及自由理念的驱动下,不同个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个人偏好得以极大地凸显。
从法学的观点看,社会组织是拟人的。具有与法律上个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本文关于“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的观点也适用于法人、专业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慈善活动。
二、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
什么是慈善活动?简言之,慈善活动即做慈善;宽泛地说,就是指人们在道德上做好事或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慈善活动”则有着严谨的界定,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下列公益活动:(1)扶贫、济困;(2)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3)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4)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5)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6)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可以说,慈善活动广泛全面地囊括了个人与不同社会组织各种具有善的性质的行为。
个人偏好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十分自然地体现在其道德生活实践中;甚至有学者把道德视为个人偏好的表达,“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具有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特征而言,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2](P14)作为道德认识的判断都具有作为偏好呈现的特征,人们在其道德认知或道德理念指导下(指引下)的道德活动或行为自然也具有相应的偏好特点。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看到在现当代社会的道德生活领域中存在着丰富多样的个人偏好现象。
所谓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即个人在道德上的偏好,是指个人在慈善活动中——个体做好人好事的行善中——呈现出来的对某些善行善事的偏爱、喜爱或爱好。虽然慈善组织、企业家或慈善家、普通民众在面对突然的、重大的自然灾害事件时,都会表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同道德情怀和道德支援;但在其日常的道德实践或慈善活动中,他们却呈现出显著的各自不同的个人偏好。
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正如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偏好一样也是普遍存在的。有人喜欢救助孤寡老人,有人喜欢照顾儿童;有人喜欢动物保护,有人喜欢自然环境的保护;有人喜欢捐资助学,有人喜欢捐助体育;有人喜欢锦上添花,有人喜欢雪中送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慈善活动中的偏好特征不仅在作为自然人的个体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慈善活动中得到了体现。不同性质的法人和不同的专业慈善组织在其各自的慈善活动中都表现出了各自对不同慈善活动的专注与侧重,也就是说,它们的慈善活动具有各自不同的偏好。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对个人而是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通过它们的活动来促进人类的健康;国际红十字会主要着眼于战伤救护(先发展为广泛的自然灾害救助和医疗救护等);卡耐基基金会把图书馆和学会的建设作为其慈善活动的最佳选择;世界自然基金会(原名“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专注于全球濒危物种的保护;“无国界医生”组织救助世界各地需要医疗救助的民众;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旨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如此等等。因为只要个人在道德上呈现出各自的个人偏好,由个人或不同个人共同创建的法人、慈善组织等等自然也会受到创建者的价值倾向、情感因素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在慈善活动中的偏好特征。
三、如何看待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
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慈善活动逐渐进入我国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众多社会人士的慈善活动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特别是著名企业家、社会名流等——的一些慈善活动受到人们的质疑。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当天,由著名企业家王石执掌的万科企业捐款200万元人民币就被很多人指责捐款太少;201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耶鲁大学读书一年的张磊事业有成后向耶鲁大学捐款888万美元,因未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款而被指“忘恩负义”;2014年7月,潘石屹向哈佛大学捐款1亿美元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如此等等。为什么做好事善事的人不仅没有受到人们的赞扬反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或责难呢?网络时代的道德舆论场人人可以发声,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普通人和企业家们(慈善家)作为个人偏好的慈善活动呢?
1.尊重和肯定慈善活动中的个性化选择
任何道德判断或道德评价都必须立足于该道德事件所处的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依据。
从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来观察,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则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应当说都大致经历了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经济的近现代社会的演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更是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当代社会显著的突出的共同特征。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当代社会采用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使得生活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接受和践行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体育、娱乐休闲等等社会生活中均表现出各具个性、各具特色的言论与行为。同样,人们在道德生活中也是如此。任何人、每一个人只要不违背社会的道德底线或底线伦理,只要不去伤害或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都可以按照他们各自的价值判定和情感偏好去做慈善,去做好事善事。这是由现当代社会的基础性价值的自由理念——当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理念——所决定的。
人们的道德生活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商品经济的生产、竞争、贸易、择业等等方面的自由要求必然渗透和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然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的和基本的价值理念。人们在道德领域的慈善活动也像在其他领域中的活动一样,成为人们可以依据个性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条件下每一个人都必须履行的义务。
生活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在遵守法律和社会底线伦理——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条件下拥有广泛的和全面的自由。道德自由无疑也是人们自由的重要内容,所谓道德自由即行善的自由,是做好事、善事,做慈善活动的自由,一个人做怎样的好事善事、做怎样的慈善活动、做多少好事善事、做多少慈善活动、做多大的好事善事、做多大的慈善活动,都是每一个道德行为主体——包括各类慈善机构或慈善组织——的个人权利,我们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或社会舆论的手段去逼迫、强迫或强制任何一个人去做好事或慈善活动。在现当代社会里,不同个体在慈善活动中呈现出十分显著的个性化选择,是由各个个人的家庭出身、经济条件、教育程度、道德理性能力、情感偏好、风俗习惯等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充分尊重和肯定每一个体在道德实践领域中的个体性、多样性、独特性的选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各种客观条件使然。
人们的道德态度与道德判断必须与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相一致。当我们对他人的慈善活动——如捐款数量、捐款次数、捐款对象等等——感到不满,甚至予以指责或责难时,这实际上侵犯、干涉了他人的道德自由,侵犯了他人做慈善、做好事善事的自由。这是与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自由——相违背的。因此,一个人只要作出了慈善活动,我们就不能以自己的认识或社会的要求等等为由予以干涉或指责。从正面的积极的视角来看,不同个人在慈善活动中的不同偏好,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确实各自满足了他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道德需要,因而理应得到社会的肯定与尊重。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3](P61)。一个人对特定道德事物或道德活动的偏爱或喜爱,既对他人和社会有益,也对道德实践者有益,如果道德实践者以此为乐,无疑会大大激发其道德积极性。在现当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只要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在做慈善活动,在做好事善事,每一个人以及社会舆论就不能只是按照该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最崇高的道德境界去整齐划一地要求具有现实道德水平差异的每一个人,而是要立足于每一个人当下所做的慈善活动、好事善事来予以必要的肯定和赞扬,这既体现了对个体道德自由的肯定与尊重,又有助于个体道德积极性的更进一步发挥。
2.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不能妨碍或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
在当代社会极其多样复杂的条件下常常会出现诸多矛盾。道德生活领域中的个人偏好因其强烈的认知因素、价值因素、情感性等等因素也会使得慈善活动与他人的社会正常活动产生冲突。因慈善活动的个人偏好引发的问题引人深思,我国2011年的“拦车救狗”事件最为典型。
2011年4月15日,一些特别爱狗的人士和动物保护志愿者在京哈高速公路张家湾收费站“拦车救狗”。当天中午约12点,在京哈高速张家湾收费站附近,一辆从河南出发开往吉林的载有520只待屠宰狗的卡车被爱狗人士拦下;当时经警方和动物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车持有真实有效的检疫运载证明,运狗车证照、手续齐全,属于合法运输和经营,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扣车。但爱狗者却拒绝放行。不少志愿者和公益组织获知消息后前往事发地点;现场有50余名志愿者和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等10余个公益组织。毫无疑问,这一事件鲜明地呈现了那些动物保护志愿者在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但他们的活动却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和谐。
一些人对狗有特别的偏好、有特别的喜爱,这是他个体偏好的表现,爱狗、收留照看流浪狗也无疑是爱心之举。但个人偏好的慈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逾越法律的约束,不能妨碍、妨害他人和社会组织正常合法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
2011年的“拦车救狗”事件之后类似事件仍时有发生,2014年广西玉林狗肉节期间发生了爱狗人士与餐饮店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争执与冲突;我们也看到不少成长中的少年就时常因各自所好的影视偶像各异而相互争吵甚至严重冲突。从理论层面来看,很多个人往往会因自己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所好与道德生活中的所好而蔑视、指斥甚至阻碍或禁止他人之所好。这些事件都启发和警示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他人理解与尊重我们之所好,我们也理应理解与尊重他人之所好;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在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而妨碍、妨害其他个人(社会组织)在日常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正当合理的活动和法律上的合法行为。不同个人在慈善活动中的不同偏好,可以并行而不悖,共同有益于整个社会的道德。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对某一慈善活动的喜爱或偏好而要求或强迫他人也喜爱或偏爱这一慈善活动。任何个人在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都不能妨碍或妨碍其他人(社会组织)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展开其合法活动的正当权利。
3.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应予以引领和提升
从观念的字义的层面和从现实的层面辩证地考察,我们都可以发现,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是利弊并存的。从字面看,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piān hào),对道德事物有所“好(hào)”当然对社会有益,是“好(hǎo)”的;“偏”又意味着有所选择,有所为(只做个人感兴趣的道德之事)有所不为(个人对其不喜欢、不感兴趣的道德之事则予以不顾),这当然在道德上是有不足、有缺陷的。孔子多次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P92)孔子所期望或希冀的不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有限的道德事物或慈善活动的喜爱或偏好,而是人们对整个道德或道德本身的喜爱或热爱,是“见善如不及”的全面的道德行为。从现实层面来看,一方面,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呈现出强烈的和丰富的个体差异性,这固然体现了千千万万不同个人在道德上的自由并造就了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的丰富多彩,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与积极性,有益于他人与社会;另一方面,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又会因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道德认识的局限性、情感的执着等等因素而在某些方面存在道德上的不作为以及和他人的个人偏好相冲突,从而有损于他人和社会。从我国《慈善法》所列慈善活动的种类可见慈善活动所包括的范围之广泛与全面,社会与他人在道德上有待他人援手的道德之需是十分多样的。因此,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需要通过社会的道德教育予以引领和提升。
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需要得到引领和提升,还可以通过深入到社会的内部予以考察来得到阐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生活其中的千千万万个人组成的。从共时性(横向)视角来看,构成任何一个社会的众多个人——从一岁的婴幼儿直到百岁及以上的耄耋老人——无疑存在着个体的代际维度(三代、四代、五代不等),这些处于不同代际的个人共同生活于同一社会之中,他们的道德态度、倾向与实践方式自然会呈现出不同代际的个人偏好差异。廖小平教授认为,道德价值观的代沟与沟通问题是代际伦理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现代与传统、国内与国外等各种道德价值观被浓缩到同一个时空并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激荡,它们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在同代的各共同体之间,而且越来越表现在代与代之间。因此,必须分析产生代与代之间道德价值观差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创造道德价值观代际沟通的条件,建立道德价值观代际沟通的机制,探寻道德价值观代际沟通的规律。”[4]处于不同代际的个人偏好不仅体现在诸多日常活动中,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的道德活动中。“上一代通过道德示范和灌输等实现对下一代的道德教育,而下一代也通过文化‘反哺’等形式对上一代产生影响。”[4]不同代的个体之间通过代际伦理的相互作用来促进和实现各自的道德变化、发展和提升。从历时性(纵向)视角来看,根据美国当代著名道德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道德发展心理学理论所得出的实证结论,每一个体的道德状况在其一生中会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每一个体的道德状况由其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思维能力)所支配和主导,随着其年龄、心理、认知能力、情感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科尔伯格为此把每一个体的道德成长发展历程概括为“三水平六阶段”[5]。构成社会的千千万万个人的道德既具有共同性又呈现出差异性。因此,我们既需要尊重不同个人的道德差异与个人偏好,又需要引领和提升不同个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境界。如果众多个人不能得到有效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引领,其个人的道德发展就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个人之间就会产生诸多道德上的对立或冲突。
用什么来引领和提升一个社会中千千万万不同个人在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呢?当然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提升作为个体的广大社会成员。我国社会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于我国社会的实际,我们需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根本原则。本来,“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是先进性与广泛性的有机统一,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我们错误地把“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看作高高在上、普通人遥不可及、无法践行的东西。“在今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顾全大局、先公后私、爱岗敬业、办事公道是为人民服务,同志间、师生间同学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为人民服务,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贫帮困、扶残助残也是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诚实劳动并获取正当的个人利益同样也是为人民服务。”[6](P108)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革新与进步,“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性与广泛性、崇高性与通俗性、层次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与教育界在理解和宣传上的普遍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党和全社会的共识。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的全方位体现,是为人民服务在多领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规范(价值准则)的具体化和具体体现。普通个人既有充分的道德自由以践行其在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又能在以“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中心)、价值目标和价值规范的教育与影响下,不断扩大其道德活动、慈善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
谁来引领和提升千千万万普通个人的道德呢?使普通个人在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在范围上不断扩展或扩大,从而在整个道德水平道德境界上不断提升呢?当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和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系为人民服务。忧人民之所忧,乐人民之所乐。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下,在弘扬正能量的社会舆论熏陶下和抑恶扬善的相关制度保障下,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实践一定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总的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我们既要充分尊重和肯定千千万万个人在慈善活动中的个人偏好,又要求各个个人不能因此而妨碍或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既尊重自己和他人在慈善活动中之所好,不以己之所好强加于他人。我们追求共同的美,也追求各自的美;我们追求共同的善,也追求各自的善。我们既要允许人们、“各善其善”“各美其美”,彰显其美的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个性和多样性,又能“善善与共”“美美与共”,共同构建社会的道德和谐与整个社会的和谐,走向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我们既要看到慈善活动中个人偏好的正当性与积极性,也要看到其蕴含的消极性与局限性,希冀和引领每一个体从慈善活动的个别的、局部的“所好(hào)”走向孔子所向往的整体的全面的“好(hào)德”、“好(hào)善”,积极接受以“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和中心的价值引领,在愈益完善的制度建设保障下不断提升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真正成为一个既尊重个人意志自由,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道德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让个人有所依归的和谐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