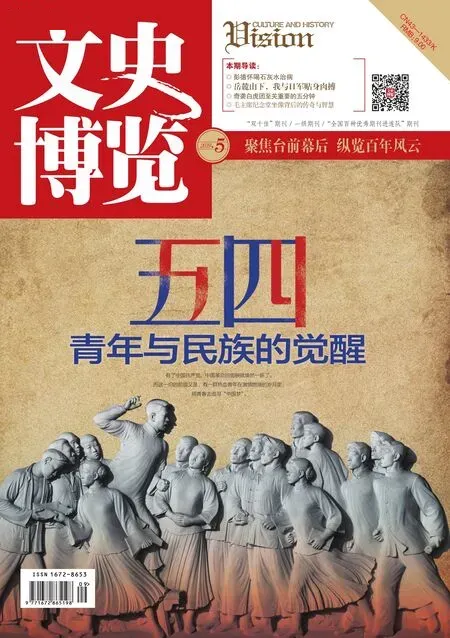胡适与梁启超的两次交锋
梁启超大胡适18岁,是胡适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启蒙者。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在各方面得益于梁启超的经过,承认“自己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但胡适对梁启超仍抱着十分敬重的态度。
1918年11月20日,胡适借赴天津演讲之机,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充满敬意、企望谒见一面的信,“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但直到第二年的3月21日,胡适才“初见梁任公”。此后,两人开始正式交往。其间,有对政治问题的交换意见,但更多的是对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进行交流和争论。
胡适与梁启超之间曾发生过两次大的学术交锋。一次是梁启超批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之邀,来到北大三院讲演,题目是《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次讲演一连讲了两天。第一天讲演,胡适因事未出席,但事后看过记录。第二天胡适亲临会场恭听梁启超的讲演。梁启超对胡适这部书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而且措辞犀利,很不客气。梁启超首先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了很高评价,指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然后重点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观方面,什九有很浅薄或谬误。”梁启超讲完后特意留下一段时间让胡适当场答辩。
胡适答辩说:“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上考虑的功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
据曾参加过这次讲演的陈雪屏回忆,当时的会场就像海边上的潮水来回翻涌一样,一开始听众还觉得梁启超讲得有理,但听了胡适的答辩后,又忽拉一片倒向胡适这一边了,“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
胡适和梁启超的第二次交锋是胡适批评梁启超著《墨经校释》。1921年,梁启超将他用了10多年时间所作的《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写了一篇长序。在这篇长序里胡适首先赞扬了梁启超20年前提倡墨子研究的贡献,并说自己就是受梁启超的影响而爱上墨子的。接着胡适本着“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直率地对梁著提了不少批评意见。梁启超听了不太高兴,虽然也赞许胡适这种“极纯笃的学者风度于学风大有所裨”,但在编排书稿时,却一反常态地把胡适的序排到书的末尾,而把自己反驳的文章放在书前。对于梁启超这种近乎孩子气的做法,胡适一笑了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不幸病逝。胡适为梁启超作了一副挽联,高度概括了梁启超的一生:“文字奇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对梁启超的个性有一段非常好的评语:“任公为人最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有人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同时,胡适在日记中也提到过去的那两次学术交锋,胡适说:“任公有时会稍露一点点争胜之心,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