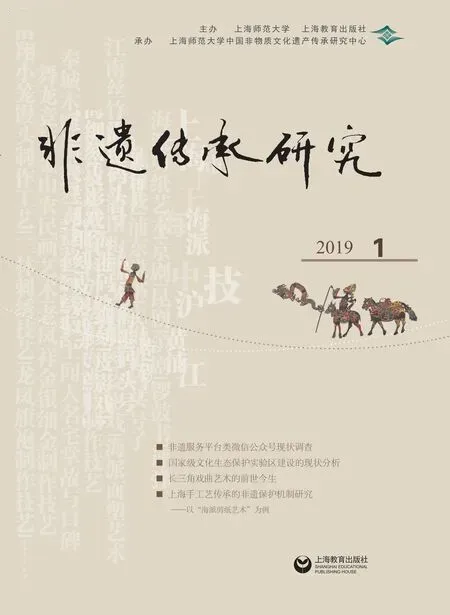都市化背景下节庆类非遗的功能研究
——以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为例
陆辰佳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都市人的精神生活施加了巨大压力,使人们变得世故、冷漠、麻木。同时,全球化也正在消解着地方的独特性,当代许多城市同质化现象严重,建设相似雷同,缺乏个性与特色。然而,只有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展示城市的价值、品味和风尚,才能成为一座城市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作为国家级的节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罗店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是宝山区特色地域文化的杰出体现,是上海市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强有力的人文基础和文化力量之一。
一、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的概况
罗店划龙船习俗始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上海的宝山、嘉定乃至江苏浏河、太仓一带富有盛名。
明代初期,带着龙船基因的雏形的“旱船”和“台阁”就已经在罗店地区出现了。明代中叶,罗店划龙船的形式逐渐演绎为繁华市镇的世俗情态,汇聚了“打招”、吹打、戏曲、雕刻、织绣等众多表演艺术,有“水上行街”之称。
清代是罗店划龙船的活跃时期,不仅全民参与到活动中来,造船匠们也在打造龙船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其进一步独具特色。由于受罗店的地理环境所限,龙船竞渡之争逐渐演化为竞技之争,这也使得罗店划龙船民俗具有轻竞技、重观赏和娱乐表演的显著特征。
此后,由于罗店前后经历了鸦片战争、英军攻打吴淞炮台、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战争、“八·一三”淞沪抗战等,罗店龙船活动也因此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使得仅存的龙船和龙船上的物品都难逃厄运,罗店划龙船习俗也渐渐地走到了濒危的边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状态,罗店龙船浴火重生。21 世纪初,镇政府将罗店端午划龙船习俗逐步恢复,使其成为黄浦江流域内唯一存留的江南端午龙船遗风。2005 年起,罗店镇决定每年举办划龙船活动,并将其定名为“罗店龙船文化节”。自此以后,龙船开始成为罗店的文化品牌,成为罗店古镇形象的特色名片。
罗店划龙船习俗在当代的时代背景下,走上了申遗的道路,并且在各方支持和努力之下形成了一套独有的非遗保护机制。罗店龙船于2008 年以“罗店划龙船习俗”为名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属于民俗类。2010 年上海世博会将当年的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名称改为端午节民俗活动。此后,罗店龙船活动一步步向端午节民俗活动靠拢,创造端午节日文化。
二、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的心理渊源
我国传统节庆最原始的功能是其祭祀功能,随着社会变迁,传统节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功能变化。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的功能演变可以追溯到以下三方面的心理渊源。
1.图腾崇拜
纵观历史,罗店在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之前属嘉定县,嘉定县在春秋时期属吴,战国初越灭吴,遂属越,战国中期楚取越之吴故地,遂属楚。[1]因此,罗店是吴文化的重镇之一,蕴含着“吴俗”的原始基因和文化体系,其文化形态来源于本土的农耕文化。罗店“划龙船”,源起于吴越远古端午龙舟竞渡习俗,在历经了地域环境、文化心理和时代的变迁之后,不断地演化发展而成。[2]
正如闻一多《神话与诗》中载:“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龙船文化来源于对龙图腾的崇拜。已经出土的带有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考古文物显示:新石器时期长江中下游有个被称为“百越族”的崇拜龙图腾的部落,他们有断发文身的风俗,并自称是龙的子孙。长江流域的上古先民出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心理,奉龙为神,将龙的形象刺在身上并刻在舟上,以此想用龙的威慑力驱除所有的灾疫邪祟。
罗店地区的百姓们对龙的崇拜可谓根深蒂固。在明清年间,罗店多次发生地震、水灾、大旱、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使罗店百姓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安放在神龙身上,在民间,龙被视为治水的“吉祥瑞兽”,人们祈求自身获得神龙的庇佑和保护。在罗店人民的心中,福为龙所赐,祸须龙所避,这种崇敬虔诚的心理正是图腾崇拜的体现,出于人类对现实灾难的恐惧和抵御,也是群体感情的宣泻,罗店划龙船就成为了当地民间端午节最重要的活动。
龙船造好之后还要举行“点睛”“立竿”“燃旺盆”“放高升”等一系列的仪式。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火被看作是沟通天地神鬼之间的桥梁,是巫术的“工具”,起到驱避妖魔鬼怪的作用,体现出了图腾崇拜的痕迹。罗店龙船上还要插彩旗、设台阁,这些也是“断发文身”的变相体现。
2.禳灾祈福
民间一直有“善正月、恶五月”的说法。在我国古代,五月也被称为端月,正值江南春夏季节交替之时,从冬眠中醒来的“五毒”开始活跃。此外,五月也是阴阳二气激烈争锋的时候,江南地区气温变化异常、阴雨连绵,正是疾病多发的时段。人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活,便把五月视作“恶月”,而五月初五更是“恶月”中的“恶日”。因此,人们选择在这个日子里划龙船,其目的本身在于禳灾,其初衷就是祈求神灵保佑平安。
罗店成镇之时是一江南水乡,主要种植棉花、水稻及三麦,以小农经济为主,由于土地少、农具简陋,加上缺乏资金,无力施足肥料,农民只能靠天收获。然而这些农作物在连绵阴雨的气候中难以生长,百姓的生存口粮和城镇的商贸经济都因此出现严重问题。
《明通典》载,洪武元年(公元1368 年)朱元璋建都应天(南京)后,即命令江南农村必须种棉花,棉花又须换成大米才能交纳官赋。苛政猛于虎,农民们受两道中间剥削,苦不堪言。于是,他们把棉花、水稻等收成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看作是神龙庇护之因。因此,全镇的百姓都把辟邪驱恶的迫切愿望变成了投入端午节庆活动的热忱。
据史料记载,龙船最早是禳灾的工具,即将不祥之物装载在船上,在顺流直下中将其送走。在罗店龙船的仪式中,“送标”也是其中一环,但过程简化成了一种象征形式,即将带蟾蜍、蝎子、毒蛇、蜈蚣和蜘蛛“五毒”图案的剪纸在“燃旺盆”时投到火中进行焚毁。
3.祭祀先人
龙船的产生与流行也与纪念具体名人、祭祀祖先有关。在众多名人之中,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无疑对世人的影响最大。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有云:“屈原以是日死于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渡,是其遗迹。”楚大夫屈原才华横溢、忠君爱国,但因遭受奸臣的谗言和排挤而不得重用,看到楚国因此灭亡而郁郁不得志,最终在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身亡,楚国百姓十分哀伤,每到这一天便划着船,把竹筒里盛的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人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为包粽子的形式,划的小船改为龙舟。于是,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成为一种端午民俗。其次是纪念伍子胥之说,伍子胥毕生效忠吴国,但吴王夫差听信太宰伯嚭的诽语,称伍子胥施诡计想要托齐反吴,于是派人送伍子胥一把宝剑,令其自刎。相传,夫差把伍子胥的尸首抛入钱塘江中的日子正好是五月初五,百姓们向江中投去食物,目的就是避免他的尸体被鱼吃掉。另有纪念曹娥的说法,孝女曹娥是东汉上虞人,其父曹盱是个巫祝,汉安二年五月初五在舜江中迎潮神伍君(伍子胥)的过程中不幸掉入江中溺死身亡,尸骸不见。曹娥当时年仅14 岁,日夜沿江悲啼找寻父亲,17 天之后也投江,5天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一段神话。后人为纪念她,便改舜江为曹娥江。
罗店地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土生土长的居民,居民都是从各地移民于此,拥有各不相同的祖籍。出于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对祖先前人的怀念,他们把端午节作为祭拜先人的日子,因此对聚众共祭尤为重视。由于各地的祭祀方式不同,加上罗店本身以商业起家,因此罗店的端午祭祀活动是在各种文化的贯通交融中产生了独特的新元素。
三、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的都市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定的社群或族群文化和传统生产生活模式密切相关,它会随着各个社区和群体因适应生活环境而与自然和历史不断互动、不断演变。罗店划龙船习俗作为罗店地区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在当代的社会经济及都市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都市特征和时代价值。只有把握住价值,才能真正认识到该节庆类非遗的历史意义和重要作用。
1.激发集体欢腾,促进社会交往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后期的宗教研究中提出了“集体欢腾”的概念,他强调定期的纪念、公共节庆、大众节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事件确保了不同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不同时代之间的聚合力。[3]在端午节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通过举办罗店划龙船活动搭建一个相互认识、共同交流的平台,把平日忙于繁杂之事的人们聚集起来,通过召唤人们共同参与节庆活动的方式,使他们感受到平日体验不到的热闹景象,从而激发起“集体欢腾”的状态,达到身心愉悦的满足。
每届的端午节罗店龙船文化节历时2—3天,有包粽子比赛、灯谜竞猜、龙船启航仪式、划龙船表演、行街表演、文艺专场演出等十多个项目,全镇有不少于2000 名群众直接参与活动,观摩群众多达30 多万。罗店端午节庆活动通过举办龙船文化节这个契机把大家召集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市民,使大家共同行动,从而激发起一种欢腾的状态,不仅缓解了来自社会、工作、家庭、生活的日常压力,而且还拓宽了市民的社交圈和社交网络,展示出了集体的创造力并使得自己焕发出勃勃生机,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吸引了更多本地和其他地区的居民投入其中,从而达到身心愉悦、暂离日常生活繁琐的共同情感体验。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所谓“人熟是一宝,熟人好办事”“有来无往非礼也”。在当代社会转型期间,熟人社会的成分愈来愈少,而陌生人社会的成分逐渐升高,尤其在大都市之中,人与人的关系网呈现松散、疏离的状态。虽然处在陌生人社会中,但我们也需要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一方面靠官方制度安排和自我的道德约束,另一方面就要主动建立与社区、邻里以及周围人的联系。而传统节日的制度安排就给予了人们这样一个良好的机会去扩大自己的社会圈子,促进人们相互认识与交流,从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保持社会活力,更好地构建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
罗店划龙船习俗当今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将蕴藏在其中的民族精神和地方信仰,通过开展活动的方式传达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以此在活动的当下把平日里松散的个人凝聚成一个有意义的群体,共同沉浸在节日的欢腾之中,从而达到了促进人们社会交往,增强城市活力的目的。
2.重塑文化身份,强化集体认同
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一种“政治动物”,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的人,生活在某种政治秩序或共同体之中,由此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我们将关于社会归属性的意识称为“集体的认同”,它建立在成员们享受、有共同的知识系统和共同记忆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点是通过使用共同的象征系统来实现的。[4]所谓共同的象征系统,可以是拥有共同的语言、信仰、饮食、历史遗迹、节日、仪式等,这些在促进集体认同的过程之中都可以转换成文化符号系统并对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共同性的编码。个体意识要上升到某种集体或文化的同属感,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即集体需要通过一些外部手段将某种个体的归属感植入到一个基于集体的认同中,使其真正成为这个集体的一份子,并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而传统节日、节庆等民俗则可以通过仪式等手段唤起群众心里深层的文化记忆。
“节日和仪式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产生。”[5]节庆类非遗借助庆祝仪式加以重复,通过众多具体节俗和时间节点的周而复始让参与者回忆起相关的意义,并不断强化他们对民族的文化记忆,从而唤醒强大的群体意识和激发集体行为。人们在观看和参与仪式的解释、操练和表演的过程中,强化文化记忆和集体认同,牵引起一种感性的力量。所以说,仪式是文化记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罗店龙船文化节有一系列的禳灾仪式,让人们在体验端午热闹欢腾的节日氛围的同时,感受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禳灾祈福仪式的独特魅力。“立竿”“燃旺盆”“放高升”“送标”“点睛”“接龙”“砍缆—启航”这一系列的划龙船祭祀仪式的存在,使得罗店人拥有了集体复苏文化记忆、确认精神归属的重要时刻。仪式强化了人们对时间的记忆,发挥了一种焦点作用。[6]可以说,罗店划龙船习俗以及龙船文化节是罗店人民重新获取、重拾起罗店地区端午文化记忆的象征物。它确保了不同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和聚合力,触发了罗店人民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层感念。这种认同感不仅包含了浓重的古老农耕社会人们的民俗信仰内容和形式,也包含了当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对国家、社会以及家庭、自身未来的美好期许与盼望。
罗店划龙船习俗,实际上是借助罗店龙船文化节这个文化活动,将停留在文化遗迹和语言文本中的集体记忆,引入到节日和仪式之中,凝聚成共同的文化记忆,并作为一种地方传统延续下来,以防止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记忆的残破与遗忘。
3.构建场所精神,存续乡愁记忆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指出,“空间是通过有意识的人类主体的活动而产生的”,罗店人民的社会实践是罗店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而空间又在整个地域社会之中具有整合的作用。[7]罗店划龙船习俗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不仅与罗店地区空间变化息息相关,也深刻反映了罗店地方社会的变迁以及罗店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演变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每一部分都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地图上的平面分割现在转化成了有自身情感和历史传统的邻里,在这种小地区范围内,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被保持下来,使其区别于其他地方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8]但是现代化却导致了“去地方化”,“空间”和“地方”的关系松散了,全球化导致了“无地方感”或“地方的终结”,流动着的人们无法与地方建立真实的关系。[9]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社区或群体,但如今连接我们的纽带却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纯粹的地理上的划分已经根本无法唤起我们心中深厚的情感。而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却赋予我们建构自身与地方之间联系的机会,通过祭祀仪式、船体装饰、水上表演的重现,居住生活在罗店的人民与罗店地区在情感关系上再次勾连在一起。
挪威建筑学家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提出了“场所精神”。他认为场所是一种人化的空间,即客观物理环境与人的主观意识系统相互交流而产生的一种和谐关系与情感体验过程,人的意识和行动在参与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文化意义和个人记忆的物体化和空间化,以及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折射出场所精神。[10]罗店划龙船习俗的实践空间一直在转换,从古代的练祁河到1994 年再次重生之时的罗溪公园,再到如今的美兰湖,从明清时代商贸繁盛的罗店古镇,到现在罗店新镇中供人们放松身心的东方假日田园,罗店龙船文化活动总是依托空间建构着场所精神。在这场所精神中,不仅包含着古时罗店人民对龙图腾的崇拜,禳灾祈福的愿望和祭祀先人的崇敬心理,还流露着人们对罗店镇自然风光的喜爱,对罗店历史文化的感怀,并唤起了罗店人对“家乡”“农村”过往记忆的特殊情愫,即称为“乡愁”的地方感。很多城市人渐渐走出市区去“郊游”“农家乐”,以填补城市文化造成的精神苍白和内心空虚,从而使得“诗意地栖居”的重新回归成为一种可能。节日本来就有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作用,人们利用节日回归自然,与大自然亲近。比如“端午临水”,端午节举行划龙船比赛等水上活动强调的就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适应自然、欣赏自然的自然伦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虽然增进了文化交流,缩短了地理距离,但必然会消磨地方文化的特质,消解地方的独特性,导致人们在情感方面的缺失,而这种“失落”需要我们从文化中去找寻。节庆类非遗是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和节庆类活动已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和身份认同的媒介,以唤起人们内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图腾崇拜、禳灾祈福、祭祀先人等原始功能,再到促进社会交往、增强文化认同、续存乡愁记忆等都市化背景下的功能,只有充分认识、挖掘节庆类非遗的当代价值和作用,才能将其通过创新、创造的转化融入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大都市生活之中,才能使人们在快速城市化的洪流中找回认同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