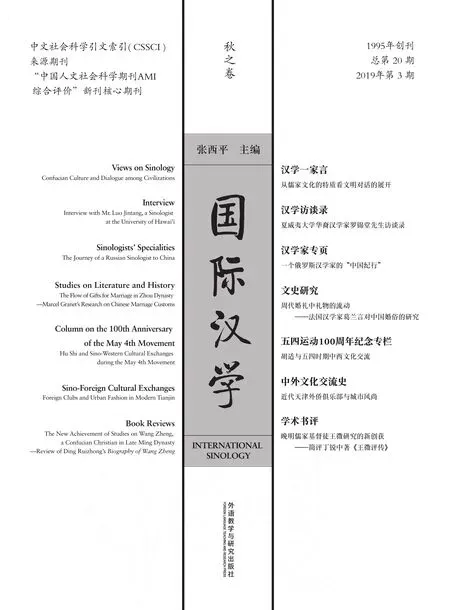刘若愚的《文心雕龙》研究
□ 闫雅萍
刘若愚(James J.Y.Liu, 1926—1986)是著名的美国华裔比较文学学者。美国华裔文史学界素有“东夏西刘”之称,“东夏”指夏志清,“西刘”即长期任教于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刘若愚,其在西方汉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刘若愚生平多用英语写作,共出版英文专著八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为中国的文学理论进入西方学术视野垦拓道路,在中西比较文学及汉学研究论著文章中总少不了对他研究成果的征引。杨乃乔曾将在西方学术语境下用英语展开比较诗学研究的华裔学者群称为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认为在这个学术族群中,刘若愚是最为声名显赫且最早具有国际影响的首席学者。
奠定刘若愚地位与名声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应是其于1975发表的用英语写成的著作《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书中采用并修改了艾布拉姆斯(M.H.Abrams, 1912—2015)的文学理论框架,用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等框架梳理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并就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西方文论中所蕴涵的共同的审美思想进行比照。刘若愚认为文学理论,无论中西,都可分为文学本论和分论,文学本论回答文学的本质及起源等本体论问题,而文学分论则解决文学创作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在一个理论的框架或体系内,所有关于文学的本体论和具体理论应该能够得以充分的讨论。因此,他修改并扩展了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一并探讨了中国及西方的文学理论。在这部著作中,刘若愚明确陈述他的终极目标是“将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与西方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①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刘若愚的这一论著在英语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不少汉学家和研究者的质疑与诟病,认为其所谓的比较与对话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单面向的呈现,并认为“这种试图以西方文论框架来讨论中国文论的方式割裂了作品的有机结构”,②刘颖:《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年,第34页。是用西方的诗学框架来切割中国的诗学传统,恐使中国的文论思想有沦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之危险。曹顺庆引用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批评,认为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③曹顺庆:《异质性与变异性》,《东方丛刊》2009年第3期,第1页。曹顺庆认为刘若愚这种“求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罔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是对西学理论话语霸权的妥协。进入21世纪,更多的学者则对刘若愚的研究给予了更为公允理性的肯定。有研究者从翻译的角度着眼,认为刘若愚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英语翻译与研究为保留汉语的源语特征宁愿牺牲可读性,这是对西方理论的一种“话语抵抗”。④蒋童、钟厚涛:《话语抵抗与理论建构—刘若愚中国古代文论的英语翻译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33页。杨乃乔对刘若愚的比较诗学研究的贡献与价值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认为他的研究真正具有比较视野,为中西文学理论的汇通与对话打开“窗口”,开拓“路径”,是卓有成就的“跨语际批评家”与“跨语际理论家”。①杨乃乔:《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45卷第5期,第67—76页。综合而言,对于刘若愚在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及文论的翻译与研究的两种相反评价,源于批评者两种不同的外在着眼点,即刘氏的中西比较研究是“求同”还是“辨异”?无论褒贬,关于刘氏的批评与研究中都没有回避其“建构”更富有解释力的共同诗学与理论的努力。两种相反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刘若愚的跨文化理论研究的内在张力,因此,考察刘氏的中国文论研究依然要重新回到其研究本身,在对其内容、方法及成就做出更公允评价的同时,揭示其对当下研究的启示。
事实上,刘若愚本人对他的研究方法—对于概念的抽象提取可能遭遇到的反对与质疑提出了辩解。他在《序言》中申明要致力于为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面目和体系,目标的设定与语境的要求决定了他首先要理清要目,然后才谈得上比较与对话,否则“对话”只能成为一种“空话”。②《中国文学理论·原序》,第1页。这同时涉及跨语言研究必然要面临的翻译问题,从文化翻译观来看,跨文化翻译中文化资本的流通仍以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理解为前提。在此意义上,在理解基础上的单面向呈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至于“割裂了(中国批评家)作品的有机结构”的批评,他认为散见于序跋中的中国批评家的零散批评话语,前后历经多年,不可能看做有机的整体。③《中国文学理论》,第18页。西方的汉学家和身居海外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为该书撰写了中肯的书评。周策纵(Chow Tse-tsung,1916—2007)在书评中认为《中国文学理论》采用了分析与阐释学的方法,主要讨论的是关于文学的本体论。刘若愚的研究使得中国整体的文学理论的呈现成为可能,“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中国的文学思想汇聚并清晰阐明,阅读该书首先要理解作者的意图”。④“One of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Liu’s book is that it brings together and elucidates those ideas, the book should of course be read with the author’s intentions in mind.Chow Tse-tsung.” in “Review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7.2,1977, pp.413—423.同时也惜乎其具体的文本分析与阐述未能充分展开讨论,失之匆促。
批评刘若愚将源于西方文学经验的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文学理论者,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刘若愚在采用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来诠释中国古代诗学思想时,并未原封不动地从该体系出发来观照中国的文学理论,而是从理论所关注的共同因素出发,如宇宙、作家、作品及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来考量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这种考量反过来对原有的框架进行了扩充,形成新的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和对话才有可能发生。
在对具体理论的阐发中,刘若愚着力于中西诗学理论的双向互动,不仅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思想及观念,同时也运用中国的诗学思想来解释西方的理论和话语。杨乃乔认为他的双向阐释“以西方诗学体系为透镜,在适配与调整中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分类,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所蕴涵的丰沛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文学理论思想,也正是在中西比较诗学的互见与互证中澄明起来,且走向逻辑化与体系化。”⑤杨乃乔:《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比较诗学与跨界立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页。从其写作目标的达成来看,他试图“促使西洋学者在谈论文学时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⑥《中国文学理论》,第18页。为中国古代诗学思想走向西方学界,成为世界性文学理论创造了可能的路径,使西方读者能够通过这一路径和窗口走近并认识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所关注的文学理论问题,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的接受,同样也扩大并加深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阐释性理解,寻求沟通中西思想与话语的共同基础,使得构建世界文学理论体系的雄心与宏愿成为一种可能。
国内学界对刘若愚的研究可参见詹杭伦著《刘若愚:融合中西之路》、①詹杭伦:《刘若愚:融合中西之路》,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李春青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海外汉学卷》、②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海外汉学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王尔敏的《中国近代之文运升降》③王尔敏:《中国近代之文运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等近年出版的专著及相关章节,本文不再赘述,仅就其《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进行详述。刘若愚并未专治《文心雕龙》及其翻译,他曾申明是以归纳而非演绎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那么《文心雕龙》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文本之一,成为归纳中国文学理论的首要资源。
一、刘若愚的学术理路与《文心雕龙》研究
在《跨语际批评家》(Interlingual Critic)一书中,刘若愚将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称之为“跨语言的批评家”。这种学术身份使得他对于“学术为何”及“学术何为”做出了清晰的认定和表述。他认为跨语际批评家的视野和学养,让他们有可能采用一种融合中西的研究方法使其研究指向寻求一种综合的、更具有解释力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如前文所述,对于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他坚持一条执两用中的途径,既不赞成不加区别地运用现代西方的批评术语、概念、方法和标准来研究中国诗歌与文学,也不认为只有采取中国的传统方法才能研究中国文学。中西理论的极度复杂自然无法用简单地归之为同异之辨,但中西之“异”显在,“同”则隐蔽。要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诗学首先要挖掘清理相异面目之下的隐在之同,求同中辨异。这应是刘若愚的研究路向的逻辑起点。夏志清(1921—2013)称赞刘若愚有成为“跨语际理论家(interlingual theorist)”的雄心,欲将中国传统和20世纪欧美的文学理论综合起来而自成一家。④夏志清:《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台北:《中国时报》1987年5月25日、26日,转引自李春青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海外汉学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17页。他致力于以现代理论的系统去发掘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普遍内涵,并使之成为现代的理论资源,贡献于世界诗学的共同体。
詹杭伦概括了刘若愚的中国诗学研究三个路向,分别为:跨语际研究中必然面对的语言问题;以现代学术观念对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系统整理;提出融会中西的批评策略及诗学观念。⑤詹杭伦:《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北京:文津出版社,第48—75页。事实上这三个路向在刘若愚的早期著作《中国诗学》中就已初步成形,在《中国文学理论》中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六大理论。
《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引用《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凡55处,居所有征引文献之首位,⑥《中国文学理论·索引》,第236—239页。数据为笔者统计。重点讨论了《原道》《神思》《体性》《情采》《养气》《总术》等篇章,将其归纳入他的六大理论范畴中。通过对《原道》篇的翻译与讨论,刘若愚认为刘勰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讨论是一种形而上理论,即文学本体论,是最有可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的;但同时他也没有忽略《文心雕龙》中综合讨论了文学的各个方面—从文学的本体论到具体的文学分论,形成了体系性的综合理论。正基于这一理解,虽已有好几种书名英译在前,他仍对《文心雕龙》书名英译提出了新的建议,认为其是一部文学理论的详论之作,应译为The Literary Mind: Elaborations(《详论文心》),同时对在讨论中涉及的重要章节,如《原道》等都进行了诠释性英译。
二、《文心雕龙》中的形而上理论
艾布拉姆斯认为讨论一件艺术作品应围绕与其相关的四个要素:作品、艺术家、宇宙和观众,后三个要素以作品为中心形成彼此的联系。所有的西方艺术理论可以根据对这四要素之一的趋向划分为四大基本类型,分别为模仿理论、实用理论、表现理论与客观理论。刘若愚认为直接运用这一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文学理论会碰到适用性的困难,因此他对这四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排列,认为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应当是一种双向关系,四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从文学创造到接受四个阶段,借此可以对不同的文学思想进行有系统的分析和批评。同时他申明通过归纳而非演绎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批评分为六种文学理论,他分别称之为形而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及实用论。①《中国文学理论》,第18页。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刘若愚给予了形而上理论最重要的地位(对其讨论占取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他认为从比较和综合的视野来看,这一理论最有可能与西方的理论进行比较,贡献于世界文学理论。的确,作为对文学本质是什么的“元理论”,中西理论对共同问题的回答使二者之间的比较具备了基础并成为可能。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开创性地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原道》与《征圣》《宗经》《谶纬》《辨骚》被视为刘勰的“文之枢纽”论,详论为文之大端, 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发生、本质等本体论问题。刘勰“道”之所谓,向来为论者聚讼,莫衷一是。认为其道有谓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自然之道(客观规律)、宇宙本体(精神或理念)。②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80—584页。
将“道”作为宇宙本体的理解使得刘勰的文学本质论具有了形而上的玄学色彩。刘若愚将“形而上”的概念界定为以“文学为宇宙原理之显示”概念为基础的各种理论,③《中国的文学理论》,第20页。其核心是探讨文学与宇宙之关系。正是基于将刘勰谓之的“道”作为宇宙本体,一种精神或理念的理解,刘若愚将《原道》作为中国文学理论中关于形而上理论最为集中完善的表述。他在文学与宇宙关系的普遍框架中,讨论刘勰所谓宇宙之道,将文学作为显示宇宙原理的概念源头上溯至《易传》中对卦象的注释和评论以及《乐记》中认为“乐者,天地之和”的思想和理论,并认为文学的形而上概念在陆机的《文赋》中初露端倪,及至《文心雕龙》得到了全盛发展。④同上,第20—29页。
刘若愚认为《原道》篇对形而上的理论进行了最为透彻的论述。《原道》体现了刘勰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文学本论),刘勰在其中表达了“文”源于“道”,并为“道”之显现的核心思想。通过将天地之文与人之文并立与模拟,刘勰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行应和的关系,认为文是人之德性,与天地并生于道,并显现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若愚翻译了《原道》篇中的重要论述,并充分讨论了“道”和“文”这两个关键词的复杂意义。的确,如果刘勰在《原道》中讨论“道” “圣” “文”的关系可以用现代理论术语表述为宇宙、作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时,那么将《原道》中所体现的文学理论归类为形而上理论,不仅仅是一种便利且具有了逻辑合理性,同时有利于将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内,为对话与对接搭建了平台。
为了呈现形而上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发展的脉络,刘若愚也指出形而上理论逐渐吸收其他理论的因素而发生的历史演变,如唐代及后期的作者继续提及“天文”与“人文”的类比,可是他们通常是把实用理论的宇宙哲学作为基础。但文学的形而上概念并未从此消亡,反而经过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产生了新的理论,并演化出理论的支派和支流,在黄庭坚提倡的“拟古主义”,严羽的“禅语论诗”,王夫之的“情景合一”之论,王士禛的“神韵说”及至近代王国维的“境界”理论中,都可以辨析出形而上概念的渊源。⑤同上,第39—70页。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文心雕龙》于后世的影响存有疑问,认为它在清代之前很少作为权威性的批评和理论而被引用,并未享有它现在的地位,⑥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84.然而刘若愚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发现形而上理论的隐在脉络,认为《文心雕龙》中的形而上文学理论对于后世有着复杂而广泛的影响。
中国文学(诗)的抒情传统作为一个异于西方传统的突出特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成为一个讨论中西比较诗学时的参考框架,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与概念也得到了更多的强调与发挥。而刘若愚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提出的文学与“道”(宇宙原理)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理论中得到回响,并可在现代理论的框架中进行比较性的会通研究,这既是对《文心雕龙》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开掘,亦是对世界文学理论体系的丰富。
三、形而上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
尽管进行了重点讨论,刘若愚同时也矛盾地指出,形而上理论并非中国文学理论中最有影响或最重要的理论,但是它作为有关文学的发生及其本质的认识和理论表述,是关于人类共同经验的追问与认识,因而可以成为中西之间互相比较与沟通的理论,并为最终的综合性文学理论贡献自己的观点。《原道》中所阐述的形而上理论与西方的模仿理论和表现理论以及象征主义理论有可堪比较之处。
首先,形而上理论和模仿理论都是探讨文学与宇宙的关系,但是中西宇宙概念的不同所指则导致这两种理论的不同走向。刘若愚以《文心雕龙》与锡德尼(Philip Sydney, 1544—1586)的《诗辩》为例,辨析这两种理论的同与异。当刘勰以“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逻辑论述文学作为道之显现的思想时,锡德尼则称“假如言语次于理性,是人类最大的天赋,那么,极力精练此种恩赐便不能不获得赞美”。刘若愚认为以上论述中将语言作为人类的独特才能,但其不同在于,相对于中国文化中将这种天赋归于自然赋予,而西方文化的传统则将其归恩于上帝的恩赐。①《中国文学理论》,第72—73页。刘若愚认为在模仿理论与表现理论中,经常使用“镜子”的隐喻,镜子代表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心灵反映外在现实或上帝,而在中国的批评思想及形而上理论中则很少使用这一隐喻。②同上,第75页。这一区别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文”作为本体实存还是作为镜像反映—将形而上理论与模仿和表现理论区别开来。在《文心雕龙》的论述中,“文之为德也大矣!”“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作为本质实存而存在,是道的实存显现(manifestation)而非镜像反映(reflection),而圣人则述而不作,以文明道。文的本体性得到了至高的肯定。
关于“文”与“道”关系的理论阐述在刘勰之前的确鲜有论及,刘勰在《原道》篇中提出的文源于道的思想以及心、言、文之间的“显现”关系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从内在发展出文以载道的理论脉络。刘勰关于文学与道(宇宙)的源生关系的论述在更大的论述框架中与西方的理论因有共同的关注中心,而具有了可类比性。差异显然存在,求同成为比较的价值所在。刘若愚以光谱作比喻,揭示中西文论的比较问题,同与异只有在同一理论框架下的范围(光谱)内才能够进行(色调的)差异比较。
刘若愚在象征主义的理论中发现了与形而上理论相似的认识。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关于诗的定义,认为诗是通过人类的语言回归其本来节奏的,是对全部存在之神秘意义的表达。刘若愚认为这与《原道》中的文与道之关系并无二致,而他的语言观念也可与刘勰的表述—“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引为同调。③同上,第83页。刘若愚还在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1995)的当代现象学理论中听到了形而上主义的回响,杜夫海纳认为“艺术和自然是有意义的存在”,艺术“出现于历史的黎明期,当人类刚脱离动物阶段时”,④同上,第87—88页。与刘勰的文之为德而与天地并生,与人共现的思想所见略同。而杜夫海纳关于艺术作为现象之存在的论断—艺术家既非有意识地模仿自然,亦非以纯粹的无意识和非自愿的方式显示它的意义—显然令人联想起“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文道之论。
如果形而上理论发生在艺术过程的第一阶段,那么表现理论则关注作家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即艺术过程的第二阶段。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及《情采》篇中提出了文学的表现作用,与文学作为作家心灵之表现的观点不同,刘勰认为文学表现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性,还有自然之理路。“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情理因内,言文符外,刘勰的表现概念呈现出情理并重,情志合一的特征。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性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不仅纵论前人著作,而且首次讨论了整个文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因而有集大成之誉。在刘若愚的文学过程论和文学理论体系中,刘勰的论述涉及文学过程所有的四个阶段和大部分文学理论。刘若愚将《文心雕龙》置于“共时性”的体系之中加以研究。对这样一部体系相对严密的论著而言,从其文本中抽取若干重要论述展示其历史源流,为解读这部文论巨著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观照;而与西方理论的比较则更具开创性的意义,一方面使得《文心雕龙》中精深理论的某一组成部分或某一侧面能够为西方的读者所理解,反过来也为其理论本身提供了新的阐释。宇文所安认为刘若愚采取了最为合理的策略将零散的批评语料呈现给现代西方读者。①“Several strategies may be adopted to present such a ‘dismembered’ critical corpus to the modern western reader, and James Liu has chosen one of the most reasonable.” in Stephen Owen, “Revi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90.6 (1975): 986—990.
总体而言,刘若愚认为,《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理念是形而上的,其他概念则附属其上。刘勰本人并未明言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但是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及其与形而上概念的附属关系可经由分析而知。②《中国文学理论》,第183页。在不同的理论分类中引用了《文心雕龙》的论述之后,他并不想给读者留下关于《文心雕龙》的零散印象,因而专门讨论了刘勰的“综合主义”的文论思想,旨在言明《文心雕龙》中的实用理论、表现理论、审美理论是统合于形而上的基本文学概念之中的,从而对《文心雕龙》的理论系统性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并为《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做了比较性的旁证。
结语
比较诗学的视野为《文心雕龙》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具有普遍性与可比性的场域,使其理论经由比较与辨析进入现代西方读者的视野。刘若愚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论诠释表现出了一种综合中西的建构性理解,这一理解经由对中西概念及其形成的同与异辨析而达成。
刘若愚终生致力于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语言—悖论—诗学》(Ianguage-Paradox-poetics)③该著作在刘若愚先生生前并未出版,而是在其身故后由其弟子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整理完成后出版。见James J.Y.Liu, 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Ed.Richard John Lyn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中,他再次将注意力集中于中西语言与诗学的比较,书中通过中西文本的并置,揭示中国传统的“悖论诗学”(如“言不称物,文不逮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等)与当代西方诗学及阐释学的某些汇聚点。“该书中所引用的中文文本的诠释显然表现了作者对于西方理论的理解,书中有不少关于中西概念及其形成的同与异的深刻见解和分析。”④Zhang Longxi, “Reviews on 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0 (1988): 191.关于这本书的目的,刘若愚的表达更加谦逊,他认为要给读者提供的“并非是比较诗学而是一种中国诗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为真正的比较诗学,一种既非‘欧洲中心主义’,亦非‘中国中心主义’的诗学开创一条道路”。⑤Longxi, op.cit., p.194.这种中国诗学不仅仅是一种神秘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异国趣味,而是在共同的诗学框架中对文学的本体问题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解。
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刘若愚尝试从文学的共同因素出发,借助文学研究的共同对象及相互间的关系,抽取中西重要的文学思想观念和理论,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加以讨论,并进行比较。在文学与宇宙关系的维度上,《文心雕龙》的文道之论作为以形而上理论为主调的综合理论得到重新认识。刘若愚的《文心雕龙》跨文化研究,始于比较,而终于建构,实现了经由比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理解,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内涵进行新的开掘与丰富。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与语境中,他的研究再次给予我们路向方面的启示,面对跨语际研究中的语言问题,清晰的呈现与诠释性的翻译是比较与对话的基础;求同与辨异不可回避且永远是一种内在的紧张存在,“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只有提出融会中西的批评策略及诗学观念,理解、对话与交流才能发生。在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与时代坐标中,要尝试将中国文化变为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一个角色或替代品,不仅需要对传统的再度发掘与重组,更需要去创造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对话与对接的平台。在这一路向上,刘若愚的研究是开端而非终点。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