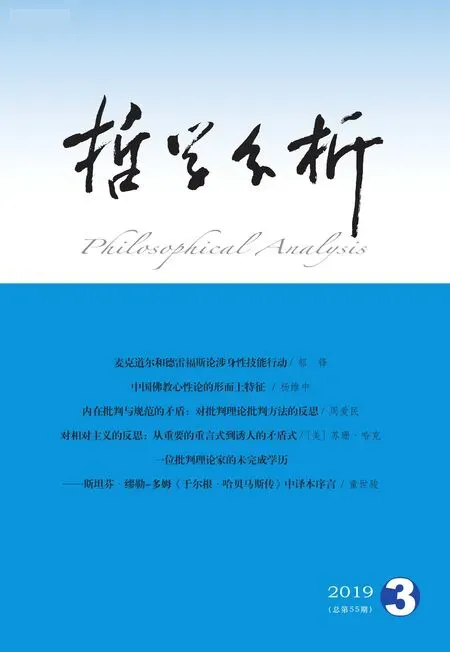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规范性与自然主义
——瑞斯乔德教授访谈
[美]马克·瑞斯乔德 袁继红
规范性与自然主义的话题与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如下核心争论紧密相连:当我们的理论越来越复杂时,诉诸规范性是否会成为前科学思想的残余?还是说规范性是不应被社会科学忽视的社会世界的不可还原维度?诉诸规范性是否可以被科学地呈现出来?近年来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为上述争论注入了新的资源和视角,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家埃默里大学的瑞斯乔德(M. Risjord)教授《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规范性与自然主义》①M. Risjord, Normativity and Natur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一书呈现了活跃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新观点,其本人也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分析的规范自然主义。笔者就此主题在访学期间,对瑞斯乔德教授进行了访谈,以期一窥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前沿进展。
问:我们知道,对社会科学而言,规范性问题是个老问题,为何最近规范性重新成为争论热点?
答:是的,规范性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问题例示了一些古老的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问题。哲学曾经主要关注道德上的“应该”与非道德事实之间的关系,那时哲学思想总是或明或暗地包含社会世界的理论。当社会科学从19世纪哲学中萌芽出来时,把社会规范视为不可还原的与寻求自然化社会规范之间的哲学分歧存留了下来。于是,“应该”是否可以还原为“是”这一哲学问题,是在越来越多的经验性和因果性社会理论的背景下展开的。举个例子:如同古尔德纳(A. Gouldner)所言:“社会学始于对世界的解魅,继于对自己的解魅。”②Alvin W. Gouldner,“The Sociologist as Partisan: Sociology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Vol.3,No.2,1968,p.103.就在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将结婚的权利写进宪法。但是,那些认为婚姻体现了道德和宗教价值的人强烈反对国家对同性婚姻的支持或容忍。在这些人看来,异性婚姻是道德上正确的社会形式。相反地,近两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一直在解魅婚姻和其他社会关系。人们结婚不是因为他们应该这么做,而是因为社会认可的两性关系满足各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因此,社会科学解魅世界是通过用经验上牢靠的理论取代解释和证成的纠缠。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充分解魅社会科学自己。社会科学理论通常会诉诸社会的、道德的或美学的价值,以及规则、习俗、标准、实践、承诺、法律。于是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社会科学中的规范性?当我们的理论越来越复杂时,诉诸规范性是否会成为前科学思想的残余?还是说规范性是不应被社会科学忽视的,并且是社会世界的不可还原维度?
近几十年,进化理论、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为社会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理论和方法论广泛地融合产生了新领域,如进化心理学、认知人类学和行为经济学。这些发展为传统规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挑战和资源。同时,20世纪后期的哲学也再次复兴起对规范性的讨论,并且开始利用新的论证和分析。我们当前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讨论正试图搭载社会科学和哲学间的桥梁,重新探寻规范与价值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
问:我们知道,传统上与自然主义相对的是反自然主义。而您关注的是规范性与自然主义,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答:整个20世纪,关于自然主义的争论,如你所说,是人文主义或诠释学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争论。那个争论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明显不同相吻合,所以争论的问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吗?那时,经验主义似乎是对自然科学的最佳特征化。关于自然主义的争论就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和理论结构对于人类研究是否充分,或者我们是否需要与经验主义不同的方法论或本体论。
温奇(Peter Winch)的书《社会科学的观念》对关于自然主义的传统争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也标志着那场争论中的变化。温奇主张规则遵从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并且不能从传统经验主义的角度理解规则遵从。当然,规则是规范性的一种形式,所以温奇的工作使得规范性成为与自然主义相反的明显部分。关于温奇立场的争论进一步发展,合理性成为焦点。合理性是20世纪80年代的热点话题。到20世纪90年代,亨德森(D. Henderson)和我开始讨论社会科学应该如何切入规范性的讨论,以及社会科学对规范现象的理解是否可以是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的这一变化追踪了更一般的英美哲学的变化,哲学家开始认真讨论规范性如何适于自然主义世界 观。
对规范性的关注与社会科学中的人文主义和诠释学进路保持着深层关系。人类社会充满着规范、规则和价值。诠释学,尤其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试图发展能捕捉人类生活规范性方面的方法。伴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式微,诠释学也不再自称是唯一能容纳规范性的科学哲学。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和表达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expressivist-pragmatic view)就提供了两条讨论规范性的自然主义进路。理性选择理论(决策论和博弈论)自从刘易斯(D. Lewis)的《论习俗》 (Convention)后获得了讨论规范性的灵感。近年来,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吸取越来越多的实验工作来发展关于规范现象的心理学上令人信服的理性选择模型。表达主义的实用主义分析规范性的进路与社会科学中的实践理论,如布迪厄(P. Bourdieu)、吉登斯(A. Giddens)等的理论,有着密切关联。
此后,如下问题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是否存在能解释规范性现象的自然主义?或者“科学地”理解我们自身是否要求诉诸规范和规范性?关于这个问题的当前社会科学哲学争论,特纳(S. Turner)和罗斯(J. Rouse)各自代表两个阵营。特纳认为社会科学解释不需诉诸任何先验的规范或者道德规范,它们在人类行动解释中是冗余的。罗斯则提出强有力的论证,把规范性作为相互负责任的实践之生态位构建结果。学者们围绕二者争论展开,大部分不认为规范性要求承诺一个外在于人类互动的本体论地位,但是也不同意由此消去规范性。对于充分解释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我们人类,关注人类社会的规范性维度是不可或缺的。困难在于:如何概念化这些规范性维度,以及为什么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问:如你书中所说,当代哲学语境下,自然主义的内容或内涵已经发生变化。那么,相比于逻辑经验主义,当代自然主义究竟有哪些发展?
答:对。尽管本书中“自然主义”有不同含义,但绝不意味着逻辑经验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科学哲学中由汉森(Norwood R. Hanson)、库恩(Thomas S. Kuhn)、塞拉斯(Roy W. Sellars)、威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萨普(Frederick Suppe)、博伊德(Robert Boyd)等人发起的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已经形成一股主流。今天,当哲学家赞同或反对“自然主义”时,并不是赞同或反对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失宠于科学哲学的一些特殊理由塑造了当代自然主义与规范性之间的争论。20世纪后期科学哲学中的三个发展尤其重要。
第一,逻辑经验主义的中心问题是理论结构和理论证实。牛顿力学是其范式。高层规律(三大运动定律)演绎地推出低层规律(例如,抛物体运动或潮汐运动的定律),而且这些规律演绎地从假设推出实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生物学哲学家主张生物学没有这种理论结构。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生物学家争论自然科学也不是都一样的。就像生物学与物理学之间大不同一样,人类学与物理学之间也大不同。自然科学不是自然主义所想象的那样统一。
第一条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不能以像20世纪早期那样的方式提关于自然主义的问题。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单一的理论或方法形式,故问题不能是:是否社会科学理论或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或方法一样?不过,早期诠释学和人文主义的问题仍然有效。人文主义强调意向性、价值和意义,这些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因此,你仍然可以问:是否意向性、意义、规范性需要特殊的方法、理论结构或本体 论?
科学哲学中的第二发展涉及价值中立问题。在逻辑经验主义时代,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科学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反自然主义常常争论科学不能或不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到20世纪90年代,哲学观点发生变化,不但认为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而且不能是价值中立的。好的科学包含价值,于是问题是:价值如何作用?如果科学都包含某些价值,那么如何区分好的科学与坏的科学?价值在科学中扮演哪些角 色?
逻辑经验主义时代,价值负载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一个明显的不同点;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有很深的关系,而这方面自然科学没有。一旦认识到所有的科学都是价值负载的,它就不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点。然而,人类研究诉诸价值的方式是非人类研究所不具有的。不但有与公共政策问题的深层关系,我们的研究对象——人类社会——也以非人类客体所没有的方式具有价值和规范。价值和规范是我们试图解释的现象部分。
第三个重要发展不是来自哲学,而是来自科学本身。在最近几十年,认知科学、进化理论、神经科学对于社会科学变得非常重要。社会科学比以前更加转向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在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中,源于自然科学的试验方法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社会科学不再把自己孤立于其他科学知识领域。他们从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中寻求发展自己的理论。
第三个发展再次瓦解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但是它比前两个发展走得更远。社会科学中的变化建议我们可以根据生物学、心理学机制来考察人类。根据这个背景,当代自然主义与规范性的问题变得非常尖锐。自然主义者试图论证用生物学或者心理学框架解释人类社会的价值和规范。规范主义者则认为规范性不能还原为心理学或生物学机制。
问:根据您的分析,自然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当代争论有点像基于新科学观之上的有关规范性的还原论与反还原论之争?
答:是的。说自然主义—规范主义之争是还原论问题的例示,这非常准确。从还原论视角看自然主义—规范主义之争突出了这个争论的两个特征。
首先,还原论问题可以是解释的或本体论的。解释的还原问题是:是否规则遵从以及其他规范性现象可以用非规范的方式解释?本体论的还原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根据非规范性实体和过程来理解规范、规则和价值?如何把规范融入世界的因果图景主要是个本体论问题。注意,这两类还原论是相互独立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不用坚持解释的还原论而坚持本体的还原论是逻辑上可能的,实际上,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坚持的立场。
第二,还原论问题可以分为理论内部的(intra-)还原或理论之间的(inter-)还原,它们之间的不同常常被忽视,但是这很重要。理论之间的还原发生在不同层理论之间,例如社会科学理论与生物学理论之间。理论间还原的一个例子是心理现象(语言、谓词)是否能还原为物理现象(语言、谓词)。在这个例子中,有两个科学领域:心理学和生物学;所讨论的问题是这两个领域的理论如何相关。传统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立场通常被作为理论间还原问题来理解,亦即社会现象是否能还原为心理学现象(信念、选择)。
理论内部的还原发生在同一个领域内部。例如“以太”概念从19世纪物理学中的消除。19世纪前的物理理论假设电磁波是在一种叫做“以太”的特殊物质中传播,就像声波在空气中振动一样,电磁波也在以太中振动。但后期的理论却表明这样的介质是不必要的。理论内部的还原是自然主义—规范主义之争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能发现“规则”或“规范”的自然主义替代性概念吗?
问:就规范性问题,您主张自然化规范性,并且提出了一种生态分析进路。请问,您的生态分析如何展示自然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融贯性?
答:可以基于我对前面三个问题的回答来看我的观点。关于理论间还原,我主张关于解释的反还原论立场,但是我坚持本体的还原论。也就是说,我的立场不把规范或者规范性现象看作外在于因果的、物质的机械世界。这是某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自然主义者。但是,我认为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诉诸规则、社会规范或价值。这些解释要素不能简单地用“低层”科学如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概念来替换。因而,我的观点不是本体上的还原论。
我所采用的立场有时被称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 (nonreductive materialism),有人认为这个立场是不稳定甚至不融贯的。亨德森和我争论这个问题已经多年,他在本书的论文作了(新的)有趣的论证,反对我这样的观点。很明显,我认为我的观点是融贯的,并且我在本书中也回应了亨德森。我是这样考虑的:只要我们采取了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立场,就会问怎样理解“规则”“规范”等概念。如果它们不能指称外在于因果世界的规范力,那么这些词用于解释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好把这个问题理解为理论内部的还原。我们是否能改变规范性概念的意义或者理论意义以使得它们是自然主义上可接受的,但同时还能执行我们所需要的解释作用?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做到,但不是通过把这些术语替换为心理学概念。信念或者心理表征并不是解释的必要条件,但心理学机制是解释的必要角色。
在我的论文中,论证是直接针对毕凯瑞(C. Bicchieri)的观点。她的观点非常有趣,因为她提供了一种对社会规范的自然主义理解。毕凯瑞认为社会规范保留其解释角色,但是可以用自然主义术语进行分析。我认为虽然毕凯瑞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成功。我理解规范性的路径与她不同,我试图既保持规范性有合适的解释角色,又与因果机制世界相一致。
问:您认为论证非还原的自然主义不是理论间的还原问题而是理论内部的还原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自然化规范时要使得它们是自然主义上可接受的?
答:坚持自然主义是我整个工作的框架。前面我说过,“自然主义”有许多不同含义。在这里,“自然主义”的意义必须处理哲学方法论。我相信科学与哲学是连续的。哲学并不优先于科学;我们没有任何形而上学或者认识论上的特殊洞见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这意味着科学研究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是相关的。
那么,使规范是自然主义上可接受的,就是把规范融入当代科学的框架。但是,把规范融入科学图景并不要求解释它们或者本体论上把它们还原为心理学或生物学上的某物。那种还原很少在科学中发生。更多的是,我们开始理解产生高层现象的低层机制,并用这些理解重新概念化高层现象。这就是我在规范性争论中所要论证的。当我们合适地理解产生人类创造力、识别力以及遵从规则的机制时,我们就会重新使规范性概念化。规范不再是神秘的非因果力。
在本书中有很多重要的论证涉及能够解释规范的机制的特征。一种进路关注表征的心理学机制。依此进路,当一定数量的个人相信存在一个规则或者以其他方式表征该规则时,社群中就存在一个规范。我在本书的文章中指出这样的理解并没有保留社会规范的解释价值,也没有解释它们与众不同的动机力。
另一条进路是我所赞同的,即罗斯(J. Rouse)所称的“规范的实践理论”(normative practice theory)。依此进路,规范的实践先于表征。这意味着关于规范的信念仅仅只能在能动者已经感受到规范后才形成。规范的实践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规范并不等同于信念、态度或行为的惯例。规范通过相互响应而产生。这意味着个体对待彼此就像允许或者要求彼此一样,通过采取一种行为来遵从规则。这样的采取和对待不必使行为适合惯例(尽管惯例也许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采取和对待必须是相互的:能动者A允许能动者B可以做某事,同时能动者B(和其他人)能够判断A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规范的实践理论需要相互响应。
规范的实践理论并没有试图消除对规范性的要求。正因为这个原因,它通常被看作是反还原论的。很明显,它是在理论间还原意义上的反还原论,因为它反对根据心理学层面(的信念或表征)解释社会现象。理论内的还原对自然主义则是开放的,在那里相互可问责的潜在机制可以得到揭示,并且我们理解了规范性实践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出现。我认为,认知心理学已经有资源来讲这个故事,至少有实质性的轮廓。在我的论文中,我的生态分析根据下面三种能力来分析:能动者对环境的适应,对行动可能性的认识,以及意识到规则的语言构造的能力。这些能力每一种都可以分解为认知机制。遵从规则或者规范,要求具有上述能力,但是因为规范依赖于相互响应,所以并不能通过提及能动者的认知状态来穷尽诉诸规范的解释。当根据认知心理学来重新概念化规范性时,规范性保持了解释的自主性。
——第十七届《哲学分析》论坛专题研讨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