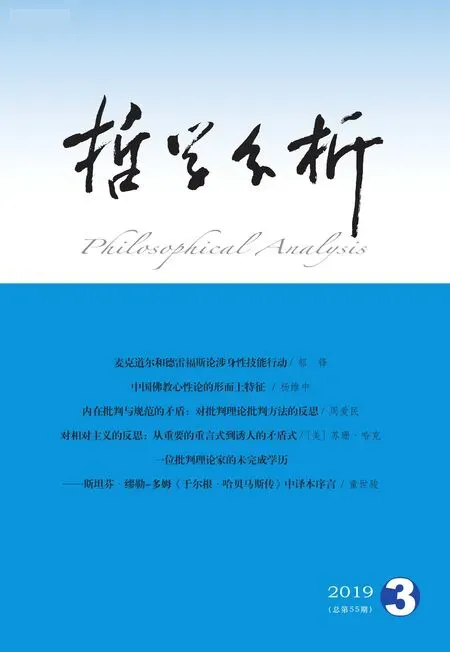如何看待“在量子测量中的意识介入”?
——评朱清时院士的反实在论
李宏芳 桂起权
一、量子的相干叠加态取消客观实在性没有?
桂起权(以下简称“桂”):由于朱清时院士在科学界的特殊地位,他的“反实在论”言论看起来又如此旗帜鲜明,因此在科学界和普通民众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思想困惑。我的多年从事高分子化学研究的老同学郑重其事地问我,现在唯物主义哲学是否真的面临挑战?我们的好友波士顿的曹天予教授是坚定的科学实在论者,又是结构实在论的积极倡导者,他希望我们武汉的“量子哲学共同体”,对此有个明确的集体表态。为此,确实值得我们专门讨论一番。①我们的量子哲学共同体的实在论立场,从总体上看,确实是高度一致的,尽管表述方式各自有所不同。不过,赵国求教授已经在《江汉论坛》等杂志撰文表态,万小龙教授连同其博士生也打算另文发表评论。
在《我们的量子哲学共同体》 (2004年)一文中,关于“月亮不看它时,它存在不存在”的议题,我们曾经明确表示过,“现象实体”与“自在实体”这两个层次是有严格区别的。在微观领域,观察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强调量子现象对观察的依赖性,算不了什么“主观唯心主义”。一方面,月亮在没人看它的时候作为“月球”(的客体)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反过来说,只当有人看它的时候,月球才作为“月亮”(现象实在)而存在。前一句话说的是“自在实体”的客观性,后一句话说的是,“现象实体”对观察的依赖性。①桂起权:《我们的量子哲学共同体》,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我们必须辩证地看问题,同时看到这正反两面,两者缺一不可,这样才算完美。重点在于,量子实在具有“关系实在”的特征,但不能忘记它仍然是实在。这是我们关于量子现象与观察测量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看来,这次朱院士对量子测量的讨论,实质上也涉及同类问题。不过,他对“薛定谔猫”的形象类比——“女儿既在客厅又不在客厅”却更有能够迷惑人心之处。芳芳,你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量子实在与“薛定谔猫”②李宏芳:《量子实在与薛定谔猫佯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让你来解释一下也许是最合适的 吧。
李宏芳(以下简称“李”):这先得从“量子叠加态”和“波包塌缩”说起。量子的神奇在于“态叠加原理”,即微观对象可以以一定的几率同时存在于不同量子态的叠加之中,形成量子相干叠加态。一个微观粒子,比如电子,没有一个精确的位置,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还可以“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即处于“这里和那里的一个叠加态”。在这个例子中,电子是非局域性的存在物,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地方。朱院士的“女儿既在客厅又不在客厅”是形象类比,对于宏观物体来说,这种“既在又不在”的情形自然很难实现。
对于微观对象来说,情形确实是这样。(桂插话:所以说,形象类比对于科学普及是有用的,对于增加普通群众的理解力是有启发性的。)在没有观察或测量之前,微观对象的存在状态,比如位置,完全不确定,究竟在哪儿,测量之前没有答案。量子随机性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化约的真正随机性,是由微观对象量子态的相干叠加性决定的。然而,微观对象的存在状态具有内禀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微观对象本身不存在,更不意味着微观对象是由意识创生的。例如,电子可以处于自旋向上的状态,也可以处于自旋向下的状态,还可以处于两者的叠加态,在未测量之前,电子的自旋状态客观上是不确定的,但这不等于电子及其量子态本身不存在。如果我们测量电子的自旋,我们将以一种完全随机的方式,确定电子自旋究竟是向上还是向下。测量作为仪器与被测量系统(这里是电子)的一种相互作用,使电子原先不确定的自旋态确定下来,并且呈现出来。至于电子本身的物质存在性,如质量和电荷,本来就有确定的值,并不是由于测量随机产生的,更不是由意识创生的。简言之,量子测量过程是微观对象从量子叠加态到某个本征态的转变,是从不确定态到确定态、从可能态到现实态的转变。即使海森伯的“潜在”和“倾向”解释也不否定客观性的实质,这里并不存在意识或测量“产生”客观世界的问 题。
桂:看来你对“相干叠加态并不取消量子对象的客观实在性”的解释,很有说服力。那么,你对朱院士所说“测量的核心是意识”,是怎么看待的呢?
李:量子测量的实质是纠缠。对于电子位置的测量,我们将以一种完全随机的方式知道电子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仪器(包括环境)与被测系统(这里是电子)的相互作用导致的纠缠,改变了微观量子的存在状态,使其从不确定的“量子相干叠加态”,以一定的几率跃迁到确定的“经典态”(早期,它被称为“波包塌缩”)。在这里,不是意识创造了微观量子态,更不可能创造微观粒子本身。现代量子场论的发展比普通量子力学更清楚地表明,“量子场”是比“粒子”更为基本的存在。在量子场中,粒子湮灭为连续的场形态,当受到激发,它才显现出来。
桂:我很赞成量子场论的“场的本体论”观点,真空是充实的,“真空不空”,即使一个实粒子也没有,却仍然充满了场物质。场就是海森伯所谓的“原物质”,“物质的第一重要属性是广延性”(笛卡尔语)。“场物质”才是真正第一性的存在物。粒子却是派生的,可生可灭的。以为粒子湮灭了,就是“物质消灭了”,那是十分可笑的。那只能说明,“原子论”曾经的科普宣传过于死板却又太深入人心。
李:“真空”就是处于基态的量子场,场的能量是有涨落的,激发和退激对应粒子的产生和湮灭。能量和质量等价,粒子的创生也是有物质基础的,绝不是意识作用的结果。诚然,“量子测量”要比“经典测量”复杂,因为量子测量涉及一个“干涉项消失”的问题,即所谓波函数的“波包坍缩”问题。
桂: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干涉项的消失”的?
李:冯·诺依曼试图在量子力学的框架内逻辑一致地回答量子测量问题。在《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 (1932年)一书中,他把仪器简化为只有一个自由度的指针,认为它也遵循量子力学的规则。然而,由于忽略了仪器的宏观特性,最终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论:为了消除相干项,切断无限回归的仪器链,必须有人眼的“最后一瞥”,即人的主观意识的介入导致了波函数的“波包坍缩”,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一假说影响深远,成为后人对量子测量进行主观主义解释的主要根源。朱院士特别提到冯·诺依曼的“主观意识影响物理实在”的思想。但是,量子测量的“波包坍缩”必须有“主观意识参与”或者说人眼的“最后一瞥”的说法,是令人费解 的。
二、关于冯·诺依曼的“最后一瞥”
桂:顺着冯·诺依曼的思路走,既可以向“右”转,也可以向“左”转。你刚才说到,冯诺依曼的“最后一瞥”,成为后人对量子测量进行主观解释的根源。但我则看到,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引出量子测量的“客观主义解释”或“实在论解释”。
李:这可能需要您做一个特别的说明。
桂:我认为,佘振苏教授的《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①佘振苏:《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就是这样做的。冯·诺伊曼在量子测量中引入意识,具有严谨科学的意义。佘振苏第一次使得人们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价值,必须认真看待它!冯·诺伊曼认为,测量过程必须涉及三个系统:被测量系统P,测量设施M和观察者O。O决定M,然后M与P相互作用。整个过程O+M+P(过程1)虽然复杂,但可以用数学来表述。他进一步认为,大脑的运作(O)也遵循量子力学规则。大脑活动涉及原子与亚原子粒子的行为,也可以诉诸量子力学描述。佘振苏从冯诺依曼那里得到重要启示,认为可以用量子观点研究意识。在解读冯·诺伊曼“在量子测量中引入意识”的思路中,他看到一个期望:期望对测量过程,甚至包括认知过程进行完整的量子力学的动力学描述,这是对一个(复杂的)德布罗意波演化的完整描述。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由于近几十年非线性动力学研究和数值计算技术的发展,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再思考这一理想,并非遥不可 及。
佘振苏注意到,“用量子观点研究意识”值得特别关注的人物是斯塔普,他也深受冯·诺依曼观点的影响。
李:斯塔普是怎么对意识、心灵作为量子过程进行分析的?
桂:斯塔普在《心智、物质和量子力学》 (1983年)中,对海森伯、怀特海和冯诺依曼的思想进行了整合。概括地说,量子测量过程分三大阶段:提出问题,系统演化,自然选择。其中有三个成分:(1)观察者的作用之一是,记录测量结果。如放射性原子究竟衰变还是不衰变,按照狄拉克说法,那是自然的随机性抉择(故称“狄拉克抉择”)。(2)观察者作用之二,是如海森伯所说,是向自然提问。故称“海森伯提问”。(3)还有:“薛定谔演化”,测量过程还存在波函数遵循薛定谔方程的演化。整合起来说,斯塔普的观点可以归结为,量子测量=海森伯提问+薛定谔演化+狄拉克说的自然选择。
李:这些只是他对量子测量的物理过程所作的分析。斯塔普在哲学上有何看法呢?
桂:斯塔普在哲学上提出的新思路是:从哥本哈根诠释出发,可以融合(1)海森伯的潜在本体论和(2)怀特海的过程本体论,并以(3)冯·诺依曼的数学理论作为技术支撑,来实现对大脑和意识的客观化理解。我特别欣赏海森伯的潜在本体论,并且清楚记得,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中所说过话的主要之点。几率波意味着对某些事情的倾向。几率波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潜在(potencia) 这个古老概念的定量表述,这是正好介乎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一种新奇的物理实在。①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页。
桂:海森伯还认为,几率函数结合了客观与主观的因素。它包含了可能性或较大倾向(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潜在”)的陈述。这些陈述是完全客观的,并不依赖于观察者。②同上书,第20页。
李:您认为,斯塔普从海森伯和怀特海身上学到了什么?
桂:斯塔普融合了他们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怀特海认为,宇宙是处于永恒运动的有机体。自然界被看作活生生的、有生机的。这种把自然过程看作有机的,从哲学上包含了海森伯的潜在性。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就是冯·诺依曼分析量子测量时所说的过程1,按照薛定谔方程演化。佘振苏认为,这是斯塔普在哲学上的一种重要拓展,通过引入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将现实的心理—物理体系综合到一个全局的、过程的动力学之中。它呼唤着量子力学的意识研究。依我看,佘振苏顺着对“量子测量中意识介入”可能做客观主义解释的思路往前走,关注量子力学与心灵的关系,但其基本立足点仍然属于“实在论”的范畴。这是科学实在论的延伸,一种新的哲学本体论。③佘振苏:《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在我们的实在论解释下,不必把量子过程归结于意识,而是反过来,可以把心灵、意识归结于客观量子过程。总之,量子测量=客观物理过程,而意识、心灵(也)=物理事件(一部分),依此回答“朱清时疑难”。
至于经络、穴位、精气等中医的理论名词,同样可以作实在论或其他的不同解释。我和王伟长在《解读经络与“气”的实在性——从场本体论与结构实在论的观点看》④桂起权、王伟长:《解读经络与“气”的实在性——从场本体论与结构实在论的观点看》,第十八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南京大学)论文,2017年8月26—27日。一文作出了科学实在论意味的回答。其要点是:(1)物理学实在是生物学实在的基础。我们采取场本体论立场,“场物质”是基本的、第一性的,粒子(从分子、原子到夸克)是派生的、第二性的。(2)从结构实在论观点看,对“潜在基本实体”的本体论承诺,对一个理论的支撑具有根本重要性。经络和“气”就是中医理论的“潜在基本实体”,就像“夸克”是对粒子物理学所起的作用那样。(3)费伦的“经络的物质基础研究”。经络是复杂生理网络,穴位是其节点,穴位在针灸临床施治时可观测。费伦实验中测试的红外光波(9—20微米)和太赫兹波(9毫米微波),还有缪强实验的生物“次声波”传播和细胞膜钙离子振荡现象,都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每一种相关的严谨的科学实验,都是从一定角度对经络和“气”实在性的表征。实际上,朱清时院士也认可经络和“气”的客观实在性。
科普宣传有时候做得太夸张。美国有一个电视剧叫做“薛定谔猫”,年轻人很喜欢看,说的是一个青年物理学家内心很纠结,担心他女朋友处于“爱他与不爱他”的纠缠叠加状态之中。表面上看,国内学界似乎对“薛定谔猫”很熟悉,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薛定谔在什么语境下提出“猫”的实验,却又很随意地夸大其荒谬之处。
李:最近,成素梅教授的论文《量子纠缠证明了“意识是物质的基础”吗》①成素梅:《量子纠缠证明了“意识是物质的基础”吗》,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从物理学的历史考证和哲学分析的高度,对该问题做了澄清,考证了薛定谔当年设计“猫”实验和提出量子纠缠概念的目标与过程。薛定谔的目的是要比爱因斯坦的EPR思想实验更明确地揭示,基于经典观念并且运用经典模型与表征概念来理解量子测量,就必然导致悖论。
桂:同时她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量子测量与量子纠缠的真谛在于,量子系统整体性的知识不可能还原为组成成分的知识。
三、薛定谔猫佯谬和量子退相干
李:1935年,薛定谔因不满“哥本哈根解释”对于物理实在的纯粹现象论的描述,尤其是不满冯·诺依曼的人眼“最后一瞥”的测量假说,提出一个“死活叠加的猫”的思想实验,使测量问题的讨论尖锐化。在薛定谔看来,猫不可能处于死活叠加态,即使不打开盒子,猫也是非死即活,而不是不死不活,或亦死亦活。而且猫的死活是独立于人眼的观察的,不会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因此,冯·诺依曼的测量假说:猫的死活取决于人眼的观察或主观意识,是不可接受的。
桂:但是,据说在新的量子测量实验中,“薛定谔猫”已经变为现实啦?
李:是的,薛定谔原先没能料想到,他通过微观和宏观的纠缠构想出来的这只“死活叠加的猫”,竟然在60年后成为了现实。1996年以降,现代物理学领域掀起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篇章,物理学家在实验室成功制备出了介观尺度甚至是宏观尺度的“薛定谔猫”。“薛定谔猫”纠缠态的成功制备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理基础,也革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量子性并不是微观世界独有的特性,宏观世界原则上也可以有。朱院士的宏观类比“女儿既在客厅又不在客厅”可能正是缘于此。但“薛定谔猫”是一个纠缠态,一个物理态,而并不是说宏观世界一只真实的猫“既死又活”。质料和形式是有分别的,物质客体和物理态不应混淆。不仅如此,量子测量实验也探测到了“薛定谔猫”如何退去量子相干性,变成经典猫的过程。
桂:我知道,你对量子“退相干”问题有专门研究,发表过不少论文。
李:研究发现,“量子猫”变为“经典猫”,是一个随着猫态的自由度或说粒子数增多迅速退去相干性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而然发生的退相干过程,不需要人眼的观察或意识的参与。①李宏芳:《量子实在与薛定谔猫佯谬》,第88—89页。并不是一经爸爸观察,女儿就从“既在客厅又不在客厅”的叠加态,坍缩为在客厅的唯一状态,或者,不在客厅的唯一状态。女儿的状态是由她自身的宏观特性决定的,不是由你的眼睛决定的。你没看她时不知她的状态,只是缘于你的无知或信息匮乏,这与量子的内在不确定性是两码事。
桂:由此看来,朱院士所说的“量子力学的基础就是:从不确定的状态变成确定的状态,一定要有意识参与。这是物理学的一个重大成就”。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是推不出的。
李:根据退相干理论,量子测量中干涉项的消失,量子态转变为经典态,是系统与其“环境”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量子纠缠所致。量子纠缠才是量子测量问题的本质,是实现“波包塌缩”和量子退相干的关键,因为这种量子纠缠会在量子力学框架内动力学地消去被测系统的量子相干项,使其发生量子退相干,实现一个确定的实验观察结果的出现。
桂:是的。现在物理学家已经很习惯用量子退相干的观点来解释冯·诺依曼的“投影假设”,从而提供了从相互作用的角度解释“薛定谔猫”的状态变化的一条思路。
李:所以,量子退相干不需要“主观介入”,也不是“意识创造了物质世界”。
四 、量子纠缠和量子隐形传态
桂:听说,朱院士在讲到量子纠缠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手套”类比。假定从北京买了一箱手套,分成两半,一箱左手手套,另一箱右手手套。比如说,这一箱寄往香港,剩下那一箱寄往华盛顿。手套寄出后,在没有观察前,其状态当然是不能确定的。只有你打开观察,确定了其中之一的状态,比如全是左手手套,另一箱不管有多么遥远,其状态(右手手套)立刻就变得确定起来了,这种关联性,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量子纠缠”现象。这就像两个处于纠缠态的远隔粒子(电子),一个是自旋向上,另一个不管多远,一定自旋向下。你对此有何评价?
李:手套的这种关联本质上不是量子纠缠,而是一种宏观的整体论,满足局域因果性。在古代中国的形而上学中,远距离作用是极其自然的,属于一个把万事万物都关联起来的普遍的和谐。量子物理学并不支持这样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在量子物理学中,不是每样东西都与其他每样东西发生纠缠,只有很少的一些事件以一种非定域的方式关联。特别说来,纠缠由量子客体诸如光子或电子携带,这些物体以小于或等于光速的有限速度传播。在这个意义上,距离和空间的概念保持相关,非定域随机性能在两个分离得任意远的地方出现。因此说,量子纠缠和远程关联与“手套”的定域因果关联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寄往香港和华盛顿的手套是左还是右,在人不打开盒子看时实际上已确定,只是人不知道而已。由于人的知识不完备而引起的不确定,与电子位置的内禀不确定截然不同。电子的关联是非局域的随机关联。
桂:任何类比都不等同于原物,类比只是针对其“相似性”方面而言的,“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我喜欢强调的是,朱院士的形象类比对于科学普及是极为有用的,对于增加普通群众的理解力还是极有启发性的。
李:量子纠缠的一个成功应用是量子隐形传态。量子隐形传态,不是隐形传送整个物体本身,比如一本书或一页纸,而是它的量子态,即它的形式或架构。量子态构成了物质的最终结构,包含着重要的信息。因此,量子隐形传态传送的不仅仅是物体的一个近似的描述,实际上是通过传送物质的实质结构而传送了物体的所有的一切。①李宏芳:《量子实在与薛定谔猫佯谬》,第68页。
当我们隐形传送一个物体的量子态时,在这儿的原初态消失了,在远方的那儿会再现出一个与之相同的量子态。这与量子非克隆定理相一致。 即在量子隐形传态中,原初物体的质料(物质、能量)保留在出发点,而它的所有结构(它的物理态)消失了。这个结构或说物理态呈现在了另一端的物体的身上,在终端出现了与在出发点原初物体相同的一个物体。
桂:我完全同意你的“隐形传态不传物”的论断。
李:那么,您如何看待“量子远程关联”与“超光速问题”?
桂:量子远程关联是一种整体同步效应,既不是出于力或相互作用,也不需要信号传递。我赞成成素梅的观点,量子纠缠的真谛在于,量子系统信息的整体关联性。信号传递仍然不能超光速,必须遵循相对论要求,这里不是什么“超距作用”。远程关联只涉及遥远的空间间隔,却不涉及时间因素(关联过程“根本不需要任何时间”),也无所谓“速度”。虽然它是一种货真价实的物理现象,但它更像是一种逻辑上的关联。当然,“超光速”可以作为形容词来看待。
李:那么,“量子远程关联”究竟对“量子通信”有无价值?为什么?
桂:我们的回答和解释是,尽管经典信息论关于信号的发送、传递、接收等概念都将失去原始含义,然而基于远程关联性,信宿与信源两端通过编码译码提取有用信息互通有无,比超级特快专递还要好得多,想必具有全新意义的通讯价值。①桂起权、姜小慧:《EPR悖论、量子远程关联及其判决性实验》,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