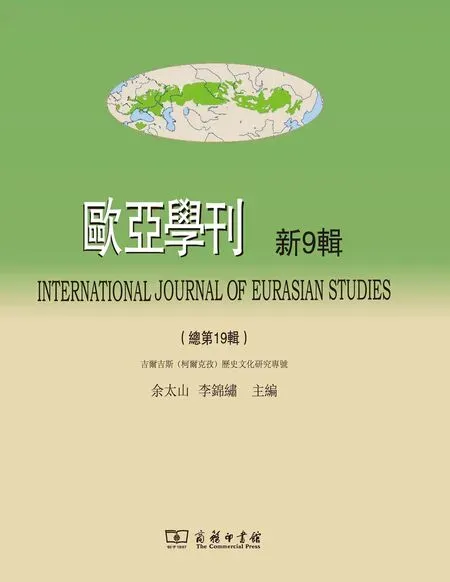會昌、大中年間黠戛斯來唐的翻譯問題
李錦繡
會昌年間,成爲漠北霸主的黠戛斯四次遣使來唐。唐高規格接待了這些使臣,并四次頒下“與黠戛斯可汗書”。但由於雙方翻譯人員水平不夠,在唐按禮制迎送使臣、接轉文書和會見使臣、瞭解國風等一系列活動中,多存在翻譯問題。本文分析了會昌和大中年間唐接待黠戛斯使臣活動中誤譯現象,并探討了誤譯產生的原因和影響。
唐開成五年(840),漠北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黠戛斯取代回鶻,成爲漠北霸主。會昌三年(843)二月,與唐中斷聯係近百年a黠戛斯與唐中斷聯係前的最後一次遣使是天寶六載(747)。見(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鳳凰出版社,2006 年,第11243 頁;并參(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錄》,中華書局,1955 年,第1303 頁。會昌二年(842)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二四六“會昌二年十月”條,中華書局,1956 年,第7968 頁)。其間相隔95 年。之久的黠戛斯遣使至長安。“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脩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并將使者繪入《朝貢圖》b李德裕:《進黠戛斯朝貢圖傳狀》,見(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一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347 頁;《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地理類》有“呂述《黠戞斯朝貢圖傳》一卷”,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 年,第6150、1508 頁。,“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c《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50 頁。,給予了高規格的接待。會昌年間,黠戛斯共有四次遣使來唐,唐按禮制迎來送往,降詔派使,宰臣李德裕親自起草詔書。會昌年間唐與黠戛斯的交互往來,爲晚唐時期罕見的外交盛事,爲日漸衰落的唐朝涂上了一抹“四夷來庭”d李德裕:《黠戛斯朝貢圖傳序》,《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二,第20—21 頁。的中興色彩,也對動蕩的漠北政治格局影響巨大。
對會昌年間唐與黠戛斯的關係,中外學者進行了詳細解說,尤以岑仲勉a岑仲勉:《李德裕〈會昌伐叛集〉編證上》,《史學專刊》2 卷1 期,1937 年,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 年,第343—461 頁。、中島琢美b中島琢美:《會昌年間に于けるキルギス使節団の到來に就いて(一)》,《史游》10,1983 年,第5—16 頁。、金子修一c金子修一:《唐代の國際文書形式について》,《史學雑志》83 (10),1974 年,第29—51 頁。、傅璇琮、周建國d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DromppeDrompp, M. R.,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5, pp.125-158, 288-311.、王潔f王潔:《黠戛斯歷史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齊會君g齊會君:《唐のキルギス宛國書の発給順と撰文過程:ウイグル·キルギス交替期を中心に》,《東洋學報:東洋文庫和文紀要》100 (1),2018 年,第1—31 頁。等學者貢獻較大。黠戛斯遣使來唐的時間、使人及唐的回應,以及唐與黠戛斯國書的格式等,已基本清晰。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試對黠戛斯與唐往來中的翻譯問題提出一些補充意見,請方家指正。
一
譯語人是不同語言族群和國家之間溝通交流的媒介。譯語人的漢學及民族語文、外文造詣,影響翻譯質量;而不準確的翻譯,不稱職的譯語人,往往會對民族關係產生不利影響,甚至釀成外交事故。
會昌年間黠戛斯使者來唐,唐之君臣高度重視。但在唐舉行的迎送及宴請使者、瞭解國風和國書接轉的一系列活動中,出現了一些誤譯和誤解的問題,與高規格的接待不相符。據筆者考證,會昌年間唐與黠戛斯交往中,官方在翻譯上的失誤或誤譯現象至少有四次。茲依次敘述如下。
1.“職使”與“刺史”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對黠戛斯民風、土俗、官制、法律等都有較詳細記載,其官制記載如下:
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員。h《新唐書》,第6148 頁。
從中可以看到黠戛斯使用的官稱有唐制和突厥制兩種i參王潔:《黠戛斯汗國政治制度淺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10 年第3 期,第116—119 頁。,這是對黠戛斯官員設置和官吏制度較爲詳細的記錄。但諸官名中,有一處翻譯錯誤。要探討音譯之誤的發生時間,首先要明確唐人何時通過何種途徑瞭解到黠戛斯的官制信息,亦即先要確定此段記載的史料來源及其時間性。
唐宋時期,《通典》、《唐會要》、《新唐書》、《太平寰宇記》、《冊府元龜》等都有關於黠戛斯土風的記載,但諸書史料來源和時間性并不一致。《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四夷二十八·北狄十一·黠戞斯》云:
黠戞斯……其人身悉長大,赤髮,緑睛。有黑髮者,謂之不祥。蓋嘉惠(運)撰《西域記》云:“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也,故其自稱是都尉苗裔。”
其五金出鐵與錫,《王會圖》云:“其國每有天雨鐵,收之以爲刀劍,異于常鐵。”曾問使者,隱而不答,但云鐵甚堅利,工亦精巧,蓋是其地中産鐵,因暴雨淙樹而出,既久經土蝕,故精利爾,若每從天而雨,則人畜必遭擊殺,理固不通。賈躭曰:“俗出好鐵,號曰迦沙,每輸之于突厥。”此其實也。a(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7 年,第3820—3823 頁。
《太平寰宇記》較多記錄了史料來源,這一段引用了蓋嘉運的《西域記》、《王會圖》和賈耽的著作。其中,蓋嘉運開元二十二年(734)至開元二十九年(741)之間,連續擔任北庭節度使、磧西節度使和河西、隴右節度使b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 年,第1232—1233、1221、1203 頁。,這一經歷是他撰寫《西域記》的基礎。因而《西域記》記錄的是開元天寶年間西域情况。《王會圖》應該是《王會篇》c(宋)董逌撰《廣川畫跋》卷二《上〈王會圖〉敘錄》云:“顔籒請比周之王會作《圖》以敘傳後世,使著事得以考焉。又爲《王會篇》上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于安瀾編:《畫品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255 頁)可見與圖并行的說明文字名爲《王會篇》。《王會篇》在宋代仍存,故而能被宋代史家徵引。。貞觀三年(629),因東謝蠻入朝,顏師古建議圖寫爲《王會圖》d《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第6320 頁。,《王會圖》由閻立德繪e湯開建:《唐〈王會圖〉雜考》,《民族研究》2011 年第1 期,第77—85 頁。,并有說明諸國風俗文字,稱爲《王會篇》,而這種說明文字在貞觀三年之後仍然繼續撰寫,貞觀中來唐蕃國皆被著錄,故而貞觀十七年(643)始派使者來唐的堅昆f《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黠戛斯》,第3820 頁。在其中。《王會篇》反映的是貞觀年間唐對蕃國的認知。《太平寰宇記》所引賈耽之言,出自其著《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此書共40 卷g《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第1506 頁。,又簡稱爲《華夷述》h《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詔敕中”下注,第79 頁。,成書於貞元十七年(801)i《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貞元十七年十月”條,第395 頁。參見丁超:《唐代賈耽的地理(地圖)著述及其地圖學成績再評價》,《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 年第3 期,第146—156 頁。,反映的是貞元年間唐域內和外蕃的情况。再加上會昌年間太子詹事韋宗卿、秘書少監呂述編纂的《黠戛斯朝貢圖傳》,《新唐書》、《太平寰宇記》、《唐會要》的黠戛斯部分,分別取材了貞觀年間的《王會篇》、開元天寶年間的蓋嘉運《西域記》、貞元末的《華夷述》和會昌年間的《黠戛斯朝貢圖傳》。《通典》成書於貞元十七年a王文錦:《點校前言》,點校本《通典》,第1—2 頁。,從完成時間看,其取材當局限於《王會篇》和《西域記》。對比《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結骨”條與《太平寰宇記》及《唐會要》所引《西域記》,可以推知《通典》“結骨”條并未引《西域記》的內容,《通典》的記載來源於貞觀年間的《王會篇》。以此爲基準,《新唐書》、《太平寰宇記》“黠戛斯”條的史料來源則可以推知了。
《通典》未記載結骨國的官制。《新唐書》、《太平寰宇記》兼取諸書,但關於黠戛斯官制的記載,則取自《黠戛斯朝貢圖傳》,亦即“太子詹事韋宗卿、祕書少監吕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覿,稽合同異,覼縷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所完成的“條貫周備,文理洽通”b李德裕:《黠戛斯朝貢圖傳序》,《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二,第21 頁。的著作。“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是韋宗卿、呂述至黠戛斯使者所住之客館,經由翻譯,從黠戛斯使者注吾合索等處瞭解到的官制信息。
韋宗卿、呂述等至客館,按制度要由鴻臚寺譯語人陪同。《唐會要》卷六六《鴻臚寺》載開元十九年(731)十二月十三日敕,云:
鴻臚當司官吏以下,各施門籍出入。其譯語、掌客出入客館者,於長官下狀牒館門,然後與監門相兼出入。c《唐會要》,第1151 頁。
鴻臚譯語、掌客出入客館,安排、陪同蕃使在唐生活和活動,瞭解外蕃土地、風俗、物產等信息d龍惠珠指出,鴻臚譯語安排蕃使會談,通過直接詢問而不是被動翻譯瞭解外蕃土地、風俗、物産等地理信息,具有較高的翻譯技巧和語言交流能力。見Lung, R., 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pp.65-68。,是譯語人和掌客的主要職掌。掌客之職此不贅論,據敕文可知譯語人是要出入客館,協助翻譯的。因黠戛斯隔絕近百年再次來唐,唐朝野轟動,故而高級別對待,與譯語人同時出入客館的是更高官太子詹事韋宗卿和秘書少監呂述,二人經由翻譯與黠戛斯使者交流,瞭解黠戛斯的土俗風物,編纂了《黠戛斯朝貢圖傳》。這一卷著作成爲《新唐書》、《太平寰宇記》“黠戛斯”部分的主要史料來源。
黠戛斯官制的記載就來源於《黠戛斯朝貢圖傳》。在《新唐書》和《太平寰宇記》e《太平寰宇記》,第3820 頁。的記述中,顯而易見的是黠戛斯官稱中的都督(Tutuq)、長史(Čangši)、將軍(Sängün)、達干(Tarqan)是音譯,都督、長史、將軍都是漢官名,而達干是沿用的突厥官稱。“宰相”是對黠戛斯官名梅祿(Buyruq)的意譯,梅祿之職相當於唐之宰相,而不是黠戛斯設有名爲“宰相”的官員。梅祿(宰相)、達干是突厥官稱。
值得注意的是“職使”。職使[ʨiək-ʃǐə]f本文所構擬的中古音,皆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以下不再一一注出。不是對突厥官稱的音譯和意譯,實際上,它是漢官刺史[ʧʻièk-ʃǐə]的音譯,在古突厥語中作Čigšia岑仲勉:《突厥集史》(下),中華書局,2004 年,第725 頁。韓儒林:《唐代都波新探》,《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326—331 頁。。刺史和都督等一樣,都是漢官稱。貞觀二十一年(647)正月丙申(九日),唐太宗“詔以迴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别部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顔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b《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第6244—6245 頁。。這是唐在漠北建立的羈縻州府制度,鐵勒諸部酋長被授予都督、刺史。貞觀二十二年(648)二月,黠戛斯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唐,唐太宗宴之於天成殿,“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七日),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䕶”c《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第6252 頁。,黠戛斯也納入唐在漠北設置的羈縻州府中。唐將軍、都督、刺史等官稱,這時開始影響黠戛斯。黠戛斯都督、刺史之設,和唐代設於漠北的羈縻體制直接相關。
黠戛斯的刺史官稱,是借自唐官名,音譯爲Čigši。但在韋宗卿和呂述在客館與黠戛斯使者面談時,譯者不明Čigši 一詞來源,誤譯作讀音相近的“職使”。這種失誤,已近乎數典忘祖了。將刺史誤譯爲職使,表明譯者不僅不熟悉唐官制,而且對黠戛斯語言的讀音,也掌握不確。此譯者的漢語和黠戛斯語水平都大有問題。
2.“注吾合素”、“注吾合索”與“行三歲至京師”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又云:
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於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京師。
此段也有幾處誤譯者。
首先是使者的姓名。《新唐書》和李德裕《黠戛斯朝貢圖傳序》、《與黠戛王書》d《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二,《李衛公集補》,第21、713—714 頁。均作“注吾合素”,應該是據《黠戛斯朝貢圖傳》中的記載。但《唐會要》卷一〇〇《結骨國》云:
會昌三年,其國遣使注吾合索(上聲呼之)等七人来朝,兼獻馬二匹。e《唐會要》,第1785 頁;王應麟輯《玉海》卷一五三《朝貢·外夷來朝》“唐黠戞斯入朝”條引《會要》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1988 年,第2810 頁)。
《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二月”條作“注吾合索”,其下《考異》云:
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a《資治通鑑》,第7973—7974 頁。
則知唐《武宗實錄》作“注吾合索”,《唐會要》和《資治通鑑》均引自《實錄》。“索”并非與“素”形近致誤,因爲《會要》特意在“索”字下注“上聲呼之”,與去聲的“素”是不同的。“索”、“素”的古音也不同,“索”的中古音爲sak,“素”的中古音爲su。
《新唐書》所謂的“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當是據陪呂述等至客館的譯語人所言,呂述等將之寫入《黠戛斯朝貢圖傳》中,故而保存了當時的翻譯之語。而《新唐書》、李德裕的《序》及《與黠戛王書》對譯者所言深信不疑,故而將使者之名寫作“注吾合素”。但《實錄》中“注吾合索”的譯名,提示了隨呂述等入客館的譯語人誤譯的可能性。素[su]可以對應突厥語中的sōl,其意爲“左”bClauson, G.,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824. Dankoff, R. and Kelly J., tr.,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Washington, D. 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5.,索[sak]則對應突厥語中的sāγ,在烏古斯語中,其意主要爲“智慧”、“潔凈”、“健康”、“正直”、“右”等cClauson, op. cit., p. 803; Dankoff and Kelly, op. cit., p.152.。隨呂述入客館的譯者將使名譯爲“左”(sōl),故而認爲使名爲“素”,而《實錄》中所體現的另一位譯者將使名讀爲sāγ(智慧、純凈等),故而記錄使名爲“索”。
由此看來,“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的翻譯是存在問題的。突厥語alp(勇敢)dClauson, op. cit., p. 127.音譯爲“合”[γəp],是正確的。注吾[ʨiu-ɳu]筆者尚無法復原,譯語人未譯而籠統稱爲“虜姓”,是否正確,待考。如果將使者名讀爲“注吾合索”,其“謂武猛善左射者”,則有了想當然的成分。
其次,黠戛斯使者“行三歲至京師”的時間有誤。
迴紇“去長安六千九百里”e《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第5195 頁。《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作“距京師七千里”(第6111 頁),爲舉其約數,見劉義棠:《突回研究》,臺北經世書局,1990 年,第758 頁。《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迴紇”條作“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第5491 頁),“萬”爲衍文。,“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f《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結骨”條,第5492 頁。《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記載:“直回紇西北三千里。”(第6146 頁),則黠戛斯去京師9900 里。若以日行百里g《隋書》卷八三《西域傳》記載高昌國“去敦煌十三日行”([唐]魏徵等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 年,第1846 頁),而(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裴矩《西域記》云:‘[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注,中華書局,1975 年,第3175 頁)《隋書》及《史記正義》均引自裴矩《西域圖記》(參內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內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 年,第115—128 頁)。“十三日行”等同於“一千三百里”,則知隋唐時期計算里程標準是日行百里。《新唐書》卷二一七下記載,黠戛斯“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第6148 頁),這是最慢的行程,馬行要比駱駝快得多。計,也只有百天而已。黠戛斯破回鶻後,遣至牢山(賭滿)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h《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50 頁。,則自牢山之南至長安,要行84 日(15+69)。故“行三歲”可能指的是“行三月”。
另一種可能則是注吾合索等人解釋來唐緣由,“黠戞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逹干十人奉公主歸之唐”,但“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逹干,盡殺之,質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a《資治通鑑》卷二四六“會昌元年十月”條,第7957 頁;《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第5213—5214 頁。,黠戛斯破回鶻後第一次與唐聯繫失敗。而“會昌中,[黠戛斯]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b《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50 頁。。注吾合索至京師,距黠戛斯第一次遣使護送公主,已經過去了三年。會昌二年(842),黠戛斯使者“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c《資治通鑑》卷二四六,第7968 頁。。但踏布合祖等未至京師。注吾合索等是自黠戛斯遣使護公主至唐後,第一個至京師的使團,故而強調經過了三年才至京師。而譯語人未能將注吾合索等人的敘述經過及複雜的歷程翻譯出來,只譯爲“行三歲至京師”,造成了唐朝野及後世的誤解。
3.“黃頭赤面”
會昌年間譯語人第三個失誤爲對“黠戛斯”含義的隨意解釋。
關於“黠戛斯”一詞的含義,《唐會要》卷一〇〇《結骨國》記載云:
結骨……身身悉長大,皙面,而綠睛、朱髪。有黑髪以爲不祥……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運撰《西域記》云:“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由然。”今有改稱紇扢斯者,亦是北夷舊號。臣按《國史》敘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則有契弊、烏䕶、紇骨子。”其契弊即契苾也,烏䕶則烏紇也,後爲迴鶻。其紇骨即紇扢斯也。由是而言,盖鐵勒之種,嘗以稱迴鶻(紇骨)d此處之“迴鶻”,當爲“紇骨”之誤,據《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譯》(第11527 頁)改。矣。其轉爲黠戛斯者,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其或稱戛戛斯者,語急而然耳。訪於譯史,云“黠戛[斯]e據《冊府元龜》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譯》(第11527 頁)補。是黃頭赤面義”。蓋迴鶻呼之如此。今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孰是。f《唐會要》,第1784—1785 頁。
此段記錄了唐人對黠戛斯得名的認識,根據“譯史”所言,黠戛斯乃“黃頭赤面”之意。《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云:
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g《新唐書》,第6149 頁。
《新傳》之“黃赤面”當是“黃頭赤面”之省,雖文字詳略不同,但與《會要》的史料來源是相同的。
“黃頭赤面”的解說來自“譯史”,即譯語人。需要考證的是,這個猜測“黃頭赤面”的“譯史”是什么時候的人?易言之,黠戛斯何時被解釋成了“黃頭赤面”?
點校本《唐會要》a《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2120 頁。和校訂本《冊府元龜》b《冊府元龜》,第11527 頁。都將自“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至“未知孰是”一段放入引號中,認爲是蓋嘉運《西域記》中的話。但“今有改稱紇扢斯者”以下,出現了“回鶻”一詞。迴紇改稱回鶻,史籍中有貞元四年(788)c《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第6124 頁。、五年(789)d《唐會要》卷九八《迴紇》,第1746 頁。和元和四年(809)e《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第5210 頁。等多種記載,f參見宋肅瀛:《回紇改名“回鶻”的史籍與事實考》,《民族研究》1995 年第6 期,第80—92 頁。本文不詳考。而開元天寶年間撰寫的《西域記》中,不可能出現“回鶻”一詞。而文中的“臣案”,“今使者稱自有此名”,也與蓋嘉運所撰《西域記》不符。因此,“今有改稱紇扢斯者”以下,當不是蓋嘉運《西域記》中的文字(《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引《西域記》只到“故其自稱是都尉苗裔”g《太平寰宇記》,第3820 頁。,可爲例證),需要重新考證其時間性。
“紇扢斯”一詞,最早見於李德裕會昌元年(841)十二月撰寫的《遣王會安撫回鶻制》、《賜回鶻可汗書》h《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三、卷五,第26—27、62—63 頁。,有“近聞爲紇扢斯所敗”句。“近聞”之聞,當聞之回鶻。易言之,“紇扢斯”一詞,首見於回鶻國破後上報唐朝的國書中。回鶻可汗給唐國書,當用回鶻文,唐君臣所讀者,是中書省翻書譯語直官i詳見拙著:《唐代的翻書譯語直官:從史訶耽墓誌談起》,《晋陽學刊》2016 年第5 期,第35—57 頁。所譯成的漢文本。故而“紇扢斯”一詞,是會昌初唐譯語人對回鶻文Qïrqïz 的音譯。李德裕稱“黠戛斯國號皆依蕃書譯字,所以不同”j《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79 頁。,“蕃書”指的是來自回鶻之書,“譯字”指的是漢譯爲“紇扢斯”等字。唐從回鶻的稱謂中知道了“堅昆”、“結骨”的異名,故而認爲“紇扢斯”是“蓋迴鶻呼之如此”。會昌三年,李德裕與武宗商量冊封黠戛斯時,依據賈耽的《華夷述》,“便以黠戛斯爲定”k《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79 頁。,黠戛斯之名才確定下來。
據此,筆者認爲《會要》“今有改稱紇扢斯者”以下文字,是會昌年間的《黠戛斯朝貢圖傳》中的內容。其中“臣案”之“臣”,是韋宗卿和呂述,“使者”指的是來唐的注吾合索等。而“譯史”,仍然是隨韋宗卿、呂述至客館的譯語人。對黠戛斯“黃頭赤面”的解說,就是這位譯者的獨創。
黠 戛 斯[γæt-kět-sǐe]、戛 戛 斯[kět-kět-sǐe]、紇 扢 斯[γət-kat-sǐe]等 均 爲Qïrqïz 的 音 譯,Qïrqïz 在古突厥碑銘中既已出現。關於Qïrqïz 的本意,中外學者有不同的解說,一般認爲與Qïrq(四十)有關。aLigeti, L., “Die Herkunft des Volksnamens Kirgis”, Korösi Csoma Archivum 1, 1921-1925, pp.369-383; Kowalski, T., “Die Erkälrung des Namens Kirgis”, Korösi Csoma Archivum 2, 1926-1932, pp.197-198; Pullyblank, E. G., “The Name of the Kirghiz”,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34, No. 1-2, 1990, pp. 98-108.陳慶隆結合吉爾吉斯人的傳說,認爲Qïrqïz < Qïrq(四十)+ Qïz(女郎)b陳慶隆:《堅昆、黠戛斯與布魯特考》,《大陸雜志》51 卷5 期,1975 年;收入李錦繡編:《20 世紀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研究論文選粹》(第二輯),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193—212 頁。,更令人信服。
會昌譯語人所謂的“黃頭赤面”,是將Qïrqïz 解釋爲Qïzïl yüz,即赤面,因爲黃頭[髪]的突厥語爲Sarïγ sač,與黠戛斯實在無法對音。譯語人說黠戛斯語源爲“黃頭赤面”,乃屬隨意解釋。推其原因,則是因爲“譯史”并不理解Qïrqïz 的詞源和漢譯,將之理解爲Qïzïl yüz(赤面),又覺得與常情不符,故而加了黃頭成爲“黃頭赤面”。這一錯誤翻譯,遂使黠戛斯詞源被誤解了近千年。
黠戛斯人的體貌特徵,唐宋史籍中多有記載。取材於貞觀《王會篇》的《通典》記載,結骨“人並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c《通典》卷二〇〇《邊防一六·北狄七》“結骨”,第5492 頁。。這里的“赤色”,可能爲“赤須”之誤。因爲《酉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云: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人髪黃目緑,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d(唐)段成式撰,許逸民、許桁點校:《酉陽雜俎》,中華書局,2018 年,第109 頁。黠戛斯人髭髯赤色。結合上引《太平寰宇記》“身悉長大,皙面,而綠睛、朱髪”,可以得出貞觀時期黠戛斯人的體貌特徵爲:身材高大,皙面,赤髭髯,朱髪,綠睛。這一時期,“有黑髮者,以爲不祥”。
貞觀末與唐交往後,黠戛斯人對黑髪者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將黑髪、黑睛者,和漢將李陵聯繫起來。景龍中,黠戛斯來唐“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e《新唐書》卷二一七,第6149 頁。。唐自認爲出自隴西李氏,爲涼武昭王之後,而李陵爲涼武昭王之先祖。李唐先祖世系有“[李]尚生廣,前將軍。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騎都尉;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f《新唐書》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第1956 頁。。唐認李陵爲祖先,黠戛斯認爲黑髪、黑睛者是李陵之後,因而唐與黠戛斯有了“同宗”之意。經過中宗的大力宣揚,黠戛斯與唐也建立了“宗盟”關係。黠戛斯黑髪、黑睛者地位提升,在蓋嘉運《西域記》中,已無“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之句,代之而來的是“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蓋嘉運據此認爲:“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由然。”
會昌年間來唐的注吾合索等人,與貞觀《王會篇》中所描寫的體貌有較大區別。宋人董逌比較貞觀《王會圖》與會昌《黠戛斯朝貢圖》中黠戛斯使人形象,揭示了百余年來的變化。其文云:
唐自貞觀逮會昌百餘年矣。其風聲習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謬誤可考。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緑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爲帽,而又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a《畫品叢書》,第255—256 頁。
會昌年間,黠戛斯使臣從貞觀時的“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緑睛”,變爲“形質不長,面赤色”,可能分屬於不同的部落。會昌時的黠戛斯“形質不長,面赤色”之部成爲汗國上層,充使來唐。也正因爲黠戛斯使臣呈“面赤色”的特徵,鴻臚寺譯語人才隨意將黠戛斯錯誤地解釋爲“黃頭赤面”之義。
4.“兩地遣書,彼此不會”
會昌年間譯語人的第四個誤譯,出現在唐與黠戛斯國書的往來中。
李德裕奉武宗旨撰《赐黠戛斯書》,記錄了黠戛斯來書和唐報答情况,其文云: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并白馬二疋,具悉……來書云:“溫仵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仵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遣使,只自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每欲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徳伊斯難珠,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逹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弘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将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b《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89—90 頁。參《冊府元龜》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第11350—11351 頁;卷九九四《外臣部·備禦七》,第11508—11509 頁。
黠戛斯來書中的“兩地遣書,彼此不會”,表明對翻譯不滿意,雙方交流不暢。可見雙方交往中的翻譯問題,影響了彼此關係。
黠戛斯的誤解之一,在於“溫仵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根據李德裕撰《與黠戛斯可汗書》,唐在溫仵合將軍歸國時送的國書中如此寫道:
皇帝敬問黠戞斯可汗,溫仵合將軍至,覽書及領所獻馬百匹、鶻十聯,具悉……朕以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将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温仵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舉留犂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朕撫有中夏,愛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略,遥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a《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83—85 頁。
唐希望黠戛斯以“堅昆”爲國號,并在溫仵合來唐時,禮部尚書鄭肅等親自與温仵合面談了以堅昆爲國之意。李德裕在《進所撰黠戛斯書狀》中向武宗匯報說:“臣請待鄭肅等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b《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87 頁。可見是鄭肅等先與黠戛斯使臣面談後,唐再頒下詔書。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鄭肅等會談的結果,《與黠戛斯可汗書》中提到“溫仵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唐認爲會談取得成效。但從將軍諦德伊斯難珠所帶國書中,并未有對堅昆的答復。很顯然“願言結成”只是唐的一廂情愿,與溫仵合的會談并未取得唐所期望的效果。究其原因,當是翻譯中存在問題。陪同禮部尚書鄭肅至客館的是鴻臚寺的譯語人,從結果看,此譯語人并未將唐堅持以堅昆爲國名一事與黠戛斯使臣順利溝通,因而造成了皆大歡喜又彼此誤解的結局。這是唐譯語人的翻譯之誤。
而在《與黠戛斯可汗書》中,最後的“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黠戛斯的翻譯人理解爲“溫仵合將軍歸國後,漢使即來冊命”,也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於是唐廷空待黠戛斯對堅昆國回復的表章,而黠戛斯則空待唐之冊命使者。雙方譯者都未能將面談與國書內容準確翻譯,造成了彼此的誤解和隔閡。
會昌三年黠戛斯使者來唐後,唐君臣對是否冊封黠戛斯可汗事展開討論,并已做出決斷。《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二月”條云: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
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a《資治通鑑》,第7974 頁。
武宗同意了李德裕的冊封黠戛斯可汗的意見,決定冊封與“敘同姓以親之”并行,與黠戛斯確立“宗盟”關係。而在具體實施中,關於冊封之名,“彼此不會”,拖延了一年之久;而將黠戛斯阿熱“著宗正屬籍”b《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50 頁。關於“阿熱著宗正屬籍”事,筆者將另撰文研究,此不贅述。事,也不了了之。之後唐與黠戛斯在冊封一事上反復討論,至會昌五年(845)五月唐才頒布“黠戛斯爲可汗制”c(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二八《黠戛斯爲可汗制》,商務印書館,1959 年,第692 頁;參《唐會要》卷一〇〇《結骨國》,第1785—1786 頁;《資治通鑑》卷二四八作:“詔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第8015 頁)。唐冊封黠戛斯可汗事的遷延曲折,主要原因在於雙方翻譯不確、溝通不暢,黠戛斯來書中的“兩地遣書,彼此不會”準確地指出了雙方交流的癥結所在。
以上我們論述了會昌年間唐與黠戛斯交往中存在的四個翻譯問題。除第四次黠戛斯譯者對唐國書也有誤譯外,其余幾次主要都是唐譯語人之失。黠戛斯與唐不但“兩地遣書,彼此不會”,而且在面談中,誤譯、誤解也在所難免。這表明會昌年間唐與黠戛斯交往中,譯語人低劣的翻譯水平令人堪憂。
這些誤譯與誤解,成爲唐與黠戛斯交往中的不和諧因素。這些誤譯對唐與黠戛斯的交往歷程影響不同,其中前三個誤譯,多屬於文化上的誤解,對兩國關係無直接的不利影響。而在冊封中存在誤譯和誤解,影響了唐冊封黠戛斯可汗的進程,成爲矛盾的癥結所在,甚至也間接影響到漠北的政治格局,不能不引人重視。
二
會昌年間爲唐與黠戛斯交往的高峰期。大中年間黠戛斯是否遣使來唐,史籍記載闕如。但在出土《崔鐬墓誌》中,記錄了一次宣宗朝黠戛斯來使的情况,而且與我們論述相關的是,這次黠戛斯來唐,正因爲存在誤譯現象,才被記錄在《崔鐬墓誌》中。
爲了便於分析,茲將崔鐬之侄“朝請郎、行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校理”崔沆所撰《崔鐬墓誌》引之如下:
府君諱鐬,字節卿……皇考元略,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贈太師……府君即太師府君第四子也……後歷太府、光祿、司農三少卿,其間累年。府君季父及沆嚴君迭秉鈞軸,由是府君踐歷,悉多久次。府君孝友恬默,未嘗爲言。
先帝時,丞相龜從一日于便殿言府君之屈,即日擢拜權知鴻臚卿,久而得真秩。時黠戛斯遣使朝貢,有稱敕使者,府君曰:“是必重譯之失也。以此名號奏御,于理未安。”乃命舌人言覆,果曰隻,使聲之悮也。其爲精識,又如是。尋拜將作監兼內作使……改光祿卿……去歲春孟……授宋州刺史……無何遘疾,以咸通三年正月廿九日,終于官舍,享年四十七。a《唐故朝請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守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鎮遏使上柱國博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左散騎常侍崔府君(鐬)墓誌銘并序》,《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403—405 頁。
崔鐬父崔元略,兩《唐書》有傳,後附元略子鉉、鉉子沆及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之傳,但未提及崔鐬。b《舊唐書》卷一六三《崔元略傳》,第4260—4263 頁;《新唐書》卷一六〇《崔元略傳》,第4973—4975 頁。崔元略長子鉉(即崔沆之父)久負盛名,武宗時爲相,崔鐬隱沒在其兄光環之後,聲名不顯。《新唐書》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中,崔元略之子只列了鉉與鎡二人c《新唐書》,第2788—2789 頁。,沒有崔鐬,當據墓誌補入。墓誌云崔鐬因其兄崔鉉及其季父崔元式在朝爲相,故而官位久久得不到提昇。考崔鉉爲相時間有兩次,分別在會昌三年(843)五月至會昌五年五月,大中三年(849)四月至大中九年(855)七月;崔元式爲相在大中元年(847)三月至大中二年(848)正月。d《新唐書》卷六三《宰相表》,第1727—1732 頁。在會昌和大中初,崔鐬一直在九寺少卿的職位上徘徊,直至崔龜從爲相時,才有昇遷的機會。考崔龜從在大中四年(850)六月至大中五年十一月任宰相e《新唐書》卷六三《宰相表》,第1731 頁;同書卷一六〇《崔龜從傳》,第4976 頁。,崔鐬“擢拜權知鴻臚卿”當在這期間。“久而得真秩”,即正拜鴻臚卿。黠戛斯遣使朝貢,就發生在崔鐬任鴻臚卿之時,由於無法推知“久而得真秩”之“久”是多長時間,無法判斷黠戛斯朝貢的具體年代。崔鐬任鴻臚卿後,又任將作監、光祿卿,并於去世前的一年咸通二年(861)任宋州刺史f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五六《宋州》部分(安徽大學出版社,第780 頁)未有崔鐬任宋州刺史記載,應補入。,以一任三年推算,崔鐬任鴻臚卿的時間當在大中六年(852)至大中八年(854)。這與崔龜從大中四年或五年推薦崔鐬“權知鴻臚卿”也不矛盾。據此,筆者將“黠戛斯遣使朝貢”的時間,定在大中六年至八年之間。g胡可先、咸曉婷《〈唐九卿考〉訂補》(《湖南大學學報》2009 年第2 期,第65 頁)一文,認爲崔鐬權知鴻臚卿在大中四年六月後。
大中元年(847)六月,“務反會昌之政”h《資治通鑑》卷二四八“大中元年閏三月”條,第8030 頁。的宣宗考慮到漠北與河西的政治軍事形勢,“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i《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第6150 頁;《資治通鑑》卷二四八“大中元年六月”條,第8030 頁。《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作:“(大中元年六月),冊黠戛斯王子爲英武誠明可汗,命鴻臚卿李業入蕃冊拜。”(第618 頁)似大中初黠戛斯也發生了權力更迭。。唐冊封之後,黠戛斯應與唐來往不斷。崔鐬任鴻臚卿時黠戛斯“遣使朝貢”,是其中的一次。
這一次接待黠戛斯使臣之時,卻在使者姓名的翻譯上出了問題。“敕”,中古音爲ȶ‘ǐək;“隻”,中古音爲ʨǐek。二者讀音極爲接近。黠戛斯貢使名音譯爲“敕”、爲“隻”,從讀音上來說,都不能算錯。但上奏皇帝,却不能用“敕”之名。唐代公文,“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冊)”a(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中華書局,2014 年,第10 頁。。皇帝頒下的詔令才能稱敕。唐初,突厥爲東亞霸主,唐與突厥在文書稱謂上進行了多番較量。《舊唐書》卷八三《張儉傳》記載:
貞觀初,〔張儉〕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禀。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b《舊唐書》,第2775 頁。
突厥給朔州的文書,使用了皇帝對臣民的敕的格式,以表明唐對突厥的臣屬關係。張儉拒不接受,嚴守唐獨立的立場,受到太宗稱贊。二百多年後,鴻臚卿崔鐬仍對“敕”字敏感。如果以“敕”名上奏,唐帝接見黠戛斯使節時稱其名爲“敕”,會令人誤以爲唐臣屬於黠戛斯,故而崔鐬堅持重新翻譯使者之名,用發音相近的“隻”字代替,圓滿地解決了問題。這次“敕”、“隻”之譯,雖不足以說明鴻臚譯者蕃語水平,但至少反映了譯語人漢語水平不高,說明晚唐時鴻臚譯語人漢語水平已大爲下降。缺乏忠誠可靠、蕃漢兼通的譯語人,應是晚唐翻譯界的普遍現象,與盛唐時的氣象不可同日而語了。
黠戛斯使臣之名可考者,有會昌二年(842)十月的“踏布合祖、達干遏悉禾、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己時等七人”c李德裕:《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八,第143—144 頁。,會昌三年二月的注吾合索(素)d《唐會要》卷一〇〇《結骨國》,第1784 頁。參《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二月辛未”條,第7973 頁;《舊唐書》卷一八《武宗紀》,第595 頁。,會昌三年六月的溫仵合e《資治通鑑》,第7985 頁。參李德裕:《與黠戛斯可汗書》,《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83 頁。,會昌四年二月的諦德伊斯難珠f《資治通鑑》卷二四七“會昌四年二月”條,第7999 頁。參李德裕:《賜黠戛斯書》,《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六,第88 頁。《冊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五》將諦德伊斯難珠入唐時間記爲會昌三年八月,見第11252 頁。。會昌年間使者之名沒有與“敕”相似的讀音,因而會昌年間沒有發生類似的翻譯事故。咸通年間,黠戛斯使臣名分別爲“合伊難支”、“乙支連幾”g《資治通鑑》卷二五〇“咸通四年八月”條、“咸通七年十二月”條,第8107、8117 頁。。“支”,中古音爲ʨǐe,與“敕”、“隻”讀音接近。可能是大中中期以後,爲避免音譯爲“敕”的錯誤,鴻臚譯語人選擇了“支”作爲類似使臣名稱的音譯。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黠戛斯傳》記載:“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黠戛斯與回鶻語同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二者是方言之別。《唐書》記載其語言同回鶻語,可見鴻臚尋找負責接待黠戛斯的翻譯是懂回鶻語之人。《崔鐬墓誌》中稱此次失誤爲“重譯之失”,表明譯者的母語可能不是回鶻語,譯者可能是粟特人,經過了回鶻(黠戛斯)、粟特、漢語多重轉換的翻譯過程。稱“重譯”,表明唐沒有能將漢語與黠戛斯語直接翻譯的譯者。而譯者不知“敕”字之用,可見其漢文水平之低。
三
在唐與外蕃的交往中,譯語人必不可少。唐代譯語人可分民間和官方兩種。民間譯語人因時因事而充任,多在市場和寺院等地活動;外蕃來唐貿易、朝貢、傳教、求法求學的隊伍中,也常活躍著譯人的身影。官府譯語人普遍存在於中央機構(中書省、鴻臚寺)、邊州和軍隊中。邊州的譯語人,或在多民族訴訟事務和涉外行政中發揮作用,或在邊境互市中充任互市牙郎等。
唐代史籍中記載了“譯語人”,中外學者研究較多,成果斐然。a相關研究,詳見謝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第189—192 页;Denis Sinor, “Interpreter in Medieval Inner Asia”, Asia and Afric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Israel Oriental Studies 16, 1982, pp.293-320(中译見《鄧尼斯· 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 年,第189—222 頁);王欣:《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譯語人”》,《新疆文物》1993 年第1 期,第150—155 頁;李方:《唐西州的譯語人》,《文物》1994 年第2 期,第45—51 頁;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206—211 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335—336、361—363、466—467頁:馬榮國:《唐鴻臚寺述論》,《西域研究》1999 年第2 期,第20—28 頁;馬一虹:《古代東アジアのなかの通事と譯語—唐と日本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遊學》第3 號,1999 年,第112—114 頁;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中華書局,2000 年,第298—301 頁;韓香:《唐代長安譯語人》,《史學月刊》2003 年第1 期,第28—31 頁(并參見氏著:《隋唐長安與中亞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127—128 頁);馬祖毅:《中國翻譯通史》第1 卷“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陳海濤、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商務印書館,2006 年,第254—255 頁;趙貞:《唐代對外交往中的譯官》,《南都學壇》2005 年第6 期,第29—33 頁。莊穎:《唐代鴻臚譯語人淺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增刊,第37—41 頁;鄭顯文:《唐代訴訟活動中的翻譯人》,張中秋編:《理性與智慧:中國法律傳統再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250—268 頁;參見鄭顯文:《出土文獻與唐代法律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231—249 頁;Rachel Lung,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畢波:《中古中國的粟特胡人:以長安爲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281—282 頁;許序雅:《唐朝與中亞九姓胡關係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180—183 頁;朱麗娜:《唐代絲綢之路上的譯語人》,《民族史研究》第12 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212—228 頁;王貞平:《口頭溝通:隋唐時期亞洲外交的多個側面》,《南國學術》6 卷2 期,2016 年,第198—213 頁;以及拙著:《唐代中書省翻書譯語直官輯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0 集,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313—336 頁;《唐代的翻書譯語直官:從史訶耽墓誌談起》,《晉陽學刊》2016 年第5 期,第35—57、131 頁。這些研究解决了吐魯番地區及中書省、鴻臚寺譯語人的職掌問題,推進了譯語人及中國古代翻譯史研究的深入。但對譯語人的誤譯問題,多未深論。而會昌、大中年間唐與黠戛斯交往中誤譯的頻繁發生,讓我們不得不對誤譯的產生和影響予以關注。
首先,我們對唐代官府譯語人的設立制度和譯語人的職能作用等做一回顧。
唐代官府譯語人的設置,詳見於《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職掌”條,其文云:
凡諸司置直,皆有定制。諸司諸色有品直:中書省……翻書譯語十人……鴻臚寺譯語并計二十人。b《唐六典》,第35 頁。
據《唐六典》記載,中書省的譯語與鴻臚寺的譯語是有區別的。中書省的譯語被稱爲“翻書譯語”,主要職掌是筆譯;鴻臚寺的譯語直官司掌口譯,其“并計二十人”,表明鴻臚寺譯語直語種衆多,各語種直官加起來總共定額20 人。鴻臚寺的譯語人主要職責在接待外使、傳播唐朝禮儀,在蕃使的日常生活和禮儀性會見活動中擔任翻譯,與中書譯語司掌國書翻譯和參與外交談判是不同的。
除了譯語直官之外,中書省、鴻臚寺還有更多的譯語直司。史籍中記載了鴻臚“譯史”在接待蕃客和外交禮儀中的作用,《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云:
于是引回鶻公主入銀台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必答,揖與進。帝御秘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a《新唐書》,第6124 頁。
《新傳》用語典雅,這裏的“譯史”指的就是鴻臚寺譯語人。b見趙貞:《唐代對外交往中的譯官》,第30 頁。稱“史”,表明譯者還是吏而不是官,故而譯史爲鴻臚寺的無品譯語,即譯語直司。會昌年間稱“黠戛[斯]是黃頭赤面義”的“譯史”也是鴻臚寺的譯語直司。由於譯史負責唐代外蕃翻譯事宜,若根據語種而設,無品譯語直司數額一定不少。這些譯語直司升遷有限制,“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c《新唐書》卷四五《選舉志》,第1174 頁。。
唐代直官的隊伍是龐大的,d關於直官制度的研究,詳見拙著:《唐代直官制初探》,《國學研究》第3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383—424 頁,收入《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1—56 頁;《唐代直官補考—以墓誌爲中心(上)》,《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4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125—137 頁;《唐代直官補考—以墓誌爲中心(下)》,《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52—72 頁。中書省的翻書譯語直、鴻臚寺的譯語直,也是如此。除《唐六典》卷二記載的中書省有品翻書譯語直10 人,鴻臚寺20 人之外,中書和鴻臚還有不可計數的無品譯語直司,更有增設的員外直官和員外直司。e龍惠珠認爲鴻臚譯語人20 人,占鴻臚寺官吏人數的10%,比例不小,可見翻譯在鴻臚寺中是必不可少的。見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63-66。但加上無品直和員外直,鴻臚譯語人比例較10%要多得多。
中書省、鴻臚寺的譯語直官,是國家最高級別的翻譯專家。他們掌外蕃來朝國書及在京蕃胡所上表疏的筆譯;也負責外蕃使者在唐活動的口譯,并在關鍵時期身肩重任,出使諸國,解决重大民族糾紛和外交問題。唐代譯語直按品階可分爲有品直、無品直兩種,按出身有本色技術直與非技術直之別,按任職名額又可分正員直與員外直,種類複雜,體制完備。史籍中記載的中書譯語10 人,鴻臚譯語20 人,只是定額有品直的數額,還有大量無品直、員外直,數額難以估算。有品直、無品直、員外直,系統龐大,等級嚴格,構成一個規模不小的國家翻譯團隊。圍繞著國書翻譯和外蕃來使的接待事宜,中書省與鴻臚寺翻譯系列的有品無品直、正員員外直各有分工,各有職司,但又密切合作,共同處理了唐的民族和外交事務,保證了成千上萬蕃人在唐的無障礙溝通。
貞觀末,“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a《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條,第6253 頁。。開元初,玄宗君臣勵精圖治,“四方豐稔,百姓殷富……奇瑞叠應,重譯麕至”b《開天傳信記》,(唐)鄭綮撰,吳企明點校:《教坊記:外三種》,中華書局,2012 年,第79 頁。。從貞觀至開元天寶時期,唐聲名遠播,“萬國來朝”。唐前期外蕃使人來唐者,成百上千,翻譯工作量極大。但中書省、鴻臚寺的無品、有品及員外直組成的團隊,不僅能在處理大唐帝國的各種民族和外交事務中游刃有餘,而且還能在跨文化交往活動中擔當重任。靈活、複雜、完善的譯語直官制度,是唐外交和學術文化交流的保證。
這些是唐前期的譯語人情况。安史亂後,唐國力下降,昔日外蕃使人頻繁來往的盛况不復存在。隨著國力變化,與唐聯繫的蕃國逐漸減少,唐越來越向內收縮,無暇顧及周邊和域外。與之相應的,是譯語人水平驟降,甚至在突發事件時尋找合適的譯語人都困難。會昌、大中年間,距安史之亂已近百年,“重譯麕至”的盛况早已是明日黃花,黠戛斯遠來“朝貢”雖令朝野轟動,但此時的譯語人正處於青黃不接時期。誤譯的出現,也在所難免了。
在黠戛斯使臣即將到長安之前,宰臣李德裕已注意到譯語人問題。會昌三年(843)正月,李德裕上《論譯語人狀》,其文云: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紇扢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于回鶻者,不爲翻譯,兼潜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可否〕?c《李德裕文集校箋》,第271—272 頁。
向達先生認爲,石佛慶爲臣服於回鶻的昭武九姓胡,在文宗、武宗之際流寓長安。向達先生還舉出了“是一卑微首領”d《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一四《論回鶻石誡直狀》,第249 頁。此狀在研究翻譯史時被廣泛引用。龍惠珠的解釋較爲新穎,她指出粟特人的語言能力是一把雙刃劍,唐人過度依賴粟特譯語人,而對粟特譯語人正直和忠誠産生懷疑,體現了唐在使用粟特譯語人中的兩難處境,是唐國力衰弱的反映,見Interpr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149-157。的石誡直e按:石誡直還回鶻事,見《資治通鑑》卷二四六“會昌二年八月”條,第7965 頁。之例,說明會昌時回鶻部族中不少昭武九姓胡人。f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8、29—30 頁。譯語人石佛慶心向回鶻,在將回鶻逐出漠北的黠戛斯g《資治通鑑》卷二四六“開成五年十月”條,第7946—7947 頁。使人到京後,不能很好地履行譯語人職能,并有可能泄密。李德裕特爲此上狀。
李德裕奏狀提到命劉沔、忠順遞送“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可能是邊州的譯語人。劉沔時任河東節度使,李忠順任振武節度使。h《資治通鑑》卷二四六“會昌二年三月”條,第7959 頁。唐《改元開成赦》規定:“其邊州合置譯語學官,常令教習,以逹異意。”a(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五,商務印書館,1959 年,第30 頁。劉沔遞送至京的可能是邊州的譯語學官,或是開成元年(836)設置學官後教習的學生。唐代軍隊中也配有譯語人。吐魯番出土“唐尚書省牒爲懷岌等西討大軍給果毅、傔人事”b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274—276 頁。文書即有“若發京多折衝、果毅、傔及譯語等,恐煩傳驛”句。此文書約寫於永淳元年(682)c孫繼民:《吐魯番所出“唐尚書省牒”殘卷考釋》,《敦煌研究》1990 年第1 期;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第265—276 頁。,這次西討大軍中除有折衝、果毅、傔人外,還有譯語人。可見譯語人是唐軍隊中必不可少的。邊州或軍隊中都有譯語人,故而李德裕奏狀中要求劉沔、李忠順“各擇解譯蕃語人”遞送。
李德裕的狀中只提到譯語人石佛慶,并未詳述他是中書省的翻書譯語直官,還是鴻臚寺的譯語人。唐接待外蕃使者是鴻臚寺的職責,鴻臚寺譯語、掌客出入外蕃居住的客館d《唐會要》卷六六《鴻臚寺》“開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第1151 頁。,司掌接待、聯絡、翻譯的任務,石佛慶若是鴻臚譯語,因之爲黠戛斯使人翻譯,也是職責所在。但中書省翻書譯語直官翻譯黠戛斯使人國書,傳遞王命,也是分內之事。而李德裕時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省是其管轄之內,中書譯語是其下屬,李德裕應更爲熟悉中書譯語。故而石佛慶也可能是中書省的譯語直官。但不管石佛慶屬中書還是屬鴻臚,譯語人的極度匱乏都是當時的現實。
石佛慶是粟特人,原是譯回鶻語的。可見唐沒有直接通黠戛斯語的翻譯。黠戛斯自天寶六載(747)後,一直沒和唐聯係,唐的譯語、翻書譯語中,均無黠戛斯語種。武宗時黠戛斯大規模遣使來唐,而唐則翻譯力量不足,沒有專職儲備人才,故而需要借用回鶻翻譯。李德裕因爲接待黠戛斯使者的翻譯問題向邊州求援,正解釋了黠戛斯使者來唐後誤譯頻出的原因。
大中十年(856),黠戛斯再次遣使來唐,與之同來的,還有業已遷至安西的回鶻使臣。《唐大詔令集》卷一二八《請立回鶻可汗詔》云:
近有回鶻來款,朔方帥臣得之,送至闕下。又有回鶻隨黠戛斯李兼e大中十年來唐的黠戛斯使臣名爲李兼,如果他不是流落在黠戛斯的漢人後裔(《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黠戛斯》記載,永徽四年[653],黠戛斯“又遣使朝貢,仍言:‘國內大有中國人。’”[第3820 頁]可見隋末唐初有漢人在黠戛斯國內生活),則體現了會昌年間“阿熱著宗正屬籍”對黠戛斯社會的影響。至。朝廷各令象胥,徵其要領,音塵可訪,詞旨必同。願復本邦,仍懷化育。皆云龐特勒(勤)今爲可汗,尚寓安西,衆所悅附。颺宰相以忠事上,誓復龍庭;雜虜等以義向風,頗聞麕至。□契素願,慰悅良多。f《唐大詔令集》,第692—693 頁。《資治通鑑》卷二四九記載此詔大中十年三月辛亥(八日)頒下(第8059 頁)。
此詔值得注意的是,爲了應對回鶻所送來款及隨李兼而至的回鶻使臣,唐“各令象胥,徵其要領,音塵可訪,詞旨必同”,并將這一行動寫進了詔敕,昭告於回鶻。“象胥”即翻譯人員,用《周禮》之典。a《周禮正義》卷七三《秋官·司寇第五》:“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 年,第869 頁。面對回鶻的來書和來使,唐要大張旗鼓地徵集翻譯人員,令其仔細翻譯,共同核對,確保準確無誤地譯出回鶻實况。
自會昌二年(842)至大中十年,回鶻與唐斷絕關係僅有15 年,回鶻來書與來使的翻譯,就成了唐廷要興師動衆的大事。此詔可以和上引李德裕《論譯語人狀》同觀,都反映了晚唐時期,唐官府翻譯人才嚴重不足實况。通過分析李德裕《論譯語人狀》和大中《請立回鶻可汗詔》提到的“象胥”問題,則不難理解爲什么會昌、大中年間黠戛斯使唐時會頻繁出現翻譯失誤現象了。會昌、大中年間,不論是與黠戛斯還是與回鶻的交流和聯繫,唐能支配的譯語人都有捉襟見肘之感。用這種倉促湊成的翻譯團隊,來應對重大的邊疆民族與外交事務翻譯,焉能保證翻譯質量!
唐後期國力衰弱、外蕃使團來唐減少是譯語人才不足的背景原因。而這一變化造成來唐胡人減少、唐學習外語人數減少,則是譯語人水平驟降的直接原因。盛唐時期來華外國人衆多,唐代胡風大盛。追求外來方物的風氣滲透至唐代社會各個階層,胡風的盛行也波及語言文字領域。b〔美〕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47—48 頁。中唐以前,唐人并不排斥外語學習,這爲更多外語教育提供了可能,唐人學習和使用胡語者也不少。c陳明探討了唐代社會的胡語學習及使用風氣,勾勒出唐代外語學習與雙語文獻的使用、傳播的大致面貌,并從這一背景分析了佛教雙語字書以及音義著作形成的原因。見氏著:《佛教雙語字書與隋唐胡語風氣》,《四川大學學報》2009 年第2 期,第58—98 頁。唐前期,成千上萬蕃胡涌入京師,長安、洛陽成爲衆多語種交會之地,也是唐人學習外語的大本營。中書、鴻臚的譯語人,應有不少習蕃語於長安、洛陽者。安史亂後士人嚴夷夏之防d傅樂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大陸雜志》25 卷8 期,1962 年,《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09—226 頁。,習蕃語者漸稀。文宗開成元年(836)在《改元開成赦》中強調:“其邊州合置譯語學官,常令教習,以達異意。”e《唐大詔令集》卷五,第30 頁。與前期士庶學習外語的風潮,已迥然不同。文宗以後雖然強調蕃語學習,但從會昌和大中年間的誤譯現象可以看到,邊州“置譯語學官”的成效微乎其微。
唐代的譯語水平,唐前期與唐後期截然不同。唐前期東西交流暢通,蕃胡涌入,譯語人業精于勤;唐人也學外蕃語,官府譯語人揀擇範圍大,譯語直能集一時之選。唐後期嚴華夷之辨,唐人罕習外語。安史亂後失河隴,除回鶻外,來唐外蕃急劇减少,譯語人翻譯練習的機會也大爲减少。武宗時黠戛斯來朝,唐迫不及待地要求邊州支援翻譯人員,可見中央翻譯人才儲備不足,翻譯力量匱乏。大中時西遷回鶻來使和來書,唐的翻譯人員又措手不及,難以應付,可見安史亂後唐翻譯水平、翻譯力量下降之嚴重。會昌、大中年間黠戛斯來唐時的誤譯現象,和晚唐的政治形勢、唐的國際地位變化與唐國家譯語人水平下降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