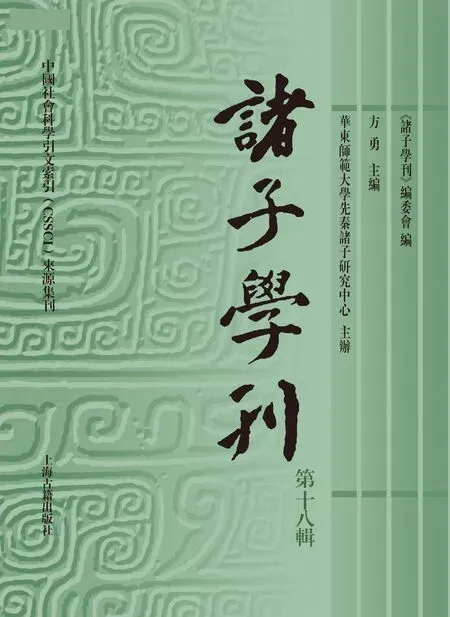爲“新子學”定性定位
(臺灣) 曾昭旭
内容提要 本文從“新儒學”涵有“何以爲新”(回應西學衝擊)與“何以爲儒”(回歸儒學之實踐本質)二義發想,以引導到“新子學”亦當有此二義。其次從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説明經爲常道,餘爲呈現常道之方式,即“即事顯道”(史),而事中有理有情,故又可分出“即理顯道”(子)與“即情顯道”(集)兩類。然後據上述二義爲“新子學”定性定位: 在“何以爲新”一點,定“新子學”爲回應西學在思辨上之衝擊而更强調以哲學思辨去詮釋道;在“何以爲子”一點,則强調(1) 不忘即子即經之身份,(2) 應重視辯證思維,(3) 應採取每篇獨立而各篇互相呼應之編排方式。
關鍵詞 新儒學 新子學 經史子集 即事顯道 辯證思維
引言——從“新儒學”談起
要釐定“新子學”這個概念應具有怎樣的内涵,我們不妨從“新儒學”談起。
在思想史上論及儒家或儒學,向有原始儒家(先秦孔、孟、荀)、宋明新儒家(程、朱、陸、王)及當代新儒家之説。原始儒家之興是由於對周文疲弊、禮壞樂崩的反思;宋明新儒家之興是因回應印度佛教佛學之衝擊,爲“道喪千載”的文化處境謀求復興;當代新儒家之興則是因回應西方文化之衝擊,爲瀕臨次殖民地危殆地位的中華民族文化謀求再一次的復興。
雖然“新儒家”之新,在思想史的論述上是爲與原始儒家作出區别,但考察儒家一次次的興起,實都是爲面對當代的文化困局而謀求更新解決之道。於是,我們便可規定儒家之性質是實踐(行)的而非徒思辨(知)的,是道德的而非徒哲學的,是重用(功能發用)的而非徒重體(本質釐定)的。因體恒定而用必隨環境之變遷而調適之故,儒家之精神乃必須是即用見體而日新又新的,吾故曰: 凡儒家皆新儒家。若抱殘守缺,對當代之人生及文化無問題感,更不思何以回應,則雖熟讀《論》《孟》,深研程、朱、陸、王,實皆非真儒而不免爲僞儒、俗儒。
我們若以此標準來衡定當代“新儒家”,便自然衍生出兩要點,即“新儒家”何以爲新,“新儒家”何以爲儒。前者是指對西方文化之衝擊有何回應之道,後者是指此回應是僅止於思辨理論學術之回應,抑更能回到生活世界作實踐的回應,藉回歸生命人性之根源(即所謂“道”)以解決生命與文化因失本而造成之困局。换言之,所面對新情境之挑戰只是一機緣,而找回失落的生命根本精神以自我再挺立才是真課題。筆者曾作《論牟宗三與唐君毅在當代新儒學上之互補地位》(1)收入拙著《在説與不説之間》,臺北漢光文化公司1992年版,第127~140頁。一文,即論及牟學重在表述當代“新儒學”之何以爲新,唐學則重在表述當代“新儒學”之何以爲儒。因回應西方衝擊有其迫切性,及其與西方哲學更有其相關性,故牟學先引領當代學術風騷,而唐學暫時不免相對弱勢而有待下一階段之繼起。
其次,儒學雖以實踐爲主,當然亦須有充分之思辨以爲輔助。尤其當代儒家要去回應之西方文化,本質即是一以思辨爲本之文化,故其回應當然亦應以開發思辨力以建立知識系統爲優先,此正牟學何以先行之故。於是吾人乃須在道德實踐中别立一哲學的領域以爲强調,此亦當代“新儒學”之表現何以大抵偏於哲學思辨,而傳統之經學亦幾爲所謂“儒家哲學”所取代矣!我們若以傳統之“經學”與“子學”概念來表示,亦即經學之子學化也。
論述至此,傳統子學在當代文化環境下當如何看待,或當如何給予其新的衡定——亦即“新子學”之定性定位問題便出現了。本文即就此問題嘗試作出一些思考,以供時賢參考。
一、 子學在經史子集之傳統分類中的地位
(一) 經學爲人性普遍常道所寄
經者常也,即指人性之普遍常道,亦即人之所以爲人之不變本質。此本質以《孟子》之言表示,即“人之性善”也。但所謂性善,並非指“人之結構之性本質上是善的”,而是指“人普遍具有創造生活之意義價值之能力”,亦即《孟子》所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如順人性之實,是人人都可創造出人生之意義價值,這才是我所説的性善)。這可稱爲人之性善的發端義(即《孟子》所謂“四端”)。
然後由此心的創造性發用或説道德實踐,人也可以推擴良心去及物潤物,賦予萬物以意義價值,亦即創造一個客觀的價值世界,即所謂禮樂文明。這整體性的合主客觀爲一的真實存在的道德世界即所謂“道”,於是人爲天地之心,負責贊天地之化育,以成全此天人合一之道。這則是人之性善的完成義,與前述的發端義相合,才是性善的完整涵義。此完整的道或“人性之普遍常道”,原則上即寄於“經”(六經: 《詩》《書》《禮》《樂》《易》《春秋》)以表示。
但這是一種什麽形態的表示呢?這不是如西方文化所主的知識之學,其知識之道(知識構成與運作的原理)如數學、邏輯可以用純粹的符號系統去表示,而是生命(創造之流動歷程)與道德(創造意義價值以自我實現)之學,因此只能以“即事説理”的方式表示——亦即通過人心所涉及之生活諸事,表述其創造性真心之發動、創造行動之發展以及創造成果(有意義的人生與禮樂社會)。儘管其間有或偏重事或偏重理的差異,但總體是即事説理的形態。
據此,我們可以對六經性格作進一步的釐定,不妨將“六經”分爲三組: (1) 《詩》《書》,(2) 《禮》《樂》,(3) 《易》《春秋》。《詩》《書》主在表現素樸的生活經驗内容。《書》主事,《詩》主情;《書》爲體(事體),《詩》爲用(即事生情,亦即事説理,理乃情之理也)。《禮》《樂》則是在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所建構的人文制度。《禮》偏理性,《樂》偏感性;《禮》爲體(制度結構之體),《樂》爲用(制度運作所産生的教化之用)。《易》《春秋》則是對人爲創立的禮樂制度作後設的反省,以避免其異化。《易》是探討道德生活的總原理,以爲反省批判的依據,是爲體;《春秋》是依據此原理以對制度之不當運作予以批判,是爲用。
綜上所述,《書》表實存之體,以顯感情之用;《禮》表人文制度之體,以發教化之用;《易》表哲學之體,以發批判之用。三體互爲表裏,事(包括生活經驗之事與制度運作之事)雖賴理(哲學原理之理)以得貞定,理亦藉事以得彰顯,事與理仍是一辯證互動之關係也。
(二) 史、子、集爲經(常道)之表述方式
據前節所述,我們已可肯認: 人性常道之表述方式必是“即事説理”的。於是經所藴涵的人性普遍常道,落實於人與整個民族之生活,便是人之生活史或生命成長史,此即史部與經部之本質關係,故有曰“六經皆史”,意即“六經”所涵之道,皆以即事顯道之方式以表現者也。道以此而得以落實彰顯,反過來説,史事亦以此而成其爲有意義價值亦即有道貫注其中之道德史也。故中國傳統之史學之所以有别於西方之史學者,即在西方史學所謂史,只是事實之流,由此成立其“知識的史學”;而中國傳統史學所謂史,則是意義之流,而成其爲“道德的史學”也。故史學與經學,實具互爲表裏、同爲一體之關係。
其次,所謂事又可有偏於理與偏於情之分。子部即人之生活言行中偏於理性思考或專顯理性思考一面之表現也,集部即人之生活中偏於感性流露或專顯感情流露一面之表現也。此兩部皆不以事爲主(史部才是),而是以凸顯事中之理性思考與感情流露爲主。故子部著作近於哲學,而集部著作近於文學也。但只説其近於哲學、文學而不直説就是哲學、文學,則因它們仍有其載道之功能,而非純馳騁其理性思辨、純發抒感情流露也。
於此,若呼應本文題旨而單就子學而言,子部著作便是將實存於生活中而本質不可説的道,轉爲可説之理而予以表出。當然它表出的方式不是以人爲設計的符號系統去表示(知識之理才是),而是以即事説理的方式去表出。雖然它不如史部著作是以叙述實事爲主而道藴涵其中,而是常以虚構之事(如《莊子》寓言)或事之常模(歸納諸事而成)爲例以顯理,但仍屬即事説理之一環。於此便可看出子部著作與西方式之哲學著作的不同了!
綜上所述,不止史學與經學是辯證相即爲一體,子學與集部之文學作品也是源出於道而又回過來以理或以文載道,終亦與道辯證相即爲一體。甚至可以説,連史、子、集三部之作品,也是互相關連滲透而爲一體的,故常言云“文史哲不分家”。此亦猶佛教華嚴宗所言,在事理圓融之外,更有事事圓融也。
二、 “新子學”之定性定位
(一) “新子學”何以爲新
由前兩節之鋪陳,我們已爲“新子學”的定性定位作好準備工作,亦即釐清了問題的本質,於是便可以正式爲“新子學”究竟是什麽這一課題給予準確的回答。
這首先仍當回到前述問題的兩端,即“新子學”何以爲新及“新子學”何以爲子來切入。首先論“新子學”何以爲新。這和“新儒學”何以爲新一樣,當然是因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衝擊,必須有所回應——亦即取西方文化之長,以補己之不足,且融會雙方以成一新的學問形態。但“新子學”與“新儒學”之所以爲新,仍有其差異而各具特色。儒學具内聖外王兩面,兼思維與實踐兩端,因此其回應西方挑戰者,亦須兼顧此兩面與兩端,即除正視西方知識之學的概念分析思維之外,亦須正視其落實之應用,此則更集中在外王事業一面,簡言之即西方文化之兩大精神——科學與民主,皆須同等正視,以求會通也。但子學性質既近哲學,其重心即當然偏於思維而略於實踐。因此回應西方文化之挑戰,亦當以思維方法之深入探討、學習、消化、吸收,且進一步發展出自家的方法論爲主。换言之,實即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會通也。亦即吾人漸漸有能力以更嚴謹之分析、更準確之概念、更統整無漏之理論系統,去重新表述儒學中之理,以與西方哲學平等對話也。此即“新子學”所以爲新之所在也。
(二) “新子學”何以爲子
對於“新子學”何以爲新,正是時潮所在,知之不難。但對“新子學”何以爲子,則相對亦正是時人盲點所在,更需要詳加論列;否則,“新子學”或中國哲學將有被西方哲學同化,而成爲西方哲學附庸之危,那麽子學不成其爲子學矣。
然則“新子學”當如何自我貞定,以確保其無論如何吸收西方哲學之長都依然保有自己的特殊性格呢?我們認爲,應有如下三點可説:
(1) 維持其即子即經之身份。所謂即子即經,即前文所謂子學與經學實相即而爲一體也。其特色只在即整體渾全之道而凸顯其理,亦即即理顯道而已(相對的,史部是即事顯道,集部是即情顯道)。當然,就哲學觀點言,即理顯道,理即是道(宇宙人生之終極原理,即可謂之道,《老子》開宗明義即如此宣示)。於是凸顯至理之子部著作亦寖寖可稱爲經了!如《孟子》即列“十三經”之一,《老子》《莊子》亦分别名爲《道德經》《南華經》,皆是也!
既然即子即經,則雖專注於哲學思辨,亦不可忘其所思辨者無非道。而道於客觀言是一整體之實存,於主觀言是一無窮之自覺與實踐,則其所思辨亦當永不離實存,永不忘實踐才是。此之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位者非徒職位之位,更是人眼前當下實存之位也。故“新子學”之所思所論,不宜是無根之游談,或徒屬資料之堆疊,否則辨析再精,仍是戲論,蒐羅再富,亦只屬小學之事罷了!
(2) 善用辯證思維。“新子學”當不離實存、不忘實踐,於是實存之道(本體)與實踐之道(工夫)皆當在進行理性思辨之時隨時涉及。其形態之一,是直接討論道(包括天、氣、心、理、誠、神、太極、良知等)此一非概念或空概念,卻當與有所指涉之物概念各各妥予安置,既不相混淆,又可恰當地重疊相即;此中分際,拿捏不易,而靈活出入於道(形上界)物(現象界)之間終證成其相即爲一體之思維方式,即所謂辯證思維。相對的,西方知識之學所慣用乃分析思維。後者是一元演繹,前者則是兩端互動,即王船山所謂兩端而一致也。
辯證思維的形態之二,即雖非逕以道爲討論對象,而只論日用尋常或日用倫常,但道仍在字裏行間時時閃動,即所謂“意在言外”,而須讀者自有所領會。此亦是一種廣義之辯證思維,即無辯證相(明顯的兩端互動)之辯證思維(仍對道實有所涉及)也。前者如《老子》,後者如《論語》,皆顯例也。
而不論其辯證思維是有相抑無相,關鍵仍在言説者或論述者其心乃是覺的。若然,道才能在其心中,他才能在論述之時敏鋭感知在道與物、道與言之間,其適可而止之分際或無過無不及之中點何在,而使其論述成真足以即理顯道之論述也。
最後,所謂辯證思維,並非與分析思維相對的另一種思維,而是即涵攝全盤分析思維在内,只是對分析活動另有一真心之監察,以權衡斟酌其之行止分際,以有助其適時顯道而已。故所謂辯證思維,即先分析再取消分析,或正在分析時已當下取消其分析(即《莊子》之旋説旋掃)而已。因此,靈活恰當之辯證思維實亦有賴分析思維之嚴謹確當而後方能共成完璧者也。
(3) 各篇獨立而又互相呼應涵攝之編排方式。西方的知識之學本質即是一系統結構之展開(如數學系統、邏輯系統),故其著作成書,亦是篇章之間,共成一整體之分析性結構。换言之,對全書而言,每一篇章皆只是整體結構之一部分、一零件,須各部分或零件分工合作,才組織成一完整的系統結構。此亦現代學術論著之寫作常規也。
但中國傳統的生命道德之學卻不然,它所關懷探問的“道”即是一不可分析的整體實存,而只能指點式地即事顯道(包括即理顯道與即情顯道)。而各事所顯,事雖不同,所顯之道則唯一,於是唯一之道與諸顯道之事之關係,乃如月印萬川,不但理事圓融,亦事事圓融,即各事之間具有互相呼應、滲透、涵攝之關係。
相應於此種特質,諸子書之寫作編排方式,也應各篇皆可獨立,但内涵又可互相呼應、滲透、涵攝。即使各篇似亦各具主題,各顯重心,亦絶非分析性的零件地位,而仍是各各獨立又互相涵攝。《論語》《孟子》如此,《老子》《莊子》亦如是。尤其《莊子》之内七篇,吾嘗謂似亦可詮釋出《莊子》完整之義理架構: 《逍遥遊》重在彰顯逍遥境界,可稱本體論(或境界論)。《齊物論》以下五篇皆討論如何方能達致此境界,可總列爲工夫論。就中《養生主》是修養原則之提點,餘四篇是修養原則之應用,即據此原則以解消人生之負累也。就中《齊物論》是總論,即説人生負累之總根源乃語言、概念、成見、意識形態之負累也。故工夫根源亦在解消對名言之執着也。總論之後列三分論,即舉名言執着中最普遍之三例以論其解消之道,此即《人間世》之人際關係、《德充符》之形體、《大宗師》之生死也。最後,藉此工夫達此境界後之人生實相如何?即無入不得之隨緣物化也,即《應帝王》之所示,而不妨名曰功效論。
但如此儼然若有完整義理結構之詮釋,實亦聊供參考,而不礙七篇雖似若有重心卻又不必爲此重心所限,而仍可涉及他篇之領域終於各篇相即爲一體之本質。此即子學著作(乃至中國傳統之各種著作)之特色所在也!
結 論
以上所論,意在爲“新子學”此一概念,試作定性與定位。定性者,釐定其言説屬哲學性言説也。定位者,意在爲釐定“新子學”在整個中國生命道德之學中之地位,乃即理顯道,而理、道不二,亦即子學、經學不二也。至於何以謂之新,即在哲學性言説當引進西方哲學更精確之分析思維,以補辯證思維之不足也。
而本文之所以作,則在應“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機緣,作此以祈願中國傳統之學問,包括子學與經學、儒學與道學,等等,皆能在此中西文化相激相盪之時代,有一日新又日新之開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