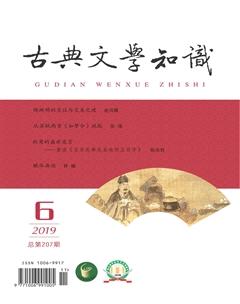自我膨胀的畸形门第观念
宁稼雨
魏晋门阀世族受到后人指责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门第观念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掣肘滞后作用。门第形成的时期,大族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扩大家族的势力及其影响上。而门第一旦形成,一种优越感所驱使的门第观念便成为把大族与庶族区分开来的强劲异己力量。这种观念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为门第的创立者所始料不及,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都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
一、 界限分明:流品尊卑意识严格
初读《世说新语》时,有一疑惑久未得解:为何有晋一代诗坛祭酒陶渊明竟然不得入《世说新语》中?经深入把玩《世说》,方悟此乃《世说》编者及当时盛极一时的门第流品意识使然。陶氏一族晋代以陶侃最为知名,但也常受人轻辱。《世说新语·容止》“石头事故”条载庾亮畏见陶侃,而温峤劝亮往之言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余嘉锡引述李慈铭言,认为“溪”当作“傒”,为“鸡”之误,乃前人对江西人之蔑语,犹呼北人为“伧父”。陈寅恪则以为“溪”为溪族,乃高辛氏女与畜狗所生后代。陶侃及陶渊明一族即出于溪族。周一良也支持陈说,并认为:“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刘敬叔《异苑》:“钓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山犹有侃迹存焉。”《世说新语·贤媛》亦载:“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所以周一良先生说:“盖陶公正是渔贱户之溪人,故贵显后犹不能逃太真之轻诋。”可见“溪狗”为人们对陶氏家族为狗裔的蔑称。正因为陶氏祖先有这样丑史,所以它一直受到人们(尤其是世家大族)的蔑视和嘲弄。
陶氏家族的地位变化始自陶侃。其经过十分艰辛:
陶公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髢,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刘注引《晋阳秋》:“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贫贱,纺绩以资给侃,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宿。时大雪,侃家无草,湛彻所卧荐剉给,阴截发,卖以供调。逵闻之叹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岂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当相谈致。过庐江,向太守张夔称之。召补吏,举孝廉,除郎中。时豫章顾荣或责羊晫曰:‘君奈何与小人同舆?晫曰:‘此寒俊也。”又引王隐《晋书》:“侃母既截发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进之于张夔,羊晫亦简之。后晫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世说新语·贤媛》)
陶母截发留宾,传为千古美谈。但时过境迁,后人往往从道德和伦理角度,注意到陶母之贤德,却往往忽略了故事的原汁原味是着意描绘和烘托出一个寒族家庭奔向贵族社会的坚定决心和艰难历程。陶母的丝丝乌发,未尝不是寒门对于士族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的强烈控诉。然而可悲的是,士族的强大势力使得寒族尽管心有不满,却又不得不惟命是从,亦步亦趋,按照士族的理念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道路。正因为陶氏家族的卑微出身,才使得尽管陶侃已经开始步入上流社会,但其他高门贵族仍然将其视为寒门。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陶氏家族的郡望至今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这本身就不是世家大族应有的缺憾。《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宋人汪藻《世说叙录·世说人名谱》中收录名门族谱凡二十六种,未见陶氏在内;另有二十六族无谱者,陶侃、陶范在列其中,未言郡望。直到唐代,陶家的郡望才在有关的姓望材料中被肯定为江州寻阳郡。北京图书馆藏位字七九号唐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和斯坦因敦煌文书第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均在江州寻阳郡下载有陶氏家族。可见陶家的郡望也只是因为陶侃的功业和陶渊明后来的名声而被肯定下来。在晋宋时期,陶氏家族还是被人蔑视的小族。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不乏例证: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世说新语·方正》)
陶胡奴即为陶侃第十子(或言第九子)陶范。余嘉锡此条笺疏云:“《侃别传》及今《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其子夏、斌复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龄羞与范为伍。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陶侃、陶范官居要位,煊赫一时,尚受此不恭,陶渊明一彭泽小令,自然属小人之列,岂能与士族大角争胜并列哉?类似情况又如: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刘注:孔子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刘尹之意,盖从此言。)(《世说新语·方正》)
顾炎武有云:“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正是因为流品的严格界限,才会出现在士族眼中,寒族小人连巴结大族的资格都不具备。在这种环境之下,有没有一个显贵的家族背景就会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孰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如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虽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世说新语·方正》)
王忱之所以对张玄前后态度有别,乃得知张玄为吴中豪族身份这一重要信息使然。晋人流品之严,于此可见一斑。强调流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士族谋求政治权力垄断的一个方面。此如近人王伊同所說:“高门巨族,以泰山压卵之势,陵忽寒士,稍撄其锋者,驱迫有司,排抑多端,固以自尊,亦所以隐操政柄,明持物望耳。”如: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夜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径便出。(《世说新语·方正》)
周、周嵩兄弟为汝南周浚之子。周氏在汪藻谱中虽然在无谱二十六族中,但《世说新语·贤媛》所载李络秀为门户计嫁给周浚,知周氏必当大族。且该条刘注亦引《周氏谱》,则汪藻偶漏耳。而刁氏一族则又在汪谱无谱二十六族之外,显系寒小之族。刁协本想借助周氏家族挤入政权核心,不想为周嵩严厉拒绝。此即王伊同所谓“隐操政柄,明持物望”者也。刘应登评:“仲智如恚弟之泣别,责兄之容佞,其言似正,亦大不近人情矣。”盖未解此中蕴藉。
二、 自矜门第:你不如我,舍我其谁!
门第观念首先表现为自矜门第。大族的地位确立后,不仅对庶族不屑一顾,即便对其他大族,也大有你不如我,舍我其谁的气势。有一次,王爽与司马道子一起饮酒。司马道子喝醉了,信口喊王爽为“小子”。王爽不紧不慢地说:“我过世的祖父王濛官任左长史,而且是简文帝的布衣之交;我已过世的姑姑王穆之为哀帝皇后,姐姐王法惠又是孝武帝皇后。这样的家族怎么能有‘小子的称呼?”(见《世说新语·方正》及刘孝标注引《中兴书》)王爽亮出的几张王牌,足以令当时天下人仰视。
又比如王述上任扬州刺史的时候,出于对信任官员的尊重,府衙主簿向他请教族讳,以免冒犯。可王述却对这种问法极为反感,于是便没好气儿地说:“亡祖先父海内知名,无人不晓。除了不该出门的妇人内讳外,余无所讳。”(见《世说新语·赏誉》)原来,作为世家大族,王述认为主簿这种问法意味着王氏家族的名气还不够大,以致还需要来打听其家讳,这不啻是对王氏家族的蔑视。他这种赌气的方式,实际上还是要张扬其家族名望。清代学者李慈铭认为王述此举乃“六朝人矜其门第之常语耳。所谓专以家中枯骨骄人者也”(《越缦堂读书记》)。
一次谢安和谢万一起去京都建康,路过吴郡时,谢万想拉上谢安一起去拜访一下王恬。谢安说:“恐怕他不一定搭理你,我想还是不去为好。”谢万听不进去谢安的话,执意要去,谢安只好让他一个人去了。到了王恬家坐了一会儿,王恬就起身进里边了。谢万欣喜异常,心想王恬一定去给自己准备酒席去了。过了许久,只见王恬洗了头发,披头散发地来到院子里,躺在胡床上晒起头发来——把客人晾在一边,毫不搭理,而且神态高傲而放纵,完全没有应酬招待的意思。谢万这才明白谢安为什么坚持不和自己一起来。当他羞愧地回到船上,大喊受到王恬羞辱时,谢安则说:“他就是这么个不会作假的人啊。”(见《世说新语·简傲》)谢安的聪明,就在于他清楚地知道,王、谢虽然同为大族,但谢姓之显赫,远在王姓之后。所以王恬才会对谢万如此傲慢无礼。而谢万的浅薄,就在于他对此关节毫不知晓,以致自讨没趣,受辱而归。可见大族之间也有小巫见大巫的尴尬和难堪。
又比如王含在庐江为官,贪鄙龌龊,声名狼藉。他的弟弟王敦为了维护哥哥,竟然在公开场合宣称王含在庐江政绩斐然,得到庐江人民的爱戴和称赞。当时王敦下属的主簿何充在座,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庐江人,从未听说过你这种说法!”有人为何充担心,可何充却神态自若(见《世说新语·方正》)。王敦颠倒黑白是出于回护门第之心,何充揭穿老底,则也未尝不是门户之见。
三、 借讳炫耀:“犯我家讳,何预卿事?”
名讳是世家大族张显和强化其门第声望的重要途径。避讳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风俗。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前后垂二千年。但其演变期间的各自内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最早的避讳主要针对死去的尊者,它是周人礼仪和祭祀的一个组成部分。周人往往以忌讳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已故尊者的亲情,并将其形成为礼仪制度。然而从秦汉开始,避讳便成了统治者权力的一种象征。《史记》年表称正月为端月,是因为它与秦始皇嬴政的字音相同;《汉书》改邦为国,改恒为常等都是为帝王讳。
不过到了魏晋时期,避讳的宗旨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成为士族炫耀家族的手段。当时最为严格的就是家讳。违犯者要受到恶报(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一“觌面犯讳”条)。据《通典·礼》卷六四“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和“官位犯祖讳”条,父祖及本人名与官职名同者,皆得改选。王舒因父名会,朝廷用为会稽内史,累表自陈,求换他郡。后来改会稽郡为郐稽,才不得已上任(见《晋书·王舒传》)。江统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见《晋书·江统传》)。
值得关注的是,魏晋时期士族阶层有不少有意犯讳的现象,其表现尽管不尽相同,但目的初衷只有一个,那就是借犯讳来炫耀家族,或诋毁他人。如一次卢志在大庭广众面前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陆机马上回敬道:“如卿于卢毓、卢珽!”原来陆逊、陆抗分别是陆机的祖父和父亲,卢毓和卢珽则分别是卢志的祖父和父亲。陆机的弟弟陆云见到哥哥如此不客气,出来便对哥哥说:“怎么至于这样?他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祖父和父亲的名字啊。”陆机严肃地说:“我们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名播海内,哪会有人不知道?小子竟敢如此无礼!”本来兄弟二人在众人心中地位还难分伯仲,谢安因为此事而一锤定音。(见《世说新语·方正》)
卢志和陆机都是“八王之乱”中追随不同政治营垒的士族人物。陆机兄弟最终遭戮,即由卢向司马颖进谗言所致。二人之间具有深深的政治裂痕,所以才会拿最不能接受的父祖名讳来向对方挑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父祖名讳在当时十分为人看重,所以才会被用为政治排斥的手段。在不重名讳的时代,倘若还想用政治对手的父讳来攻击对方,倒是愚蠢之举。因为对此未能深谙,所以后人有对陆机兄弟的优劣看法与谢安及时人不同者。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以吾观之,机不逮云远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不孝。而亦从而斥之,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自忘其过,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桥之败,使机所怨者当之,亦必杀矣。云爱士不竞,真有过机者,不但此一事。方颖欲杀云,迟之三日不决。以赵王伦杀赵浚赦其子骧而复击伦事劝颖杀云者,乃卢志也。兄弟之祸,志应有力,哀哉!人惟不争于胜负强弱,而后不役于恩怨爱惜。云累于机,为可痛也!”凌濛初也评道:“士龙亦自雅量。”都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地设想当时作为家族利益重要体现的家讳在士族心目中的位置是如何远远超过了其他因素。余嘉锡似乎看到了个中三昧:“六朝人极重避讳,卢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為无礼。此虽生今之世,亦所不许。揆以当时人情,更不容忍受。故谢安以士衡为优。此乃古今风俗不同,无足怪也。”
还有一种不带有政治色彩和非恶意的有意犯讳,但其效果也是彰扬大族名讳。比如一次晋文帝司马昭和陈骞、陈泰一起乘车经过钟会家,便招呼他一起上车,可没等钟会上车就驾车走了。钟会赶到后,晋文帝反倒嘲弄他说:“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钟会回答说:“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司马昭又问:“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钟会的父亲名繇,所以司马昭用“遥遥”来调侃他。陈骞的父亲名矫,司马昭的父亲名懿,陈泰的父亲名群,祖父名寔,所以钟会用来回敬司马昭(见《世说新语·排调》)。又如一次晋景王司马师的宴会上,有陈群的儿子陈玄伯、武周的儿子武元夏在座。大家都一起来嘲弄钟繇的儿子钟毓,司马师问:“皋繇何如人?”钟毓回答说:“古之懿士。”又回过头来对陈玄伯和武元夏说:“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见《世说新语·方正》)
这是一场君臣之间互相以祖上名讳取乐的玩笑。可能令人不解的是何以这样的玩笑双方竟然能够相安无事,而且似乎还乐在其中?答案就在于他们所谓犯讳与其说是犯讳,还不如说是一种善意的恭维。其潜台词实际是向对方暗示自己没有忘记对方的家讳。这照样可以看出大族的头脑中是如何时刻将各族的名讳烂熟于心的。类似情況还有,一次庾园客去拜访秘书监孙盛,正遇上孙盛外出,只见孙盛的儿子孙齐庄在门口玩耍。庾园客想试试这孩子的灵气,就故意问道:“孙安国(孙盛字安国)何在?”齐庄应声答道:“庾稺恭(庾园客的父亲庾翼字稺恭)家。”庾园客一边大笑,一边用孙盛的名字打趣说:“诸孙大盛,有儿如此!”齐庄又答道:“未若诸庾之翼翼。”又把庾园客父亲庾翼的名字含在了里边。回到家中后,孙齐庄还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还是我赢了,把那家伙父亲的名字连叫了两遍!”(见《世说新语·排调》)这种犯讳既非恶意,也非善意,而是有些知识竞赛的味道。而这种试题的目的,就是为了检测应试者的家族名讳意识及其基本常识扎实与否。
至于那些无意犯讳的故事,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使人看出家讳意识是如何深入人心。晋元帝初次召见贺循的时候,问起东吴的一些往事:“听说当时孙皓烧红了锯子锯断了一个姓贺的人的头颅,那个人是谁?”贺循没有回答,元帝自己回忆起来说:“好像是贺劭吧?”只见贺循泪流满面地说:“我父亲遇上了无道昏君,我万分痛苦,无法回答陛下的问话。”元帝听了非常惭愧,三天没有出门(见《世说新语·纰漏》)。又如殷仲堪的父亲生病而心跳发慌,听到床下蚂蚁爬动,竟然以为是牛在相斗。晋孝武帝有一次想起这件事情,就问殷仲堪这是谁干的。殷仲堪流着眼泪起身说道:“臣进退维谷。”(见《世说新语·纰漏》)桓玄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后赴任路上,船停泊在荻渚。王忱服用了五石散后带着醉意去看望桓玄。桓玄以酒宴相待,没想到王忱服用五石散后不能喝冷酒,就频频告诉侍从说:“温酒来!”(桓玄的父亲叫桓温)桓玄立刻呜咽哭泣起来,王忱莫名其妙,起身就想离去。桓玄对王忱说:“犯我家讳,何预卿事?”事后王忱赞叹说:“桓玄的确很旷达!”(见《世说新语·任诞》)
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无论是君臣之间,还是士族权贵之间,都难免有一时疏忽而忘记别人家讳的情况。对此,被犯者既不能表示无动于衷(那样等于认可对方尽管是无意的冒犯),也不能大动肝火(那样又显得气量狭小)。被犯讳者的共同举动是流涕而哭。这正是当时的普遍习俗。余嘉锡云:“……闻讳而哭,乃六朝之旧俗。故虽凶悖如桓玄,不敢不谨守此礼也。”可见只要不是政治对立的原因,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犯讳,都是可以容忍甚至是会意其内涵的。但无论何种原因,被犯者的反应必须敏捷。因为这是维护家族声望,炫耀家族地位的必要准备。则避讳一事至魏晋其内涵的转变也就可见一斑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