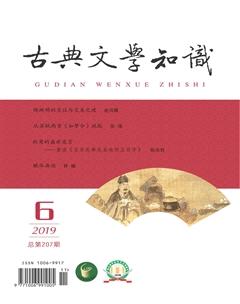见仁见智与以己度人
莫砺锋
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题中的“九年”指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由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正是“甘露事变”发生的当日,后人皆认为诗人所“感”之事即甘露事变。当然此诗不可能作于事变当天,因为洛阳距离长安六百余里,不可能获知当日长安突发事变的消息。况且诗人于题下注云:“其日独游香山寺。”很像事后追记的口吻。那么此诗究竟作于何日?不妨从甘露事变的进程稍作推测:十一月二十一日,事变爆发,宰相王涯被宦官逮捕,不胜拷掠之苦,自诬谋反。二十二日,文宗在宦官的胁迫下使令狐楚草制宣告王涯反状。贾被捕。二十三日,李训于奔亡途中被捕,自请押送者斩其首。二十四日,神策军用李训的首级引领王涯、贾、舒元舆至刑场处死。白诗“当君白首同归日”一句,乃用晋人潘岳、石崇之典故。《晋书·潘岳传》载潘、石二人被孙秀诬以谋反之罪,“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耶!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白诗用此典咏王涯、贾、舒元舆、李训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这说明白诗的写作定在“甘露四相”被戮之后,题中所云“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追记之辞也。
宦官专权是中唐政治肌体上最大的毒瘤,当时宦官们掌握着左右神策军,连皇帝自身都受制于他们,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63中评议中唐宦官之嚣张气焰:“劫胁天子如制婴儿”,“使天子畏之如乘虎狼而挟蛇虺”。白居易对此深恶痛绝,曾公开宣言“危言诋阉寺,直气忤钧轴”(《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早在宪宗元和年间,时任学士和拾遗的白居易就曾奋不顾身地上书抨击宦官头子俱文珍、李辅光、吐突承璀等,甚至不惜批皇帝之逆鳞。可是当“甘露事变”发生的时候,白居易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位无所畏惧的英年朝士了。早在元和四年(829),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便开始了他的“中隐”生涯。到了元和九年九月,朝廷任命他为同州刺史,辞疾不赴,十月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那是一个“月俸百千官二品”(《从同州使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的闲职,白居易对之相当满意。当“甘露事变”的惊人消息传到洛阳时,白居易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当然痛恨宦官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他又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那么,白居易对王涯等“甘露四相”又持什么态度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后人见仁见智,歧见纷纭。
北宋苏轼《书乐天香山寺诗》云:“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苏轼文集》卷六七)苏轼未点明“不知者”之名,今考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六《甘露诗》条云:“沈存中谓:乐天诗不必皆好,然识趣可尚。章子厚谓不然,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虽私仇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当形之歌咏也,如‘当公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沈存中即沈括,章子厚即章惇,都与苏轼有所交往,苏轼所谓“不知者”或即章惇。苏、章二人乃进士同年,入仕后交往密切。章惇所言,苏轼当有所闻,但驳议时姑隐其名。章惇称白居易与王涯有“私仇”,当指苏轼所云“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之事。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刺。身居卑职的白居易最早上书要求捕贼雪耻,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执政者奏贬江表刺史。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落井下石,上疏论“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况且王涯其人,“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为相后因行苛政而招民怨,“甘露事变”中赴刑场,“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旧唐书·王涯传》)。即使白居易对其下场有幸灾之意,亦不过分。但事实并非如此。白居易与王涯虽有前嫌,其后的关系也很疏远,但白居易从未在诗文中对王涯有过微词。王涯在“甘露事变”中惨遭宦官杀害,白居易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刻产生幸灾之心。况且“当君白首同归日”所用之典乃潘岳、石崇同日罹难,这个典故的重点是同归于尽,不能用于单数的对象。如果此句中的“君”独指王涯,那样怎能用“同归”二字?所以“君”字应是泛指甘露事变中遇害的多位朝官,尤其是指“甘露四相”。白居易与贾、舒元舆一向交好,两个月前被任命为同州刺史即因舒元舆之荐。“甘露四相”同时遇害虽出偶然,但那确是朝士与宦官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身为朝士的白居易怎会对遇害朝士幸灾乐祸!
苏轼与章惇对白诗有不同解读也许可归因于学养或见识有异,但与他们的人品相殊不无关系。苏轼胸襟坦率,潇洒磊落,虽在政治风波中树敌甚多,但从未因私怨而怀恨于心,即使对政敌王安石也是如此。章惇却性格褊狭,睚眦必报。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章惇与苏轼同时进士及第。因是年状元乃章惇之侄儿章衡,章惇耻其名次居于章衡之下,竟于两年后重新应举高中后方肯出仕。苏、章二人入仕后一向交好,即使在苏轼遭受乌台诗案时,章惇还曾上书论救。但到了哲宗绍圣年间,新党重掌政权,章惇登上宰相宝座后,却对苏轼一贬再贬,直到“非人所居”的海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章惇对苏轼的迫害,虽有党争的因素,但也未尝没有自私自利的阴暗心理在起作用。黄庭坚说“时宰欲杀之”(《跋子瞻和陶诗》),佛印说“权臣忌子瞻为宰相尔”(见《钱氏私志》),可见章惇之用心路人皆知。相反,苏轼却以不念旧恶的胸怀对待章惇。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突然去世,朝局又变,章惇罢相,并于次年远贬雷州。遇赦北归的苏轼在途中获知此事,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说雷州并无瘴疠,让他转劝章惇之母以宽心。此后朝野相传苏轼即将还朝拜相,章惇幼子章援持书来见苏轼,为其父求情。苏轼当即亲笔给章惇回信,多方劝慰,且在书信背面亲笔抄录一道“白术方”,让章惇服用以养年。南宋刘克庄评此事曰:“君子无纤毫之过,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负丘山之罪,而君子爱怜,犹欲其生。此君子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欤!”(《跋章援致平与坡公书》)苏轼与章惇对白诗的不同解读,与“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当后人对古诗意蕴产生完全相反的评判时,见仁见智固然是可能的原因,以己度人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西谚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们也可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李白、一千个杜甫和一千个白居易。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