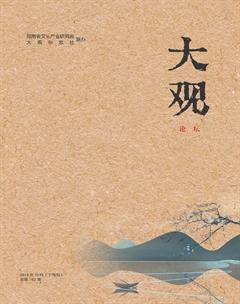技道并进
姚灼
摘 要: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而当今时代也掀起着学习书法的热潮,但对于书法的治学之道也有待我们书法爱好者学习研究,书法艺术虽是以线条的形式呈现,但其背后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书法学习要有一定的方法,技道并进就是我们当前学习书法一条重要准则。
关键词:书法;技道并重;治学之道
注: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师范生‘现代学徒制书法教学模式实验研究”(JG18DB439)研究成果。
对于书法的学习,我们理应与时俱进,但也不能抛弃原有的书法理论内涵。笔者认为《历代书法论文选》是我们书法学习的重要理论支撑,其包含了历代书家关于书法理论和技法的种种见解,对于我们的书法学习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学习书法既要有勤于学习的毅力又要有广于博学的能力,做到理论和技艺并步前进。
一、勤于学习的毅力
关于勤学,历史上不乏闻鸡起舞、凿壁偷光之类,而在书法上刻苦努力的人也是不计其数,历史上关于勤学书法的名人轶事也有很多。
东汉赵壹的《非草書》是较早的谈论书法的理论著作,尽管其表达的是对当时人对草书过于狂热的态度的不认可,但字里行间也体现了当时人对于书法学习的痴迷,以及用工。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1]
西晋书法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曾提到关于张芝勤学苦练的故事。
“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2]
虞世南曾在《劝学篇》中对张芝学书之勤奋也有提及,道:“张芝学书,池水尽墨,当其雅趣,求彼真意,无图其形容而滞于体质,此贵乎志意专精,必有诚应也。”[3]
苏轼作为一代大文豪,曾在《题二王书》中写“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字里行间也体现了对书法学习过程中勤学苦练的强调。可见笔墨“用尽”,是成为一代书家的必经之路。
北宋书学理论家朱长文在《续书断》中也有对书法学习需刻苦的记载:
“初,绛州碧落尊像之背,有篆文极奇古,阳冰见之,叹美服膺,寝食其下,不得影响。”[4]
“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里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得法,其精如此。”[5]
“始其临学勤苦,故笔颓委,作笔冢以瘗之。”[6]
笔者以为对于书法的学习和理解,代代书法家徐浩在《论书》中的见解是最为贴切的。他提到:“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盖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7]
所谓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书法艺术同其他的艺术形式是一样的,是瞬间的艺术却是一生的功夫。历代名留史册的书法大家无不是经过了刻苦努力才达到了笔下生花,挥洒自如的境界,这些都是勤学一词的最好代表。可见对于书法的学习首先要有勤于学习的毅力。
二、广于博学的能力
书法艺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线条的表现,更是文化的体现,是线条艺术与文化魅力的完美结合,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例如我们所熟知的王羲之《兰亭序》,其书法被评为“天下第一行书”,其描述的“流觞曲水”的场景也是美轮美奂。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书法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书谱》是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的完美结合,对书法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书谱》是重要的草书作品,是书法爱好者争相学习的法帖。其书法理论内容涉及到了中国书学的各个方面,其内容见解独到,不乏一些经典的理论。如对各书体关系的见解:“图真不悟,习草将迷。”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9]
另有对书法五体特点的总结(“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10])和书法创作五乖五合的论述(“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11]),都对今天的书法学习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熙载在《艺概》曾经提及“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12]。
王僧虔在《笔意赞》曾提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13]。
古代书家多注重内外兼修,一些著名的书家同样是博学家,关于书学,清代著名书法家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提到自己的见解:
“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14]
对于任何艺术形式,首先需要承认人自身“天分”的存在,但更多的是需要后天的努力。需要“多写”“多见”。其中提到的“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笔者以为是对书法学习的一个有力见解。读书增加读者文化内涵,跃然纸上表现在书法的字里行间,其书写的是文化内容,流露出来的是书卷气息。
在古代,书法家多博学多识,以唐宋时期的书法家为例。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出生于东南名门望族,年幼丧父,过继于叔父,幾经辗转,入唐受知于李世民。《宣和书谱》载“太宗乃以书师世南”。虞世南擅长诗文,史记类似徐陵,有称“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旧唐书·虞世南传》)。唐太宗以“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15]称之。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年幼因兵乱家口籍没,由父友收养。欧阳询自少孤寒,其后来之所以能博览经史,精通《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三史,尤其书法“八体尽能”笔法绝伦,盖出自当年养父的教诲与影响。[16]
关于书法,苏轼在诗《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中曾提到“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再一次强调了在书法艺术当中文化理论对书法的重要性。
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在书法造诣上,和苏轼、米芾、蔡襄合称为“宋四家”。对于书法中的“书卷气”黄庭坚也有论述:“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17]即书法要有书卷气,若脱离书学仅有勤学也无法避免俗态。
人们常用金石气和书卷气来形容书法艺术,这亦是书法风格的两种类型。金石气更多是依赖外在的形式给人以视觉的冲击,体现出一种浑厚、朴拙之气,多是在青铜器上有所体现,还体现在一些钱币、铜镜中的铭文和碑、摩崖等石迹之上。而书卷气更多是体现书法的内在,书卷气历来备受文人书家强调,亦可称学问气,体现了一个人的风度和气质。书家的内在文化气质跃然纸上,亦是书法注重博学的体现。
古代书家对于书法学习,既做到了注重勤学也做到了注重书法艺术的博学。技道并进,自然书写,书法理论和书法技艺的双重并进是书法的治学之道,过于追求技艺避免不了在长期的书法学习当中过于匠气无神,而完全投入到对理论的追求则是更多是理论层面的学习,只有理论没有实践也不是对书法艺术的真正领悟,书法理论指导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检验书法理论,博学多采才会促进书法艺术的提升。只有书法理论和书法艺术完美结合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书法学习效果。在当今书法学习热潮中,传承与弘扬书法艺术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需注重技道并进,加强技法和理论的学习,注重文化的积累,推进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赵壹.非草书[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
[2]卫恒.四体书势[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6.
[3]虞世南.劝学篇[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37.
[4]朱长文.续书断[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27.
[5]朱长文.续书断[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28.
[6]朱长文.续书断[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31.
[7]徐浩.论书[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76.
[8]孙过庭.书谱[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4.
[9][10][11]孙过庭.书谱[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6-127.
[12]刘熙载.艺概[C]//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5.
[13]王僧虔.笔意赞[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2.
[14]杨守敬.书学迩言[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12.
[15]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29.
[16]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20.
[17]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335.
作者单位:
沈阳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