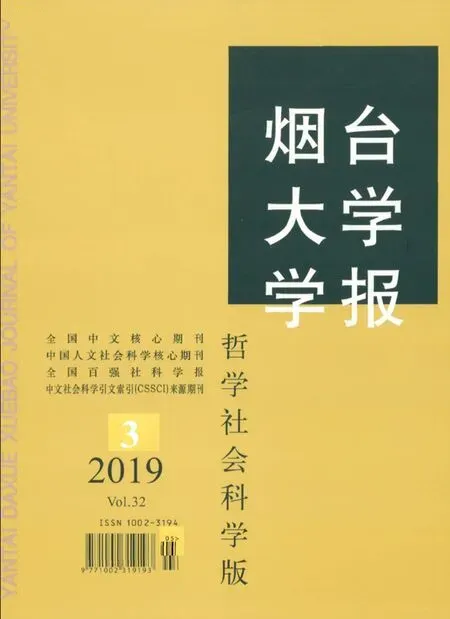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再厘定及适用探讨
梅夏英,朱开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29)
之所以规定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是因为其主观上有可以归责的事由,即对于在线侵权事实的明知和应知。[注]参见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状态的判定在现阶段相对容易,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认和法定化的“通知取下规则”加以实现。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状态的判定则始终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适用上的困境:从学理角度讲,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制度内涵和规则标准始终未能明确界定,导致理论对实践缺乏应有的指导作用;从立法角度讲,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既有法律和相关解释过于零散和混乱,导致审判实践中个案认定的差异。本文从“应知规则”的制度价值定位出发,在剖析我国现有理论和立法不足的基础上,对“应知规则”的本质内涵和规则标准重新进行厘定,并通过系统化的分析方法来解决其适用上的困境,以期从理论角度为后续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制度价值与适用反思
(一)“应知规则”的制度渊源探寻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起源于美国判例法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帮助侵权责任制度。美国加州地方法院早在1995年审理的RTC v. Netcom一案中便将著作权帮助侵权责任引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领域,指出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但仍为直接侵权人提供实质性帮助时,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帮助侵权责任,并将其中的“知道”阐释为“实际知道”(clearly know)和“有理由知道”(should have known),即我们所说的“明知”和“应知”。[注]See Religious Tech. Center v. Netcom Online Comm. Cite as 907 F. Supp. 1361 (N.D.Cal. 1995)
美国国会于1998年出台了《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案在总结判例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避风港制度”的形式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规则予以成文法化,并赋予了“应知规则”一个更形象的名字“红旗规则”。[注]“红旗规则”是指当某事实或情况对于理性人而言已经如红旗般明显时,如果行为人采取鸵鸟政策,装作看不见事实,则推定“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See Melvile Nimmer &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Mattew Bender & Company, Inc., 12B.04 [A][1](2003)对于“避风港制度”的规定主要存在于《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之中,该条款通过条件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四类可以享受著作权侵权责任豁免的网络服务类型。免责条件的第一项便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直接侵权事实不存在明知和应知的情形,或在满足知道要件的要求后毫不迟延地采取制止侵权的有效措施,才可以进入到侵权责任避风港之中。[注]See17 U.S.C. §512 (c)(A)(i) does not have actual knowledge that the material or an activity using the material on the system or network is infringing; (ii)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ctual knowledge, is not aware of facts or circumstances from which infringing activity is apparent; or (iii) Upon obtaining such knowledge or awareness, acts expeditiously to remove, or disable access to, the material.《数字千年版权法》将“应知规则”法定化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缺乏实际知道的情况下,不存在明显昭示侵权的事实和环境来认定其对于侵权活动的知晓”。此后,“应知规则”作为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核心依据被世界各国所借鉴和采纳,例如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德国的《电信媒介法》以及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等等。
(二)“应知规则”的制度价值定位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领域,“应知规则”长久以来一直是理论探讨的焦点和实务认定的难点,原因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规则特征所产生的独特制度价值。“应知规则”的制度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其是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核心要件。从比较法角度来讲,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体系由帮助侵权责任、教唆侵权责任和侵权替代责任三大部分组成,但实践中帮助侵权责任一直是纠纷发生的重点领域。[注]参见吴汉东:《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网络侵权责任解析》,《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由“知道要件”和“实质性帮助要件”组成,但现实纠纷表明“实质性帮助要件”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不大,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此领域责任成立与否的关键在于对“知道要件”的判定。[注]See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Cite as 239 F.3d 1004 (9th Cir. 2001)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中的“知道要件”由“明知”和“应知”两种情形构成,并作为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成立与否的主观过错依据。基于上述原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和“明知规则”一起构成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完整规则体系。另一方面,相较“明知规则”,对于“应知规则”的合理化认定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体系中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需求。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状态的认定是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认和“通知取下规则”加以实现。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对侵权事实知道的自认相对简单且直接,而“通知取下规则”具有明确的法定流程和标准。因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状态的判定在理论层面无较大争议,在操作层面明确易行。然而,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状态的判定则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根据侵权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和事实来加以认定。如何科学地设置“应知规则”的判定因素和认定标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长久以来都是理论和实务中的难点。最后,从网络侵权现实纠纷来看,在大部分案件中都不存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状态的基本条件,而是需要我们根据侵权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和事实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应知状态进行推定。因此,相较“明知规则”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在现实纠纷中有着更为强烈的适用需求。
(三)“应知规则”的立法现状反思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在我国既有法体系项下首先体现在被称为“网络侵权专条”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之中。《侵权责任法》第36条虽仅有短短的3款规定,但仍通过该条第3款内容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加以囊括:“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为了和第2款中的“通知取下规则”相区别,该条款中的“知道”便被解释为在缺乏权利人“取下通知”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若根据侵权发生的具体环境和事实对具体的侵权行为存在认识,那么若不采取制止侵权的有效措施便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注]参见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虽然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纳入其中,但相关条文的具体内容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既有法条的立法技术过于粗糙,没有针对日益专业化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类型化的责任认定;另一方面,既有法条的内容过于抽象,造成了法院系统在规则的适用上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侵权形势和不断变化的网络侵权类型,《侵权责任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既有规定在具体适用中愈发显得捉襟见肘。[注]参见刘晓海:《〈侵权责任法〉“互联网专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责任的影响》,《知识产权》2011年第9期。因而需要我们从理论角度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进行内涵厘定,并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方法建立“应知规则”的适用标准体系。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内涵再厘定
(一)“应知规则”的两个认识误区
自“应知规则”在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领域确立以来,理论界长期对其存有两个认识误区:一个认识误区体现在“应知规则”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先审查义务的关系认定方面;另一个认识误区体现在“应知规则”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形态的关系认定方面。
1.认识误区一:“应知规则”是对于在先审查义务的肯定
根据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避风港制度”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若希望获得侵权责任的豁免必须对于在线侵权事实不满足“知道要件”的要求,或者在满足“知道要件”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这其中的“知道要件”被具体阐释为“明知”(actual knowledge)与“应知”(in the absence of such actual knowledge, is not aware of facts or circumstances from which infringing activity is apparent)。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使用了语意较为模糊的“知道”一词,未将其明确规定为“明知”或者“应知”亦或是“明知或应知”。这不但在我国侵权理论界引发了热议,而且直接影响了各级法院对于此项规则在具体审判实践中的应用。[注]相关争议直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出台针对《侵权责任法》的专门解释才慢慢消弭,“知道”一词的含义被认定为既包括“明知”也包括“应知”。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94-195页。
我国理论界对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争议的核心在于,该款条文中的“知道”一词是否包括“应知”的含义。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应知”侵权事实而承担侵权责任,实际上便令其承担起了主动审查网络空间中是否存在侵权事实的义务。[注]参见徐伟:《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认定新诠——兼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论》,《法律科学》2014年第2期。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对侵权事实的在先审查义务早已被国内外立法成例所肯定,[注]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先审查义务的免除,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通行立法选择。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检视网络、寻找侵权活动的义务。《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要求各成员国不得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监视其传输或储存的信息的义务,不应施加积极查找表面为非法活动的事实或背景的一般性义务,以免其负担过重,不利于其更好地提供服务。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中的“知道”便不应含有“应知”的意思,由此便将“应知规则”排除在了既有法条的规定之外。笔者认为此种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和在先审查义务做一体化认定进而质疑其存在价值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应知规则”内涵的误读。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厘清该规则和在先审查义务的关系:一方面,虽然广义上的“应知”可以被解释为“有理由知道”和“有义务知道”,但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规则之中,“应知”一词实际只具有“有理由知道”的含义。美国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规则起源地,其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应知规则”的表述始终是“have reason to know”(有理由知道)而非“have duty to know”(有义务知道),此中便可见一斑。但实际上只有“有义务知道”才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先审查义务相对应,因而“应知规则”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先审查义务并没有本质联系。另一方面,“有义务知道”实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替代责任规则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对侵权事实存在控制权利和控制能力的情况下,若从侵权事实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那么便有采取主动审查并且制止相应侵权行为的义务。[注]参见宋哲:《网络服务商注意义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我们不应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项下的“应知规则”(有理由知道)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替代责任项下的“在先审查义务”(有义务知道)相混淆。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事实的“应知”厘定为“有理由知道”并与“在先审查义务”相分开,便澄清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论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个认识误区。
2.认识误区二:“应知”与主观过错形态中的“过失”相对应
“故意”和“过失”作为对侵权行为人主观过错形态的二元划分,源于侵权责任法理论对于刑法理论的借鉴。在刑事责任认定过程中,行为人故意和过失的区别直接决定了其主观恶性的大小,并通过量刑的轻重来最终得以体现。在侵权责任认定过程中,对侵权行为人故意和过失的区分相应地便落脚于对其主观可归责性大小的判断并反映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大小。[注]参见叶名怡:《侵权法上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及其意义》,《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领域,理论界存在一种认识误区: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侵权行为的存在,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认定为故意侵权;而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认定为过失侵权;进而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状态下的主观恶性要大于“应知”状态下的主观恶性。[注]参见杨明: 《侵权责任法第36条释义及其展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上述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和过失状态关系的阐释,在理论角度实际上很难自圆其说。从“应知规则”的制度渊源来看,美国法院系统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实际上是普通法上“漠视规则”(Willful blindness doctrine)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领域的适用。[注]See EMI Christian Music Group, INC. v. MP3Tunes LLC Cite as 844 F.3d 79 (2nd Cir. 2016)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对像随风飘摇的红旗一样明显的侵权事实视而不见,那么其主观上便存在可归责性,也便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注]See 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ATION, Cite as 334 F.3d 643 (7th Cir. 2003)因此,在“应知规则”项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是如同“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要求的那样对于侵权事实应当知晓而没有知晓或认为侵权事实不会造成相应的损害后果,而是在认识到侵权行为实际存在之后故意视而不见,鼓励或放任侵权损害后果的继续。[注]参见冯术杰:《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过错形态》,《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因此,那种将“明知”和“故意”、“应知”和“过失”进行简单对应处理的做法,以及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状态”较之“明知状态”主观可责性要轻、危害程度要低的认识应当被摒弃。
(二)“应知规则”实质内涵和规则标准的确立
在破除了理论界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存在的两个认识误区以后,我们需要科学厘定“应知规则”的实质内涵和规则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在我国属于一项对域外制度的舶来品,对其实质内涵和规则标准的探讨首先应当立足于对域外立法状况的还原,并在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化的认定。
1.实质内涵:“应知规则”是对于“知道标准”的客观化认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肇始于美国,在总结既有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纠纷判例的基础上,美国法院系统为了更好地发挥“应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作用,从“明知标准”和“应知标准”的区别出发,对二者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界定。[注]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 cite as 801 F.3d 1126(9th Cir. 2015)在《数字千年版权法》出台之前,法院系统即认为判例法体系项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中“明知”和“应知”的区别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直接侵权事实是否存在主动审查义务无关,也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直接侵权事实的认识标准无关。“明知”和“应知”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直接侵权事实的一个主观判断标准,后者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直接侵权事实的客观判断标准。《数字千年版权法》颁布以后,各级法院就“避风港制度”中“应知规则”的内涵也进行了具体界定。在美国第二巡回法庭2012年审理的Viacom v. YouTube案中,法官明确指出,“避风港制度”中的“明知标准”和“应知标准”的差别本质上在于前者是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侵权事实的主观标准,后者是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侵权事实的客观标准。[注]See Viacom Intern, Inc. v. YouTube, Inc. Cite as 676 F.3d 19 (2nd Cir. 2012)
从此种解释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地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规则”和“应知规则”的内涵加以认定:所谓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事实明知,指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证据来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内心对于侵权事实是知道的,一般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认和权利人发出适格的“取下通知”加以证明;所谓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事实应知,指的是我们在无法通过直接的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事实知道的情况下,通过其他的证据可以间接推断出其对于侵权事实存在主观上地认识。换言之,“应知规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否主观感受到那些在理性人看来使得具体侵权行为变得客观明显的事实。[注]参见梅夏英、刘明:《网络侵权归责的现实制约及价值考量——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切入点》,《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应知规则”因其采用理性人的注意义务标准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事实是否客观知道而没有被“明知标准”所取代,二者在各自规则认定领域发挥着独立的适用价值。
2.规则标准:“应知规则”是对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的认识
明确“应知规则”的实质内涵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要件”的客观化判定之后,我们需要解决如何合理界定“应知规则”项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事实知道的程度和标准。在美国,法院系统长期以来存在对“应知规则”的标准探讨,焦点体现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应知规则”的要求时,其对于侵权事实应达到何种认识程度。[注]See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Cite as 710 F.3d 1020 (9th Cir. 2013)在“应知规则”项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是要求仅仅概括性的认识到平台空间中存在侵权事实,还是应当和“明知规则”项下对具体的、可识别侵权事实知道的要求相同。美国法院系统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领域的相关判决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达到对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知道的前提下才能满足“应知规则”的要求。[注]在2011年纽约地方法院审理的Capitol Records, Inc. v. MP3tunes, LLC一案中,法官指出:“我们不认为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法享受到侵权责任的豁免,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存在侵权事实,但缺乏‘红旗规则’下对于具体侵权链接的了解。”美国第二巡回法庭在2012年对Viacom v. YouTube案做出的判决中指出无论涉及“明知标准”下的“通知取下规则”还是涉及“应知标准”下的“红旗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直接侵权事实的认识程度都必须达到对于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的知道。在2013年审理的UMG Recordings, Inc. v. Shelter Capital Partners LLC案中,美国第九巡回法庭指出:“我们不能放宽对于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知道程度的要求无论是在明知标准还是在应知标准之中,因为我们不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去查明具体的信息是否存在侵权的状况。”
美国法院系统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采纳上述认定标准的原因可以从联邦第二巡回法庭在Viacom v. YouTube案的判决中得到集中反映。该法庭指出对于《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应知规则”的阐释不应当使得法条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依据避风港制度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论是明知还是应知在线侵权事实都不必然导致其侵权责任的承担,其可归责性在于对侵权事实知道以后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然而若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事实的知道不能达到对于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的认识,那么其便不存在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条件。按照上述分析进路,若不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认定标准定位于对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的知道,将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要满足“应知规则”中的一般认识标准,无论是否采取制止侵权的措施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荒诞结论。[注]See Viacom Intern, Inc. v. YouTube, Inc. Cite as 676 F.3d 19 (2nd Cir. 2012)
笔者认为,对于“应知规则”项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标准的认定应当坚持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对于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的认识。首先,既然我们已经厘清“应知规则”和“明知规则”的差别在于二者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中“知道要件”的主观认定标准和客观认定标准,那么其差别便仅存在于判定维度而非认识程度。其次,无论是来源于判例法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规则还是《数字千年版权法》中的避风港制度,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获知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的前提下才需要承担相应的作为义务。因为面对网络空间中海量且随时变化的信息,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一般抽象认识下的作为义务,将会令其在技术和经济上存在不能承受之重。最后,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来看,仅仅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而只有当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得知侵权事实后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才会被归责。[注]参见梅夏英、姜福晓:《数字网络环境中著作权实现的困境与出路——基于P2P技术背景下美国音乐产业的实证分析》,《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制止侵权有效措施的前提恰恰就在于其对具体、可识别侵权事实的认知。
三、多元视角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适用探讨
(一)域内外“应知规则”的适用标准差异
从比较法角度来讲,域外各国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适用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一个抽象标准,而由法院系统在审判实践中根据个案情况加以具体认定。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状态”的定义是“存在对于明显昭示侵权活动的事实和环境的知道”(be aware of facts or circumstances from which infringing activity is apparent)。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美国法院系统一般用“红旗规则”一词来代称“应知规则”,但也仅仅是将“红旗规则”原则化的解释为“当侵权事实像随风飘扬的红旗一样明显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便不能再称其对于侵权事实不知道”。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和德国《电信媒介法》也明确肯定了“应知规则”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中的适用。[注]根据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14条第2款的内容,就信息储存服务提供者而言,若希望获得责任限免则应当对违法活动或违法信息不知情,并且就损害赔偿而言,提供者对显然存在违法活动或违法信息的事实或者情况毫不知情。德国《电信媒介法》第10条规定,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除了知道行为或信息,还要知道明显昭示违法的事实或情况。但欧盟和德国理论界、实务界都没有就什么情况下侵权事实足够明显或显然,从而引发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状态的成立进行详细说明。在德国,理论界认为只有在考量个案一切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对明显昭示侵权的事实或情况做出判定;而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通常则认为只有当相关事实和情况的侵权属性如此之明显以至于不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进一步调查认定时,“应知规则”才可能成立。
不同于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采用抽象适用标准的做法,我国法院系统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明确了“应知规则”的一系列详细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注]该规定第9条列举出六种判定网络侵权事实是否明显的因素:第一是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第二是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及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第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第四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第五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设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并及时对侵权通知作出合理的反应;第六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第10条[注]该规定第10条则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视频作品在线播放服务时,如何判定其是否构成对于侵权事实的应知专门加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第12条[注]该规定第12条则针对提供信息储存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对于侵权事实的应知加以规定,主要的判定因素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将热播影视作品等置于首页或者其他主要页面等能够为网络服务用户明显感知的位置;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对热播影视作品等的主题、内容主动进行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或者为其设立专门的排行榜。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进行了具体阐释,总的原则反映在条文内容上便是:“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然而我国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上述规定缺乏必要的体系化建构,相关判定标准、因素过于分散和混乱,因而我们需要在总结既有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笔者认为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适用探讨:一是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线服务属性的角度,来判断其是否存在对侵权事实的应知状态;二是从侵权信息的特征角度,来判断涉案信息是否足够明显从而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意识到侵权事实的存在;三是从其他客观环境角度,来判断是否存在第三人的侵权通知使得涉案侵权信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足够明显。
(二)网络服务属性视角下的“应知规则”适用标准
从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角度来探讨“应知规则”的适用标准,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我们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线服务的一般属性来判断其是否会直接接触到可能的侵权信息。若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系统的技术特征或“用户协议”的规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会在用户每一次上传和发布信息的时候从事实质性的修改、编辑或者加工等直接接触到信息内容的行为,那么我们原则上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其控制下的平台空间中是否存在侵权信息构成应知。若网络服务提供者经营的平台空间属于自动化的信息处理系统,用户无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介入便可以实现信息的自动上传和发布,那么我们原则上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其控制下的平台空间中是否存在侵权信息不构成应知。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考察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涉案的侵权信息是否采取了不同于平台空间中一般信息的特殊处理方式。例如,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般运营模式下,其不存在对用户信息上传和发布行为的实质性影响,因而原则上不满足“应知规则”项下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认识的要求。但是对于涉案侵权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为在其中添加了商业广告而具备了实质性接触此信息的条件,从而例外地符合了“应知规则”对于侵权事实知道的要求。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有可能因为根据网络用户的点击量以及其他信息热度统计方式,将本来在上传发布之初未实质接触的信息内容通过编辑加工的方式予以置顶或者添加到网页排行榜的前列,从而构成对于此类侵权信息的应知状态。[注]参见沈森宏:《论〈侵权责任法〉网络侵权“知道规则”的适用》,《法律适用》2018年第10期。
(三)侵权信息特征视角下的“应知规则”适用标准
从侵权信息自身特征角度来考察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适用标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可以根据涉案信息本身的知名度或社会影响力来判断此侵权信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是否足够明显。以专业的视频播放网站为例,对正处于热播期的影视作品、知名演员或导演参与的影视作品以及其他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影视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理应保持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并应当意识到凡没有正版授权标识的作品都属于侵权内容。[注]参见陈锦川:《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认定的研究》,《知识产权》2011年第2期。
其次,可以依据涉案信息在网络平台中所处的位置来对其是否构成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项下的明显侵权信息加以判断。我们一般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那些处于网站显著位置或者位于网站内特定排行榜前列的信息,应当保持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若此类信息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那么我们原则上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此类侵权信息符合“应知规则”的要求。
最后,可以根据涉案信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控制下的平台空间中是否曾经发生过侵权的事实,来判断该信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是否构成“应知规则”项下的明显侵权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自身网站已经发生过的侵权事件中涉及到的特定权利,相较于其他一般权利而言,应当保持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注]参见曹阳:《互联网平台提供商的民事侵权责任分析》,《东方法学》2017年第3期。上述特定权利一旦再次发生被侵害的状况,我们可以推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代表此类权利的信息符合“应知规则”项下的要求。若其不能及时采取制止侵权的有效措施,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帮助侵权责任。因为在此情况下,我们并不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一种盲目的在先审查义务,而是采取一种在技术和经济上成本都可控的、针对特定权利的侵权审查义务。
(四)第三人通知视角下的“应知规则”适用标准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具体适用,除了从上文提到的网络服务属性视角以及侵权信息特征视角加以判断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第三人特定行为的视角,特别是根据第三人是否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过“侵权通知”来加以认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此处所讲的“侵权通知”区别于“通知取下规则”中的“取下通知”,因为二者的发出主体不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要收到权利主体发出的适格“取下通知”,即负有法定义务采取屏蔽、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等制止侵权的措施,否则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帮助侵权责任。[注]参见梅夏英、刘明:《网络侵权中通知规则的适用标准及效果解释》,《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但是对于第三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因为其并非权利遭受侵害的适格主体,故而不享有直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制止侵权措施的法定权利。但只要第三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侵权通知”存在实质性的侵权证据,尤其是在符合“通知取下规则”中对于适格“取下通知”的要求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便可以被推定为符合“应知规则”的适用要求。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此时已经获知了侵权信息的定位、侵权事实成立与否的基本判断以及其他处理侵权行为的必要信息,所以按照理性人的一般判断标准其对于此项侵权行为便存在主观上的认识。[注]参见王利明:《论网络侵权中的通知规则》,《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在2013年美国第九巡回法庭审理的UMG v. Shelter案中,法庭便指出:“虽然作为权利主体的原告没有就侵权事实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取下通知,但是作为第三人的全美唱片工业联合会曾就被告网站存在的侵权事实向其发出过警告,此种警告可以作为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满足应知规则的一个重要依据。”[注]UMG Recordings, Inc. v. Shelter Capital Partners Cite as 718 F.3d 1006 (9th Cir. 2013)
——从“实际作用”转向“规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