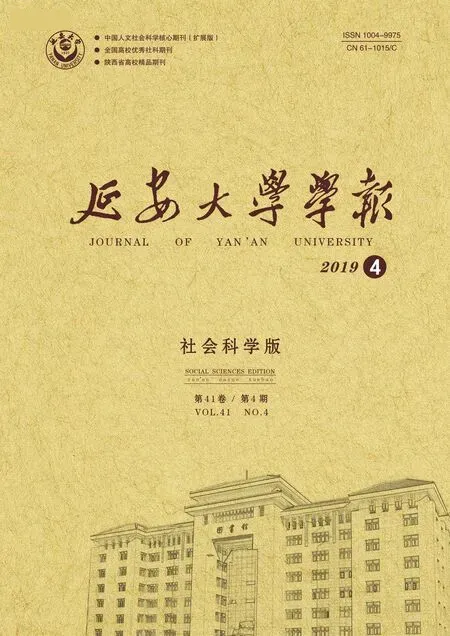在学术创新中体现人文情怀
——评阎浩岗著《茅盾丁玲小说研究》
袁盛勇,邱跃强
近年来,阎浩岗教授在现代中国小说研究领域用力甚勤,先后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论》《“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现当代小说论稿》等学术专著。现在,又出版了《茅盾丁玲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一书。该书是一部较为优秀的学术著作,其进一步推动了茅盾和丁玲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茅盾和丁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存在,由于作者在中国茅盾研究会和中国丁玲研究会都担任学术职务,对两位著名作家的关注较早,能持续了解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也正因如此,作者在研究中才会独辟蹊径,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且在其自我学术特色的形成中有着较为自觉的学术创新与追求。
笔者认为,《茅盾丁玲小说研究》至少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具有较为明确而实在的思考与论述角度。对于茅盾,作者从其小说创作方法出发,针对研究界认为茅盾小说创作方法与主流创作方法是一致的这种较为普遍的认识,作者通过细致而深入地分析与研究,表示并不认同,而是认为茅盾的小说创作方法与主流创作方法并不一致,存在诸多差异。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作者对茅盾的创作方法探本溯源,既弄清它和主流创作方法之异同,又探究其创作方法的中外美学渊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茅盾作品的重新研读,作者发现茅盾小说与主流创作方法之间有同有异,但“异”尤其不可忽视,也正是“异”,才决定了茅盾小说的美学特性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丁玲思想和创作,既与五四新文化发生了深刻联系,更与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化与文学密切关联,丁玲文学是左翼文学链条中的优秀一环,不可或缺,而丁玲更是一个具有丰富革命内涵和现代性文学价值的传奇存在。阎浩岗显然注意到了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丁玲的小说。同时,作者也对丁玲小说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在这方面,丁玲小说与茅盾小说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能坚守一定的独立创作追求。阎浩岗认为丁玲的早期作品,比如《阿毛姑娘》和《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表现出一定的复调性或价值选择的两难,而这也是丁玲“革命”性格的一种表现。丁玲最后虽然成为了“革命作家”,但五四时期的独特个性依然保持着,虽然在某些时候要略微减去它们的光芒,但这种个性却一直在丁玲的骨子里,不论时代如何变化,环境如何改变,这种渗透在骨子里的性格却是不变的,而这也恰是丁玲之所以为丁玲之所在。
第二,注意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在书中,阎浩岗在论述茅盾小说时,将其创作方法与沈从文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在创作态度、创作对象、创作过程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茅盾小说是“投身政治”,沈从文小说是“远离政治”;茅盾创作是“表现社会整体”,沈从文创作是“展示一角人生”;茅盾小说不无“主题先行”,沈从文小说是展现“情绪的体操”;茅盾创作忠于“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沈从文创作是“坚持独立思考”。但是,不同路径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经典作品,阎浩岗从两人明显的差异中,看到了两人在忠于具体感受、坚持独立思考、尊重艺术规律方面的一致性。茅盾在一个革命大时代的动荡中,其实更加体会到了一些在革命旋流之中不断沉浮的历史内涵,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不无犹疑和穿越;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更加具有鲜明的艺术表达和人性考量。关于丁玲小说,此种比较也是非常明显。作者在下编第四章《丁玲的土改叙事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中,将丁玲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暴风骤雨》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丁玲土改叙事中的“异端”成分,是和丁玲本身的个性、“革命”性格息息相关的。作者这样论述,可以看出茅盾和丁玲在文学史的地位及其价值的形成,也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文学更为丰厚的面影。
第三,在研究和书写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人文情怀。阎浩岗在该书上编第一章写道:“文学是人学,评价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应当是对于人性揭示的深刻程度及艺术形象本身的生动真实程度和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大小,而不是其他什么标准。”(第5—6页)这可以看作是阎浩岗进行茅盾丁玲小说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正因如此,对于学术界公认的茅盾小说创作与主流创作方法是一致的观点,作者才能够提出新的观点,即“茅盾小说创作方法的非主流性”,茅盾的创作方法是与主流创作方法有差异的。这是因为,作者看到了茅盾作品中蕴含着个人的生命体验,看到了茅盾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有着不同的思想情感基调,而这又与茅盾“本身的人格结构有关”。而对丁玲,阎浩岗看到了她身上所具有的独特个性,看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看到了丁玲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忠实。阎浩岗在书中,每每为作家丁玲所具有的自我存在而击节叹赏,其实,丁玲文学的现代性和经典性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正在此处。当然,丁玲对革命的向往和书写,其实已经成了她的信仰,成了其生命的一个重要构成。对此,阎浩岗在书中写道:“丁玲那种为理想信念飞蛾扑火的精神,虽不必、也不可能人人做到,但它却值得尊敬。我们不应用世俗的日常理念衡量它。”(第140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字里行间所具有的人文情怀。
第四,具有一定思想性。《茅盾丁玲小说研究》一书,尽管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书中有一定思想性的语言表述,它们或是作者有感而发,或是作者就某一作品、某一文学现象的感想,而这些语言表述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思考与感想,而且也使读者有所思考和感触。例如,在上编第一章《茅盾小说创作方法的非主流性》中,作者在分析《动摇》主人公方罗兰对于革命暴力的矛盾心态时,认为也暗含有茅盾本人对于革命暴力的矛盾心理,指出“茅盾笔下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场闹剧,一场狂欢”,认为“革命可能在量变条件具备的前提下通过暴力手段完成质变,使社会发展出现飞跃,使社会利益得到一定平衡、社会结构实现新的稳定,但不可避免的流血也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加深,使人心变得坚硬。”(第7—8页)这些论述就较为明确地体现了作者的思考:是革命,就必然有流血,它一方面促进着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会使人心变得坚硬,甚至麻木和残忍。这不仅是茅盾对革命的思考,也是阎浩岗在对茅盾作品深切了解和研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感悟与思考。此外,在作者看来,“中国大陆文学界一直似乎有一种公论:凡是乐观的观点便是健康的、进步的,凡是悲观的观点便是消极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对此,作者认为“深刻的悲观远胜过廉价的乐观”(第13页)。这个认识在我们看来,也是较为准确而发人深思的。茅盾不少作品,如《虹》《路》《三人行》等表现的其实就是悲剧,但是它们仍然能给人以有益的精神导引。
综上所述,阎浩岗在书中对茅盾丁玲小说的研究,显然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抱负,也确实在研究和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体现了学术求真求新的本质。对于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者也能在论述中予以认真回应,富有学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这就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发生了一种对话关系,人们对茅盾和丁玲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判断,也就会受到影响,发生某些积极变化。阎浩岗在茅盾和丁玲研究路途上,仍在不倦前行,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令人备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