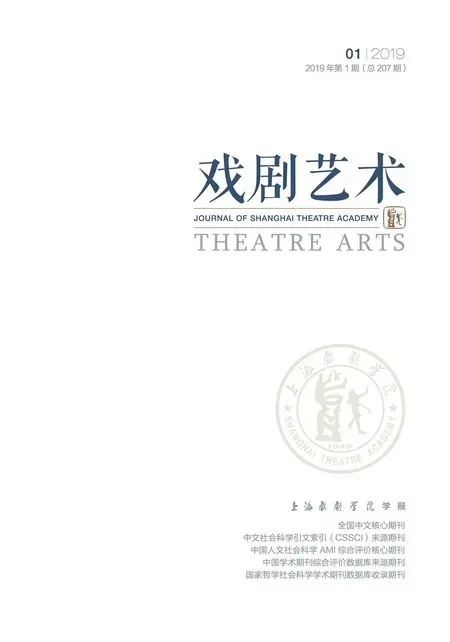重思余上沅写意戏剧论
余上沅与赵太侔、闻一多等人在1920年代中期发动的“国剧运动”,从1924年夏天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在纽约开始演戏算起,到1926年秋天《晨报副刊·剧刊》停办为止,前后持续的时间差不多两年。对于一场艺术运动来说,尤其是考虑到戏剧创作的周期较长,两年左右的时间跨度确实太短了。“国剧运动”并没有留下成功的剧目,其理论和主张也被批评为保守落后,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戏剧和美学研究者所遗忘。但是,在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文化潮流由百年前的“西学东渐”,转变成了百年后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回过头来看这场“国剧运动”,会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启示。不过,我感兴趣的,还不是作为艺术运动的“国剧运动”,而是支撑“国剧运动”的戏剧理论,尤其是余上沅的“写意戏剧”理论。
一
在1924年发表的《表演的艺术》一文中,余上沅提到一种特殊的表演类型,他称之为“写意”:
表演可以分作四类:第一类是“写实”,第二类是“派别”,第三类是“内工”,第四类是“写意”(这四个名词非常不妥,我们暂且不论罢)。第一、二两类是相似的:扮演什么人便是什么人;其不同之处:第一类能够变作各种各样的人,第二类则流入扮老人则始终是老人,扮青年则始终扮青年的派别。第三类的表演,不在乎化装(第一、二两类是一部分借重化装的)。这类的表演,非大演员不可;譬如卓别林一样,演员能随时随地用音节、面容、举止来表现他们内心的感觉。第四类与前三类都不同:前三类的表演是舞台为范围,演员自己忘却了是在演戏,他们自己已经变成剧本中的人了。第四类是不要忘记了自己是演员,是在舞台上对着观众表演戏剧的演员。他们的主要精神,是要把他们对于剧本的解释,从台上传达到台下去,使剧场成为一个整体。[注]余上沅:《表演的艺术》,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15-116页。
这里的四类表演,其实可以区分成两类,前三类都可以归入“写实”的表演,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内部区别或者小类区别。第四类表演与前三类都不相同,而且这种不同是大类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余上沅称作“写意”的表演类型,是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新类型,与当时的戏剧要打破剧院的第四堵墙的新运动有关。余上沅说:“如今的运动,就是要打破这堵隔开演员与观众的墙,使他们彼此成为一体,换句话说,从前的舞台是一个‘西洋景’,观众从‘镜框’里看它。如今要戳穿西洋景,让观众也做这幅西洋景上的一部分。”[注]余上沅:《表演的艺术》,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16-117页。“写意”表演,是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戏剧运动而发展起来的。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种新的表演类型,余上沅还把它与绘画做了对比:
要详细讨论这个运动便不能不牵涉到别的艺术上去,尤其是绘画的艺术。写生画(representational)是与写实派的表演平行的;写意画(presentational)是与这个新运动平行的。写意画是要把若干形体的关系宣达出来,不问这些形体是否属于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内。新式的排演也是一样:与其用画的布景,立体的布景,不如老老实实就让后面的幔子去做幔子,让建筑物去做建筑物,并不强勉地要人去相信幔子是城墙,建筑物是宫门。新式的表演也是一样。化装作老人,便自信是老人;站在舞台上,偏要说站在起居室内;咬定牙关不承认这全是假的;又装着不理会台下有一大群人在看他。与其这样,不如老老实实地自己承认自己是演员,台下有人在看他,他的职务是要用他的艺术去得观众的赞赏。[注]余上沅:《表演的艺术》,《晨报副刊》1924年5月6日第101期,第3版。这段文字,在三个版本中有些出入。在余上沅《戏剧论集》(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中,题目由“表演的艺术”改成了“论表演艺术”,“写生画”改成了“写实画”,保留了括号中的英文(见195页)。从这些改动来看,《戏剧论集》中收录的文字应该经过余上沅的校订。在《余上沅戏剧论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中,题目改回了“表演的艺术”,“写生画”改成了“写实画”,括号中的英文去掉了(117页)。
需要注意的是,余上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美国匹兹堡,他所说的剧场史上发生的新运动,指的是欧美的戏剧运动。他用来与写实派和写意派表演对应的写生画和写意画,也是西方的两种绘画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绘画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再现型绘画和表现型绘画。更确切地说,余上沅这时是在介绍西方20世纪初期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写意戏剧和写意绘画是现代主义运动在戏剧和绘画领域中的表现,尽管用了“写意”一词,但指的可能不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绘画。对此,刘思远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写意”一词的灵感并非研究者通常认为的来源于中国绘画。余没有提到中国画,他的写意画也不是与“工笔画”对应,而是与西洋“写生画”对应,指现代派绘画和阿皮亚和戈登·格雷等的现代舞台美术,其英语分别是presentational和representational。这两个词后来在学习斯氏体系和20世纪60年代初“演员的尴尬”讨论中被译作“体现派”和“体验派”,分别以哥格兰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可见这两种表现手法的区分源远流长。[注]刘思远:《国剧运动的戏剧史学研究——以余上沅1922-1926年的戏剧活动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不过,我的看法与刘思远稍有区别。尽管余上沅这里介绍的是西方艺术,但是“写意”和“写生”是中国绘画美学中的概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在余上沅之前,由于康有为和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美术革命”,美术领域关于“写生”与“写意”之间的争论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写生”指的是工笔花鸟,被认为是“写实”在中国绘画中的表现。余上沅用“写生”来对译西方的“写实”,用“写意”来对译西方的“表现”,但不能因此认为“写生”和“写意”这两个概念也来自西方。由于国画中的“写生”不完全等同于“写实”,因而容易造成歧义,余上沅后来很快就用“写实”来代替了“写生”。
刘思远这段文字中更大的问题,是将“写实派”和“写意派”与后来的“体现派”和“体验派”联系了起来。余上沅用“写实”来翻译“representational”,用“写意”来翻译“presentational”,与后来的“体现派”与“体验派”之争完全不同。哥格兰被认为是“体现派”(也称之为“表现派”)的代表,对应的是“representational”,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被认为是“体验派”的代表,对应的是“presentational”。但是,事实上,余上沅所说的“写意”(presentational)表演,既不同于哥格兰的“体现派”,也不同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体现派”和“体验派”讲的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根据“体现派”,演员与角色之间可以保持距离;根据“体验派”,演员与角色需要融为一体。但是,余上沅所说的“写实派”和“写意派”讲的是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写实派”的表演,演员与观众之间没有关系,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将他们隔开,也就是所谓的第四堵墙。“写意派”的表演,则打破了这堵墙,演员与观众可以交流互动。从余上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体现派”还是“体验派”都是“写实派”,都建立在第四堵墙的理论的基础上。余上沅所说的“写意派”,与哥格兰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没有关系。尽管也可以用“presentational”来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但是它的意义与余上沅的“写意派”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将“presentational”翻译为“在场”,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加清楚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指的是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角色在场,演员完全消解在角色之中;余上沅所说的“写意派”指的是演员自己在场,演员的表演本身成为欣赏的对象。就像伊拉姆(Keir Elam)指出的那样,在戏剧理论领域,“presentational acting”,也即余上沅所说的“写意派表演”,通常指的是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即演员通过特定的语言、扮相、姿态、符号等等直接或间接向观众表示自己在表演。[注]Elam, Keir, The Semiotics of Theatre and Drama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0), pp. 90-91.
如果余上沅的“写实”与“写意”的区分,与哥格兰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争,或者哥格兰和欧文之争无关,那么余上沅的“presentational”和“representational”这两个概念究竟源自何处?从余上沅涉猎的文献来看,它们极有可能源自20世纪初爱尔兰的戏剧革新运动。在《演员与剧作家》一文中,麦克布莱恩(Peter Mcbrien)就讨论到爱尔兰的戏剧革命。在麦克布莱恩看来,这种革命的实质,就是“表现派”战胜“再现派”。“表现派”戏剧主张演员中心,强调演员表演具有独立价值,而不只是再现剧本所描写的角色。相反,“再现派”戏剧主张剧本中心,强调演员的表演自身没有价值,除非成功地再现了剧本中的角色。麦克布莱恩说: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t)表演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呈现性(Presentational)表演,以区别于常规戏剧中的普通表演,普通表演是再现性的(representational)。这就是说,常规戏剧是被假定要发生的某事的照片或者再现,相反,呈现性戏剧可以说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件,它们就像在真实生活中一样是第一次发生的。[注]McBrien, Peter, “The Actor and the Dramatist,” Studies: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12, No. 48 (Dec., 1923), p.640.
被余上沅译为“写意”、我译为“呈现”的,是同一个英文词“presentational”。在麦克布莱恩那里,“写意派”表演或者“呈现性”表演,其实是表现主义表演的代名词。表现主义表演或者“写意派”表演与现代主义艺术关系密切,将它放在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背景下来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它的基本内容。
二
事实上,麦克布莱恩用“呈现”(presentation)来阐明“表现”(expression),同时将它与“再现”(representation)对立起来,这已经非常清晰地揭示了20世纪初欧洲现代艺术运动的实质,即强调艺术本身“在场”的价值,而不是它们所“再现”的内容的价值。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论概括,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在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那里才获得清晰的表达。在格林伯格看来,现代主义艺术的核心是分门别类,让艺术回到各自的领地,就像康德当年给知、情、意或者科学、审美和道德活动所做的区隔和划分那样。1960年格林伯格做了一个题为“现代主义绘画”的讲演,后来被整理成文字发表。在《现代主义绘画》中,格林伯格首先指出,现代主义不只涉及绘画和文学,它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文化中有活力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现代主义。要保持艺术的活力,就要通过自我批判而确保每门艺术的权限,让它们变得更加纯粹和独立,不要相互越界。就绘画来说,就是要保持它的平面性,免得它进入雕塑和建筑领域。格林伯格指出:
写实的幻觉艺术掩盖了艺术媒介,艺术被用来掩盖艺术自身,而现代主义则把艺术用来唤起对艺术自身的注意。绘画媒介的某些限制——平面外观、形状和颜料特性——曾被传统的绘画大师们视为消极因素,只被间接地或不公开地加以承认,现代主义绘画却把这些限制当作肯定因素,公开承认它们。[注]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周宪译,《世界美术》,1992年第3期。
格林伯格强调让平面去做平面,让色彩去做色彩,让形状去做形状,而不是让色彩和形状去做在二维平面上制造三维幻觉的工具。这与余上沅强调让布景去做布景,让建筑去做建筑,让演员去做演员,打破横亘在舞台与观众之间的那堵墙,非常类似。它们都是让艺术媒介直接“呈现”或“在场”。如果余上沅用“写意”来翻译“呈现”或“在场”是成立的话,我们不仅可以将20世纪西方的表现主义戏剧称之为“写意戏剧”,也可以将表现主义绘画乃至所有的现代主义绘画称之为“写意绘画”。
对于现代主义绘画对“写实”的反叛和对“写意”的追求,早在20世纪初就有批评家揭示出来了,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弗莱(Roger Fry)和贝尔(Clive Bell)。
贝尔给艺术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即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跟它再现的内容无关。贝尔据此全面否定崇尚写实的文艺复兴大师的艺术价值,转而支持原始艺术和后印象派艺术。尽管“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概念有些含混,但是贝尔强调从关注艺术再现的内容到关注艺术本身的呈现,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来看看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解释:
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注]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
绘画中的线条和色彩本来是为造型服务的,现在成了绘画的目的。换句话说,线条和色彩本来是不显现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物、风景等内容或题材显现,是隐藏在内容或题材背后的媒介。根据“有意味的形式”的主张,这些隐藏在内容后面的形式或者媒介走到了前台,成为欣赏的主要对象。对此,弗莱在《线条之为现代美术中的表现手段》一文中,有更加清晰的说明。弗莱区分了两种线条:一种是“书法式线条”(calligraphic line),一种是“结构式线条”(structural line):
……我试图表明至少有两种审美愉快,可以从线条赋形中推导出来——从线条本身有韵律的序列中,即我称之为书法性的因素中得到的愉悦,以及造型形式,亦即我称之为结构性因素作用于人类心智而得到的愉悦。人们可以说,书法式线条之为线条,停留在纸面上,而结构性线条则进入了三维空间。书法式线条试对一种姿势的记录,事实上是对那种姿势如此纯粹、如此完整的记录。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一种愉悦来追踪它,就像我们追踪着一位舞者的运动一样。它倾向于比任何其他赋形的品质更多地表现观念的不稳定性与主观性的一面,而在结构性线条中,艺术家表现出自己几乎完全投身于形式的客观实现之中。[注]罗杰·弗莱:《线条之为现代艺术中的手段》,见《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稍有改动。
“书法式线条”是在画面上直接显现的线条,是我们直接看见的线条;“结构式线条”在画面上不直接显现,而是消解到对象的再现之中,我们直接看见的是对象的形状而不是线条。尽管弗莱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在这两种线条之间做出价值判断,只是将它们明确地区分开来,但是结合他的其他文字可以发现,“书法式线条”就是表现性的线条,是现代绘画和东方古代艺术中线条;“结构式线条”就是再现性的线条,在欧洲古典绘画中可以找到。弗莱说的“书法式线条”与“结构式线条”之间的区分,其实就是“表现”与“再现”之间的对立在绘画领域的表现。正如弗莱所说,“整个19世纪都在孵育这两种不同美学之间的斗争,但是只是到了这个新世纪才破壳而出。”[注]Fry, Roger, “Modern Paintings in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Art,”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37, No. 213 (Dec., 1920), p.304.
三
对于贝尔所说的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弗莱所说的“书法式线条”与“结构式线条”的区别,以及“表现”与“再现”的区别,余上沅相当熟悉,他把它们归结为“写实”与“写意”的区别。在1926年发表的《旧戏评价》一文中,余上沅以绘画为例来说明“纯粹艺术”:
譬如画家看见了一面墙,墙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他忽然起了创造冲动。他越看越真切,越想把他所看到的画在纸上。假使他是写实者,他可以一笔不苟地把这些东西全摹下来;假使他真是个艺术家,他一定看不见墙,看不见桌子椅子,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些线条和颜色彼此在发生一种极有趣味的关系——形象。他要画的又只是些形象的关系,不是可以靠的墙,可以用的桌子椅子。因为这幅画只是些形象的关系,它是不是代表桌子椅子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去正看倒看,左看右看,它都能给你一种乐趣。绘画要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叫它是纯粹的艺术。中国的各种艺术,至少是趋向于纯粹的方面,如果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方面。[注]余上沅:《旧戏评价》,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50-151页。
如果将这段文字中的“形象”改为“形式”,就与贝尔的表达差不多一样了。但是,与两年前的《表演的艺术》不同,余上沅在这里明确将中国艺术归入“写意”“表现”“纯粹艺术”之列。在《表演的艺术》中,余上沅主要谈的还是西方艺术,他在介绍以“再现”“写实”“内容”为主的古典艺术,与以“表现”“写意”“形式”为主的现代艺术之间的区分。到了两年后的《旧戏评价》中,西方艺术中的今古之争,变成了跨文化视野中的中西之别。中国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被归入“写意”之列,西方古典艺术被归入“写实”之列。余上沅在《旧戏评价》开篇即说:
在艺术史上有一件极可注意的事,就是一种艺术起了变化时,其他艺术也不约而同的起了相似的变化。要标识这一个时期的变化,遂勉强用某某派或某某主义一类的符号去概括它。所以写实派在西洋艺术里便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与之反抗的非写实派或写意派,也是一样。近代的艺术,无论是在西洋或是在东方,内部已经渐渐破裂,两派互相冲突。就西洋和东方全体而论,又仿佛一个重写实,一个重写意。这两派各有特长,各有流弊;如何使之沟通,如何使之完美,全靠将来的艺术家的创造,艺术批评家的督责。[注]余上沅:《旧戏评价》,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50页。
尽管有了现代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西方艺术重“写实”,东方艺术重“写意”,这是余上沅到了美国留学之后得出的看法,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余上沅与这些留学欧美的学者一样,发生了由推崇西方艺术到崇尚中国传统艺术的转变。[注]关于余上沅思想的转变的考察,参见刘思远:《国剧运动的戏剧史学研究——以余上沅1922-1926年的戏剧活动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宗白华1921年自德国写回来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他的思想的转变:“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所以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注]宗白华:《自德见寄书》,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留学欧美的学者的“转变”“反流”“顽固”,不是因为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正在发生的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换句话说,他们从西方的角度看到了中国艺术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体现为艺术的纯粹性。中国传统艺术都有追求“纯粹性”的趋向。关于中国旧戏的纯粹性,余上沅说:“假使旧戏的唱(音乐)是抽象,做(动作,舞)是象征的,布景等等又是非写实的,彼此调和,没有破绽,那么我们说它‘有做到纯粹艺术的趋向’,也并非过誉吧。”[注]余上沅:《中国戏剧的途径》,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202页。
追求艺术的纯粹性,是欧洲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重要内容。据邓以蛰回忆,当时留美学者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和他自己等人,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发表具有西方现代美学倾向的文章。邓以蛰说:“翻开那时的《晨报副刊》,就很清楚了。我们这些人都常有文章。据我看,形式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是主要倾向吧。”[注]邓以蛰:《〈艺术家的难关〉的回顾》,见《邓以蛰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正是通过现代形式主义美学视角,余上沅发现了中国旧戏与西方新戏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非“写实”的,或者说都是“写意”的。进一步说,中国艺术的“写意”可以为西方艺术走出“写实”的窠臼提供启示。
四
这些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的观察是否准确?西方现代艺术跟中国传统艺术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根据包华石(Martin Powers)等人的研究,欧洲现代艺术的确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包华石特别重视批评家弗莱和宾庸(Laurence Binyon)等人的作用。
作为欧洲现代艺术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弗莱敏锐地发现欧洲现代绘画与东方传统艺术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在一篇介绍克勒克安(Kelekian)的收藏的文章中,弗莱阐释了欧洲现代绘画与东方古代艺术之间的相似性。克勒克安本来是一位收藏东方古代美术的收藏家,后来开始收藏巴黎现代画家的作品,是欧洲现代绘画的早期推动者。表面上看,克勒克安的这两种收藏相距甚远,但是弗莱却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弗莱将当时的艺术界分为两大阵容:一种是追求“美”(beauty)的艺术,以古希腊罗马和盛期文艺复兴艺术为代表;一种是追求“表现”(expression)的艺术,以欧洲现代绘画和东方古代艺术为代表。正是由于有了由东方古代艺术训练出来的眼光,克勒克安才有对巴黎现代绘画的慧眼识珠。“因此,他对现代绘画的收藏,证明他的方法是极为正确的。长期在东方早期艺术之中的浸染,练就了他的鉴赏力,让他可以找到艺术作品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给了他选择现代作品的勇气,一种没有辜负他的勇气。”[注]Fry, Roger, “Modern Paintings in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Art,”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37, No. 213 (Dec., 1920), p. 304.
前面提到的弗莱在“书法式线条”与“结构式线条”之间的区分,则明显受到了中国书法的影响。在谈到马蒂斯的素描时,弗莱指出:
它显然展示了马蒂斯强大的感受力,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暂时将它称为书法式的。“书法式的”一词传达给我们的略有贬义之意。我们从来不像中国人或波斯人那样崇敬书法,我们立刻会想到那些老式的书写大师的浮华之名。但是,事实上,纯粹线条中存在着表现的可能性,其节奏也许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类型,以表现心境与情境的无限多样性。我们称任何这种线条为书法,只要它所企求的品质是以一种绝对的确信来获得的。不过,这省略了这样获得的究竟是何种品质这一真正要点,是雅致而敏感的,还是粗野而自以为是的。因此,在称这种素描是书法式时,我并不是指责它,因为事实是,马蒂斯线条的品质是如此超级敏感、如此细腻、如此不同于华丽的表演或炫耀,以至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真的欺骗了无知之人,使其以为这只是无能而已。[注]罗杰·弗莱:《线条之为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手段》,见《弗莱艺术批评文选》,第213页。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弗莱所说的雅致而敏感的线条,是中国书法线条,不是西方书法线条。西方书法线条是粗野而炫耀的,因而往往被当作贬义用。马蒂斯的线条是否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尚待考证,但是弗莱是在用中国书法美学来解读马蒂斯的线条,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宾庸既是一位批评家又是一位汉学家,对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都非常熟悉。宾庸认为,由于各种因素的蒙蔽,西方直到20世纪初才认识到中国绘画的价值。[注]Binyon, Laurence, “A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Fourth Centur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4, No. 10 (Jan., 1904), pp. 39-40.西方人之所以很晚才认识到中国绘画的价值,原因在于他们以前过于专注于写实,只有到了20世纪初的现代艺术才开始重视线条、笔触的绘画形式或语言自身的价值。换句话说,是西方现代艺术照亮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包华石指出,西方现代绘画对于“节奏”“笔触”“姿势”“表现”等等的推崇,受到了中国绘画和画论的影响。“唐宋理论家的‘形似’与‘写意’的对比是通过宾庸和弗莱直接影响到欧洲的现代主义理论而在现代形式主义理论的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注]包华石:《中国体为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
由此可见,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的确存在相似性,它们都是非写实的,都强调艺术本身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赵太侔自信地说:“现在的艺术世界,是反写实运动弥漫的时候。西方的艺术家正在那里拼命解脱自然的桎梏,四面八方求救兵。中国的绘画确供给了他们一枝生力军。在戏剧方面他们也在眼巴巴地向东方望着。失望得很。却不曾得到多大的助力。”[注]赵太侔:《国剧》,见余上沅编:《国剧运动》,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第10页。余上沅、赵太侔和闻一多等人发动“国剧运动”,也许是想仿效中国传统绘画给西方现代绘画的影响,让中国传统戏剧也对西方现代戏剧产生影响。
五
最后,我们来检视一下余上沅的“写意”戏剧的实质。
余上沅直接谈论“写意”戏剧的文字并不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表演艺术》和《旧戏评价》之外,他没有在其他文章中集中讨论“写意”。后来余上沅还采用凯尔茜(Vera Kelsey)的说法,用“象征”来取代“写意”作为“写实”的对立面。[注]余上沅:《中国戏剧的途径》,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201-206页。遗憾的是,他对“象征”也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在《再论表演艺术》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余上沅对于戏剧表演本质的认识。从余上沅1927年在编辑自己的《戏剧论集》时将此前发表的《表演的艺术》一文的题目改为《论表演艺术》可以看出,他自己也认为这两篇文章是有关系的。
在文章一开头,余上沅以孩子的游戏为例,对表演艺术的两个特点加以说明,第一个表演的态度,即无目的的态度;第二个是表演的天才,即“象”真而不是“真”的表演。余上沅说:
天下有一种人,他们艺术家的态度最充分,他们表演的天才最显著,这种人不是成人,却是我们所习见的小孩子。第一,小孩子成群的玩耍,甚至于一个人独耍的时候,除了玩耍而外,他们别无目的。你理会他们也好,不理会他们更好,也许理会他们反倒不好。这是他们艺术家的态度。第二,小孩子们能够就他们观察所得,运用变化,做出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来。这些故事虽然是近于摹仿,可其中必少不了一大部分的新创造。你留心看看小孩子们的娶亲,打仗,便可体会出多少神妙的意象。他们的家伙,器具,仪式,方法,态度,精神,都“象”真的,却一毫也不“是”真的。这里就是他们流露出来的表演天才。[注]余上沅:《再论表演艺术》,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86页。
余上沅所说的表演的天才,触及表演的本质,同时与他所说的“写意”有关。表演或者“写意”表演,并不是毫无规定性的任意行为,其中既包含摹仿,也包含创造。“写实”表演是纯粹摹仿,或者是干脆把原物搬上舞台,它追求的是“‘是’真”。“写意”表演是摹仿与创造的结合,它追求的是“‘象’真”。与“‘是’真”不同,“‘象’真”要让人感觉到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余上沅引用了蒿俄得(Bronson Howard)关于表演的定义:“根据剧中人依照剧本情形所指定的实际生活而发出的语言、动作和形状,在舞台上去作出‘似是而非’的语言、动作和形状,这个艺术,就是表演艺术。”[注]余上沅:《再论表演艺术》,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87页。为了做到这一点,演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这样做;另外做点别的东西罢。”[注]余上沅:《再论表演艺术》,见《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88页。借用瓦尔顿(Kendall Walton)的术语来说,演员的表演就是“假装”(make-believe),“假装”不是全真,也不是全假,而是真假参半,真假之间。[注]有关讨论,参见彭锋:《从身心关系看“虚构的悖论”》,见彭锋:《重回在场: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98-109页。黄佐临在总结他的“写意戏剧观”时,也有同样的表述:“虚戈作戏,真假宜人,不像不成戏,太像不是艺,悟得情与理,是戏又是艺;画有三:绝像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此亦欺世盗名之画,惟绝似又绝不似者,此乃真画。”[注]黄佐临:《我与写意戏剧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编辑出版前言第2-3页。就像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绘画那样,写意戏剧追求的是真假参半。
写意戏剧的实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这里只是将写意戏剧与写意绘画对照起来,做了点初步的探索。对于写意戏剧与其他几种主要的戏剧类型之间的关系,有待另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