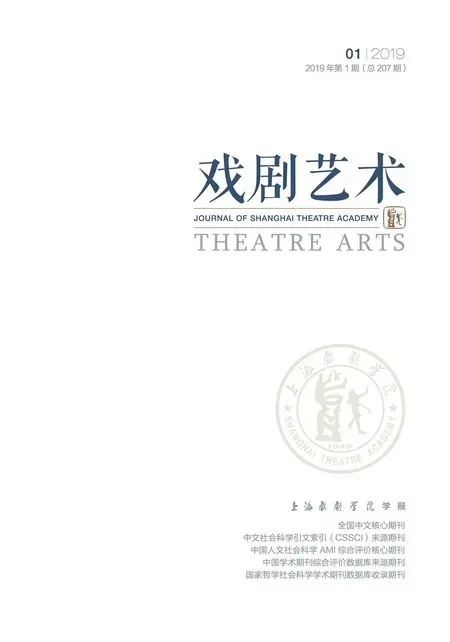1932-1933程砚秋赴欧考察“精神私史”考略
1932年,以虚岁算程砚秋已至而立之年[注]程砚秋生于1904年1月1日。,不仅坐稳“四大名旦”第二把交椅,还在1930年6月15-16日《新北京报》举办的平津男女名伶大选举中,当选为男旦主席。[注]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54页。1931年7月12日他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地址在北平)副院长,与梅兰芳的中华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副院长分庭抗礼,至此,个人声名已臻其极。而令戏迷想不到的是,在1932年1月13日[注]程砚秋离平赴欧的时间有的文献说是1932年1月14日,但据当时报刊登载(如1932年1月13日《北京晨报》“定于今日下午四时二十分,由东站出发”,1932年1月14日《京报》“于昨日(十三日)午后四点二十五分启程”,因此准确时间应为1932年1月13日。这一天,他不带任何演戏行头,离开北平,开启为期一年多的欧洲考察之旅。在对社会的公开声明中,他说:“梅先生去年到美国去,是把东方戏剧介绍给西方,这是个很伟大的工作,这是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相沟通的先声。砚秋技术太不成熟,不敢以个人艺术代表东方戏剧艺术,所以不敢到西方去演剧,只能到西方去游学。不过,砚秋也想把西方戏剧的原理与趋势认识一些,以作中国戏剧的参考,这也许是沟通东西两方戏剧的一部分比较消极的工作吧。”[注]程砚秋:《在北平缀玉轩梅兰芳为程砚秋赴欧游学举行的欢送会上的致谢词》,《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5-16页。这些话阐明了赴欧动机,欧游回来发表的《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可视为这一动机落实之凭证。但每个行为的发生都是由诸多心理情势交汇而成,有的现诸于外,有的隐藏于内,如果能够将促成程砚秋赴欧考察行为发生的各种心理情势、赴欧考察期间心理线索的交织与冲突、欧游之后话语变化的深层原因,通过具体史料的勾沉、爬梳,勾勒出一张疏密相衬、隐显互现的心理图谱,藉此,既可看清一个著名的京剧男旦演员与那一时代总体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情态,亦能以斑窥豹地呈现京剧在特定历史时间段内的发展理路。
一、“我”是谁
1932年4月11日,程砚秋身在法国巴黎,自当年1月13日离开北平,时间已过去近三个月。这一天的日记上留下一首诗:“神龙降落世海中,欲始湖海互相通。数年未达先天志,卸风摆脱复腾空(摆脱淤泥复腾空)。身入世海担艰苦,最喜风波处处同。”[注]程砚秋:《程砚秋先生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日记》,《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1932年6月7日,在德国柏林,他的日记又留下一首诗:“虎降龙伏生双翼,超过鹏程万里行。已生人中龙,为来河海欲枯。已生人中龙,与虎走,河山陷,海欲枯。”[注]同上,第181页。两首时间相距不远的诗中均出现“龙”,意指为何?翻阅程砚秋日记,并没有留下更多的人事线索可供解析。但笔者认为,考证“龙”之寓义,对理解程砚秋“赴欧考察”行为的发生至关重要。
在梨园行成名的角儿中,程砚秋是非常少见的非梨园世家出身。关于他的祖先,曾有几种不同的版本[注]程砚秋的先祖是谁说法不一。有的说其五世祖名英和,字煦斋,号树琴,为乾隆朝仕官,也有传说曾任道光初年相国;有的说其曾祖父是阿昌阿,是皇族身份;有的说其曾祖父是穆彰阿,嘉庆进士 ,任内务府大臣、直上书房、翰林院掌管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虽无定论,但程砚秋是贵族血统却是共识。参见李伶伶《程砚秋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5-6页。,这些说法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贵族血统。将这一身份巩固与发挥的是以罗瘿公[注]罗惇融(1872-1924),广东顺德人,字掞东,号瘿公。为中心的文人集团。
罗瘿公在程砚秋13周岁(1917年)倒嗓之时,将他从荣蝶仙手中赎出,从此担任他的教师、编剧、演剧策划人等多重角色。1918年,程砚秋14周岁时,罗瘿公请徐悲鸿绘制了一张砚秋扮王宝钏的画像,装画木匣上镌有其题铭,“程艳秋[注]程砚秋原来的艺名为“程艳秋”,1932年1月1日正式改名为“程砚秋”。正黄旗人,世宦,父棣内务府籍颇沃饶。国变后冠汉姓。父殁渐困,因券伶人为弟子……”[注]杨先让:《1918年徐悲鸿为梅兰芳、程砚秋画像的缘由》,《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63页。1926年,在瘿公殁后接替辅佐程砚秋的金仲荪[注]金兆棪(1879-1945),浙江金华人,字仲荪。主编了收录有介绍程砚秋家世、生平、为人,及社会人士评价程砚秋剧艺的专辑——《霜杰集》。其中有多篇关于程砚秋的传记都不约而同强调其贵族出身[注]如茀怡《程艳秋小传》,丁丁《程艳秋小史》,芚盦《义伶程艳秋小传》,髯侯《程艳秋小传》等,见金仲荪编:《霜杰集》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显然,作为罗瘿公的好友,金仲荪接受瘿公重托编辑《霜杰集》,是深谙其用心的。瘿公的另一好友袁伯夔[注]袁伯夔(1879-1939),湖南湘潭人,名思亮,字伯揆,亦作伯夔。同样极为爱护程砚秋,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程生玉霜本世家子,幼失怙,以贫鬻于歌者。”[注]袁伯夔:《霜杰集·序》,《霜杰集》(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5页。在当时伶人普遍遭受轻视的世风之下,不管罗瘿公、金仲荪还是袁伯夔,都反复强调程砚秋的贵族血统,除了欲借此抬高其社会身份,还对他有另一种期勉。
袁伯夔在《霜杰集》序言中说得很明白:“盖吾所期于玉霜者,将欲穷声音之道使渐复于古。”[注]同上,第6页。“渐复于古”所指为何?序言开宗明义:“古之伶工,隶于乐官,非贱役也,执龠秉翟,贤人隐焉。”[注]同上,第5页。接下来略论伶人社会功能与地位演变历史,从“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命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诗颂延年”,到“唐宋梨园子弟所歌者,大抵当时文士所著诗词为多”,到“元明南北曲盛,格调少不逮古犹为尔雅”,再到“末调纷起,则里巷鄙琐猥亵之词,缙绅先生所不道”,“流品日下”的原因是,“士大夫玩而弄之,其人亦不复自爱重,因循所习,无复能究,心律吕以合八音之调者,其势然也。”[注]袁伯夔:《霜杰集·序》,《霜杰集》(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5页。
以袁伯夔梳理的伶人剧品流变史相参照,程早期所演剧目如《骂殿》《青霜剑》(罗瘿公编剧)《金锁记》(罗瘿公改编)等剧“贞节义烈”“芬芳悱恻”[注]同上,第6页。,已接近元明南北曲的“格调尔雅”;而1925年首演的《文姬归汉》(金仲荪编剧)以“胡笳十八拍”入曲,则接近唐宋梨园子弟的“所歌者,大抵当时文士所著诗词为多。”但在袁伯夔看来,仍有遗憾,“惜乎不生当盛汉之隆,从司马相如诸人雍容弦歌于庙堂坛壝之上也。”[注]同上,第6页。《乐记》有言,“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注]《乐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8页。“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注]同上,第1527页。也就是说,“乐”与“礼”“政”“刑”一样,均可“治国”。这应该就是袁伯夔期望程砚秋“欲穷声音之道,使渐复于古”的本意了。《霜杰集》出版于1926年,1931 年程砚秋演出了金仲荪创作的抨击战争罪恶的《荒山泪》,使京剧的政治批判功能得到空前的展现,这虽非袁伯夔期待的“弦歌于庙堂坛壝之上”,却从另一个向度将伶人/京剧的社会功能推向极致。
罗瘿公在兼具新旧特点的广雅书院与万木草堂接受过教育,与梁启超等同列康(有为)门高第,清末官至邮传部郎中,民国成立后,先后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参议、顾问、礼制馆编纂”[注]朱文相:《罗瘿公生平及剧作资料辑录》,《戏曲艺术》,1982年第1期。等职,后愤于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弃政攻文、寄情氍毹。金仲荪出生于浙江金华望族,幼承家学,清末曾协佐闽蒋少珊氏充幕邑逾九载,后就读过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参加过辛亥革命,历任浙江临时参议会议员、国会参议员、福建省福清县知事、广东军政府秘书厅长等职[注]程永江:《记金仲荪爷爷》,《我的父亲程砚秋》,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83-85页。。然“护持民元约法与北洋诸军阀斗争历十数年”“最后始发现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失望之余,决不问政坛诸事。自43岁以后即摒除一切,改字‘悔庐’。”[注]同上,第86-87页。他们都不是埋头于书斋的文人,都参加过社会政治运动并从事过政务,只不过都是“从政潮中警醒而退出来的人”[注]程砚秋:《检阅我自己》,《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6页。。袁伯夔同样在清末与民初都曾短暂步入仕途,然而“谋多不见用”“筹安会起,弃官归侨居泸上,从此绝迹仕途”[注]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页。。以罗瘿公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极力强调程砚秋的贵族身份,赋之以“欲穷声音之道使渐复于古”的重任,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些文人们在世变道崩之时将自己无法实现的“治平”抱负寄托到了程砚秋那里,而这对程砚秋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儒家事功角度,作为京剧演员的程砚秋所取得的堪可一书的成就当属在张学良东三省易帜中发挥的作用。据程砚秋三子程永江记述,“据说1928年国民政府派李石曾、吴铁城赴奉天与张学良谈判东三省易帜以实现国家统一的事件中,李石曾利用先父赴东省演唱《南北合》与《文姬归汉》以侧应其工作。”[注]程永江:《先父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之缘起》,《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1页。查《程砚秋史事长编》,程于1930年春天赴东北演剧[注]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而1928年则未有此事,所以时间应当为1930年而非1928年。“侧应”之事程永江用了“据说”来表述,并不一定能确定为实事,但如果联系这之后的1930年11月13日,程砚秋应李石曾主持的“中华戏曲音乐学会”的邀请,前往首都南京,参加李石曾发起、学会主办的“庆祝东三省易帜赈济伤兵和辽宁水灾游艺大会”,并于次日应《南京晚报》记者之请为报纸题词——“大地皆春·四海升平”[注]李伶伶:《程砚秋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329-330页。亦可参见《程砚秋史事长编(上)》第269-270页。,这件事的可信度应当是颇高的。即使在促使张学良支持蒋介石,最后实现国内统一的东三省易帜这件事上,程砚秋的演出不一定起到直接作用,但此事的结果却鼓励了他。甚至可以说,1931年两部反战题材剧作《荒山泪》与《春闺梦》[注]这两部剧作的创作缘起均与程砚秋的提议有关。的问世与此事的成功亦有一定的关联。
看到京剧能够产生影响国家政局,促进和平运动的效力,显然让具有士子胸怀的程砚秋振奋异常。“砚秋本此志愿,想到西方去,和西方许多戏剧家作一商榷;如果大家认为这是可能,并且必要,砚秋就想与他们联合起来,大家来做这世界和平运动”[注]程砚秋:《〈世界社〉于中南海福禄居公饯郎之万、程砚秋赴欧宴上的答谢词》,《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20页。。除此之外,与京剧相关的更为切实的赴欧动机则在于“要使社会认识我们这戏剧,不是‘小道’,是‘大道’,不是‘玩意儿’,是‘正经事’。这是梨园行应该奋斗的,应该自重的”。“但是砚秋的学识太浅陋了,能力太薄弱了,怎能负起这样重大使命呢?因此便生了游学西方的动机。”[注]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出行前致梨园公益会同人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3页。赴欧考察这一行为是本着借他山之石以改良京剧,使之从“小道”跃升为“大道”的动机而生成的,藉此可以理解1932年4月11日诗中“欲始湖海互相通”“身入世海担艰苦”之意。
从这些行为事迹来看,程砚秋的自我身份认同绝非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伶人,甚至也不仅是袁伯夔等所期望的“欲穷声音之道,使渐复于古”的儒家士子,而是汲取了时代新风,自觉向着陈独秀所言的“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三爱(陈独秀):《论戏曲》,《新小说》,第二卷第二期(1905年)。进取,由此可见程砚秋对伶人与现代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自觉追求。那么,“龙”之寓义为何?显然是——“社会精英”意识的自明。据张次溪《程艳秋传》记载,程砚秋十四岁(虚岁)时,“余叔岩方创春友票社,邀玉霜串演。甫终一曲,四座皆惊叹曰:‘是儿非池中物,行见如云龙飞矣。’”[注]张次溪:《程艳秋传》,《戏剧月刊》,第三卷第三期(1930年)。。如果说,当年“龙”是观众的美誉,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程砚秋诗中两次出现“龙”,早已将此美誉内化为人格与理想的自觉追求。
以戏(京)剧来促进世界和平运动以及借他山之石以改良戏(京)剧是程砚秋赴欧考察最重要的心理动因,除了受其精英意识驱动,还交织着另外一些心理情势。“五四”以来,新文化阵营对传统戏曲的攻击不可谓不猛烈,虽然“五四”时期批判戏曲甚力的胡适后来对梅兰芳的访美之行还起到引介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新文化阵营的批判之音就此绝迹。
1929年,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发表了一期“梅兰芳专号”,数篇文章对梅兰芳所代表的男旦文化(包括京剧文化)进行了火力集中的抨击。署名西源[注]西源系郑振铎笔名之一。的《打倒男扮女装的旦角·打倒旦角的代表人梅兰芳》一文语气尤为激烈。他在列举了京剧的种种落后、不合理之处后,特别强调,“最使我们引起恶感的却是所谓男扮的旦角——一种残酷的非人的矫揉做作的最卑下的把戏”,“他那逼紧了喉咙,以尖锐的做作的娇声出之的伪造的女性的歌喉”,“他那矫揉造作的体态与特种的轻佻的‘台步’‘工架’,那种非人的,不合理的,似模仿又似创造的女性的举动”,“打倒这种非人的不合理的男扮的旦角,与这种非人的不合理的艺术!”[注]西源:《打倒男扮女装的旦角·打倒旦角的代表人梅兰芳》,《文学周报》,第八卷第三号(1929年)。文章针对的是梅兰芳,但梅兰芳代表的是京剧的男旦艺术,程砚秋当然也包含在其中。程看过这篇文章吗?以他经常出入梅宅及京剧界“通天教主”——王瑶卿府上的行迹,再加上身边来往不乏报界中人,程砚秋即使没看过这篇文章,也完全有可能听说过其中观点。在1932年1月1日的荀令香拜师礼上,他教给弟子的第一出戏是《骂殿》,并解释道,“为什么要叫他先学骂人呢,因为我们唱戏的人无权无勇,遇见什么不平的事,或是受委屈,都不敢说话,只好借着唱戏发发牢骚,大概这骂字是不能免的。所以不妨先教他骂殿。”[注]张体道:《荀令香拜师记》,《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参加过拜师礼的徐凌霄认为:骂的人为“报”字号人物[注]参见徐凌霄:《附录:“骂殿”与“无冕皇帝”》,《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1页。。那么,“报”字号人物除了那些造谣生事的小报记者外,是否也包括如《文学周报》上这些出语凌厉的批判者们呢?显然是可能的。
要说新文化阵营对梅兰芳的攻击远远大过于程砚秋,但从没见过梅兰芳在公开场合回应过,而程砚秋的“刚烈”个性却使他对这些攻击不可能置之不理。但他对这些攻击的回应绝不只以《骂殿》来反击,贵族血统、儒家士子的使命感,以及他自觉交往的具有新文化意识的学术圈子都决定了他会尽可能从批判之辞中寻找能够改进自身的合理成份。“赴欧”显然就是在新文化“向西求索”的主流思路引导下生成的选择。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现代,网购成为大多数人的购物方式,这对大型商场的产品销量会产生很大影响。为吸引更多的顾客,对商场内部环境的设计进行创新和改进势在必行。本文首先对室内设计和竞争力的关系进行探析,接着介绍其相关的设计要点,最后总结目前室内环境设计的特点。从中可看出目前我国大型商场的内部设计正在不断改进当中。
与《文学周报》批判男旦相伴而生的是同一时间段内坤旦的崛起。“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是京剧界女性伶人迅速崛起的时代。”[注]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1页。1930年6月15-16日,《新北京报》办平津男女名伶大选举,先选得旦角主席男女各一人,男为程砚秋,得6889票,女为新艳秋,得13875票。[注]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54页。虽然程砚秋被选上旦角男主席,但与旦角女主席新艳秋相比,票数悬殊,其中原因自然很多,但亦可见出,大众对坤伶的兴趣与热情正与日俱增。京剧演员新艳秋原名王玉华,原是梆子演员,因对程派艺术非常痴迷,通过到剧场偷学程砚秋的戏而成名,成名后公然将艺名改为“新艳秋”,不无与程砚秋相抗衡之意。为此,程砚秋在情感上自然对她有所排斥。而此时,随着新艳秋风头日盛,曾经捧程的某些戏迷也极力揄扬新艳秋之演技,“自新艳秋出,程艳秋遂有老艳秋之称,足见玉华在剧界,实占有伟大势力,然非其色艺之果妙,乌克成名之速如此。……余为玉华征诗词,陈散原、樊樊山、陈筱石、程子大、许静仁、夏剑丞、谭瓶斋、袁伯夔、……俱惠佳作。”[注]《新秋消息》,《申报》,1928-08-13。这一摞名单中,陈散原、樊樊山、袁伯夔等原本都是著名的程迷。当然,老先生们对新艳秋的赞美亦有垂青程派艺术的原因,但在程砚秋自己,难免会有此一时彼一时之感。他不像出身于梨园世家的梅兰芳,对梨园行的此起彼伏见惯不怪,刚正、孤傲、自尊的性格,使他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然而,这又不仅只是程迷们喜新厌旧的问题,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审美取向的悄悄转变。而程砚秋本人对坤伶的崛起有何看法?苏少卿于1941年曾回忆:“程砚秋氏数年前曾向余云:此后趋势,戏中女角,必让之坤伶,可谓先觉之言。”[注]苏少卿:《后四大名旦论》,《苏少卿戏曲春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不能确定这话是哪一年说的,但在程砚秋赴欧之前,应当已经觉察到新艳秋所代表的坤伶对京剧市场的占领,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在旦角这个行当,女演女对男演女的反超,反映着整个时代对“写实”“及物”“变革”的文化心理需求。如此看来,程砚秋的赴欧考察应当还有对男旦文化的危机意识。他在旅欧期间对话剧导演艺术格外留意,回国后写出《话剧导演管窥》,想改行当话剧导演等,都可视为危机意识的一种显现。
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三十岁(虚岁)生日,他于《北平晨报》登启事,改名“艳秋”为“砚秋”,改字“玉霜”为“御霜”。同一日,他举行收徒仪式,收了程门第一个弟子——荀令香。按说,不论是“艳秋”还是“玉霜”,与程作为一名男旦演员的身份都是相称的,他没必要改自己的名字。四大名旦中,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艺名白牡丹),在其艺名确立之后,虽然都不无女性色彩,但终其一生,并未改变。而程砚秋为何要改?在这一天到场的嘉宾言论中,可以看到赴欧考察之事在此前已经落实。因此,将改名与赴欧考察联系起来,并非牵强。值得注意的是,程砚秋提到:“原来的名字早就要改,因为朋友阻拦,未能实现。”[注]张体道:《荀令香拜师记》,《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这一次,在三十岁而立之年,伴随着为人之师的身份确立,他不仅改了名,也改了字。“艳秋”与男旦身份是相称的,而“砚秋”更像学者的名字;“玉霜”与个人品貌是相称的,而“御霜”更强调了对命运与困境的驾驭与超越。赴欧对于程砚秋来说同样是一次身份的改换,从一个梨园界扮演旦角的名演员变成一个到西方游学以改进传统戏曲艺术的学者,改名对于程砚秋来说,是身份转变之前不可缺少的“换装”行为,而这一切,都选择在“而立”之年来进行。程砚秋通过明确“我”是谁,实现了他的“而立”。
赴欧考察给予程砚秋改换身份的短暂时空,他由一个梨园行里整日为生计而奔忙的演员转成为改革京剧而向西求学的留学生,通过“换装”享受着一段自觉自愿的角色扮演。但即使在异国他乡,即使是孑然一身,程砚秋的日常行为、个人形象、去留选择等都得受到他的京剧演员、大家庭里的顶梁柱、戏班里的领头人,及弱国子民等多重身份的制约。
在《报告书》及1933年4月8日至11日《华北日报》记者访谈中,程砚秋均简要提到,欲在德国定居两年,入柏林音乐大学当留学生,“利用西方技术把中国戏曲来一个大改革”[注]程永江:《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的五个问题——关于〈读《程砚秋先生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日记》后记〉》,《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但据友人回忆,欲留德国实际上还有另一原因,“乌发亦有意请程先生去演出。当时,乌发演员工资极高,还可以在世界上出名,程在到底进入乌发还是入音乐大学问题上发生了思想波动。”[注]同上,第223页。两种意愿曾有过斗争,“以后,这一意愿(指入大学,引者注)占了优势,程先生执意不回国,却一心要考大学。”[注]胡天石口述、程永江整理:《读〈程砚秋先生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日记〉后记》,《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以程砚秋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对电影表演的领会(出国前就经常看电影,在欧洲期间更是乐此不疲),京剧表演的扎实基础以及自身形象的优势(长相俊秀,且身高不输于洋人),他在乌发电影公司的发展前景可想而知。且“进乌发可以一举成名成为百万富翁”[注]程永江:《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的五个问题——关于〈读《程砚秋先生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日记》后记〉》,《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这对于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重负(不仅要负担自家老小,还要时常接济三位兄长,并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但程砚秋最后还是以入柏林音乐大学学习作为居留德国的动向选择,其中原因何在?
程砚秋赴欧的主要动因是通过考察西方戏剧以促进京剧的改良,如果中途改行去电影公司当演员,某种意义上已经背叛了出国前向梨园行作出的承诺,这应该是程砚秋在两个意愿之间作选择的重要心理筹码。当然,演电影的效应绝非只是满足个人兴趣或成名立业,在德国与他过从甚密的胡天石就认为:“过去在德国演的电影,有关我国的尽是极坏的影片,……御霜是早已声名远扬的京剧演员,是一位大艺术家,如能进入乌发肯定有利于扭转西方人士对我国人的错误看法。”[注]胡天石:《在欧洲考察的日子里》,《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胡天石的分析确有道理,也打动了程砚秋,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入大学学习音乐,除了遵守出国前的承诺之外,应当还与他此时觉察到的德国留学生中仍然存在对“京剧演员”的轻视有关。初到德国时,中国驻德公使刘文岛曾对他流露出不信任与不尊重的态度[注]同上,第121页。,即使在欧洲这样演员地位很高的国家,留学生群体中仍然存在着轻视伶人的态度,“程是有雄心壮志的人,这点留德学生均不了解,他们认为程是李石曾的人,是戏子。”[注]程永江:《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的五个问题——关于〈读《程砚秋先生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日记》后记〉》,《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这显然挫伤了程砚秋的自尊,入乌发当电影演员从某种意义上仍是留学生眼中的“戏子”,而进柏林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则不同。回国后程砚秋向媒体提起过欲入柏林音乐大学学习,却不曾提过入乌发电影公司作电影演员,想来就是这一心理所致。
程砚秋对无法入柏林音乐大学学习始终是耿耿于怀的,“他终日唉声叹气,并赋诗表白当时内心的郁闷情绪:来时白草今渐绿,消消绿叶复变黄,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注]胡天石:《在欧洲考察的日子里》,《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促使程砚秋回国的原因除了陈叔通发来的剧团同人生计告急的电报之外,还有此时的“国难”[注]指的是1933年日军侵占山海关,平津告急。。“这时我的考察工作并未完成,本不能匆匆回国;无如中日纠纷扩大,山海关发生变故,平津动摇,我不得已而要赶着回国省亲,因了这意外的挫折,使我连必须要去的英吉利也没有去。”[注]程砚秋:《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62页。面向媒体的程砚秋愿意展现自己的国家意识与家庭观念,但在家人面前,他却赌了一肚子气,赴欧回来一进家门,就说:“难道我程砚秋就是为了养活那百十口子人的剧团唱戏的吗?我……”[注]果素瑛:《追忆砚秋生平》,《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5-26页。对程砚秋来说,个人志趣不敌为京剧发展谋出路,所以他选择了入柏林音乐大学,不入乌发;而为京剧长远发展谋出路同样不敌他作为大家庭、戏班子经济支柱的眼前重担,当同业、亲人因经济而告急时,他就得放弃自己的选择马上回国。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国难”,程砚秋在留德与回国之间可能会抗衡得更久一些。留学生、京剧演员、大家庭里的顶梁柱、戏班里的领头人、弱国子民,多重身份相互掣肘与妥协的结果生成其行为、话语的最终样式。
二、西洋“镜”
赴欧之前程砚秋强调东西方戏剧的沟通,中国戏剧向西方的借鉴,“替中国戏剧找一点西方的参考品回来。”[注]程砚秋:《在北平缀玉轩梅兰芳为程砚秋赴欧游学举行的欢送会上的致谢词》,《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6页。“使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的沟通”[注]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出行前致梨园公益会同人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3页。“中国也有借重西洋艺术之必要”[注]程砚秋:《在北平市长周大文饯行宴上的答谢词》,《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7页。“把西方戏剧的长处取来贡献给中国戏剧”[注]程砚秋:《〈世界社〉于中南海福禄居公饯郎之万、程砚秋赴欧宴上的答谢词》,《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21页。。欧游之后,并没有否定这一切,但对传统戏曲艺术自有价值的强调显见突出了,他特别指出:“中国也有中国的长处,艺术是大公无私的,我们也要贡献给外国。”“勉强去学别人徒然是束缚自己,消灭自己而已。”“中国人自己有些不满意于中国剧,就把中国剧看得没有一丝半毫的好处,以为非把西方戏剧搬来代替不可;假如知道西方戏剧家正在研究和采用中国戏剧中的许多东西的话,也该明白了。”[注]程砚秋:《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70-71页。赴欧回来程砚秋的戏剧观似乎从“激进”反向了“保守”。
他特别向媒体介绍西方人对京剧的评价,“下火车后,就有俄国的戏剧家,……他很对中国的旧剧表同情,他说中国舞台不讲究布景,这是很对的,……假如布景少些,演员在舞台上自然得尽力把剧情表演出来,演员的成功,也就很快的。又说中国戏剧注重到‘写意’的这一层也是很好的。”[注]程砚秋:《周游欧陆返平之程砚秋对各国戏剧之印象谈——1933年4月8日至11日〈华北日报〉记者访谈》,《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50页。“《小巴黎报》的主笔很惊奇地对我说:‘中国戏剧已经进步到了写意的演剧术,已有很高的价值了,你还来欧洲考察什么?’我起初疑他是一种外交词令,后来听见欧洲许多戏剧家都这样说,我才相信这是真话。”[注]程砚秋:《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72页。而他自己也在观察:“不过我总觉得他们奏演,似乎太机械了,一举一动,都不得自由;说起来似不如我国演员可以表现本人的天才。”[注]程砚秋:《自巴黎致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同人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23页。“中国之戏剧,往往使人废寝忘餐,成为一种之戏迷阶级。欧洲戏剧,其价值如何,吾人不便妄下雌黄。然不能使人废寝忘餐,不能使人成为戏迷,则可断言。”[注]程砚秋:《〈世界日报〉记者柱宇访问程砚秋纪实》,《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针对以西方戏剧为参照的新文化阵营对传统戏曲的批判,程砚秋在《报告书》及访谈中说出这些话,自然不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在《报告书》里,他还分别就“五四”时期广受批判的如无布景、程式化动作、脸谱等传统戏剧特性,转引西方人的意见,同时因“独白也是中国戏中一件被攻击过的东西”,他举实例说明“欧洲戏剧也并不是绝对排斥独白”[注]程砚秋:《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72页。,从而论证“独白”存在于戏剧的合理性。对中国传统戏剧自有价值的强调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对新文化阵营攻击传统戏曲的一种反驳,而往小的方面来看,这些话语都与左翼戏剧家马彦祥在程砚秋刚刚动身赴欧不久发表的《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注]马彦祥《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一文原出处不详,该文引文均出自程永江编《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11-313页。一文有着针锋相对的回应。
在马文之前,批评京剧远为激烈的文章有的是,但对程砚秋指名道姓进行批评的要算这篇最严厉。程永江《程砚秋戏剧艺术三十讲》中的第十一讲也特别提到这一篇,表示程砚秋“对此不予争论”,“不但以自己和志同道合者们的辛勤劳作来证明对京剧进行民族虚无主义的指责是荒谬的,而且积极吸收片面攻击中的合理成分,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京剧事业必须注重剧本建设。”[注]程永江:《程砚秋戏剧艺术三十讲》,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73页。可见程砚秋是看过这篇文章的,虽不能确定是在欧游期间接到国内亲友信中所阅还是回国之后所阅。马文认为,“程以这样匆促的时间考察(六国),究竟会有多少成绩带回来,实在不敢预约。”[注]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而程回来之后不仅写出洋洋数万言的《报告书》,而且还写出《话剧导演管窥》这样在中国导演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奠基之作”[注]焦尚志:《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有力反击了马彦祥的“不敢预约”。马文在引用了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出行前致梨园公益会同人书》中对中国戏剧“脸谱”的看法之后,认为:“事实上,在戏园子里,观众有了限制,脸谱之原始功能早已失去,其无需存在,正如人类之不必再拖尾巴一样。”[注]马彦祥:《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11-312页。而程砚秋在《报告书》中,特别指出,“我并不说脸谱必须要用,我也不说脸谱必不可废,我更不因欧洲戏剧中有一个红脸便拿来做主张脸谱的论据;我只觉得反对脸谱者并不具有绝对的理由,因反对脸谱而连带排斥中国戏剧者更不具有绝对的理由。”[注]程砚秋:《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72页。马文认为,“关于中国旧剧的表现方法,非驴非马地与欧洲的象征主义相提并论,实不只是程砚秋君一人”[注]马彦祥:《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12页。。而程赴欧回来的《报告书》中在谈到中国戏剧的特性时已经不用“象征”一词,均以“写意”代之。唯有一处——“脸谱是一种图案画,在戏剧上的象征作用有时和灯光产生同一的效果”[注]程砚秋:《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72页。,这里的“象征”是作动词用,并非对传统戏剧本质的界定。这既可看成对马文中“非驴非马”一说的避嫌,也可看成,赴欧回来的程砚秋对中国传统戏剧特性的认知有了更多的自信,更愿意在本民族文化美学话语系统内来讨论京剧美学。
欧游回来之后,程砚秋在1933年11月对《申报》记者的访问中认为“伶界现在是一个很严重的时代,改革是不容再缓了。怕人家批评纠正,譬如讳疾忌医”。但接下来,他又明确表示:“现在的京剧,好像一幢旧房子,虽然急需改造,但是在新屋未完工以前,是不能不加以保护的。因为在这旧屋下面,有许多我们伶界同业靠它来掩护,而且很有价值的旧房子修葺起来,或者比偷工减料的新房子也许还来得可靠些。”[注]程砚秋:《对于改良旧剧的感想·新屋未成旧屋须爱护——1933年11月4日〈申报〉记者在上海沧州饭店访问程砚秋记》,《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在之后不久的另一篇文章里,他极力强调京剧技艺的独特价值,“许多人恭维旧剧,说它是‘纯艺术’,……旧剧的唱、做、表情,确已成了专门的技术,而值得人们单独地去欣赏了。它的坏处且不必说,单就技术而言,许多旧剧的老前辈,他们之所以享名,有几个不是在这个上面用了毕生之力,换了来的。仅仅因为谭先生的表演技术好,那怕《盗宗卷》再没有趣味,观众们依然会塞满了剧场。由此可以推知,观众们是没有一些主见的;除了花钱是为的欣赏杰作,才是他们唯一的主见。”[注]程砚秋:《谈非程式的艺术——话剧观剧述感》,《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艺术就是技术:也许我武断了。”[注]同上,第141页。细究马彦祥文章中的如下论断之后,便知道欧游之后的这些话从何而来。
在历数了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落后之处后,马文认为:“以上不过略举几条,说明旧剧的表演实在还有研究和改良的必要。旧戏在现在已经是走到了‘以伶为本’的末途,而且只是个人的,不是集团的,假如不早设法予以挽救,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马文还认为:“在表演方面,旧剧自有其特殊的技术,……演戏不仅要演什么人,像什么人,只是技术;更要演什么人,是什么人,像什么人,便是艺术。”[注]马彦祥:《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言下之意是旧剧只有技术,没有艺术。程砚秋的“艺术就是技术:也许我武断了”显然与之进行了正面交锋。
马彦祥的文章既包含着“五四”以来新文化界对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的批判,又夹杂着1930年代左翼文艺界新的论调,提倡“集团”胜于“个人”;重视“意义”过于“技巧”;只要“新手段”不要“旧技法”。这些观点基本也可代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普遍立场,程砚秋在欧游之前发表的系列文章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程艳秋致老摩登函——谈“皮黄与摩登”》认为,“艺术是社会的、公众的,绝不是个人私有的,我很希望由我们现在的工作把环境逐渐改变过来,使皮黄上的个人主义色彩逐渐减轻以至消失。”[注]程砚秋:《程砚秋致老摩登函——谈“皮黄与摩登”》,《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2页。在《检阅我自己》中,他检讨了梨园界“私有剧本”的自私,“这也许是私产制度下的社会现象之一吧?我也自然被转入这个漩涧。”[注]程砚秋:《检阅我自己》,《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3页。他对自己早期所演的剧目如《花舫缘》《红拂传》《玉镜台》《风流棒》《赚文娟》《玉狮坠》等一一进行了“原罪”,并对罗瘿公的另一些作品如《鸳鸯冢》《青霜剑》《金锁记》等进行了高度评价,后者显然与“五四”以来的反包办婚姻、以弱抗强、人定胜天等主流思潮是一致的。《检阅我自己》甚至在文章体式与价值立场上都与田汉发表于1930年的《我们的自己批判》相近。在《我之戏剧观》中他说,“我们演剧的呢?我们为什么要演剧给人家开心取乐呢?为什么要演些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注]程砚秋:《我之戏剧观——1931年12月25日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演讲》,《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8页。“所谓观众的感情,并不是从叫好或叫倒好的上头去分辨其良好与否;而是要从影响于观众的思想和行动去分辨其良好与否。”[注]同上。这些都可以看成,程砚秋在新文化阵营的围攻中,在京剧界集体“失声”的情势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恰恰是新文化的声音,其价值观与改良路径是新文化设定的,其中还夹杂些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左翼流行话语,如“土豪劣绅”[注]同上,第7页。“私产制度”[注]程砚秋:《检阅我自己》,《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3页。“我们要和工人一样,要和农民一样,不否认靠职业吃饭穿衣”[注]程砚秋:《我之戏剧观——1931年12月25日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演讲》,《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8页。等。
由此可以看出程砚秋与时代思潮的密切互动,对大众趣味的“原罪”,对“意义”的强调,对“伶人”个人意识的检讨都可见出时代思潮的内化。也正因为程砚秋不是“罩上玻璃罩”[注]鲁迅讽刺梅党成员将梅兰芳“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而梅兰芳“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见鲁迅《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之人,欧游经历也在改变着他,使他回国之后的艺术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在1935年的《谈非程式的艺术——话剧观剧述感》中,他说:“演员与观众之间,没有一种专门技术的关系,作为两者间的维系,则后者对于前者,势必因轻视而远离。”[注]程砚秋:《谈非程式的艺术——话剧观剧述感》,《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在1939年接受记者的访问中,程谈到,“戏院为吸收中下阶级的观众,便不能不以神怪剧和彩砌布景来号召。故演变成京剧神怪化,但为维持营业起见,是相当要加以原谅的。”[注]程砚秋:《程砚秋谈剧——1939年7月某报记者于裕中饭店访问之专题报道》,《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这与欧游之前的言论显然有所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从时代思潮发展脉络来看,这与1930年代“戏剧大众化”运动的自我纠偏有关,特别是与《剧学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形成观点上的呼应。[注]可参看:马肇延:《戏剧大众化的问题》,《剧学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34年);马肇延:《中国戏剧对于戏剧艺术之启示及其美的观念之完成论》,《剧学月刊》,第四卷第九期(1935年)。除此之外,欧洲游历也是促成程砚秋艺术观念变化的重要原因。
欧游之后,程砚秋在发表对中国戏剧的看法时常会引用西方戏剧作参照,如谈演员需要以技术吸引观众时,他举出“在欧美各国,每一个舞台上或银幕上的艺员,都要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经导演认为合格以后,然后再派定他的角色,参加排演。”[注]程砚秋:《谈非程式的艺术——话剧观剧述感》,《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在谈京剧竞排神怪戏需要被原谅时,他认为“在外国有国家设立的剧场,当然一切可以尽善尽美,演员也有余暇去研究纯艺术的戏剧。反观我国,连个市立的剧院都没有,演员都为维持生活,戏院为竞争营业,如何还有工夫去研究国剧的真精神呢!”[注]程砚秋:《程砚秋谈剧——1939年7月某报记者于裕中饭店访问之专题报道》,《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欧洲戏剧的参照,程砚秋对京剧(也包括其他剧种)的理解反而更具有一种本土立场与务实态度。同时,在欧期间他由一个演员转换成纯粹的观众,看了大量的戏剧与电影之后,对观众爱看什么不爱看什么有了更为切实的了解。欧游回来之后,他为新编的几出戏如《锁麟囊》《女儿心》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意见,前者为喜剧,后者服装藻丽、文武并重,都充分考虑到本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与需求,与欧游之前如《荒山泪》《春闺梦》等剧更注重主题意义,更强调精英批判意识显然有所不同。这些都可以看成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欧游之后,程砚秋对观众需求、对戏剧功能产生了更宽泛、更多元的理解,从而能够超越“五四”、左翼的观念偏颇,显现出以本民族观众为本位的更为务实、也更为自信的京剧艺术观。
但另一方面程砚秋对京剧界的痼疾比谁都感受得更深切,汲取西方戏剧优长来改造京剧的初心并未稍减,在自己主持的戏班,在自己参与主管的戏校,也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改良,如把“文场”改置在幕后,掩盖起简陋的乐器,使观众的听视集中。取消“饮场”,以免松懈剧中人的表演。[注]程砚秋:《程砚秋谈剧——1939年7月某报记者于裕中饭店访问之专题报道》,《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新排的《春闺梦》在灯光、音乐甚至舞蹈上均借鉴了国外戏剧。但改革并非畅通无阻,在1933年11月4日接受《申报》记者的访问中,即谈到:“我在欧游报告书里十九个建议,除关伶界自身救济的几项,已经在勉力试验之外,关于舞台上的一方面,因为环境和经济的关系,虽然用了一点心思,但是还是事与愿违 。”[注]程砚秋:《对于改良旧剧的感想·新屋未成旧屋须爱护——1933年11月4日〈申报〉记者在上海沧州饭店访问程砚秋记》,《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1939年接受记者访问时,仍然说,“但是谈起整个改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注]程砚秋:《程砚秋谈剧——1939年7月某报记者于裕中饭店访问之专题报道》,《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基于此,上面所说的“新屋未完工”“保护旧屋”又有着无奈与务实的另一层原因。尽管欧游回来之后的程砚秋处处强调京剧的自有价值,但他从来不是封闭狭隘之人,他认为:“若一味固守着旧剧的壁垒,对于新兴的话剧,尽其严峻拒绝之能事,实较诸旧时从事话剧诸公,以为有了话剧,便恨不将旧剧宣布死刑,其度量还要窄小!其行为还要愚蠢得可笑!个人既以热心的观客自居,而且兴趣不拘一面,所以随着近数年来,话剧运动之风起云涌,各个话剧场、电影院中,也到处布满了我的足迹。”[注]程砚秋:《谈非程式的艺术——话剧观剧述感》,《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他写出《话剧导演管窥》即是基于其多元文化价值立场与对新文化艺术形式的兴趣,赴欧期间的观剧经验、学识积累使他可以将这种文化姿态与个人兴趣表达得淋漓酣畅,虽然终究无法实现得彻底圆满。
与梅兰芳对京剧“男旦”身份的自觉认同与接受不同,程砚秋对此身份始终存在内心的挣扎,这种挣扎伴随欧游之后眼界拓宽、学识增长而越加复杂。在赴欧回来答记者问时,他说:“中国戏剧之乐趣,为写意的。既属写意,则以男扮女,以女扮男,亦未始不可。且吾国之习惯,妇女之美,以秀雅为依归,男扮女角,尚具有天然的美。女扮男角,相差亦不甚远。”[注]《〈世界日报〉记者柱宇访问程砚秋纪实》,《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第48页。这既可看成他对新文化阵营普遍存在的鄙视男旦演员的一种回应,也可见出他能以相对超脱的态度来看待易性扮演问题了。他在形体发胖之后,似乎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控制自己的体重,反而以超高的自信借助卓越的技术弥补体形上的不足,这应与中国戏剧男扮女之“写意性”的认知不无关系。“写意性”的认知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欧游之后的程砚秋在表演上却同样显现“写实”倾向。据苏少卿发现,1941年程砚秋在扮演《贩马记》中的李桂枝时,居然涂抹红色之指甲油。苏少卿说,“此事在砚秋手上发现,觉得甚艳。”[注]苏少卿:《程砚秋成名经过》(下),《苏少卿戏曲春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382页。“甚艳”的原因在于这与程砚秋台下绝不扭捏作态形成强烈反差。1940年演出《锁麟囊》时,苏少卿也发现,“砚秋于做工欲像真”。[注]苏少卿:《观砚秋初演〈锁麟囊〉》(下),《苏少卿戏曲春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266页。在欧洲看了许多写实派的电影与戏剧表演之后,程砚秋自然会将写实化的欧洲表演方法借鉴到京剧表演中来。而如果从心理成因来看,欧游之后,程砚秋从心底建立起演员的价值感与尊严感,这有助于降低其易性扮演的心理障碍,舞台上的他可以尽情投入演出,舞台下,他仍是程砚秋,不必因为台上的“女扮”而感到低人一等。
但欧游之后的程砚秋对是否继续走这条路却有了更多的犹豫与思考。他屡有“转行”的念头。“今年八月中[注]查《程砚秋史事长编》,时间应该为1934年10月3日到7日,旧历八月二十五到二十九之间。见《程砚秋史事长编(上)》,第368页。程砚秋到南京来,和他在京友人刘大悲博士说:‘我不能再演国剧了,因为‘男扮女’的戏,演起来究竟不像样。’在当时听着这句话的,并不止是刘博士一位,在座有好多是懂得艺术的学者和大学教授们,他们都静默着不表示可否,意思是在嘉奖程君已有了觉悟似的。”[注]王平陵:《国剧中的“男扮女”问题》,《剧学月刊》,第三卷第12期(1934年)。1943-1945年,程砚秋告别氍毹隐居青龙桥务农、读书,虽因时势所迫,却也甘之如饴。而在1957年的入党自我介绍上,他这样写道,“在这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我要求,希望党给我去做一些新鲜的平凡的事情,去尝试尝试……”[注]李伶伶:《程砚秋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632页。
陈叔通在1934年的信中曾鼓励程砚秋:“有相当生活即可抛弃此业专从事导演研究矣。”[注]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68-369页。他也写出了《话剧导演管窥》这样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但终其一生,他并没有从京剧男旦表演转行,舞台演出几乎伴随他一辈子,去世前一天还在询问《锁麟囊》能否上演之事。这其中应该有与当初行期未满却被逼促回国相似的原因,即,他是大家庭、戏班子里的经济支柱。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从小受过非常严格科班训练的演员,他的声名、价值、成就或者说安身立命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京剧旦角表演之上。虽未能脱离梨园行,但他在京剧教育、京剧改革、京剧发展规划、戏曲文化遗产保护、戏剧理论创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中亦可见到赴欧考察这段经历作用于程砚秋心路历程较为隐密的一面,也即通过这次考察,他对自己除了京剧男旦演员之外的其他身份有了更多的自信与自觉。
继罗瘿公之后对程砚秋帮助最大的金仲荪先生在他赴欧临行之前,有诗相赠:“匹骑檐簦万里走。翻菊部史古未有。英年绝艺归盛名。人为伸眉子摇首。曰吾不学无术耳。蒙马虎皮马亦狗。九洲之外环灜海。文物琳琅此渊薮。敢诩乘风作壮游。乐律异同穷析剖。我闻此语神抖擞。丈夫立志要不苟。古来伶工量以斗。盛时饱誉衰则否。孰者先传孰启后。毋以小道时自忸。未必峨冠皆不朽。行矣海天风雪吼。老夫临歧但执手。十年心力一杯酒。纵酬宿愿吾衰久。高阳爱士期许厚。回步西山告亡友。”[注]程永江编《程砚秋史事长编(上)》第308页录有该诗全文,但有几处错误,此处录自李伶伶《程砚秋全传》第369页提供的诗作原稿。
这首诗阐明了程砚秋赴欧之动因与志向,其中,可以看到罗瘿公(即诗中的“亡友”)、金仲荪的身影。此外,他身边还汇聚着袁伯夔、陈叔通这样亦旧亦新的社会名士,徐凌霄、王泊生、刘守鹤、张次溪等民国时期的学者型文人,以及李石曾这样留学过法国的国民党官员,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切磋激励着程砚秋艺术上的进取与远大志向的生成。因此,程砚秋的这一场赴欧游学,又可看成晚清到民国,一批受过新式教育或受到新思想熏染的文化人汇入京剧发展大潮中,以其胸怀、眼界、学识共同汇聚、推动了一场京剧向西取经的现代化进程。而程砚秋欧游回来之后,以其欧洲考察所得和《剧学月刊》的同仁们在办刊方向、观点生成上产生着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并以在欧期间对戏曲音乐教育的考察直接影响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办学方向与教育体制,培养了许多京剧界的新生力量,这对1930-1940年代及之后的京剧发展同样发生着重要而长远的影响。因此,对程砚秋赴欧考察“精神私史”的梳理与述描,亦呈现出中国现代京剧发展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一个阶段的某些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