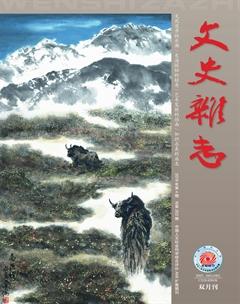《诗经》中人是怎样从畏天命转向反天命的
闻衷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在《诗经》里,有不少“畏天命”或“敬天命”的思想表现,如《雅》《颂》中的许多篇章或许多诗句。但翻检整部《诗经》,却又发现更多的骂天怨天抗天命反天命的情绪宣泄。宣泄者除了所谓“不知天命”的一般平民与奴隶外,也有应知天命的王公贵族;甚或天子(周王)本人也对天命有大不敬之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该说,反映畏天命、敬天命思想主要集中于《周颂》《鲁颂》与《商颂》中,仅以《周颂》为例,其《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这是对天命昭昭,无所不显,无所不灵的热情赞美。《我将》则云:“我将我亨,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讲要对天虔诚祭祀,因为天帝会保佑世人;所以世人早晚注意,敬畏天命,方可确保社稷的安宁。《敬之》又唱道:“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这是周王在警诫自己要时刻顺从天命,不可违抗天命——不要以为天帝高高在上而不知情,他实际日日都在监视、考查着自己哩!……
一、渊源有自:《甘誓》《洪范》之说
那么,周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畏天命、敬天命的观念呢?我们从《尚书》以及殷墟卜辞中可以了解到,周以前的人们对人类自身的力量鲜有认识,也就是说,周以前人们的世界观是一种纯粹的、完全的宗教天命观,人的自主意识十分淡薄,总将自己置于天帝的意志之下。据说治水英雄大禹在率先打破“禅让制”,把王位交给儿子启以后,同姓诸侯有扈氏不服,起兵造反;启于是率大军亲征有扈氏的大本营甘(今陕西户县西)。临战前,启召集六军将领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段话,见载于《尚书·甘誓》,历史学家们推测在公元前2196年。这里的“五行”,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所知晓的金、木、水、火、土五物,也就是《尚书·洪范》里所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之一的“五行”;“三正”,大致是与五行有关的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夏启称有扈氏侮慢五行,抛弃三正,犯了逆天之罪,今奉天命予以剿灭惩罚。这说明至迟在夏代,天命观便已流行于氏族及奴隶主贵族之中。
在殷墟卜辞中,我们发现奴隶主时代的殷王室十分迷信,凡大小事必须卜筮问“天”问“上帝”,如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晦暝,年辰的丰歉,时日的吉凶,用人用牲之多寡,分娩男或女等;且每卜必经多次,待确定无疑方可行事。当时大约已出现了五方观念(即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和中商观念)与祭祀五方神的仪式。《尚书·洪范》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亲自造访被俘的商末名相箕子,垂询治国之常道。箕子侃侃陈述“洪范九畴”即治国安民的九种大法。箕子说,相传禹的父亲鲧采取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把五行胡乱安排一气,惹得上天大怒,没给他洪范九畴,造成治水失败。禹承父业后,按上帝(上天)所赐予的五行行事,上帝这才赐予他洪范九畴,使治水治国相得益彰。《甘誓》《洪范》之说,显示周以前的奴隶主贵族已具有一套完备的宗教天命观;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宗教天命观至迟在商末周初已具有后来“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的意蕴了。
二、君权神授:道德评判的参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来细细地翻检《诗经》里所展现的畏天命、敬天命内容,其实应是附着于人们自主意识(虽则还稚嫩)或者说是初步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意识之上的。例如就前举《周颂》中那些对天命、上帝毕恭毕敬的诗行来看,便显示出这种关系。因为第一,这些看似阿谀、敬畏上帝的话,乃是建立在人本位之上的——即围绕着周天子的德行政绩而言的,名为歌上天,实为颂周王。(按《诗序》,《维天之命》《我将》是祀文王的,《敬之》则是诫成王的。)第二,与这些虚情假意的畏天命、敬天命诗行相对的是,在《诗经》更多的篇幅里,其实是毫无遮盖地透溢出天人合一观甚或天人分离,以至抗天命、反天命的初步的人文主义色彩。
所谓“天人合一”观是在敬天命的基础上又重人事的一种革新思维,它虽然最终形成于春秋战国之时(由孔子、老子、墨子、子思、孟子等逐渐完善),但却滥觞于商、周之际(《尚书》之《甘誓》《洪范》中天人互相照应、相辅相成的记录,可为佐证)。就周民族而言,其最初的天命观是以自己的祖宗神与上帝神的结合为基础的。周人的祖先原住于邰(今陕西武功县),公刘迁居于豳(今陕西邠县),到大王古公亶父方“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终至“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诗经·鲁颂·閟宫》)。在这一过程中,周人由一个居于西岐的落后部族,勇敢地挑战拥有先进文明的商族,除了物质力量(包括武装力量)的积蓄外,还须要面对上天的态度。换言之,就是要在天命观盛行的世界里,取得上天的认可(其实质是取得天下人包括商人的认可),以不违天命,使将要赢得的政权合法化。

“周人的解决方式是,在殷商化的过程中,把商人的祖宗神也认成自己的祖宗神,或者说周人将自己的祖宗神與商人的祖宗神合而为一。透过这种方式,上帝由祖宗神一变而带有道德神的性质,是一位公正无私的上帝,代表着正义和公道。这样的上帝对于政权的付与,不再无条件地带有宗族的私情,而是经过公平的选择,选择的标准在于政治的好坏与行为的合不合理。”(林戴爵:《人的自觉——人文思想的兴起》,见《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其实是在“天人合一”观之外,又补充进道德评判与政治审查思想。周人思想观念上的这一变化,体现在《诗经》里的被认为是写于周初的一些诗篇里。
《大雅·文王》第一章唱道:
文王在上, 文王巍巍居殿上,
於昭于天。 德行昭昭动天堂。
周虽旧邦, 岐周虽为旧小邦,
其命维新。 天命变革新气象。
有周不显, 有周前程似锦绣,
帝命不时。 上帝授命准而当。
文王陟降, 文王在世与在天,
在帝左右。 不离上帝侍两旁。
《诗序》说,是诗为“文王受命作周也”。说是受命,其实是假天命,“克配于天,视之为天神”,以此解释上天何以夺殷之社稷而改授于周的道理。在《大雅·皇矣》(《诗序》云:“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里,又进一步解释说,上帝之所以“乃眷西顾”(特别照顾西方的小周邦),是因为上帝曾降临人世,亲自考查后作出了英明抉择。上帝甚至还向文王有过一长串谆谆告诫,如“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大意是不要对外轻易用兵,而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致力于社会的安定,人心的凝聚)等,“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周颂·时迈》又写道:“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诗的要点是讲,天帝爱武王就跟爱他儿子样,实在保佑我宗周。又如《大雅·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等,大意也相同,都将周天子说成是上帝依照严格之道德与政治标准认真选拔出来,托付他代表上帝管理人间的天子——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君权神授”。所以,《诗经》里出现的不少对天的礼赞(如《周颂》中的那些篇章),其实质是对周天子奉天之命掌握政权、管理人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禮赞。
三、不畏于天:理性太阳的升起
值得重视的是,在《大雅·文王》第五章里,周天子在因自己受命于天而沾沾自喜的同时,又流露出对“天命靡常”(天命的取舍定夺是无定数的)、“命之不易”(要上天长期信任是不容易的)的无可奈何之叹。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问题——即道德与政治评判是周人带给宗教天命观的一种新标准;而关于天命并非永恒不变的认识,则当视作周人的又一种新思维。这种新思维,是周人在所发动的周武革命中,在亲眼目睹了原本也是上天授命的殷商王室终被上天迅速抛弃的过程而产生的感触。它既是一种兔死狐悲式的慨叹,也是一种对上天权威的怀疑和大不敬。对此,林戴爵指出:“‘天命靡常的要旨在于指出天命既不可信赖,则惟有通过人的行为才能把握。”(《人的自觉——人文思想的兴起》)而周人在由一个地处西岐不打眼的小邦国而逐渐强大、崛起并进而克殷代商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意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大雅》里的《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等诗篇,便展示出这一艰难进取的历史进程以及周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与坚强意志。因此,这些诗篇尽管也打着敬畏天命的幌子,却并不使人感到是对天或天命的称颂,而是对人的力量的讴歌。今人之所以多视上述诗篇为民族史诗,其原因也在乎此。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前述关于上帝以德选天子一类的诗行,与其说是在赞美上帝的慧眼明鉴,不如说是在炫耀周先民们自身的智慧、勇敢、团结与坚忍不拔。
正是由于周人在实践中对人的自身力量的觉悟或者说是周人自主意识的兴起,使得《诗经》里的大多数诗篇,基本上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位而展开并倾吐感情。这种情况,愈到西周后期,便愈加突出。大家知道——周厉王以降,国内政治动乱不已,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最终演成镐京失陷,平王东迁的结局)。普通人民(以奴隶为主)饱受剥削又蒙受战乱之苦而悲愤难平,广大有识之士(包括王公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与一般知识分子)目睹“百川沸腾,山冢崪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的沧桑巨变而忧心如焚……这一切遂演化成《诗经》里一行行呼天抢地、指天骂神的“怨诉之言”: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
“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小雅·巷伯》)
“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雅·小弁》)
“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唐风·鸨羽》)
“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节南山》)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小雅·雨无正》)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遁。”(《大雅·云汉》)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秦风·黄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大雅·板》)
“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大雅·云汉》)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
……
在上述诗行里,不仅骂了上帝——天神,而且还骂了列祖列宗——祖宗神——连天王老子也全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人间的子民、后世的子孙吃大苦、受大累而不动声色,不援手相助,因此还敬他们干吗?还怕他们什么?这里需要知道,在商周社会,天神(上帝)和祖宗神是宗教天命观这个精神信仰世界里的两大支柱。它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坍塌后,人们还靠什么,还有精神支柱么?有的,这就是处于严峻现实中的人的自主意识。请听听《小雅·何人斯》的声音: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既然连祖宗都无所敬了,还怕天神做什么!
再听听《小雅·十月之交》的呐喊: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
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并不是上天降临的(这里一语戳穿了天神的纸面具——天神并没有本事来管人间的是非善恶),而是人类中另一部分(统治阶级中的暴戾昏庸者,如周幽王)造成的。既然上天不管用,还是自己去寻求解脱苦难的方法吧!
至此,我们在西周末的风雷激荡、陵谷巨变中明确读到了周人作为人的自主意识的初步觉醒,清晰地看到了人的理性太阳喷薄而出,惊喜地发现了指向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跨海大桥的架通……末了,特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里的一段以为说明:
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