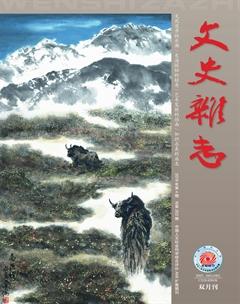试论茶馆的兴起与近代四川的茶馆文化
江玉祥

一
四川不僅是茶树的原生地之一,也是中国人工种植茶树和茶饮的发源地。据王褒《僮约》记载,西汉时期蜀中待客均要“烹茶”,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饮料。西汉蜀茶亦已作为商品买卖,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在汉代已有茶市或已成为茶叶的集散地。然而,至今还找不到确实的史料证明中国的茶馆起源于四川。虽然西晋太康初年,张载至蜀省父,在所写《登成都白菟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全晋文》卷五十二载傅咸《司隶校尉教》亦有“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无为,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独何哉”之说。所谓“南市”,即洛阳的南市。晋惠帝元康年间,蜀妪远至洛阳卖茶粥,那可能仅是供人渴饮的茶摊,还够不上茶馆的规模,最多算茶肆的雏形。
茶馆又叫茶楼、茶肆、茶坊、茶寮、茶室,四川人叫茶铺,它是以营业为目的、供客人饮茶的场所。隋唐时代,茶叶贸易兴旺,饮茶风气盛行,茶肆应运而生。唐人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卷六:“开元(公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原注:一本无“学禅”二字)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唐代商业交通发达,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从京城长安、洛阳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大中城市,都出现了茶肆。

旧时茶馆掌柜(雕塑,李鉴踪摄于新场古镇)
《封氏闻见录》又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今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社会上还出现了擅长茶道的“煎茶博士”。唐代长安有茶肆。如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宦官仇士良等发动兵变,宰相王涯等人从宫中“苍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1]中唐以后茶馆开始供茶神陆羽。唐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巩县陶者多为磁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赵璘著《因话录》卷三云:“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陆羽成了茶祖,成了茶馆日常祭祀的行业神,足以证明唐代饮茶已成了风俗,茶肆开设已经比较普遍。
宋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茶馆文化也发展到了相当高度。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又投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2]
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梅花酒。绍兴间,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间,正是论角,如京师量卖。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乾茶钱。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寻常月旦望,每日与人传语往还,或讲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为名,乞见钱物,谓之龊茶。”[3]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茶肆》:“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的吗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期约友会聚之处。……”[4]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中瓦内王妈妈家茶市,名一窟鬼茶坊。而《一窟鬼》正是当时说话人常说的话题。宋代《京本通俗小说》有《西山一窟鬼》一篇(《警世通言》叫《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可以推想王妈妈家茶肆是以有说话人说《一窟鬼》而得名的。宋代说话四家,此为说烟粉、灵怪、传奇的“银字儿”;又据南宋洪迈《夷坚支志》丁卷三“班固入梦”条称,吕德卿曾和他的朋友王季夷等四人,出临安嘉会门茶肆中坐,看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5]则属说话四家中“讲史书”一家。《西湖老人繁胜录》说:“余外尚有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此处疑脱“肆”字)中作夜场。”[6]可知宋代的茶坊又是说话等伎艺的活动场所,而且在茶坊中作场的可能多在晚间。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条:“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7]歌馆卖茶,茶坊也有歌伎卖唱。当时临安茶坊之多,各种茶馆艺术之兴盛,可以想见。
宋代南北茶肆皆置双陆及棋,以娱饮者。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云:“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有了这些休闲娱乐项目,茶客更容易消磨时间。
南宋洪迈《夷坚丙志》卷十言“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岁儿,父母连日出求访,但留幼女守舍。一黄衣卒来啜茶……”这是谈南宋湖南平江县民间茶肆老板失儿事。《夷坚支乙志》卷二《茶仆崔三》:“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淳熙八年春夜,已扃户,其仆崔三未寝,闻外人扣门,问为谁,曰:‘我也。崔意为主公,急启关,乃一少年女子,容质甚美,骇曰:‘娘子何自来?此是李家茶店耳,岂非错认乎?曰:‘我是只左侧孙家新妇,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终夜无所归,愿寄一宵。崔曰:‘我受佣于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请,泣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肆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寝。”说明南宋民间茶肆有佣工。
综上所引宋代史料说明,宋代茶馆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后世茶馆的功能已大致具备。
元代,饮茶已成为全国各族、各阶层的一种共同嗜好,成了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十·茶》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元代民间谚语:“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8]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六《七件事》曰:“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盖言人家之所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词有云:‘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些,醋也无些。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折桂令》也。我朝余姚王德章者,安贫士也,尝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即此可以知其操矣。”
元代四川是重要的产茶区,全国统一之前,川茶是北方茶叶的主要来源,元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用运使白庚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9]全国统一以后,四川设盐茶运司,兼管井盐和茶的产销。
四川的雅州名山县蒙顶山自西汉以来便以产茶闻名,到了元代,“蒙山顶上茶”便成了老百姓口中的俗語。当时,茶肆中便以扬子江心水烹蒙山顶上茶名号来吸引茶客,元李德载(李乘)有一首小令《喜春来·赠茶肆》吟道:“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学士更风骚。应笑倒,销金帐饮羊羔。”它后来便演变为谚语:“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明嘉靖陈绛《辨物小志》:“世传:‘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之句。而宋范景仁《东斋纪事》称:蜀茶数处,雅州蒙顶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方生。则云雾复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晁氏客语》亦称:雅州蒙山常阴雨,谓之漏天。产茶最佳,味如建品。竟不知昔诗所称蒙山茶配合江心水者,定是谁茶也。”明万历谢肇淛撰《五杂组》卷十一《物部三》:“昔人谓:‘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顶尤极险秽,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扬子江心水,指流动的活水。活水活火烹香茶,即是苏轼苏辙兄弟所称的“西蜀煎茶旧法”。宋代眉州丹棱人唐庚著《斗茶记》说:“吾闻茶不问团胯,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10]

蒙顶山茶场
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记成都岁时节俗云:“天禧三年(1019年),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11]不但宋、元时代成都有茶坊,而且达官贵人的晚宴上,歌妓常以“新词送茶”。是否茶坊中也有歌妓唱茶词,则不得而知,文献阙如。
中国的饮茶方式,到明代发生了划时代变化,从食茶粥,到吃末茶,发展到开水冲泡散茶,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二《茶式》曰:“饮茶精洁,无过于近年。讲究既备,烹瀹有时,且采焙俱用芽柯,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盖始于本朝。”卷一《贡御茶》:“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中之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中国从五代末至宋元时代流行的“茶道”即“分茶”传统(举行茶礼的仪式)直至“茶百戏”的绝技,也简化为“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12]饮茶方式的改变,就为茶馆的普及创造了条件。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南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然富家燕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傲之。旬日之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然特以茶为名耳,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13]田汝成说“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而我们知道南宋的杭州不但有茶肆茶坊,且多有文化韵味。这里的“先年”应该指元朝至明嘉靖二十六年这段时间,为什么这段时间杭州无茶坊?可能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对南宋旧都采取的统治措施有关,与明朝前期的政治形势有关,个中真相,史料缺乏,不便妄测。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关于茶馆的文字记载,便多起来。例如:
明顾起元撰《客座赘语》卷四《徐十郎茶肆》:“徐常侍铉无子,其弟锴有后,居金陵摄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有铉、锴诰敕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诰,云‘归明人伪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银青存其阶官也。人第知金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时已有之矣。”[14]顾起元生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卒于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客座赘语》最早的刻本是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戴惟孝刊本,书中所言“人第知金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时已有之矣。”乃明代中后期金陵(南京)的情况。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八《露兄》:“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取米颠‘茶甘露有兄句也。”[15]张岱《露兄》一文反映了崇祯末年茶艺与茶道的特色,注重清雅洁净。一般的市井茶坊,也很讲究品味,这从明末出现的拟话本小说故事背景描写中,有所反映。明凌濛初著《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叼世爵》:“学对面有个茶坊,但见:木匾高悬,纸屏横挂。壁间名画,皆唐朝吴道子丹青;瓯内新茶,尽山居玉川子佳茗。张客入茶坊吃茶。茶罢,问茶博士道:‘此间有个林上舍否?”[16]据王古鲁先生介绍,此篇演明代故事,来源于明陆粲《庚巳编》卷三《还金童子》。因此,可以书中的风俗描写来佐证明末茶坊摆设和装饰。
清代茶肆,长江下游以扬州为盛。扬州的茶肆分荤茶肆、素茶肆两种。荤茶肆的茶食精美,素茶肆仅饮茶而已。清乾隆时,李斗著《扬州画舫录》卷一:“双虹楼,北门桥茶肆也。楼五楹,东壁开牖临河,可以眺远。五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筯,无不精美。辕门桥有二梅轩、蕙芳轩、集芳轩,教场有腕腋生香、文兰天香,埂子上有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陆轩,广储门有雨莲,琼花观巷有文杏园,万家园有四宜轩,花园巷有小方壶,皆城中荤茶肆之最盛者。天宁门之天福居,西门之绿天居,又素茶肆之最盛者。城外占湖山之盛,双虹楼为最。其点心各据一方之盛。双虹楼烧饼,开风气之先,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之分。宜兴丁四官开蕙芳、集芳,以糟窖馒头得名,二梅轩以灌汤包子得名,雨莲以春饼得名,文杏园以稍麦得名,谓之鬼蓬头,品陆轩以淮饺得名,小方壶以菜饺得名,各极其盛。而城内外小茶肆或为油镟饼,或为甑儿糕,或为松毛包子,茆檐荜门,每旦络绎不绝。”[17]
《扬州画舫录》卷四:“六安山僧茶叶馆也。僧有茶田,春夏入山,秋冬居肆。东城游人,皆于此买茶供一日之用。郑板桥书联云:‘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
《扬州画舫录》卷六:“小洪园后门为旧时且停车茶肆,其旁为七贤居,亦茶肆也。二肆最盛于清明节放纸鸢、端午龙船市、九月重阳九皇会,斗蟋蟀,看菊花,岁时记中胜地也。”
《扬州画舫录》卷九:“合欣園本亢家园旧址,改为茶肆,以酥儿烧饼见称于市。开市为林媪。有女林姑,清矑窥牖,游人集,遂致富。”“小秦淮茶肆在五敌台,入门,阶十余级,螺转而下,小屋三楹,屋旁小阁二楹,黄石巑岏。石中古木数株,下围一弓地,置石几石床。前构方亭,亭左河房四间,久称佳搆。”“郡城烹茶,不取汲于井水”。
《扬州画舫录》卷七:“明月楼茶肆在二钓桥南,南岸外为二道沟,中皆淮水,逢潮汐则江水间之。肆中茶取于是,饮者往来不绝,人声喧阗,杂以笼养鸟声,隔席相语,恒以眼为耳。”卷十一:“玉版桥王廷芳茶桌子最著,与双桥卖油糍之康大合本,各用其技。游人至此半饥,茶香饼熟,颇易得钱。”
《扬州画舫录》卷十:“乔姥于长堤卖茶,置大茶具,以锡为之,少颈修腹,旁列茶盒,矮竹几杌数十。每茶一碗二钱,称为‘乔姥茶桌子。每龙船时,茶客往往不给钱而去。杜茶村尝谓人曰:‘吾于虹桥茶肆与柳敬亭谈宁南故事,击节久之。盖谓此茶桌子也。”宁南为宁南侯左良玉。杜茶村,即杜浚(1611—1687),原名诏先,字于黄,号茶村,湖北黄冈人。柳敬亭,明末清初卓越的说书艺人,曾参加晚明将领左良玉武昌军幕,以说书人身份参与机要。
扬州之外,苏州的茶坊也很有特色。清嘉庆、道光时人顾禄著《桐桥倚棹录》卷十“虎丘茶坊”条:“多门临塘河,不下十余处。皆筑危楼杰阁,妆点书画,以迎游客,而以斟酌桥东情园为最。春秋花市及竞渡市,裙屐争集。湖光山色,逐人眉宇。木樨开时,香满楼中,尤令人流连不置。又虎丘山寺碑亭后一同馆,虽不甚修葺,而轩窗爽垲,凭栏远眺,吴城烟树,历历在目。费参诗云:‘过尽回栏即讲堂,老僧前揖话兴亡。行行小幔邀人坐,依旧茶坊共酒坊。”[18]

《扬州画舫录》(清乾隆乙卯年刻本)
成都的茶馆到了清朝末年,便以蓬勃之势发展起来。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茶》云:“成都之茶铺多,名曰茶社。如文庙街之瓯香馆则名馆,顺草湖之临江亭则名亭,山西馆口之广春阁则名阁,亦不一定名曰社也。现经警署发有规则,每铺皆用栏干,省城共计四百五十四家。在前之斗雀、评理等事已禁止,惟评书、洋琴二事尚仍旧也。瓮锅之名瓮子,水多系井水,俗名圆河水,可以随意买回,一文一罐或一文一竹筒,可做洗脸之用,热度不到不能食也。劝业场开后遂发生特别茶铺数家,茶香、水好、座雅、楼高,宜春楼、第一楼、怀园均好。茅茶每碗四文春茶六文白毫六文香片三十二文。”[19]
20多年后,成都《新新新闻》报1935年1月统计,成都的茶馆有599家。到1941年原成都市政府编制的统计表列,成都茶馆为614家,其会员人数居全市工商业第五位。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统计,茶馆数目为598家。由此可见,从1909年到1949的40年中,成都市茶馆少则400家,多则600家以上,增减变化并不太大,这个行业是比较稳定的。
再以成都的街巷数字来看,据《成都通览》说,1909年成都有街巷667条。也就是说,成都全市600余条街巷,几乎每一条街巷都有一家茶馆,可见它和市民的生活关系相当密切的。[20]
二
著名川籍作家李劼人在小说《暴风雨前》中说: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上具有三种作用:一种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另一种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
第一,它是一种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
李劼人先生写道:
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这其间有三层好处。第一层,是可以提高嗓子,无拘无束地畅谈,不管你说的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你尽可不必顾忌旁人,旁人也断断不顾忌你;因此,一到茶铺门前,便只听见一派绝大的嗡嗡,而夹杂着堂倌高出一切的声音在大喊:“茶来了!……开水来了!……茶钱给了!……多谢了!……”第二层,无论春夏秋冬,假使你喜欢打赤膊,你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假使你要剃头,或只是修脸打发辫,有的是待诏,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通不妨事,因为“卫生”这个新名词虽已输入,大家也只是用作取笑的资料罢了;至于把袜子脱下,将脚伸去登在修脚匠的膝头上,这是桌子底下的事,更无碍已。第三层,如其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作,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
如此好场合,假使花钱多了,也没有人常来。而当日的价值:雨前毛尖每碗制钱三文,春茶雀舌每碗制钱四文,还可以搭用毛钱。并且没有时间限制,先吃两道,可以将茶碗移在桌子中间,向堂倌招呼一声:“留着!”隔一二小时,你仍可去吃。只要你灌得,一壶水两壶水满可以,并且是道道圆。[21]
成都的茶馆一般都开得早、关得迟,大多数是凌晨5时开门,晚上10时才关门。还有开得更早和关得更晚的,如棉花街的泰和亨,因地当菜市,清早上市的蔬菜贩子需要落脚,每天清早3点钟它就开门营业。又如湖广馆的茶馆,为了供应春熙路、东大街一带饮食业工人收堂以后来喝茶,它延长到晚上12点以后才关门。[22]成都的居民向来有吃早茶的习惯,作家沙汀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喝早茶的人》,很生动地描写过这种人。他说: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
一從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这种过早的原因,有时是为了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
然而,即使不是为了这些,而是因为习惯出了毛病,这也不会使他们怎样感到扫兴。他们尽可以在黎明的薄暗中,蹲在日常坐惯了的位置上,打一会儿盹。或者从堂倌口里,用一两句简单含糊的问话,探听一点自己没关照到的意外的故事。[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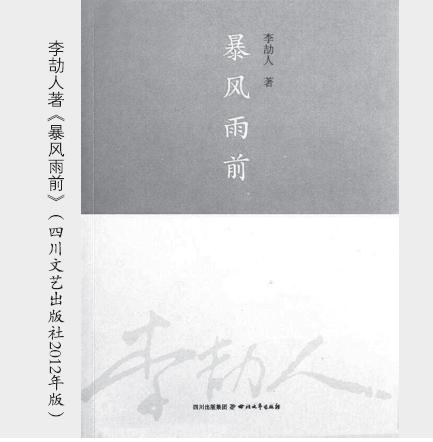
第二,它是一种各业交易的市场。
茶馆和工商界的业务,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从前茶馆有一副对联:“湖海客来谈贸易,缙绅人士话唐虞。”这就说明茶馆既是谈古论今的处所,也是洽谈生意的地方。有的行业干脆以茶馆为市场,还有各行各业的大小商人的聚会和活动,也都有固定的茶馆。比如,从前茶叶交易的茶社,一般在提督东街三义庙茶社,沟头巷中心茶社,城守东大街的华华茶厅。货色并不必拿去,只买主卖主走到茶铺里,自有当经纪的来同你们做买卖,说行市。这是有一定的街道,一定的茶铺,差不多还有一定的时间。这种茶铺的数目并不太多。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是校长、教师会聚的地方,每逢六月腊月,寒暑二假,那里便成了教师找工作的场所[24]。
第三,它是一种集会和评理的场所。
李劼人先生在小说《暴风雨前》中说:
不管是固定的神会、善会,或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要商量什么好事或歹事的临时约会,大抵都约在一家茶铺里,可以彰明较著地讨论、商议乃至争执;要说秘密话,只管用内行术语或者切口,也没人来过问。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十几桌茶钱一并开消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两面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警察兴办以来,茶铺少了这项日常收入,而必要如此评理的,也大感动辄被挡往警察局去之寂寞无聊。[25]
李劼人先生这里的讲述,即所谓吃讲茶。沙汀著名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写的邢幺吵吵为儿子被抽壮丁,同联保主任在其香居茶馆吃讲茶的事。那时各街袍哥码头设于茶馆。1911年的保路运动,成都保路同志会串联各家码头,各码头都在茶馆里插上保路同志会的旗子。一是因袍哥习惯于坐茶馆;二是在人来人往的茶馆里集会,不惹人注意;三是在公共场所接待各路同志,出了事情,不致连累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关方面作过统计,全市就有大大小小1000个以上的袍哥码头,90%以上都在茶馆里“插旗子”“摆堆子”“扯把子”。
第四,它是一种民间艺术表演的场所。
有一些茶馆,还设置讲评书、说相声、打围鼓、唱竹琴、打扬琴、演灯影戏、木偶戏的场所。讲评书的茶馆叫书场,书场的茶叫书茶,其茶钱比平常的茶钱高,高出部分归书场人所得。清末民初,东城根街锦春茶社长期有竹琴圣手贾瞎子(树三)演唱《祭塔》《安安送米》,声情并茂,夜夜座无虚席。有名的评书艺人钟晓帆在成都各茶馆说评书,讲“清棚”评书《孟丽君》,技艺高超,善于加“瓤子”,会留“门坎”,听众十分踊跃,名噪蓉城。
阳翰笙回忆20世纪20年代成都的茶馆:
四川茶馆是一个热闹的所在,一个小天地,一个浓缩的世界。有说评书的,有唱清音的,有拉胡琴的瞎子,有掷骰子赌钱的,有在袖筒子里捏指头做生意的,有闭目养神的,有全神贯注看热闹的,有吃讲茶打官司的。卖小吃的也不少。胸前背一个掌盘,用榔头把凿子敲得叮当响,是卖麻糖的;头顶蒸笼,嘴里吆喝,是卖包子和发糕的。最有趣的是卖烟的,我不是说手提竹篮、内装香烟和瓜子的那一种;我说的是卖水烟的。这种人都是老头,围裙上缝两个大布包,一边装烟丝,一边装纸捻子。手捧白铜水烟袋,那细铜烟嘴有一公尺多长。他把烟丝按在烟斗上,纸捻子总是吹燃的(即燎着火苗)。他在茶桌之间穿梭走动,将长长的烟嘴凑近他认为会抽烟的人的嘴巴。凡是偷懒省事、要抽他这种烟的人,不用伸手,甚至不用抬头,只需张嘴衔着烟嘴,往内一吸,那边烟斗下的水咕咕咕一响,这口烟就算抽了;如果不松口,表明还要抽第二口,老頭手脚麻利,立即就橐橐两下抖掉烟灰,重新装上烟,点燃火,你再一吸,又是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随你。抽完之后,从摆在桌子上的茶钱中拣出最小数的钱给卖烟人,他的烟嘴便又伸向另一个人的嘴巴。若只抽一口烟,不给钱,卖烟人也不在乎。老头的烟嘴伸向你的嘴,你没有反应,他就立即移开。要是夏天,还有专门给人打扇的小娃儿。当然,这些都卖不到我们这种穷学生的钱。我们坐茶馆的目的是读书。即或饿了,我们也只买一个锅魁,就着茶水充饥;若讲究一点,就请茶馆的吆厮到附近的小吃店去给我们买个凉面锅魁来吃。锅魁类似北方的火烧,但薄;将锅魁的边沿开一个口,两层分开,盛一碗凉面或凉粉进去,吃起来辣嘘辣嘘的,既可口,又饱枵腹,还不贵。[26]
四川的茶馆分两大类型:一是以成都茶馆为代表的川西类型,二是以重庆茶馆为代表的川东类型。两种类型茶馆的社会功能都差不多,但饮茶方式却大不同。李劼人先生在比较成、渝两地茶馆坐具的差异,分析成都人和重庆人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态度时指出:“成都人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爱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如此一下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而重庆茶馆一般是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27]这里,我要说的是:成、渝两类茶馆所反映出的两地不同的生活和心态,是在特定的地域中形成的。川西平原有都江堰自流灌溉系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长期的安逸(又作“安佚”,意为“安闲逸乐”)生活,养成了慢节奏和慵懒的生活方式,体现在茶馆是矮桌子,安然舒泰的竹椅子。重庆山高坡陡,旱地劳作,“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华阳国志·巴志》)连坐茶馆,“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庄子·至乐》)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茶馆文化,成、渝二地有差别。如果把四川的茶馆文化同扬州、苏州的茶馆文化比较,也大不相同:扬州、苏州的茶坊茶肆将园林的布置和琴棋书画的欣赏结合起来,饮茶分荤素,非常重视茶食的配搭,显得雍容华贵,贵族化;四川的茶馆则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更平民化。长江上游的四川茶馆和长江下游的扬州、苏州茶坊都是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又是承载民间文化的文化空间。
注释:
[1]《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王涯传》。
[2][3][4][6][7]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94—95页,262页,124页,443页。
[5]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991页。
[8]元代杂剧中常用此语,如武汉臣《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佚名《月明和尚度柳翠》,见《元曲选》第474、1335页。
[9]《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茶法》。
[10]叶羽主编《茶伴书香(茶经·茶书集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11]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五十八,线装书局2003年点校本,第1711页。
[12]明·张源:《茶录》,见叶羽主编《茶伴书香(茶经·茶书集成)》第148页。
[13]明·田汝成辑《西湖游南志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
[14]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133页。
[15]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八《露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第76页。
[16]明·凌濛初著,章培恒整理,王古鲁注释《初刻拍案惊奇》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页。
[17]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26页。
[18]清·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市廛·虎丘茶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页。
[19]清·傅崇榘编撰《成都通览·成都之茶》,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53页。
[20][22][24]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21][25]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340页,第337—340页。
[23]原载1934年11月27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尹光。《沙汀文集》第六卷“散文”,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119页。
[26]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出川之前》三《“五四”风潮——青年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27]李劼人:《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旅渝随笔》,《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原载1946年1月1日《新新新闻·柳丝副刊》。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四川省民俗学会会长(执行)